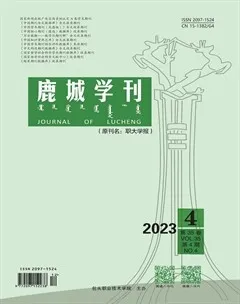論現代歌詞對徐志摩詩歌的改編
高羽
摘 要:早期白話詩人的詩作在20世紀20年代相繼被譜曲入樂,徐志摩詩歌的音樂化因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流傳效應成為此中尤為值得關注的問題。其詩歌本身具有的音樂性,及詩歌向歌詞轉化過程中進行的諸多改編,都助力了詩作與歌曲在彼此借重中再度實現審美意義、擴大傳播范圍。考察現代歌詞對徐志摩詩歌的改編,目的在于探究中國現代詩樂結合的可行路徑,引發現代學人再度思考身陷困境的詩歌與歌詞創作,以探求如何實現詩歌受眾群體的擴大及歌詞藝術水平的提升。
關鍵詞:徐志摩;歌詞;詩歌;改編
Modern adaptations of Xu Zhimos poetry with lyrics
Gao Yu
(Institute of New Poetry of China,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 Qing 400715)
Abstract:The poetry of early vernacular poets in the 1920s was gradually set to music,and the musicalization of Xu Zhimos poetry stands out due to its unique aesthetic value and impact.The inherent musicality of his poetry and the numerous adaptations it underwent during its transformation into lyric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expanded reach of his works and songs.The examination of the modern adaptation of Xu Zhimos poetry into lyrics aims to explore feasible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music.This study prompts contemporary scholar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lyrics,both of which are confined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boundaries,and seeks ways to expand the audience for poetry and enhance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lyrics.
Key words:Xu Zhimo;Lyrics;Poetry;Adaptation
詩與歌合是一部中國文藝的既往史。“詩”與“歌”自古以來密不可分,二者共同的精髓就是“樂”的境界。[1]20世紀20年代始,以趙元任、蕭友梅、黃自等為代表的音樂人力圖借鑒西樂,以詩入樂,將胡適、劉半農、劉大白等早期白話詩人的詩作相繼譜曲,推動了中國音樂的現代性發展。以徐志摩詩歌為原型譜寫的現代歌曲是此中的代表之作,徐志摩詩歌也緣此獲得了視覺與聽覺上的雙重傳播渠道,擴大了傳播范圍。考察徐志摩詩歌音樂化的學術動向不難發現,諸學者的研究策略多是以徐詩本身的音樂特性,或是由詩歌到歌詞的改編過程,或是徐詩歌詞化改編后的流傳效應等某一視點切入。本文將在吸收這些先行成果的基礎上,擴大視野,試圖對徐志摩詩歌音樂化全過程構建較為完整的詮釋空間。徐志摩詩歌與曲調能和諧、融洽地實現共生,溯其根源,在于徐詩本身具有的音樂性,這個特性生成了文本再生的可行性,為作曲家、作詞者、歌手等創作主體二次創作提供了更多的彈性空間。本文將以徐志摩詩歌的音樂化為立論中心,具體剖析“改編的基礎為何”“改編的過程如何”“改編的結果又何”等核心問題,試圖探求破除當下詩歌與歌詞創作迷霧的可能之法。
一、與詞同構的文本基礎
徐志摩作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在詩歌理論和實踐上都高度遵循著“音樂美”的原則。“你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只是音樂。”“我不僅能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2]徐志摩將其天生的音樂感知力投諸詩歌創作,使詩作文本內部就有著與歌詞同構的樂性肌底。
第一,規范的體式,自然的語法。“考察新詩入樂的實踐,就會發現,凡是入樂的詩歌,其體式都是有一定規范性的。”[3]《再別康橋》四行一節,首尾節體式相同,中間五節體式以詩人的思維跳躍為軸靈活變化。“河畔金柳”“軟泥青荇”“榆蔭一潭”“長篙撐船”,對景物的漫溯呼應詩人離別康橋時的情感起伏,“輕輕的來”又“悄悄的走”,來去之間情感得以圓滿收攏。不刻意追求奇崛險怪的語法,字句明白曉暢,充盈著涓涓細流般的輕緩、靈動。語言形式隨承載的情感內容流動,形式美與音樂美相協,實現了雙重審美價值。《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體式大體整飭均齊。全詩由六個小節構成,采用四行一節的形式,每節體式相同,每行字數大致是五到八個,以短句為主。每節中一、三句,二、四句字數相同,錯落有致、起伏有序,均齊中不乏參差變化,整齊中不顯呆板,具有突出的形式美。節與節之間邏輯連貫,每節之內句間邏輯清晰,句法完整明晰,符合自然語言的規范。六節中每節前三句均保持相同,重復的章節便于譜曲時旋律的反復,歌眾的印象被不斷加深,瞬時性記憶轉換為長期記憶。僅靠每節末句的變化體現抒情主體的情感流動,構成文本自身的內在情感旋律——“我”在夢中的“依洄”“迷醉”“悲傷”,一個關于愛情的迷夢出現又破碎,天然地便可嵌合于外部旋律。徐志摩規范體式、語法自然的書寫策略使文本的情感邏輯清晰可見,內在的情感旋律充盈其間。
高 羽:論現代歌詞對徐志摩詩歌的改編
第二,用韻巧妙,節奏鮮明。韻是詩歌音樂美的重要表現形式,徐志摩注重詩的韻腳靈活恰當,押韻形式自由無拘、隨性多變。詩人在遣詞造句時多使用雙聲疊韻,字音的連綿凝滯間接促成了詩情氛圍的暈染,如《再別康橋》中雙聲詞“艷影”“榆蔭”“清泉”,疊韻詞“蕩漾”“青荇”“招搖”;《我有一個戀愛》中雙聲詞“異樣”“閃爍”“淚零”,疊韻詞“明星”“晶瑩”“殷勤”等,讀者無意識便進入了語音圍促的輕柔低回之中。徐志摩在英國留學時深受19世紀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雪萊、濟慈等影響,重視某一音素有規律地反復出現,即聲母的前后勾連,常常是前用一個聲母,后用一個相同的聲母。[4]《沙揚娜拉》中“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x”“d”“sh”“l”“sh”“l”“d”“x”前后勾連,形成綿延流暢之感,輔以雙聲疊韻詞,自然形成的吟哦旋律中又不乏一唱三嘆的曲折變化。多重韻律帶來的立體音效使詩作節奏鮮明,也更具有譜曲入樂的可塑性。“節奏作為表現手段的重要作用是在于能給曲調以鮮明的性格,具有強烈特點的節奏使人易于感受并且易于記憶,這大大有助于音樂形象的確立。”[5]徐志摩嘗試運用“音步”以增強詩歌的節奏感。《梅雪爭春》中“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每行拍數大體相同,整飭中貼合全詩低沉緩慢的旋律,增強詩人的憤慨悲切之情,為譜曲定下情感基調。
第三,抒情主體的出場,語境的褒義傾斜。“歌詞的基本結構是呼喚和應答。歌詞的外向語義主導,就是從發送者到接收者的情感呼應。”[6]考察徐志摩入樂譜曲的詩歌,基本上都有著顯性抒情主體的出場,即存在“請聽我說”的呼應姿態,強烈的主觀抒情得以有效顯露。《雪花的快樂》中,“我”是一片飛揚的雪花,追尋“她”的身影;《海韻》中“我”留戀單身的女郎。“我”代詩人而言,直接抒發情感。明確抒情主體的出場便于歌眾在瞬時性的接受中捕捉到“我”的情感經驗,“我”與歌眾之間的情感距離在雙向互動之中生成又消解,最終歌眾在回溯中產生情感共鳴并進行傳唱。需要指出的是,與歌眾產生共鳴的情感經驗須明朗易懂,具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色彩,語境向褒義傾斜,能喚起歌眾對美的向往和追求。《雪花的快樂》中寄托著詩人對愛與美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愛情雖然看起來可望不可及,但“她”身上朱砂梅的清香依然召喚“我”去追求愛的圣潔與高貴。《渺小》中“我”沒有復雜的情感糾葛,也沒有晦澀的意圖,詩人借“我”眼中的空谷幽景,描繪出一份寧靜自由的人生況味。可譜曲的徐詩大多意象簡單,情感明晰,抒情主體始終保持顯在,承載積極的價值導向,為詞化后歌眾實現情感共鳴提供文本支撐,感染歌眾追尋愛與美的理想。
二、詞化中的文本動態
對徐志摩詩歌的音樂化改編,筆者在本文中以是否進入語言文本內部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涉及語言文本內部改編,僅進行章節的刪減、重復,如分別由黃磊、鳳飛飛演唱的《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曲丹演唱的《雪花的快樂》等;一類是進行語言文本內部的改編,即保留詩歌的主題、主要意象,根據全新的創作意圖進行再創作,如由莊奴作詞、鄧麗君演唱的《海韻》,由文雅作詞、S.H.E組合演唱的《再別康橋》等。無論是否涉及詩歌文本內部的改編,歌詞文本的生成都要屈從于作曲家、作詞者、歌手等創作主體的顯性運作與時代環境、文化、政治等因素的隱微操作。
第一類不對詩作原有的文本空間進行徹底顛覆,僅對詩句的排列順序與形式進行必要調整。如曲丹演唱的《雪花的快樂》對原詩進行了重復,調整原詩的情感邏輯,將情感重點從原作中愛情的可望不可及適度游移,落在積極勇敢地追尋中,進行更正面的情感導向——為了保有全詩飛動飄逸氛圍,全曲由慢速到加速再到慢速,情感在雪花對方向的找尋中緩緩展開,節奏的舒緩讓這種對理想的找尋近似于凝滯;“在半空里娟娟地飛舞/認明了那清幽的住處/等著她來花園里探望/飛揚/飛揚/飛揚”在加速的節奏中重復兩次,全曲在“我”找到了“她”的欣喜中到達了旋律和情感的高潮,在加速的昂揚中反復渲染這種抵達理想之境的歡悅;“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瀟灑/我一定認清我的方向/飛揚/飛揚/飛揚”又在曲末的舒緩中再度重復,與起首四句相呼應,雖然最終“我”消融了,但還有無數的“我”在繼續追尋愛與美。
在歌曲傳播機制中,表演主體即歌手是最后一個關鍵環節,即歌曲的表現形態須與歌手個體表征保持契合。“歌星的闡釋有示范意義,當歌眾接受一首歌時,歌星的‘文本,對他來說是一個強有力的理解”。[6]259不同身份特征的歌手促生了不同的歌詞文本,也滿足了不同歌眾群體的期待視野。黃磊演唱的《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承續原詩低回婉轉的情絲,作曲采用深情、低沉的曲調,在較為慢速的節奏中對原有的抒情空間進行拓展延伸,以男性抒情者的身份娓娓道來。在此版本中,原詩的最后兩段被刪除,保留前四段的基礎上,以首段引入,對二至四段進行兩次重復。與原詩進行對讀,歌詞的體制明顯走向簡短化。與詩作可以反復進行情感體驗不同,歌曲的欣賞更側重于瞬時性、一次性。歌詞文本融合進旋律中變成聲音形態,歌眾在瞬息捕捉到聲音信息后,隨旋律推進不斷獲取新的情感共鳴,很難對已過去的聲音信息進行反復體味。此版本歌詞的簡短化既考量了歌眾的審美心理,又嵌合旋律邏輯調整情感變化過程,更符合歌詞語境向褒義傾斜的期待。歌詞的抒情邏輯被調整為“在夢的輕波里依洄”為始,在“她”的“溫存”與“負心”中曲折流轉,并隨著旋律變化在“甜美是夢里的光輝”中達到高潮,在“我的傷悲”中收束全曲。此種調整讓歌曲的情感重心落在追求愛與美的理想中,結尾的“傷悲”不過度渲染,點明了愛也有憂傷,歌眾在對愛的正面引導中完成對歌曲的情感體驗。
鳳飛飛演唱的版本其歌詞同是對原詩的刪減與重復,將其與黃磊版本對讀可見,黃磊版本除重復外無另做改動,配合低緩的節奏,更符合男性抒情者含蓄內斂的特征。而鳳飛飛作為女性歌手,情感體驗更加細膩,糅合進更加快速且輕柔靈動的曲調中,創造出不同的情感場域,目標歌眾群體也在一定程度上發生游移。緣此鳳飛飛版本的歌詞貼合于一個女性傾訴者的情感邏輯——“我不知道風”“他的溫存我的迷醉”等句反復兩次,“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改為念白的形式在曲中和曲末兩次出現,保留“在夢的悲哀里心碎”一段。相較于黃磊版本中詞段的重復,此版本的情感抒發在“我不知道風”“我是在夢中”等句的重復中更顯細膩幽微。女聲念白的加入讓情感體驗更具真實感,讓流動的樂聲短暫停滯,松弛中拉大情緒張力,再現了追愛卻不得的情感體驗,凸顯現代都市女性勇敢為愛付出的時代心理。
第二類保留原詩文本空間的意義指向,對具體文本空間的搭建進行再創作。徐志摩的原詩《海韻》情節單純,呈線性展開,通過完整的情節將詩意的表達予以攏合。單身女郎在海邊徘徊——高吟低哦——飛旋婆娑——海沫中蹉跎——海潮中吞沒,浸透著明顯的悲劇氛圍和哀嘆基調。語言口語化、意象簡潔清澈,且具有強烈的主觀抒情性,但作為抒情主體“我”對單身女郎情感復雜,或說女郎內質上是“我”理想追求的化身。有肯定也有否定,有歌頌也有惋惜,困惑迷茫縈繞其中,不適于直接原詩入詞。1927年趙元任用十天時間為《海韻》譜曲收錄在其《新詩歌集》中。此舉也就意味著《海韻》的譜曲有了文化功能的著重考量,配合趙元任推動中國音樂現代性發展的目的,真正將歌詞與譜曲定位為現代藝術門類,對青少年進行美育教育,彰顯“五四”文化精神。所以趙元任的改編使詩作文本徹底轉變為歌詞文本,刻意突出不同藝術門類的界限。將“暮靄”改為“暮色”,“急旋”改為“旋轉”,語言適應了口語化要求且在配曲演唱時發音更加清晰可聽。作曲家保留了原詩中“我”與女郎的對話姿態,添補“我是多希望你身旁”“和你去看大海去看那海浪”等語句強化“請聽我說”的召喚結構,原作中復雜纏繞的情感迷霧被廓清,“我”對女郎抱有更多積極期待,歌眾接收到趨向單純、正向的情感投射。發表于1974年的電影同名主題曲《海韻》,在保留原詩女郎意象的基礎上,由作詞人莊奴進行改編。囿于電影主題曲的文化功能,歌詞內容的改編須與電影情節互文同體,消融在影片中以輔助情節推進與情感抒發,獨立演唱時又具備電影宣傳的功能。“我”與女郎之間的呼喚應答,更著力表現對于愛情、品性等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訴諸鄧麗君婉轉的唱腔與輕柔的曲調,迥異于趙元任式的莊嚴磅礴,此版本的改編展現了女性坎坷的情感經歷。海浪是“我”“美麗衣裳飄蕩”,“我是多么希望圍繞在你身旁”,“我”與女郎徹底割裂成獨立的情感體驗對象,“我”既是抒情主體又起到情感上烘托、鼓舞的作用,鼓舞女郎也是在鼓舞歌眾追尋自由與美好。
歌詞對詩歌的改編多是“化繁為簡”,深刻曲折的詩體被消解,淺顯直白的詞體生成。上文中考察的改編無不是在做這樣的口語化處理,而由文雅作詞,S.H.E組合演唱的《再別康橋》卻在原作的基礎上走向復雜語態。這種復雜化既是作詞者主觀性凸顯,也體現著時代浪潮的裹挾——歌詞文本的語言陌生化、敘述方式的零度情感等均體現著世紀初現代詩的特性。首先是語言陌生化,打破自然的語法邏輯,將原詩的意象進行重新排列組合,產生全新的審美意義。“雨后水洼教堂傾倒意識流的四十度角”“壁爐終日孤獨吐著火苗/煤油燈下歲月不被驚擾”,打破對歌詞簡明易懂的期待。“教堂”與“意識流的四十度角”、“煤油燈”與“歲月”以一種逸出常理的順序勾連起聯系,句間邏輯也被隱藏或取消,這種陌生化的表達充滿著游戲意味,很難在歌眾的瞬時接受中被精準捕捉,歌眾的情感體驗在對歌詞的含混理解中導向多樣。其次是強烈主觀抒情性的隱匿,近似于“零度敘述”。在此版本中抒情主體“我”隱而不顯,詞作以局外人的視角對“你”展開觀照。取消“我”對歌眾情感體驗的顯性召喚,將歌詞的情感高潮置于“你在劍橋一身寂寞穿黑色學袍/你用詩句歌唱愛情押美麗韻腳”等句,反復刻畫“你”,即徐志摩的抒情形象。歌眾隨著歌詞畫面的漸次展開置身于局外人的視角中,將自身情感體驗放諸徐志摩的情感時空中以實現共鳴。此版本的改編不拘囿于歌詞明白易懂的原則,選擇在時代背景的催使下走向復雜向度的拓荒,彰顯了獨特的美學效果,這也不失為破除歌詞創作困境的敘說方式之一。
三、詞化后的文本流傳
歌詞對徐志摩詩歌的改編,是歌詞與詩歌在彼此借重中實現雙贏,二者在審美價值、傳播范圍上均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詩與樂的結合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中綿延未絕,直到五四時期,即新詩問世之初,少數新詩作品仍被作為歌詞入樂,也有少數新詩詩人直接譜寫歌詞。然而這種詩樂結合的局面并沒有延續,新詩的散文化、去格律化沖決著詩樂結合的藩籬。新詩只“看”不“聽”,走向了書面化的發展困境。中國新詩的傳播僅限于報紙、雜志、書籍等平面化的無聲世界中,不僅與樂結合的選擇被遮蔽,也在根本上對新詩的受眾進行了揀選,即只有具有一定文學素養的人才能品讀新詩。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加速了人們的生活節奏,也提供了多樣的娛樂方式,文學逐漸邊緣化,能靜心品讀詩歌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新詩發展前景的凋敝使“華語流行音樂成為中國新詩極富意味的一個參照系”。
徐志摩詩歌歌詞化改編的成功對身陷困境的中國新詩有著重要的啟示意味。對徐志摩詩歌的音樂化改編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起步,多數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被譜曲的詩歌共計四十余首,僅《再別康橋》就有十余版的改編,《偶然》《海韻》《雪花的快樂》也有眾多改編版本。歌詞改編后的文本變得清晰易懂、明朗簡潔,消解了新詩受眾精英化的阻礙,書面文字不再是唯一的傳遞符碼。多群體的歌眾被召喚進入抒情空間,為詩歌受眾群體的擴大提供了通達取徑。這也啟示著,面對新詩受眾群體大范圍缺席的境況,新詩的傳播應從單一的視覺性傳播向綜合多元的傳播方式轉變,嘗試入樂演唱等多種傳播渠道,以雅俗并存的方式實現突圍。在實現新詩與樂再度結合的運作中,不妨以徐志摩詩歌此類名家名作為先入手。一則這類詩作入樂實踐多,可借鑒范例多,考察其“一詞多曲”的情況鉤沉聯結出不同時代、不同音樂人的獨特選擇;二則這類作品的受眾群體相對廣泛,歌眾的期待更高,更容易在眾多音樂作品中被選擇聆聽。《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作為電視劇《人間四月天》的主題曲,隨著電視劇的熱播而廣泛被人熟知,在后續的傳播中抽離了電視劇主題曲的限定而單獨被歌眾接受,原詩、歌曲、詩人都獲得了更廣泛的傳播,即詩樂結合困境的突圍可由一定的物質載體、語境載體承擔。歌曲通過電視、電影、演唱會等各種語境載體開始其流傳過程,并在傳唱的過程中,實現“歌不附體”,由歌眾自發傳播。歌眾傳播的同時也在累積新的情感體驗,容納更多重情感共鳴的發生,以衍生出新的傳播動力。歌眾又可將入樂的徐志詩歌下載進CD、MP3、智能手機等電子媒介中,徐志摩詩歌便憑借豐富的載體深入日常生活中,再度出發、再度流行。
四、結語
歌詞對徐志摩詩歌的成功改編是詩歌與歌詞創作雙重困境突圍的嘗試,將“歌詩”傳統再度帶入現代學人視野,摒棄詩詞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復歸詩樂結合的文學傳統,在雅俗共賞中完成審美意義、流傳價值的再生。作為中國古典詩歌中重要組成部分的“歌詩”,如何在現代語境下實現傳統的賡續、煥發新生,是值得現代學人共同思考的課題。
參考文獻:
[1]郝亞莉.析中國現當代詩歌與音樂之關系[J].理論學刊,2008(7):118-120.
[2]徐志摩.徐志摩詩全編[M].浙江: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563.
[3]苗菁.入樂的新詩:體現雙重特質的歌詞:現代歌詞形態淺析(二)[J].詞刊,2006(3):33-36.
[4]張桂玲,姚慧卿.華美的樂章:論徐志摩詩歌的音樂性[J].宿州學院學報,2005(2):53-55.
[5]吳祖強.曲式與作品分析[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62:20.
[6]陸正蘭.歌詞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