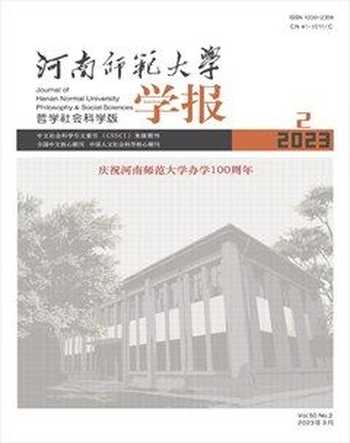歷史還原與關系重構: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新探
摘 要:“五四反儒學”作為支配學術界的主流觀點,反映的并非歷史的真實情況,此種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關系的誤讀根源于傳統與現代二元割裂的思維模式。究其實,五四新文化運動政治層面的批判主要因孔教運動而起,其實質是反對借宗教之名來行帝制之實;倫理層面的反思主要指向以三綱為核心的禮教制度,并未攻擊“仁”“義”等儒家形而上學價值;學術領域的“整理國故”更非對儒學的全盤清除,實為對儒家文化正本清源的價值重估。重新審視和還原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關系,發現兩者在歷史情境、儒學轉型、現實意義等領域具有重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應當在會通傳統與現代的基礎上,一方面用五四的革新精神促進儒學的創造和更新,一方面在廣義儒學的視野下將五四精神納入其體系之中,從而實現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的真正融通。
關鍵詞:五四新文化運動;儒學;歷史還原;重構
作者簡介:張少恩(1979—),男,河北邯鄲人,哲學博士,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儒學史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BZX069)
中圖分類號:K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359(2023)02-0122-08
收稿日期:2021-12-13
作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以來思想史上的關鍵性事件。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學界一般有兩種認識:狹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指1919年發生在北京的學生游行示威和上海的“六三”工人罷工,屬于政治愛國運動;而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除1919年的政治運動外,還包括此前興起、此后得到發展的文化革新或思想改良運動,其跨度從1915年的文學革命開始,至20世紀20年代的“整理國故”與“科玄論戰”等。廣義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已逾百年,百年來學界圍繞該運動的詮釋和評價經歷了深刻復雜的變遷與發展,呈現出歧異性、矛盾性、復雜性等多重面相。其中不乏學術上的誤解,最為典型的是將“五四反儒學”視為貫穿整個運動的主旋律,支配著五四研究中的主流話語和普遍共識。具體表現為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視五四與儒學為截然對立,以五四代表現代來否定作為傳統的儒學,認為建構現代性則必須徹底摧毀傳統性;另一種觀點從啟蒙精神出發,憑借西方的理性主義來考量東方的傳統價值,對儒學進行單向度化約,認為傳統儒學中存在與現代脫節的成分,應被剔除。這兩種觀點無論基于何種立場,基本上都堅持五四與儒學的二元割裂。即使在海外,“五四反儒學”的論調同樣盛行,如林毓生通過對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事跡分析,剖析了五四徹底反傳統主義的內涵,指出這種激進的學術觀點起源于傳統中國的唯智主義,即以思想來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思維模式。在此思維模式下,新文化人試圖通過對儒學的批判來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84頁。]。
“五四反儒學”的誤讀是學界在研究、解讀和構建的過程中逐步確立的,而這種詮釋多是后來學者在建構自己歷史觀過程中將已有成見強加給歷史事件,發展至今仍爭論紛紜。如何對此事件做出客觀、公允的評價是相關研究應關注的重點,對該事件的評價必須考慮五四運動發生的歷史脈絡和當時的國內背景。因此圍繞五四與儒學關系的探討,既要從近代學術思想史發展的脈絡著手,又不能脫離當時的國內、國際政治時局變動,盡量避免將事后詮釋者的邏輯強加于事件本身[ 龔群,安昭君:《思想觀念現代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南昌大學學報》,2020年第4期。]。目前,如何評判學界將“五四新文化運動”詮釋為“批孔反儒”的論斷,當務之急應通過厘清史實、還原現場、重構語境來發現五四運動的歷史事實,澄清其與儒學的誤解,并嘗試推動兩者的融通。
一、反孔教而非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
伽達默爾在哲學詮釋學中指出,任何歷史的理解都不是簡單的事實陳述,而是根據詮釋者本身固有的歷史理解、自身現有的知識結構以及當時的生存語境所做出的價值判斷,如果拋開詮釋語境,則難以對歷史事件進行合理解讀[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第34頁。]。因此,其中特定事件的發生語境是歷史評判中的關鍵,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解釋亦如此。從表面上看,五四健將“反儒”言辭激烈,很容易造成五四反儒學的假象。因此只有還原到五四前后的時代背景和五四新文化派的學術淵源中,方可揭示歷史真相。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儒”觀點具有明顯的政治指向,體現出鮮明的現實色彩。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于傳統儒學的攻擊,主要針對的是當時的儒學宗教化即孔教運動而發。在他們看來,民國初年的尊孔復辟中,孔子已然變成了一種符號而并非儒學本身,一些專制擁護者借孔教之名來行帝制之實。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五四健將群起而攻之。
從歷史發展來看,孔教思想起源于清末,康有為曾在維新變法時提議過,后由于變法失敗,立孔教為國教的主張也無從實現,但康氏并未停止創立孔教的努力。1903年康有為作《官制議》,提出設教會、罷淫祀、立孔教為國教,同年在海外華埠創設孔教會。之后不久,留美學生陳煥章于1907年在紐約建立昌教會,并于1911年9月28日以“倡明孔教,救濟社會”為宗旨,在上海成立了孔教總會。
最初的孔教設立并未引起思想界的爭論,但是隨后由于孔教與政治的結合,尤其是當立孔教為國教的呼聲愈演愈烈時,孔教問題就成為五四運動反對的焦點。1913年7月,陳煥章、嚴復、夏曾佑等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提出在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定孔教為國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維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 陳煥章:《陳煥章文錄》,岳麓書社,2015年,第241頁。]同年9月23日,趙炳麟議員提議立孔教為國教,遂在表決之后將其列入議題。隨后陳銘鑒、汪榮寶等人表示贊成,他們認為孔教對中華影響深遠,當下中國思想混亂,將之定為國教實為當務之急。10月13日國會議案付諸表決,但由于票數未過三分之二,立孔教為國教的議案未予通過。到10月28日,經過激烈爭辯之后,最終天壇憲法草案通過“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在此事件中,雖孔教未被定為國教,但是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為孔教的奔波及其與政治的過多牽涉為新文化運動中反孔教埋下了導火索,并最終導致了新文化運動將目標對準了孔教,并由對孔教批判的矯枉過正導向了對儒學的過度詮釋。
圍繞康有為等人的孔教方案,陳獨秀從1915年10月到1916年1月在《新青年》刊登《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再論孔教問題》等文章,主張儒學是人文教化,而非超世俗的宗教。“孔教決無宗教之實質與儀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 陳獨秀:《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9頁。]強調宗教沒有存在的必要性,人類逐漸進化,宗教將被科學所取代,將來一切的問題都可以由科學解決。胡適亦反對康有為等人的孔教說,認為孔子是人(圣人)而非神,更反對孔教運動將孔子當教主一樣崇拜,提出以孔教為國教有違信仰自由,為反孔教提供了學術依據。
在思想界反對孔教的同時,孔教會又卷入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中,這更加重了思想界的擔憂,激起了陳獨秀等人對孔教的激烈反對。袁世凱1912年就任大總統,進行了一系列的尊孔活動,如同年9月頒布《通令國民遵崇倫常文》,1913年發布《通令尊崇孔圣文》,1914年1月提出祭天祀孔案,1915年3月舉行祭孔典禮。趁著袁世凱、黎元洪等人的尊孔活動,康有為四處奔走,于1916年底撰《致黎大總統段總理書》,再度請愿立孔教為國教,陳煥章等人聯合各地方孔教團共同請愿。會議中發生爭辯,投票數次均無結果,最后達成妥協,廢去天壇憲草“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大本”而代之以《中華民國憲法》之“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緊接著,1917年7月,張勛、康有為等人擁立溥儀稱帝,結果遭各方反對,復辟失敗。由于康有為是該事件的主要策劃人,孔教會的支持者也曾參與其中,因此事件失敗后,孔教會再度遭到思想界的圍剿。
圍繞袁氏帝制與張勛復辟,反對者一致認為尊孔與復辟關系密切。代表性人物陳獨秀認為孔教與共和絕不相容,提倡孔教必定破壞共和,而信仰共和必定排斥孔教。他指出如果儒學被政治勢力綁架而失去了人文價值的學術獨立性,那就不是真正的儒學了,必然會淪為政治的附庸。李大釗亦認為以儒家修身之道為教育根本宗旨固然可行,但是如果只遵循此宗旨而一并取消授課、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則必定為專制背書、為君主充當護符[ 汪榮祖:《從文化與政治角度解讀“五四”前后的李大釗》,《文史哲》,2019第2期。]。
縱觀天壇憲法草案、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幾乎都與孔教會有聯系。然而清末民初以來,伴隨共和肇建、民權勃興,人們在觀念上對帝制深感痛恨。因此只要一提孔教,立刻有人敏感地聯想到恢復專制的企圖,尤其是孔教運動支持者是割據地方的軍閥,更增加了學界的擔憂。所以圍繞一系列孔教運動,五四新文化派提出“非儒”“反孔”等激進言論。質言之,與其說是“反孔”,不如說是針對利用尊孔名義來開展政治上的帝制與復辟活動。正如黃玉順指出:“孔子儒學被專制復辟政治勢力綁架,一些儒者成為專制勢力的幫兇或‘幫閑,這對于現代儒學來說無疑是一種深刻的歷史教訓。”[ 黃玉順:《新文化運動百年祭: 論儒學與人權:駁“反孔非儒”說》,《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而孔教和一系列政治運動的結合成為思想界的眾矢之的,其實與儒學并無必然的聯系,故反孔教并非反孔子。
客觀來講,拋開當時的政治因素,孔教自有其特殊的價值。中國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孔教的存在可以為現代社會提供精神支撐與信仰寄托,為社會生活提供合理的處事規范、德行價值及文化歸屬。其實,復辟與尊孔之間也沒有必然關系,尊孔的人不一定復辟,復辟的人也未必尊孔。就袁氏來講,其稱帝事件并未以儒家倫理作為依據,其尊孔動機亦非為帝制鋪路,而是期望用傳統道德來維系社會秩序。不可否認,孔教與帝制、復辟的諸多牽連造成人們對孔教的憎惡,加上孔教制度本身的缺陷,反對者的聲勢愈發強烈,終于由反對孔教而導向激烈地批評儒家禮教的反省。而思想界并未詳細辨別孔教與儒學的差異,逐漸將對專制的摒棄情緒轉而詮釋為反儒學,五四時代全面反傳統的誤解亦由此產生。還原到當時歷史中,結合五四的具體語境,綜合各種因素來系統考察五四中的反孔言論,究其實而言,應定義為反“孔教”。
二、反“禮教三綱”亦非反“儒家倫理”
正如五四新文化派反“孔教”而非學界所稱之反“孔學”,五四的“禮教”批判亦非所謂“非儒”。如果說批判“孔教”屬于政治活動的話,那么對“禮教”的批判則屬于倫理方面的反思,即新文化人名義上所批判的“儒學”事實中應指“禮教”。“儒學”與“禮教”各有所指,禮教基于三綱理論,強調忠孝。這是因為新文化運動所批判的“禮教”亦有明確的批判目標,其矛頭指向傳統時代的社會倫理和政治倫理,亦即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形成的傳統規范,并非儒家的核心價值[ 黃玉順:《新文化運動百年祭: 論儒學與人權:駁“反孔非儒”說》,《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4期。]。
從哲學角度來考察,文化現象可分為包括物質、制度等的形而下學具體層面和精神范疇的形而上學抽象層面。而傳統儒家在中國的影響既涉及形而上學,亦包括形而下學。詳細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儒”言論,其重點主要圍繞宗法禮制、禮儀規范等展開批駁,關注的是形而下層面的批判。而對儒家的形而上學層面,如仁、義、心、性等倫理價值則幾無涉及。歐陽哲生曾指出五四對于傳統倫理的批判主要在三個方面展開,分別是服務于君主專制的重視尊卑階層的政治倫理、壓制人格主體性的社會生活倫理以及重義輕利、只講虛文的價值倫理[ 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82頁。]。
當時的禮教“三綱”是批判的目標。陳獨秀將“三綱”視為禮教的核心,同時也指出“三綱”是維護社會等級的工具。陳獨秀在《吾人最后之覺悟》中說:“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明貴賤制度者也。”[ 陳獨秀:《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頁。]在陳氏看來,禮教的忠君、孝父、從夫是傳統倫理的根本,其他規范如風俗、鄉規、律法等都是從這“三綱”演繹出來的,從而形成了一整套忠君政治倫理體系。此禮教體系移孝作忠、家國同構,為歷代統治者所利用,并充當愚民的工具。吳虞被稱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從中國思想發展史的角度指出儒家禮教在歷史上的負面作用。他指出,秦漢以來,統治者以愚民為主,堪稱中國千百年來的最大問題所在,這種崇尚禮、忠、孝的愚民制度造成了國民的劣根性,加強了專制的程度,阻礙著中國社會的發展。他甚至還認為儒家禮教對于后世的危害要大于盜跖等人,“盜跖之為害在一時,盜丘之遺禍及萬世;鄉愿之誤事僅一隅,國愿之流毒遍天下”[ 吳虞:《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頁。]。魯迅參加到新文化運動中稍晚一些,其在五四運動中的影響主要從文學上展開,其關注的對象也是“禮教”。如在《狂人日記》中,魯迅展現了一個人的病態,剖析了傳統禮教的殘酷,揭露了禮教被傳統統治者利用并為其專制統治服務的本質。
要言之,陳獨秀等人對儒家的批判主要圍繞禮教展開,認為禮教作為形而下的社會約束性規范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在現代轉型中應該被徹底改造和清除。然而批判中未涉及形而上的價值理性,諸如對天、命、性等概念不僅沒有否定,而且還給予充分的發揚[ 張先飛:《對話的倫理與新文化道德規范建構:以“五四”新舊思潮論戰為中心》,《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陳獨秀、胡適等五四諸人莫不如此。即使當時健將吳虞亦承認其所攻擊的主要是禮教,并非禮儀。高力克曾指出:“新文化運動之反傳統主義的困境,在于其雖以全盤廢棄孔教為名義目標,但實際上真正攻擊的只是儒家的禮教規范,而并未涉及其仁學的德性價值。”[ 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東方出版社,2019年,第92頁。]
三、“價值重估”而非“全盤否定”
與政治、倫理學術領域一樣,現在史學領域對于新文化運動的評價也充斥著五四“拋棄儒學”和“全盤西化”的誤讀。然而,當時的歷史背景并非如此。以20世紀20年代“整理國故”思潮為代表,此運動與其說是否定儒學的文獻整理,不如說是正本清源的學術評價。胡適等人以理性的懷疑精神為出發點,結合傳統的文獻考證方法與西方近代以來的科學主義方法論,通過系統整理儒學文獻,平等地看待儒家與諸子,既反對將儒學奉為官學,亦反對強化儒學獨尊意識形態的努力[ 歐陽哲生:《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96頁。],從而進行價值重估,將儒學從傳統的一尊還原為現代多元的一支。
從學術淵源上看,胡適等五四健將都是承接清代樸學而來。樸學又稱漢學、鄭學,注重歷史文獻的翔實考證。而五四激進派早年皆受過系統的私塾教育,如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都生長于晚清末年,經史功底深厚,博學多聞,無所不包。具體言之,蔡元培精于考證、醫學、算術等各類學問,其對樸學“是偏于詁訓及哲理的,對于典章名物是不耐煩的”[ 蔡元培:《蔡元培談教育》,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7頁。]。陳獨秀雖從小即具叛逆性格,但迫于祖父的權威而隨其兄研讀經學,年僅17歲即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秀才,足證其舊學修養出色,尤擅長文字聲韻之學。胡適也是在清代樸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從小恪守嚴謹的學術探索風格。要之,五四諸人的早年學術熏陶對其后來的治學模式影響很大,使五四新文化人培育了對文獻考證的濃厚興趣和對學術整理的科學精神。
從中國傳統學術脈絡來看,新文化運動也是明清以來學術發展的一個階段,其對儒學的價值重估是三百年學術的延續與演進,同時也受清代學術范式變遷的直接影響。簡單拋開近三百年“復古解放”思潮,則無法說明新文化人重估傳統價值的緣由。歐陽哲生指出,清初以來“以復古為解放”的思潮和漢學家的治學路徑,是五四新文化的傳統根源[ 歐陽哲生:《新文化的源流與趨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89頁。]。梁啟超將明清以來的學術史進程定義為“復古解放”,從明末顧炎武的“復宋之古”開始,歷經乾嘉學派的“復漢唐之古”、康有為的“復西漢之古”,直到章太炎以古文經學的“復先秦之古”。而這種復古具有內在邏輯層層推進的發展歷程,其中始終貫穿著證偽的批判精神。到五四時期,學界對整個傳統的重新評價便應運而生,作為一面文化革新的理論旗幟,胡適以“整理國故”的批判態度對待傳統儒學,成為新文化人的新抉擇。此價值重估包括消極與積極兩部分:消極方面是質疑“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舊經學權威,清除其不可懷疑的神圣性;積極方面是用引入的新的研究范式對傳統儒學進行重新整理和價值重估。在新文化人“破舊”與“立新”的價值重估中,體現出三個典型的特征。
首先,理性與懷疑精神。胡適等人以理性立場來評價儒學價值,以質疑的態度對待儒家經典。此理性與懷疑精神既有中國傳統的學術影響,亦有近代以來西方的啟蒙熏陶。當然,所謂理性的評判并非全然地拋棄和清除,而是審慎地考察與重估,并探索其有益的價值。如圍繞儒家“三年之喪”的禮制,胡適根據傅斯年在《周東封與殷遺民》中對于宋、魯等殷商后裔喪禮風俗的文獻資料,依照《論語·陽貨》篇的“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的記載,并且這些行三年之喪的代表人物太甲、高宗、帝辛等都是殷人,因此推斷出“三年之喪”應該是殷商遺俗,主要通行于宋、魯、衛等國。除了引用以上材料之外,胡適還以其他文獻予以佐證。如在《公羊傳》中魯僖公死后,第三年其子文公娶妻,應該不符合魯國守喪三年的宗法制度,但在《公羊傳》中認為文公娶親事件并未違背當時禮制[ 胡適:《胡適文存》,第4集,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7頁。]。因此,胡適證明“三年之喪”并非周王朝的通行之禮。陳獨秀盡管在新文化運動中出于反孔教而矯枉過正反儒學,但在《孔子與中國》中是認同儒家的學術價值的,并通過系統的文獻考察,梳理了儒學發展的歷史,闡釋了儒學史上四個階段的轉型歷程。此觀點盡管在學術上存在爭議,但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他能夠客觀地站在理性、科學的立場上評價儒學,而非學界所認為的對儒學的徹底清除。此理性的懷疑精神在當時的學術界影響深遠。如提倡疑古的顧頡剛到晚年依然強調:“當五四之后,人們對于一切舊事物都持了懷疑的態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適、錢玄同等經常討論如何審理古史和古書中的真偽問題。”[ 顧頡剛:《我是怎樣編寫〈古史辨〉的》,《古史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頁。]這種理性與懷疑精神體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求真態度,也即通過客觀的學術評價,還原儒學的本來面貌。
其次,重視哲學方法論。國故整理時各派學人普遍重視學術背后的方法論,認為這種“以一御萬”的金鑰匙是研究的關鍵。如胡適融合理學、樸學、進化論、實用主義,融會貫通形成一套哲學方法論,然后以此理論體系來解析整個儒學傳統,并且胡適的整個思想已經方法論化了,甚至連民主與科學也是方法而已[ 史云波,董德福:《五四思潮與五四人物研究》,江蘇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0頁。]。這種方法論哲學作為多元解讀的“他山之石”,為儒學儒家經典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推動了儒學的現代轉型,使之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以儒家的歷史哲學考證為例,胡適在《孟子·公孫丑下》中談到歷史哲學:“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胡適借鑒西方希伯來宗教中預言事例來論證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歷史哲學存在價值,并根據《公羊傳》“魯襄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而獲狩磷”的史實與儒家互為引證,將孔子比作殷民族的“將有達者”的圣人,正合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歷史哲學預言。胡適稱:“上溯歷史距殷商武庚已經有五百多年,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早就有,因此宋襄公事例也可以證實,當時這種預言的存在……可見,孔子是民眾之中五百年應運而生的圣人。”[ 胡適:《胡適文存》,第4集,首都經貿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頁。]
再次,求真務實,經子平等。五四新文化人完全以平等的眼光評判儒學,將之視為客觀的研究對象,并將一元獨尊的經學視為多元諸子學的一支,同時隨著學科范式的演進,將儒學進一步分化到文史哲現代學科體系之中。如此一來,無論是在諸子研究視域中,還是西學分科體系中,儒家思想都是平等的一元。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諸子平等、今古文平等,包括文學、歷史、哲學的諸學科平等,甚至文學內部的小說、戲劇、詩歌、散文等皆雅俗共賞。
具體來講,胡適基于諸子平等的立場對儒學進行客觀評價,以平行的眼光來評判孔、孟、老、莊、墨等諸子,并主張在儒學的研究中應跳出儒家的局限,用純粹學術的視角來評判儒學,“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以儒家的立場來詮釋儒學,在價值認同上以孔子為旨歸,難免會產生偏頗,有違價值中立。如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中認為孔子、孟子在哲學史上地位重要,稱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等同于西方歷史中的蘇格拉底。與馮氏觀點不同,胡適從文獻考據出發,認為孔子曾問禮于老子,因此傾向于老子先于孔子;同時指出馮友蘭的哲學史撰寫尚未跳出儒家的視域,在價值上偏袒儒家。蔡元培曾稱贊胡適具有平等的眼光,“適之先生此編,對于老子以后的諸子,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短處,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是很平等的”[ 胡適:《中國古代哲學史》,蔡元培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李大釗作為早期唯物史觀學者,亦以求真務實的平等眼光對待儒家思想,并在評判儒家學術地位時突出諸子平等,同時也否定了把圣人言論作為判斷標準的迷信。他尤其強調孔孟的真精神,而非獨斷化、權威化的孔子,反對盲目崇拜孔孟,并認為只有能夠“自我做主”,才能體會到孔孟的真精神:“孔子嘗示人以有我矣。孟子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孟子亦示人以有我矣。”[ 李大釗:《史學要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2頁。]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儒學的選擇性批判立場,以審慎的理性態度來分析儒學的學術價值,一方面致力于探索儒學的歷史發展流變歷程,剔除其與現代社會不契合的成分,還原儒家學術的本來面貌;另一方面,褫奪儒學的獨尊地位,使之回歸到學術平等之中。因此,五四新文化派對儒學的評價與其說是全盤否定,不如說是對儒學的“價值重估”。
四、融通何以可能
五四新文化運動至今已逾百年,百年來學界圍繞五四與儒學的關系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縱觀“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對儒學的反思,經由政治文化層面的孔教批判推向倫理層面的禮教反省,再到學術層面的價值重估,發現五四運動使儒學土崩瓦解的學術判定并非歷史事實,新文化陣營對待儒學并非全盤否定,究其實是對儒學的“價值重估”。而以往學界將五四解讀為“批孔反儒”的主觀臆斷更像是激進反傳統主義的斷章取義。因此,學界應還原五四時代的儒學批判,全面考察五四健將的價值取向,尤其是重構五四與儒學的關系,二者在內在邏輯上是否沖突、能否融通,及如何融通是當下中國學界應該首先考慮的主題。
首先,從五四的歷史情境與問題解決方式來看,五四與儒學的思維模式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此為融通的邏輯基礎。從事件起源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源起于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政治、思想等問題,同時亦包括當時被學術界放大了的民族危機。五四新文化派對于傳統儒學的批判正是解決當時社會危機的一種倡議。從問題解決模式來看,與傳統的唯智主義類似,五四新文化派致力于通過文化革新來應付社會問題,探索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而此方案與儒學中以人文來化成天下的模式具有內在一致性。換言之,這種以文化解決政治問題的模式展示了唯智主義一貫的思維模式,在此思維模式下,五四新文化派試圖通過對儒學的批判來推動中國的現代轉型,體現了中國人文傳統自身演進的內在規律,暗示了新文化運動的發生、發展是以儒學作為自身的基礎,并以之為基礎來對傳統進行現代性改造的。包括林毓生在內的一些海外學者也認為五四的反傳統思想中透視著傳統儒家的思維結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五四新文化派是“批判的儒家”。
其次,從儒學史的發展歷程來看,新文化運動推動了政治儒學的解體和多元儒學的新生,兩者具有融通的思想史基礎。在傳統中國,政治化儒學通過掌握經典詮釋話語權來享有獨尊的社會地位。然而進入20世紀,伴隨著科舉制的廢除、天壇憲法修身之學的確立、孔教運動的政治風波,獨尊的政治儒學遭遇極大的挑戰,尤其是五四的沖擊使其失去了政治“話語霸權”的特殊地位,趨向式微與解體。但政治化儒學的消解不但沒有使儒學走向衰落,相反被政治儒學壓制的其他層面的儒學迅速走向前臺,構成了儒學發展的新起點,給新儒學帶來了自主與繁榮,推動儒學向學術、社會等方面的轉型,在多個領域尋求庇護與發展。當然,這種現代轉型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因為只有經歷多元化的轉型才能被現代世界接受,從而保持“在場”的機會。在此背景下,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多元儒學的崛起開啟了儒學現代轉型的序幕:一是哲學化儒學。在此脈絡中,心學是儒家哲學現代轉型的主要進路。熊十力、梁漱溟等新儒家學者以心學為理論框架,找回失落的中華人文精神,彰顯儒學的生命特質。繼之,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第一代新儒家基礎上,繼續以心學為立足點,通過吸納西學、會同中西,從而重鑄儒家形而上學的體系,為現代社會提供心靈慰藉和信仰寄托。二是史學化儒學,同時也是知識化儒學。唯物史觀學派和西化派依據西方學術范式來研究儒學,此脈絡主要分布在大學和學術研究部門,其研究模式將儒學作為一客觀的對象來對待,圍繞儒家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展開研究[ 徐慶文:《20世紀儒學發展研究》,山東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83頁。]。三是社會化儒學。即儒學關注生活、走向民間的社會化訴求。在傳統中國,儒學與禮教一起被政治化了,然而進入現代社會后,隨著宗族的解體,儒學轉向新的存在方式。社會儒學即儒學的民間存在方式,也就使儒家教化在鄉間社會、城市社區扎根,切入百姓生活,化民成俗。五四之后,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標志著社會儒學的崛起,這種儒學社會化脈絡成為儒學的新形態。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社會儒學踐行者走出了“學而優則仕”的眷戀,呼應民間訴求,順乎人心需要,在社會各領域發展迅速,從而推動了儒學的現代轉型。
再次,從后五四時代的學術評價來看,后來的新儒家也認同五四批判精神的積極意義,兩者具有融合的價值認同。當然在五四初期,學衡派等文化守成主義者處于批判漩渦中,出于對儒家道統意識的維護,他們對五四的偏激態度頗有微詞,大力為儒學申辯。但隨著新儒家的崛起,梁漱溟等人對五四的評價大有改觀,深刻反省了儒家倫理的流弊,肯定了五四以來解構政治化儒家的必要性。如錢穆曾指出:“當新文化運動進行方銳之際,對于本國舊有文化思想道德,每不免為頗當之抨擊,篤舊者已不能無反感。”[ 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341頁。]梁漱溟曾自稱在拯救中華民族的選擇上與陳獨秀、胡適等人意見相左,但對于新文化人的禮教批判和文化擔當精神還是認同的[ 梁漱溟:《漱溟卅后文錄》,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21頁。],并表達了與五四反傳統主義者多個領域相近的觀點。這種對五四批判的認同到第二、三代新儒家時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確認。由于人生體悟、時代背景、思想趣向的不同,新儒家能夠以海納百川的文化氣魄,客觀地省察五四的功過,從而對之進行全面、公允的評判[ 董德福:《現代新儒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省察梳要》,《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并從“相反相成”的意義上肯定了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認為五四的沖擊并非造成“儒門淡薄”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儒學史上,無論是諸子非儒還是佛教東傳都是儒學之外的否定,這種外在的學術沖擊從未擊垮儒學,真正造成儒學衰落的原因主要來自非學術的腐蝕和批判精神的喪失。如康有為利用政治推動孔教國教化、袁世凱等借尊孔之名而行復辟之實是造成儒家式微的真正原因。其實五四新文化健將們對儒學的批判性反思如同黑格爾的否定之否定理論,充當了儒學發展的外在動力,激發了儒學吸納新事物的契機,推動其螺旋式上升,從而進行徹底的轉化、改造和蓬勃發展。如賀麟曾認為五四是推動儒學更新的重要契機:“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大轉機……新文化運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軀殼的形式末節,及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它并沒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學術,反而因其洗刷掃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顯露出來。”[ 賀麟:《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6頁。]杜維明稱贊“五四”新文化人的啟蒙精神:“當時中國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聯合陣線,對儒學進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義……陳獨秀提出新青年應該有開拓的、前進的、面向未來的志趣,和胡適提出的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價值觀念,以及科學與民主的提倡,在當時都有深刻的意義。”[ 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54頁。]
最后,從當下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來看,五四與儒學的關系重構關涉到中華民族現代性的重塑問題,兩者的融通與互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中國作為有深厚歷史積淀的民族國家,在現代轉型中如何塑造自我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黃玉順稱之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 黃玉順:《論儒學的現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他認為現代中國的崛起與傳統儒學的復興密不可分,必然在內在邏輯方面需要吸納儒學的價值資源。因為傳統與現代并非截然割裂,現代中國不可能拋棄傳統橫空出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的中國需要在傳統的基礎上進行多個維度的除舊更新,推動中國向現代革新轉型。因此沒有儒學的復興就沒有中國的崛起,沒有中國的崛起就沒有儒學的復興。進言之,現代中國崛起的必經之道路,應該是將以儒學為主干的古典傳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革新傳統結合起來。正如朱承指出的:“我們應該將‘孔夫子代表的儒學傳統與‘胡適之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傳統從對立的歷史糾結中解脫出來,實現二者之間的和解。”[ 朱承:《儒學傳統與時代精神:兼論儒學與新文化運動的和解》,《船山學刊》,2015年第3期。]即五四通過對儒學的批判為禮樂文明的儒學補充了民主、科學等現代性價值,這種思想的補充與融合使得“孔夫子”與“胡適之”一起合力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即中華人文精神與西方個體價值在古典精神與現代精神互為涵攝的視域中發掘儒學傳統資源,推動中華民族的現代轉型與崛起[ 耿云志:《五四:現代中國的新起點》,《歷史研究》,2019年第2期。]。
結語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的批判給儒學帶來了重大變故,影響了儒學的發展進程。但這種外在的沖擊作為儒學史上的考驗和淬煉是儒學發展的動力和契機,推動儒學實現自我否定、自我改造、自我更新的現代轉型。換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學的批判,與其說是儒學的解體、崩潰,不如說是在革新儒學和重構儒學[ 歐陽軍喜:《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誤解與其他》,《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畢景媛,傅永聚:《“五四”儒學反思的當代再反思》,《甘肅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正如黃玉順所指出的:“儒學的再次跨越歷史時代、穿越歷史時空,乃是以五四運動為一個關鍵契機的。這為我們評價五四運動提供了一個特定的視角: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現代性的儒學。”[ 黃玉順:《儒學與中國之命運:紀念五四運動90 周年》,《學術界》,2009年第3期。]并且在當代世界,文化走向多元,儒家思想必須經過現代性革新方可融入現代社會,傳統價值只有經歷個體價值的洗滌才可進入世界的新格局。因此,面對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學界既要全面認識儒學的傳統價值,也要接受新文化運動的維新精神。在對待五四新文化運動與儒學傳統的關系方面,既要避免全盤西化的反傳統立場,也應杜絕反對吸納西學的復古主義,防止非此即彼的二元割裂。將現代與傳統對立的二元論立場無助于推動中國的民族性崛起與儒學的創造性轉化。因此在古今兩種傳統匯合的基礎上,一方面要用新文化人的革新精神推進儒家思想的創造與更新,另一方面要在廣義儒學的視野中將五四批判精神納入儒學體系之中,從而實現儒學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真正的融通。正如《文史哲》編輯部在舉辦五四運動百年學術研討會時提出用儒學價值來紀念五四百年的倡議:“如果說長程的歷史總是遵循‘正—反—合的辯證邏輯的話,那么,在整整一百周年之后,世變時移,是不是也該輪到一度被置于‘新文化對立面的‘儒學,在更高的層次上與‘五四握手言和了呢?”[ 鄒曉東:《儒學與“五四”能和解嗎》,《中華讀書報》,2019年6月12日。]
Historical Restoration and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A New Probe into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Zhang Shaoen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23,China)
Abstract:
“May 4th anti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stream view dominating the academic circles, does not reflect the real situation of history. The misrea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is rooted in the thinking mode of the separ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fact, the political criticism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mainly due to the Confucian religion movement, and its essence was to oppose the practice of monarchy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The ethical reflection mainly points to the ethical system with the three guiding principles as the core, and does not attack the Confucian metaphysical values such as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heritage” in the academic field is not a total elimination of Confucianism, but a r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the source of Confucian culture. Re-examine and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and find that they have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fields of historical situation,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o on.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connect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on the one hand,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the creation and renewal of Confucianism,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irit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should be brought into it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oad Confucianism, so as to realize the real integration of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Confucianism.
Key words: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Confucianism;historical restoration;reconstruction
[責任編校 王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