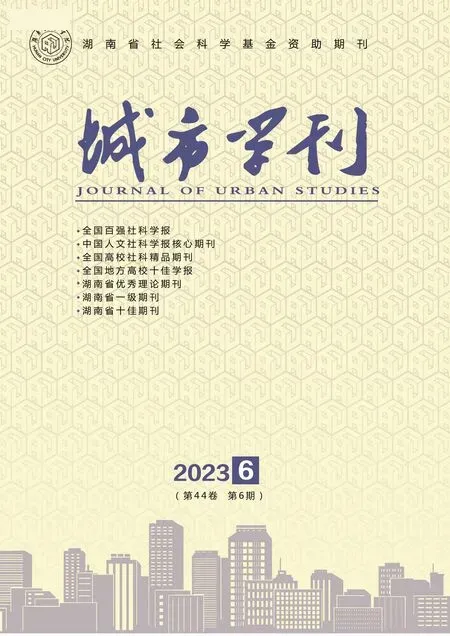情欲與創作的對話──論林白小說的身體詩學
秦世瓊,鄧福艷
(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小說創作開始從人性復蘇逐步轉向身體回歸,其中以鐵凝的《玫瑰門》、王安憶的“三戀”為發端,繼之有莫言與王小波的小說創作,他們對“身體與性”的探索凸顯了身體所蘊涵的深意;90 年代又逐漸出現女性作家“身體寫作”的熱潮,它不再傳達抽象化的“思想”符號,也不再囿于女性傳統意義上被壓抑的靈肉沖突,它超越女性的一般歷史情境和現實境遇,深入女性生命本真,以童年記憶、成長期性意識、同性之戀和自戀以及母性意識作為書寫對象,展現女性的身體與欲望,捕捉人物靈魂深處的真切感受,從而對人的生命意識作全方位觀照。林白的小說《一個人的戰爭》在20 世紀90 年代末掀起學界對女性文學論爭的一個高潮,丁來先、王小波、徐坤等評論家相繼加入這場聲勢浩大的論爭。論爭之中,林白有回應與澄清,也有其深陷詈罵與詰難時的自辯與矯枉,論爭余波延續至21 世紀,至今未有明確的勝負之分,但通過這樣的辯駁與反思,學界達成共識,即1990 年代林白的身體寫作是女性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品具有女性文學的顯著特征。2021 年林白新作《北流》橫空出世,王春林盛贊林白徹底打開了自己,打開了生活,打開了世界,打開了人類的存在,可見林白在文學創作過程中實現了身體品格的文化提升。而林白小說世界所呈現出的女性身體的生命本能,又可視為女性感知外部世界的肉體生命意識取徑,這反映了她對女性身體的“愛恨交織”,展現出有別于男權中心話語與主流敘事的顛覆性特質,是她在努力尋找屬于女性自我的話語空間。
一、異質空間的身體凝視
福柯(Michel Foucault)以“異質空間”(heterotopias)來研究對立社會關系,他認為在異質地方總是預設了開放和關閉的系統,事物可以同時性地并置或呈現。在異質空間中可能存在一種混合的、中間的經驗,可能是鏡子。鏡子作為一個烏托邦,是一個沒有場所的場所。鏡子作為異質空間的作用是:它使得我注視鏡中之我的那瞬間,我所占有的空間成為絕對真實,和周遭的一切空間相連結,同時又絕對不真實,因為要能感知其存在,就必須通過鏡面后的那個虛像空間。[1]福柯“異質空間”理論徹底顛覆了人們習以為常的隱蔽的空間秩序,打破了單一秩序的宏大敘事,從社會關系出發對空間重新界定。
林白的寫作手法巧妙地與福柯的異質空間相結合,鏡子在她的小說里反復出現,小說人物在鏡子里成了自己的公主,鏡子是通向性別、真我、記憶的康莊大道。通過鏡中之我與鏡外之我的相互凝視,分裂的自我在亦真亦幻間獲得了暫時的妥協,也是女性展露自我情欲的手段,而不僅僅是“宣泄女性內心情感的文字堆積以及對女性身體的瘋狂迷戀和‘自囈’”。[2]林白的小說注重自我的真實書寫,大膽地將女性成長中的生理感知與心理流程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林白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身材瘦弱的女孩,她們自小養成獨自洗浴的生活習慣,唯有身體處在隱秘狀態下才會覺得安全,即便是與其它女性在公共澡堂共浴,將身體裸露在同性面前也會讓她們感到難堪、絕望。這種對自我身體的嚴密保護也造成了其內心的孤獨,而此種面對自我身體的觀感向外延伸,間接影響到她們與外界的交往,加強了她們性格中自我幽閉的傾向。“鏡子”是窺視林白小說人物內心的捷徑,她“將鏡子里的那個形象當作女性的本源,‘鏡像’意味著女性本來面目的呈現”。[3]《玫瑰過道》中有一段極具代表性的陳述,故事的敘述人稱在“我”與“她”之間隨意切換──當敘述者以“她”發聲時,實際上即是“我”的自我反省,具有反諷的效果。
她無數次在夜里面對穿衣鏡絕望地看過它們,看久了會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既不像男人也不像女人。看久了連她自己都會感到害怕,但她常常不記得這點,因為她已經習慣了,甚至由習慣變得有點自戀了。[4]
由“絕望”“害怕”等字眼,可以看出敘述者“她”對自己的身體不符合男人喜好的標準而深感苦惱,更將戀情的失敗歸咎于自身“丑陋不堪發育不好”,從而一再否定自我,無視兩人交往過程中情感付出不對等的危機。
鏡子成了阻隔女人將欲望的觸角向外延伸的屏障,就有一些女人試圖破鏡突圍,自我情欲從封閉狀態中流泄而出,而這個過程中往往給她們帶來更多的傷害。璩是一個有錢卻孤獨的女人,她選擇以金錢豢養男人,試圖從中培養出一種類似愛情的幻覺,最后卻因殘酷的現實而引發強烈失落感,在自殺前發瘋地用口紅涂繪赤裸的身體:“她對著亮光在鏡子里欣賞自己,她異常細膩的白色體膚上布滿了艷紅的印記,既像鮮血又像花朵”。[5]
當女人的內在情欲公然宣泄失敗后,她們只能退回房間內對鏡自我欣賞。《致命的飛翔》中有描繪女性對鏡自照的情景,北諾由此對自己身體產生一種近于迷戀的自信:
在鏡子里她看到自己細腰豐乳,她有些病態地喜歡自己的身體,喜歡精致的遮掩物下凹凸有致的身體。[5]59
北諾和林白小說中其它女性一樣,只對自己的身體有著深刻的迷戀,甚至只是通過對鏡想象便能使身體獲得致命的快感體驗,但一旦涉及與男人之間的性愛,她們對于性的美好想象便蕩然無存。
二、疼痛失落的身體記憶
女性主義學者認為:性愛是人類生存繁衍的基礎,也是文學亙古的文化母題。“性”是林白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她以女性性意識的“異化”為切入點,充分展示其特有的女性寫作立場和極端個人化的寫作姿態,向人們嶄露出當代女性擺脫被男權文化敘述命運的努力,充分表達了實現女性自我價值的強烈愿望。
在林白的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性事往往充滿痛苦與難堪的晦澀記憶。多米在某次只身旅游途中受到男子矢村誘騙而失身,“初夜像一道陰影,永遠籠罩了多米日后的歲月”。[6]在那次性經歷過程中,她收獲的不是快感,而是傷害,被陌生男人強暴的絕望感使多米墜落到黑暗的“深淵”,她因男性對她的性侵犯而感覺到自己只是作為性對象的命運。后來與青年導演N 的性經歷,同樣沒有喚起她任何身體快感,而僅僅是通過性愛來證明自己在他心目中還有地位。正是在這種感受的指引下,她明白,她對N 的感受不過是一種自憐與自戀,因此在離開N 之后,她幾乎馬上就忘了他。
在林白那里,即便是在婚姻秩序內的兩性關系也遠非和諧,《說吧,房間》的敘述者老黑自承“我從來沒有過青春年少水乳交融的性生活”,為應付沉重而瑣碎的生活壓力,老黑已是精疲力竭,對性愛毫無興趣,做愛中的丈夫“變形的面容、丑陋的動作、壓在我身上的重量,這一切都使我想起獸類”。[7]此處的性愛徹底淪為使女性備受壓抑的動因。
不難發現,床第之歡在林白筆下經常被描寫成令人不悅的交媾行為。但在偶然出現的美妙時刻,林白多選擇從女性視角呈現性愛的高潮感受,男人則被有意淡化處理,遭到大幅度的剔除,仿佛男人只是協助女人獲得性快感的工具。
這聲音又像是一根鞭子,抽打在男人的身體上,它被策動起來,奮力撞擊,頻繁往返,節奏有如奔騰的烈馬,馬鬃在飄揚,背部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它的下面就是土地一樣的女人,如同草原般芬芳起伏。她濃黑的頭發散落在乳白色圖案的枕頭上,左右滾動、掙扎,像是要掙脫一次酷刑,她像一個瘋子用指甲掐進那個想要制服她的男人的背部。[8]
性愛過程中的女人把男人想象成待馴服的烈馬從而尋找自我快感,這恰恰是林白小說的特殊之處。在林白的有意形塑之下,女人作為對身體異常敏感的感受主體,更是主導、掌控自己情欲的主人。
不難發現,林白對于身體的書寫是有節制的,她并不將身體寫作當成一種游戲的消費主義實踐,她筆下的身體書寫,并不像衛慧、棉棉一樣致力于展現女性生活的癲狂狀態以及欲望的裸露,而是清醒地與身體書寫的商業化及游戲化傾向保持距離。林白小說中男女之間的愛情總以失敗而告終,缺乏情愛的性愛關系又令人不忍卒睹。有無愛情早已不是男女發生性關系的必要因素,即使沒有男人,女人依然能以自慰的方式宣泄內心的情欲,并能獲得比男女性愛更強烈的滿足。
三、心靈創傷的身體療治
西克蘇(Helene Cixous)指出,女作家“通過寫她自己,婦女將返回到自己的身體,……她通過身體將自己的想法物質化了;她用自己的肉體表達自己的思想。”[9]林白在小說中虛構了一個驅逐男性的女性世界,這個世界里的女性用自慰與同性戀的方式逃離與反叛男權的壓抑。
林白小說中表現出對女性她者美妙軀體深層的欣賞與迷戀、女主人公自慰所帶來的無窮的快感,這一切都成了女性療治心靈傷痕的靈藥,“她的人物并非毫無欲望,只是在男性一頭的絕望使其欲望變成無對象的展示,情色成為一種真正的自娛,在純粹的意義上完成了女性的自覺”。[10]
《一個人的戰爭》中的多米由于當地居民習慣單獨洗浴,致使她對體態優美的女性產生一窺其裸體的念頭,而女演員姚瓊“身體修長,披著一頭黑色柔軟的長發,她的腰特別細,乳房的形狀十分好看”,[5]16成為多米最佳的幻想對象。當多米目睹姚瓊在她面前更衣時,“我的內心充滿了渴望。這渴望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想撫摸這美妙絕倫的身體,就像面對一朵花,或一顆珍珠,再一就是希望自己也能長成這樣。”[5]17年幼的多米身材瘦小,因此將美麗的姚瓊視為女性形象的典范。在面對真實女體的當下,多米自認為她只是純粹地欣賞女性美,而這種女性審美的目光中不含任何肉欲的成分,因此未曾興起觸摸她者身體的渴望,更不愿意由此被誤貼上同性戀的標簽。
《回廊之椅》里朱涼的身影顯得虛幻而詭秘。朱涼雖然是被敘述的對象,卻未真正現身,她只存在于七葉的懷想和陳述中,而“我”則成為七葉用來倒映朱涼身影的鏡子。在“我”對朱涼的幻想中,朱涼是一名具有不可思議美感的女人:
在酷熱的夏天,朱涼在竹榻上常常側身而臥,她豐滿的線條在淺色的紗衣中三分隱秘七分裸露,她豐滿的線條使男人和女人同樣感到觸目驚心,在幽暗的房間中既像真實的人體又像某幅人體畫或者某個虛幻的景象。[4]163-164
“我”對于朱涼的靜態美以“遠觀”“遙想”的方式呈現,雖不是對女性之軀的實質描繪,卻呼應著林白屢次在小說中精心雕塑的理想女體。
無論是《一個人的戰爭》對女性主人公接觸她者身體經驗的實寫,還是《回廊之椅》虛寫的神秘而美麗的女性形象,都傳達出一個明確而重要的信息:女性借助同性之間身體的觀照,進一步確認出自我身心認知的位置。這既是作品主人公所向往的理想女性形象,也反映出林白欣賞女性之美的審美趣味。
潛隱于女性內心的情欲一旦流露于外,其具體展現便是“自慰”。“自慰”是林白筆下的女性人物出現頻率最高的性行為,她以詩意、優雅的方式描寫女性從中獲得的快感;而男女之間的性愛則多半丑陋而令人恐懼,兩相對照之下產生強烈的反差。多米具有這種“經常性的欲望”,其自慰的舉止被賦予優雅的詩意,游魚與水液的意象彼此融匯,女人在 “掙扎”“猶豫”而又“固執”的自我撫觸中得到一種“致命”的高潮,讓自己心甘情愿地被極致的自足感所“吞沒”。然而,林白對身體的自慰書寫是節制的,她筆下的身體是敏感度極高的感受器,且所有的感受都指向了女性身體的自由與解放。
而在同性戀方面,林白展現給讀者的模式更是充滿失落和無望,在涉及同性戀的性關系之前,女主人公往往從一段可能發生的愛情中落荒而逃,早早遏止了同性戀的發生。多米雖然承認“我真正感興趣的也許是女人”,但僅止于此,她一再辯稱“在我沒有愛上男人的同時也沒有愛上女人”,[5]15《玻璃蟲》的林蛛蛛也如此說:“雖然我向來喜歡欣賞美麗的女性身體,但僅限于欣賞,她們的身體從來沒有引起過我的性的欲望,我也從來沒有要與她們發生肉體關系的想法”。[11]兩位敘述者聲口一致,表現出對女性身體的渴望,卻又極力否認其中具有同性戀因素。在林白的小說文本中,很難找到兩情相悅的同性戀情,“林白在表現同性之愛時始終缺乏那種蔑視世俗觀念的勇敢無畏的精神。她一直處于無法擺脫的矛盾沖突中:既對同性的身體充滿憧憬和渴望,又不遺余力地壓抑這種難以啟齒、不為世人所容的欲望”。[12]不難發現,林白對同性戀的理解與想象仍較為保守,根本不及對異性之間愛欲書寫那般大膽,這與林白主要關注異性戀女性面對同性戀關系的心理感知過程不無關系。林白小說中的同性戀偏向“無性”交往,即便是《玻璃蟲》這部已經觸及同性戀之間性愛的小說,結局依然設定為敘述者好奇有余而勇氣不足,最后臨陣脫逃。林白也承認,“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不過是一個理想的宣言而已,甚或只是市場需求于女作家的一種姿態罷了。林白小說所書寫的同性戀大多缺乏穩固的情感基礎,在世俗社會中掙扎生存的同時,更因彼此地位不平等或付出的多寡而導致分崩離析,女主人公最終選擇遠離同性戀的國度,開始向“自然的女性”(即“母性”)的身體回歸。
四、回歸母性的身體展演
美國當代女詩人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認為,“母職”是父權體系建構出來的;在父權社會的象征體系中,一直有兩種女性概念齊頭并進:一是女性是“魔鬼之門”,女體是不潔、腐化的,會造成道德敗壞及健康惡化,對男性造成危險;二是女性是“圣潔的母親”,作為母親的女人善良、純粹,無私地付出關愛養育子女,且與性無關。[13]林白關于母性的書寫似乎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其小說逐漸剝落母親神圣的面紗,回歸女性性別本真,顯示出其凡俗而駁雜的內心世界。林白對女性生命歷程中母性的書寫主要包括未婚先孕、人流以及生兒育女等女性獨有的身心體驗,而這恰是當代女性寫作中較少關注的話題。
在林白一系列著重描繪女性成長歷程的小說中,不少女性有未婚先孕的人生經歷,這往往聯系著一段她們自認為刻骨銘心的愛情。《一個人的戰爭》的多米和《玫瑰過道》中的“我”即是例證。在她們看來懷孕是確認愛情存在的唯一證據,“因為我們之間什么都沒有,照片、信件、誓言以及他人的流言,如果我不提到孩子,對我來說,一切就像是虛構的,是我幻想的結果”。[4]196-197她們對孩子的認定僅限于此,但孩子和愛情卻構成了相互矛盾的兩端,男友只要自由而不愿負起做父親的責任,她們的選擇卻是拿掉孩子,“放棄了孩子,卻獲得了愛情,我想這是值得的”。[5]77多米與“我”在盲目的愛情中左沖右突,作為一個女人對愛情的執著遠勝過成為孩子母親的渴望。當女人為了保全愛情而決定放棄成為母親的機會,終結孩子的生命使她們永遠感到懊悔與歉疚,而愛情還是無法避免地走向幻滅,“我失去了孩子同時也失去了他”,[5]77女人成了最大的輸家。她們的愛情并未因此得以延續,自以為神圣的犧牲在世俗面前顯得蒼白無力。
對置身于婚姻內的女性而言,懷孕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賦予的神圣使命,然而對未婚女性來說卻是非常可怕的。她們對懷孕更多時候體現出茫然無助,不僅伴隨著生理方面的不適感受,更有沉重、壓抑的心理重擔,具體表現在女性面對未婚先孕的心靈恐懼。當多米發現自己懷孕時,“這是一個異常嚴重的事情,我驚慌失措神經緊張”。[5]26曾經二度未婚先孕的老黑時刻感到自己就是個異類,她們一旦發現自己未婚先孕,往往陷入絕望無助的深淵,畏懼、恐慌像幽靈般揮之不去,令人窒息。
為了掙脫這層苦痛的糾纏,未婚先孕者萬般無奈下躲進私人診所施行人工流產。此舉雖然解決了這些女人淪為單身母親的窘境,但她們卻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她們“身體深處”被刻畫出一道永遠改變往后人生的“傷痕”。此外,整個人流過程也是一個令人不安、被人羞辱的過程。從手術器械、診所招牌到醫生處的問診,這一切在她們看來,無不透露出凜冽的寒光與歹毒的惡意。人流在此被描寫為極度不堪的人生經歷,醫生缺乏人性的制式指令使她們飽受威脅與羞辱,一切尊嚴喪失殆盡,手術對身體造成的疼痛緊隨其后。毋庸置疑,林白為讀者描繪出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通過小說人物的訴說使讀者在逼真的感受中發抖冷顫,從而對現實女性的處境多一分關注、理解與同情。
當然,在林白的小說中,也有少數女性已婚并兼具孩子母親的身份。在成為母親的前后,這類女性主人公的心理認知也產生了極大轉變。《說吧,房間》塑造了“袋鼠母親”的鮮明形象,老黑“年輕時決心不要孩子的隱秘理由之一就是擔心自己變成一只難看的袋鼠”。[6]45然而,當老黑生下女兒之后,她的心態發生了極大轉變,女兒成長過程中的點滴變化都給她帶來驚喜:
這時候我完全跟袋鼠認同了,我完全不記得袋鼠有多難看了,我從來就不認為袋鼠難看,我現在堅信袋鼠的體型是世界上最合理最自然同時也是最優美的體型,我將以這樣的體型向整個草原炫耀![6]48
自內心深處萌生的母性本能使老黑認同了“袋鼠母親”的形象,她原本認為母親一律是難看的丑婦,但當她自己成為母親后,袋鼠形象卻變成了“最合理最自然同時也是最優美”的姿影,這是對母親形象的一次美化。盡管撫育孩子犧牲她們的事業和既有相貌,但孩子激發出了女性內心深處的母性,成為引導女人蛻變為母親的華麗轉身和美好救贖。
“肉體只有經過了詩學轉換走向了身體的倫理性,它才最終成為真正的文學身體學……肉體必須拉住靈魂的衣角,才能完成文學性的詩學轉換”。[14]林白小說的身體詩學可以說已經做到了精神與肉體的結合,她以詩性的語言、唯美的意象塑造一系列女性軀體,并以女性視角獨自欣賞,賦予其特殊的審美內涵,亦著墨于女性對自我身體及情欲的探索,傳達了女性自我肯定、自我認同的美好愿景。林白透過書寫女性的身體及欲望,最終抵達女性精神層面的深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