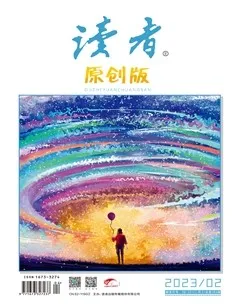一段合唱
文|方和斐
早上睜眼,微信彈出一條新消息,是一位相交多年的老教授發來的一條合唱視頻。
這位教授是我大學所讀院系里的老師。他早已退休,現在年屆耄耋,須發全白,賦閑在家,零星發表幾篇署名論文。
他的人生跌宕起伏。本科畢業后,他曾揮著大錘,建設了10年長江大橋。他也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批甚至第一位到哈佛大學留學的理科生。在那兒,他結交了兩位與自己同齡的外國同行,三人開啟了長達40年的學術合作生涯。
他們的研究項目是用射電望遠鏡觀測星系,這種研究非常昂貴、非常復雜、非常耗時,但也非常有意義。他們發表的一篇論文被《科學》雜志選登并在封面推介,同期刊載了國外專家的評論,認為這“開啟了天文學的新分支”。
他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和他合作的兩位同行之一,做了德國一所著名研究所的主任,后來當上德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另一位同行也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官網介紹他為“XX學之父”—這門學問,幾乎完全是在他們的合作中發展起來的。
這位老教授一邊領導這項合作近20年,一邊做了一輩子普通教授。在學校時,他帶著需要通宵熬夜的實驗課,直到退休也沒有一官半銜。他主持的項目拿了國家自然科學獎,他卻讓團隊里他的學生作為代表去領獎。學校想為他發新聞稿,也被他婉拒,他還專門打電話給負責新聞稿的學生編輯道歉。
我有時難以理解他的想法。即便如愛因斯坦,傳記里記錄的他也不是毫不計較的。但老教授似乎無視榮辱,讓他高興的,只有學生們的成就。這種程度的謙虛和善良,我沒在別處見到過。
在人類歷史上,他主持的項目第一次繪制出了銀河系的確切模樣,確定了銀河系是一個擁有4條旋臂的旋渦星系。他所研究的脈澤,是一種致密而明亮的“宇宙激光”。在地球上觀測這種光芒,就能確定銀河系里每處脈澤源的位置,從而將整個銀河系的模樣繪制出來。形象地說,脈澤就是銀河里閃亮的浪花。
他退休后,系里再沒人從事這一研究領域,新來的學生甚至無從知道系里有過他這位老師。我聽別人轉述,說他多次訪問哈佛,哈佛的天文學者對他十分尊敬。曾有中國學者到哈佛求職,因為他的一句推薦就被錄用了。
我預備出國讀博時,詢問他的意見,他主動提出要幫我寫推薦信。畢業之前,他給我打了兩小時的電話長談。我逐字逐句記下他的叮嚀:
“99.9%的人,都是默默無聞地重復工作的。可能有一些人—0.1%的人,包括天文學家,做出了一點兒成績。但這些工作,可能也只是天文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而已,有一點兒貢獻,但那只是一點點,一滴水。我們這個人生,在歷史上,真是太渺小了。
“所以,要堅持做一件事情,要做好它。只要是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你就認真地去做。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高,不要想著我要做出多么大的成果。不要這樣。大部分的人,連腳印都沒有。多少年來,我們也都是慢慢地去做,做出一件件小事。有可能它就是一塊鋪路石,就是一個腳印。”
這樣的品德,是否和現在的一些說法相容?在多年的學術訓練中,我曾被建議不能流露出一絲怯意,要凸顯自己的研究的歷史意義,即使那工作本身十分渺小。
過去的這個冬天,是個“截止日期”堆積的季節。這樣的日子里,我格外感受到學術界中那種競爭的壓力。研究與學習的快樂消失了,仿佛必須自證自我之優越,擠進最頂尖的一小撮兒,才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他知道我要答辯,突然發來信息。他說自己雖然不懂我的研究,但愿意聽聽我的報告,給我提些意見。我講了講我的打算,他大加贊賞,說之前不知道我的工作原來到了這種程度。
所有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極為提攜后輩,總是鼓勵多于批評。在他發來的視頻里,我看見他裹著好幾層棉衣,白眉毛亂糟糟的,心里有些難過。沒想到他已經這樣衰老。
他說起之前戰勝癌癥病魔的事,也是一派云淡風輕。前幾天他和我說,去年大年三十下午,他到大院兒里曬太陽,“大樓還是那樣的高,天還是那么的藍,桂花樹還是那樣的茂盛”。我想象著他矮小的身軀,和夫人在小區里蹣跚步行,應當真的和世間的其他“糟老頭子”沒有什么區別。
我已經幾年沒回過母校所在的城市了。每次說要去拜訪他,他總是說:“你我是朋友嘛,歡迎你來我家玩—是來玩,不要說拜訪。”
今早,我從一段不安的睡眠中醒來。我點開他發給我的視頻。那是中科院老科學家合唱團的演出,視頻的封面是錢學森。他們唱的是一首寫給衛星測控科學家的歌。那些白發蒼蒼的老人齊唱: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個
在奔騰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
在征服宇宙的大軍里
那默默奉獻的就是我
在輝煌事業的長河里
那永遠奔騰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認識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進
融進祖國的江河
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
祖國不會忘記,不會忘記我
我想到他從前和我說,“要做一朵浪花”。吃著早飯,淚落進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