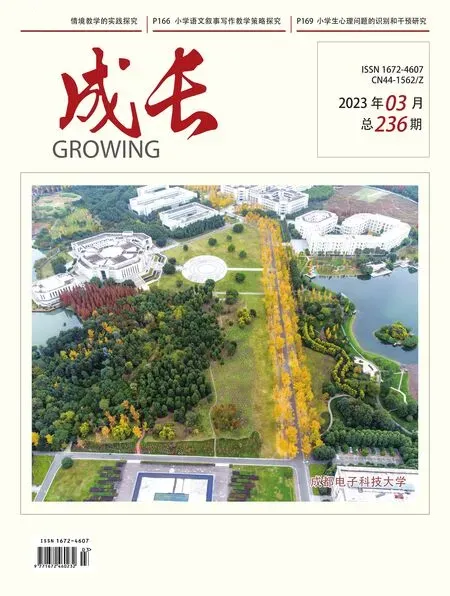數字勞動視域下網絡游戲玩家的勞動邏輯研究
——以手游《王者榮耀》為例
許馨月
中央民族大學 (北京市 100081)
1 引言
互聯網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移動設備的全面普及進一步加深了人們所處的當下社會的數字化程度,在此背景下,網絡游戲的種類與規模迅速擴大,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常見的休閑娛樂方式之一。
網絡游戲所具有的移動化、碎片化和社交性等特征使其愈發凸顯出當下其之于玩家使用過程所展現出的媒介屬性,并不斷汲取著玩家們的時間與精力。至此,網絡玩家群體已不知不覺被納入進了游戲產業的生產鏈條之中,他們主動參與游戲來獲取休閑的行為實質以數字勞動的形式被轉化成了游戲進行數字資本的獲取與積累、達成逐漸擴大自身產業規模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
因此,本文嘗試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以數字勞動為核心理論,將熱門手機游戲《王者榮耀》作為研究案例,試圖理解并分析網絡游戲玩家的游戲參與行為及其背后的勞動邏輯,在此基礎上對當下存在的游戲過度依賴、沉迷等負面現象進行更為明晰的認知與了解,并提出相應的防治、管控建議。
2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2.1 從“受眾商品論”到“數字勞工”
在傳播與媒介研究的學術脈絡中,受眾/ 用戶的媒介使用與內容消費被普遍認為具有勞動的成分(曹書樂,2021)。最早對這一規律進行闡釋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家達拉斯·斯麥茲,他于1977 年發表的文章《盲點》中,第一次提出了“受眾商品論”的概念。受眾商品論對“受眾、媒介、廣告商”三者間的關系進行了討論與解釋,在其概念中,交易過程的主要商品并不是媒介生產的節目、信息,這些內容只是為了吸引受眾的存在,真正與廣告商進行交換的,實則是受眾的時間與注意力。
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西方學者對“受眾商品論”的概念與內涵進行了進一步的延伸與發展。用戶在互聯網使用過程中留下的豐富信息及痕跡,被網絡媒體公司進行了收集與分析,用于進行其資本積累和利潤獲取,這也正適用于受眾商品論對用戶活動的商品化行為詮釋路徑。在此基礎上,“數字勞動”的概念進入大眾視野。英國學者福克斯對對數字勞工和數字勞動研究進行了清晰的界定與建構:數字勞工是電子媒介生存、使用這樣的集體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一個確定的職業,他們服務的產業定義了他們,他們受到資本的剝削(胡婷,2019)。謝芳芳(2017)闡述了數字勞動的概念相比于受眾商品論之于三方面的進化,分別表現在勞動主體由靜態的、可測控的集體到動態的、可監視的身體的轉換,勞動力由“注意” 能力向“情、智”能力的轉換以及勞動力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從單向性向雙重性的轉換,這些轉換正體現出當下數字環境對于數字用戶及其行為的全方位、高程度的吸納與利用。
2.2 “玩工”與“玩勞動”
游戲作為數字時代的重要媒介形式之一,其中玩家的使用與游戲間的關系同樣能夠被數字勞動理論所解釋與分析,普通玩家的在游戲數字資本世界中的地位、交流、傳播和娛樂等都以勞動的形式被納入進了生產性勞動的范疇。
在此背景下,“玩工”的概念首先被朱利安·庫克里奇提出,他認為游戲模組愛好者的參與和創造等游戲行為對游戲本身帶來的貢獻標志著一種新的資本積累模式的形成。此后,國內外學者不斷加強對于“玩工”概念的重視與發展,并討論出作為數字勞動形式之一的“玩勞動”的概念,用于解釋游戲對玩家所帶來的勞動剝削與控制,如蔡潤芳(2018)揭示了電子游戲產業“平臺化”趨勢下,平臺壟斷資本主義對網絡游戲用戶的壓榨;吳鼎銘(2017)在研究中對游戲中“玩工”進行“普通玩家”、“電競玩家”和“金幣農夫”的具體分類,揭示數字勞工群體所面臨的多種形式的勞動剝削與生存困境等。
總之,當下學術界已充分認識到數字資本主義語境下,各產業的媒介用戶正在逐步異化為勞動力的現實,也對游戲產業中存在的“玩工”群體和“玩勞動”現象有了批判性的簡介;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除對于游戲的剝削與控制所進行的批判外,少了些站在中立、理性視角對網絡游戲玩家參與至此種數字化“勞動”過程與邏輯的探究和細致分析。
3 網絡游戲玩家的數字勞動邏輯
通常,游戲玩家參與游戲被看作是休閑娛樂導向的主動行為。但從數字勞動視域下看待此過程,又可發現,玩家主動參與游戲的行為使得自身生產與消費、工作與閑暇之間的邊界日益模糊,參與行為實則被轉化為了一種數字化的勞動:網絡游戲玩家在游戲中消耗的時間被數字資本轉化為了勞動時間,其游玩過程則被轉化為非物質勞動過程,玩家于無形中被吸納進游戲資本的生產與積累過程中,成為了游戲的免費勞動力。因此,我們不能只將眼光局限于批判抨擊,更需要從網絡游戲玩家的角度出發,分析其整個勞動的邏輯,從而對整個游戲生產環節更清晰的認識。
《王者榮耀》(以下簡稱王者)是騰訊公司旗下天美工作室于2015 年底推出的一款移動端MOBA 類游戲。據騰訊官方報道數據,截至2020 年底,王者注冊用戶量已達5 億,平均日活量達5000 萬。自其面世起就迅速風靡全國,吸引大量用戶投入其中,游戲本身也作為一種勞動場域,不斷獲取來自游戲玩家的“勞動”貢獻。
3.1 起點:不設限的游戲時空
移動互聯設備的普及,不斷突破著時間和空間對人們行為的限制,不斷增強著用戶對以移動設備為載體的信息與體驗的黏性。手機游戲招徠玩家進行游戲勞動的起點,就在于能夠使玩家不考慮時間、空間,自由地出入游戲世界。
與同類型的熱門端游競技游戲《英雄聯盟》相比,王者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吸引大量玩家轉移陣地,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它的載體——《英雄聯盟》此類端游,普遍對玩家的游戲設備及其配置具有一定的門檻要求,因此玩家進行游戲行為的空間通常只能夠被限定在家中或網吧的能夠支撐游戲運行的電腦前;而對于王者的玩家來說,他們只要擁有一部智能手機,就能夠在任何空間進行游戲,玩家的游戲使用場景被不斷擴展遷移至臥室、辦公室、室外等各種空間中。
阿多諾曾表示,在資本主義的語境下,閑暇的時間已經成為對自身的反諷,因為閑暇本身已經被納入定價的范圍(徐晶潔,2020)。王者之所以能夠實現對游戲玩家時間全方位侵占,一方面在于移動設備對時間限制的全面突破,另一方面在于其對游戲世界及單局游戲時長的基本設定:首先,王者作為虛擬的游戲世界并不存在晝夜之分,除游戲停機更新外,玩家可以在全年、全天的任意時間進行游戲;其次,王者中各游戲模式的單局時長通常為10-20 分鐘,該種具有彈性的、快節奏式的游戲體驗符合當下用戶的碎片化、快餐式的使用習慣,一定程度上給予玩家自由參與的權力;另外,即便王者對未成年群體設定了防沉迷系統以及針對在線時長過長的玩家進行強制休息的機制外,但對于狂熱的王者愛好者來說這些規則如形同虛設,他們可以通過“借號”等方式將自己的所有時間投入至游戲當中。
由此可見,以王者為代表的手機網絡游戲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給予了玩家高度的參與自由,而正是由于這種“自由”感的存在,成為了玩家進入游戲的起點,并于無形中不斷誘使玩家消融著自己休閑和工作的時間空間邊界,從而滿足了游戲對玩家勞動時間獲取的基本需求,為數字資本的積累奠定了時空基礎。
3.2 動力:游戲與玩家的“同意”創造
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邁克爾·布若威沿襲了馬克思的勞動理論,認為在當代資本主義語境下,勞工對資本的依賴開始削弱,“強制”逐漸失去了操作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吳鼎銘.2017)。在當下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的社會背景下,人們擁有了更多的行為以及信息選擇的自主權,因而資本想要通過強制途徑實現對人們勞動壓榨與控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數字勞工群體的勞動行為必然需要建立在一個看似與資本獲利主體間更為平等的、雙向性的“同意”或“共識”的達成基礎之上。
網絡游戲更是如此,想要吸引玩家自主、自覺地投入其中,必定需要揣摩和順應玩家的需求與心意,與玩家間達成某些“同意”,而不能指望單純采用強制納入的形式。網絡游戲中普遍存在的積分制和排名制就是最典型的“同意”制造方式,以王者為例,王者排位賽中存在著不同的段位(如,青銅、鉆石、王者、榮耀王者等)劃分,玩家通過獲得勝利積累“星星”,從而達成段位的提升,段位越高、達成的成就越多,則擁有的身份標識與頭銜越華麗、在游戲世界中越能得到更多玩家的“賞識”與“羨慕”——因此在此過程中玩家除了享受游戲本身的樂趣外,會更輕易地被激發勝負欲,促使其投入更多時間來提升“技巧”,獲得勝利,提高段位。
這種現象在布若威看來,應當被稱作為“趕工競賽”,布若威認為資本家通過精心設計“趕工超額”機制,使得勞工在乏味的工作中享受到“趕工競賽”的樂趣:王者正是利用了玩家此種心理,將玩家吸納進了競賽型游戲的漩渦中,使其情緒不自覺地跟隨游戲的勝負而波動,在享受你追我趕的過程中不斷主動向游戲貢獻著自己的時間精力,為游戲創造著數字資本。
3.3 加碼:游戲玩家的資本積累
當前數字勞動價值的雙向性在游戲中的體現,在于游戲能夠將通過玩家的參與和貢獻作為勞動轉化為數字資本,而玩家也能夠通過游戲獲得不僅限于休閑娛樂的“報酬”。這種“報酬”,既包括游戲內的線上資本,也能夠延伸至玩家現實生活中的線下資本中,這些資本都是不斷促使玩家沉浸于游戲的重要砝碼。
王者玩家通過長期的游戲,能夠在游戲對戰中不斷積累“鉆石”、“金幣”、“碎片”等,用以換取英雄、皮膚及其他道具,也能夠在各類活動中通過達成任務目標獲得裝扮、特效等。這些“游戲財富”通常為玩家個人所擁有,被視作為其在王者中通過個人勞動所得到的“固定資產”,并且隨著游戲總時長的不斷增加,資產的總量也在不斷增長,這既成為了玩家成就的一種象征,同時也成為留住玩家的一種羈絆。
王者具有的另一個突出特性是它的社交媒介屬性,這是給予游戲玩家以線下社會資本的重要前提條件。首先,王者作為騰訊旗下游戲,以QQ、微信平臺作為賬號認證平臺,玩家可以現實生活中的已有人際網絡進行線上拓展,與好友一同游戲,享受游戲樂趣,增強相互聯系;同時,玩家還可在游戲中與陌生人建立好友關系甚至是“親密關系”,其中也不乏大量玩家將線上好友轉化為實際生活中的朋友,拓寬了自己的社交網絡。其次,游戲戰隊、小隊的存在,使得以游戲為紐帶的社群得以建立,進一步方便著玩家對于游戲的資本積累,強化著玩家對游戲的情感依賴。此外,前文中提到的玩家所積累的游戲財富,還可通過線下交易轉化為線下資本,即現金收益。
由此可見,王者除了耗費游戲設計者以及運營者的人力成本外,在給予玩家豐厚獎勵與線上線下雙重資本的過程中的消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玩家卻能在王者所給予的游戲場域中獲得資本獲取的滿足,并能為此更加投入游戲勞動,不斷加強著對游戲的認同與依戀,在獲取滿足的同時也在無形中進一步淪為王者的游戲勞工。
3.4 異化:職業“玩工”群體的涌現
隨著游戲產業鏈的不斷延伸壯大,主動或被動參與至游戲生產鏈條的人數始終呈現上升趨勢。馬克思的異化勞動在這些游戲玩家被完美詮釋,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普通玩家群體外,近年來,職業“玩工”群體的不斷涌現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
職業“玩工”與普通游戲玩家的主要區別體現在他們的游戲目的,此類群體以獲取報酬、甚至是將游戲作為職業作為參與游戲的出發點,通常以“代練”、“陪玩”、“游戲主播”為主要人群代表。職業“玩工”相較于普通玩家,徹底消解了自己的生活空間與職業空間以及自己的娛樂時間和工作時間,和雇主間建立了直接的雇傭關系,又與游戲平臺建立了隱性的依附關系,他們將游戲作為工作場域,使得玩游戲的行為本身轉化成了無異于身處辦公室進行辦公的勞動行為。
筆者作為王者的資深玩家,曾主動“雇傭”過游戲代練,在此過程中筆者了解到,通常代練的價格會根據“星星”數或游戲時間來計算,如贏一局賺一顆“星星”的價為從5-30 元不等;按時間則通常以每半個小時為單位,同樣具有并不算廉價的價格區間。而游戲代練對于以筆者為例的“雇主”來說是隨叫隨到的存在,他們對自己的游戲工作孜孜不倦甚至可以至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們始終對以游戲作為獲取報酬的途徑深信不疑,通過不斷地游戲提升技術,獲得更多的酬勞。
相較于普通玩家之于游戲的數字勞動,職業“玩工”群體游戲行為的勞動屬性更為顯性。可見游戲對玩家的影響與控制范圍已不僅限于個人生活與休閑習慣,其作為資本與媒介平臺給玩工群體提供了勞動機會與勞動場域,對職業“玩工”群體進行了更深程度的異化,在此基礎上,游戲只需置身事外,就能一邊享受著“機遇給予者”的美名,一邊坐享數字勞動之利。
4 總結
本文以王者榮耀為例,在數字勞動的理論視角下探析了網絡游戲玩家的勞動過程與邏輯。研究發現,移動設備對游戲時空限制的突破使得玩家可以自由地進出游戲世界,擴展著自己的游戲時間與場景,將游戲作為充斥閑暇時光的重要選擇;在被吸納進游戲世界的基礎上,玩家與游戲間達成“同意”,玩家以游戲為場域進行“趕工競賽”,并以此為動力不斷投入進更多的時間與精力;玩家通過自己在游戲中的勞動行為不斷賺取并積累著包含線上和線下在內的雙重資本,在獲得滿足的同時也進一步增強了對于游戲的歸屬感、認同感與心理依戀;此外,職業“玩工”的涌現進一步加深著游戲對玩家勞動的異化程度,消解著玩樂、生活與工作的邊界,促使玩工投入更多的勞動體力與精力。
本文雖期望站在較為中立的視角客觀分析網絡游戲玩家的勞動邏輯,但在研究與分析過程中,我們仍能夠清晰感受到網絡游戲在資本獲取、積累以及對玩家群體勞動力與勞動成果的剝削目的的指引下,通過各種形式對玩家所進行的誘導與欺壓。
近年來,對于網絡游戲所帶來的身心危害、游戲成癮等負面聲討與報道屢見不鮮,這使我們更加意識到正確看待游戲、避免陷入數字勞動漩渦的重要性。一方面,要逐漸完善對于網絡游戲的監管體制,除保證良好端正的游戲內容外,還要繼續補充如“限時令”等強制把控措施;另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加強對于游戲玩家的正向引導,使其正確認知游戲利弊,避免培養游戲成癮等消極習性,同時,規范與引導職業“玩工”群體,對青少年進入該群體進行管制,對成年玩工進行職業規劃與未來計劃的合理規勸;此外,游戲玩家也應不斷提升個人媒介素養,正確看待游戲利弊,合理規劃個人工作與生活娛樂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