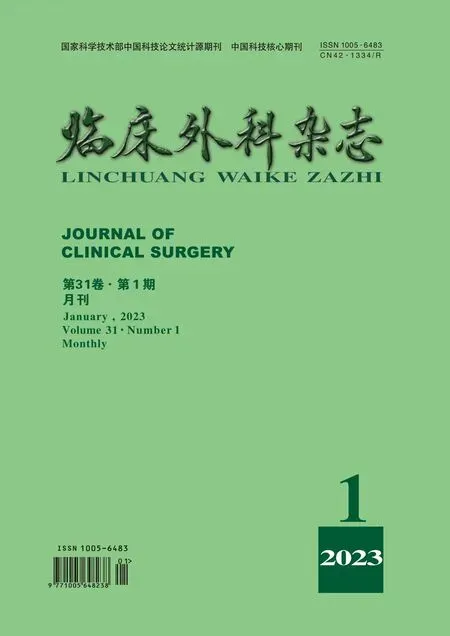乳腺癌外科治療十大熱點
沈浩元 胡超華
乳腺癌的外科治療經歷了腫瘤按解剖部位有序播散的Halsted時代、放療參與下的局部手術范圍不斷縮小的后Halsted時代、Fisher通過基礎研究提出腫瘤的播散是無序的全身性疾病理念下的保乳前期時代、NSABP B-06研究Milan研究等一系列臨床研究證實了保乳的長期安全性的保乳時代,從擴大根治術、改良根治術、保乳術、前哨淋巴結活檢術到現在的標準全身治療保駕護航下的個體化、精準化局部治療,乳腺外科正在朝著治愈率越來越高、局部手術范圍越來越小、乳房重建技術的新時代邁進。
一、導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DCIS)的局部治療
DCIS約占新診斷乳腺癌的20%,被認為是一種浸潤前病變,其本身并不威脅生命。文獻報道,空芯針穿刺診斷為DCIS的病人,術后病檢升級為浸潤性癌的比例高達18%,其中高級別、ER(-)、PR(-)DCIS病人更容易診斷升級為浸潤性癌,提示DCIS如果僅根據空芯針穿刺結果來決定局部手術范圍,則意味著至少18%的病人被低估[1]。一篇DCIS的長期隨訪數據顯示,35 024例DCIS病人中,最終有2 076例(5.9%)進展為浸潤性乳腺癌,而死于乳腺癌者有310例(0.89%)。保乳+放療、保乳不加放療、全乳切除三種局部治療策略15年累計復發率分別為7.1%、9.4%、2.8%[2]。DCIS行保乳手術后放療的價值一直存在爭議, Lawrence J等報道了低臨床和低病理風險DCIS保乳術后不加放療隨訪12年結果提示同側乳房復發24.6%、浸潤性同側乳房復發13.4%,提示DCIS保乳術后不加放療復發風險明顯高于放療者[3]。2022年NCCN指南將保乳+放療作為DCIS局部治療的1類推薦。
二、DCIS的保乳切緣
DCIS的保乳切緣是否應有更高標準,比如2 mm、5 mm、10 mm,文獻報道仍有爭議。一篇Meta分析4 660例保乳手術+術后放療DCIS,隨訪觀察同側乳房局部復發率,結果發現,2 mm的切緣復發率明顯低于<2 mm的切緣。當切緣擴大到5 mm時,復發率并沒有明顯獲益[4]。另一篇Meta分析顯示,與切緣寬度>2 mm的DCIS病人相比,切緣寬度>10 mm能顯著降低病人的復發率[5]。ASCO專家組對切緣寬度和復發率進行Meta分析顯示,2 mm的切緣寬度局部復發風險最低,更大的切緣并不會顯著降低復發風險[6]。一項前瞻性管理的癌癥中心數據比較切緣<2 mm和≥2 mm的局部復發率以及放療的影響,結果發現,在總體人群及放療組,二者無差異,但在沒有放療組,切緣<2 mm時局部復發率升高。該研究提示,對于DCIS保乳術后發現切緣<2 mm時,常規附加手術可能不適用于接受放療的病人,但對于放棄放療的病人則應進行常規附加手術[7]。
目前NCCN指南及2021年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治指南與規范均推薦DCIS的保乳安全切緣為2 mm,但對于部分基地或表面切緣不足2 mm又無法進一步補充切緣時,<2 mm的切緣也是可以接受的[8]。
三、前哨淋巴結(sentinel lymph nodes,SLN)微轉移時的腋窩處理
SLN微轉移時腋窩非前哨淋巴結轉移概率約13%~20%,進一步的腋窩淋巴結清掃(ALND)可能會使部分病人分期提高,進而改變輔助治療決策,但ALND是否能給病人帶來生存獲益尚不確定。IBCSG 23-01研究主要探討SLN微轉移 (≤2 mm)時的腋窩處理方法,共入組934例病人分為臨床隨訪組和ALND組,研究結果提示兩組10年DFS分別為 76.8% 和74.9%,提示當SLN微轉移時,豁免ALND是安全的[9]。因此,2022年NCCN指南建議僅發現SLN微轉移時,不再需要腋窩手術。但2021年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療指南與規范建議SLN微轉移病人接受保乳手術(聯合全乳放療)時,可不施行ALND,如僅行全乳切除未放療時,大多數中國專家建議腋窩處理同宏轉移[8]。
四、SLN 1~2枚宏轉移:ALND 或腋窩放療
SLN宏轉移病人腋窩非前哨淋巴結(no sentinel lymph nodes,nSLN)轉移概率明顯升高,因此ALND是SLN宏轉移病人的最常用腋窩處理方式。AMAROS研究入組1425例浸潤性導管癌(IDC)、T1/T2、cN0、保乳術/乳房切除術、前哨1~2枚宏轉移病人,分為ALND組和腋窩放療組,結果提示兩組腋窩復發率分別為0.54%和1.03%, 5年的DFS和OS分別為86.9%、93.3% vs 82.7%,92.5%,均無統計學差異[10]。ACOSOG Z0011研究入組891例IDC、T1/T2、cN0、保乳術、前哨1~2枚宏轉移病人,分為僅行前哨組和ALND組,結果提示,兩組10年OS和DFS分別為86.3%,80.2%,vs 83.6%,78.2%,無統計學差異[11]。OTOASOR研究共入組526例IDC、cN0、cT≤3 cm、保乳術/乳房切除術、前哨N1、Ⅰ-Ⅱ期病人,隨機分為ALND組和腋窩放療組,結果提示兩組腋窩復發率為2.0%、1.7%,8年的DFS和OS分別為72.1%、77.9%和77.4%,84.8%,均無統計學差異[12]。因此2021年中國抗癌協會乳腺癌診療指南與規范建議對于未接受過新輔助治療的臨床T1/T2、cN0、前哨1~2枚宏轉移且會接受后續進一步輔助全乳放療及全身系統性治療的保乳病人,可免除ALND。對于接受乳房切除術的1~2枚SLN宏轉移病人,如果ALND獲得的預后資料不改變治療決策且病人同意不行ALND,腋窩放療可以作為ALND的合理替代[8]。
五、新輔助治療(NAT)后的前哨淋巴結活檢(SLNB)
NAT后的SLNB主要關注的問題是前哨淋巴結的檢出率和假陰性率(FNR)。SENTINA研究主要研究SLNB的FNR,分為四組:A組NAT前cN0,NAT前SLNB為pN0,NAT后腋窩不處理;B組NAT前cN0,NAT前SLNB為pN1,NAT后SLNB+ALND;C組NAT前cN1或cN2,NAT后轉為cN0,行SLNB+ALND;D組NAT前cN1或cN2,NAT仍為cN+,行ALND。結果顯示:A組SLNB檢出率99.1%;B組兩次前哨,新輔前SLNB檢出率99.1%,新輔助后SLNB檢出率60.8%,FNR 51.6%;C組SLNB檢出率80.1%,FNR 14.2%[13]。有研究顯示,新輔前和新輔后兩組SLN檢出率分別為98%和95%,SLN陰性率分別為54% 和67%,ALND或腋窩放療的比例分別為45% 和33%,提示NAT后行SLNB病人SLN檢出率稍低,但其保腋的概率更大[14]。
乳腺癌NAT可使40%的病人達到病理學完全緩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將腋窩淋巴結陽性轉為陰性,對于NAT前cN+,NAT后轉為cN0的病人,能否進行SLNB,一項META分析顯示NAT前cN1新輔后轉為cN0病人,其總體SLN檢出率為90%,FNR為14%,亞組分析顯示,單染法FNR為19%,雙染法為11%,當SLN=1、2、3時,FNR分別為20%、12%、4%[15]。PEONY研究也發現,在NAT后腋窩淋巴結由陽性轉為陰性的HER2陽性病人中,使用了雙示蹤劑SLN檢出率100%,總體FNR為17.2%。當檢出SLN分別為1、2、≥3時,FNR分別為33.3%、14.3%和0[16]。2021年召開的St.Gallen會議對于NAT前cN+但NAT后轉為cN0的病人,多數專家支持在檢出≥3個陰性SLN時可豁免ALND。
新輔后SLN 1~2枚陽性時,能否以放療替代腋窩清掃? 2021年召開的St.Gallen會議進行了專家投票,若SLN微轉移(<2 mm)或僅有孤立腫瘤細胞,分別有60%和89%的專家同意免除ALND。若SLN宏轉移,73%的國際專家建議直接行ALNB[17]。
六、NAT后的保乳
NAT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降期保乳,但乳腺外科醫生往往擔心復發風險高、切緣陽性等問題而心生畏懼。一項美國安德森癌癥中心的340例NAT后保乳數據顯示,僅4%的病人切緣陽性,5年的無同側乳房復發生存率和無局部復發生存率分別為95%和91%。該研究還發現,與復發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cN2-3、新輔后殘余腫瘤直徑>2 cm、殘余腫瘤為多灶、切片上的脈管侵犯[18]。一項來自早期乳腺癌臨床試驗協作組(EBCTCG)的Meta分析對比了新輔助化療和輔助化療病人的保乳率和局部復發率(LR),結果發現,新輔助化療的病人有更高的保乳率,和更高的LR,但二者的15年遠處復發率、乳腺癌死亡率、任意疾病死亡率均無統計學差異[19]。因此,在合適的人群中,新輔助治療后的保乳是安全可行的。
NAT后保乳的切緣寬度是否會影響局部復發率和生存率,一項NAT后保乳研究顯示,總體人群局部復發率9.9%,遠處轉移率16.8%,當切緣分別為<1 mm、1~2 mm、>2 mm時無局部復發生存率和無事件生存率無統計學差異[20]。在臨床實踐中,NAT降期后實施保乳手術需要詳細的NAT前后原發病灶的定位和療效評估,以及規范化的病理學切緣評估。更多專家認同切緣陰性的定義為“no ink on tumor”,也有部分專家認為2 mm及以上是相對安全的切緣[21]。
七、NAT后手術時機的選擇
大量臨床數據顯示,乳腺癌NAT與術后輔助治療相比病人的無病生存(DFS)率與總生存率(OS)差異無統計學意義[22]。乳腺癌NAT完成至手術間隔時間(TTS)與病人長期生存的關系目前文獻報道不一,C.Omarini等[23]研究顯示, TTS>21天組較TTS≦21天組OS和RFS明顯更差。但Katherine 等[24]將NAT Ⅰ-Ⅲ期乳腺癌分為TTS≤4周、4~6周、≥6周3組,結果3組5年OS和DFS無統計學差異,而當TTS大于8周時,其總生存率明顯更差。
NAT過程中,對于療效良好的病人,建議完成既定的NAT方案[8]。對于療效欠佳的病人,更換治療方案是否有效成為選擇手術還是繼續化療的關鍵。GeparTrio試驗評估了根據NAT反應更換全身治療方案的療效,病人接受2個周期TAC方案治療后經超聲評估療效,對臨床治療有效的病人繼續完成4或6個周期TAC方案化療后手術。無效的病人隨機接受4個周期TAC或4個周期NX(長春瑞賓聯合卡培他濱)方案的化療,然后接受手術治療。結果發現,對2個周期TAC方案治療有效的病人,延長2個周期TAC的強化治療后未提高pCR率和保乳率。對于治療反應欠佳的病人,更改方案為NX也未改善pCR率和保乳率,DFS有的延長,但未改善OS。該研究提示,對于NAT療效理想的病人延長療程不可取,但療效不佳的病人及時更換全身治療方案是有必要的[25]。
有研究提示,NAT可能通過促進乳腺原發腫瘤釋放細胞外囊泡,如外泌體,促進腫瘤的轉移。也可通過改變腫瘤微環境促進疾病的進展[26-27]。因此,在NAT過程中,不能為了達到pCR而延長治療周期,延誤病人手術的時機,適時停止NAT,及時行手術治療至關重要。
八、年輕乳腺癌的處理
目前多數研究表明,年輕是保乳手術后局部復發的高危因素。一項研究顯示,保乳術后5年LR為2.1%,其中年齡23~46歲、47~54歲、55~63歲、64~88歲5年LR分別為5%、2.2%、0.9%、0.6%[28]。另一項研究報道了1 000例年齡<35歲乳腺癌,含保乳手術或全乳切除術,結果提示,總體人群術后5年LR為3.5%,HR(-)/HER(2+) LR為5.6%,三陰性為3.4%,HR(+)無論HER2狀態為1%[29]。POSH研究比較了年輕乳腺癌保乳對比全乳切除的復發風險,結果提示,雖然保乳組LR高于全乳切除組,但保乳組的無遠處轉移病間隔和總生存率卻優于全乳切除組[30]。
年輕乳腺癌,特別是有BRCA基因突變的年輕乳腺癌,行預防性對側乳房切除術(CPM)比例較高。一項來自國家癌癥數據庫的14 627例年齡≤45歲乳腺癌病人,其中29.7%的病人行CPM,但結果提示,CPM對年輕的早期乳腺癌病人沒有生存益處,對ER(-)的病人也沒有益處[31]。
九、Ⅳ期乳腺癌的手術治療
手術治療是否能改善Ⅳ期乳腺癌的生存率目前文獻報道不一。印度TATA NCT00192778研究共入組350例初診Ⅳ期乳腺癌,首先進行全身治療,全身治療有效者再分為接受局部手術治療和不接受局部手術治療兩組,結果提示,沒有證據表明對一線化療有反應的Ⅳ期乳腺癌進行手術治療會影響病人的總體生存率[32]。土耳其MF07-01研究,共入組278例初診Ⅳ期乳腺癌,一組先接受局部手術治療再行全身治療,另一組只進行全身治療,顯示原發灶手術治療顯著改善生存率,亞組分析顯示,ER/PR(+),HER2(-),年齡<55歲,僅單發骨轉移亞組手術獲益更明顯[33]。Whitney等[34]將原發腫瘤完整且在診斷后12個月仍存活的初診IV期乳腺癌病人按治療順序分為三組:先全身再手術治療、先手術再全身治療、單獨全身治療。結果提示,三組5年OS分別為44.5%、41.1%、27.5%,10年的OS分別為20.2%、14.4%、8.5%,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2022年發表的EA2108研究,共入組256例初診IV期乳腺癌病人,先進行4~8個月的全身治療,病情穩定者分為兩組,一組行原發灶手術,另一組繼續全身治療,結果提示兩組3年OS分別為68.4%、67.9%,無統計學差異,3年的局部區域進展率分別為16.3%、39.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對原發灶進行手術治療并不能提高轉移性乳腺癌病人的生存率,雖然它與改善局部區域控制有關[35]。
十、植入物乳房重建術后放療的時機
放療可造成胸壁組織損傷和假體損傷,放療引起的假體損傷中,近期并發癥包括感染、血腫、假體移位、假體外露等,遠期并發癥包括假體包膜攣縮、假體泄漏或破裂、感染等。對于植入物乳房重建術后放療時機的選擇目前尚存爭論。一項Meta分析提示,擴張器放療和假體放療兩組重建失敗率分別為20%、13.4%,Ⅲ/Ⅳ度包膜攣縮率分別為24.5%、49.4%[36]。一項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提示擴張器放療對比假體放療,兩組任意并發癥發生率分別為30.8%、23.9%,包膜攣縮發生率分別為2.9%、2.2%,重建失敗率分別為11.5%、8.7%,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37]。有研究提示,放療應用于以假體為基礎的乳房重建與重建失敗和包膜攣縮的高風險相關。
乳腺外科的發展目標是在保證手術療效的前提下,盡可能保留病人功能和外形,在提高生存率的前提下,提高病人的生活質量,目前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指導臨床,讓乳腺癌的外科治療更加精準化、規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