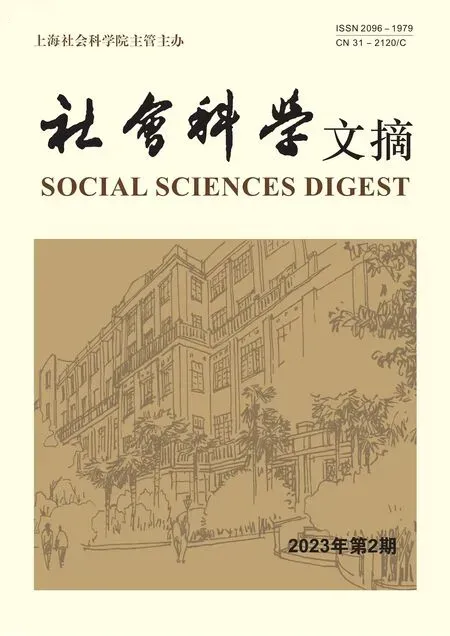人類學轉向:新文科的跨學科引領
——以李澤厚、楊伯達、蕭兵、王振復為例
文/葉舒憲
新文科先驅:人類學轉向
新文科建設近年來成為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推行的自上而下之方針,相當于高等教育的文科改革的國家策略,其現實意義在于突破西學東漸以來所有的文科設置唯西學馬首是瞻的全盤照搬局面。這一方面需要打破各個學科之間的隔閡,鼓勵文理交叉和文科各學科間的交叉,以激勵學術創新;另一方面需要更加面向中國本土現實,更關注傳統文化的世界意義,更進一步發掘中國經驗。
教育部2021年3月發布《新文科研究與改革實踐項目指南》(簡稱《指南》),寫入這樣的原則:探索推進跨專業、跨學科門類交叉融合的有效路徑。《指南》針對現有的文史哲藝專業劃分的改革方針,有如下表述:推進文史哲之間、文史哲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打破原有以固化學科專業培養人的“傳統模式”。可見,以文學、歷史、哲學、藝術、政治學、宗教學等各個學科本位式的模式,已成為舊文科束縛學術創新發展的現實瓶頸。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所有曾經倡導過跨學科研究和無學科界限(non-discipline)的呼吁和努力,都屬于自下而上的突破現有瓶頸的嘗試。這方面雖然成績斐然,但是畢竟都不足以撼動由教育制度本身所支持的分科教育的模式,也就無法讓廣大學子走出學科本位主義的瓶頸。唯其如此,才需要來一場自上而下的文科發展大變革。分久必合,這就是當下學術發展亟待突破的大方向。
這場文科學術的大突破,需要怎樣的學術理念來引領?回顧20世紀以來的當代學術史,不難看出,實際上已經有某種學術理念在引領著各個原有學科思維的突圍與創新,那就是文化人類學的核心觀念——“文化”。這個概念已經提供給學者們走出語言、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本專業領地后,某種統領意義的整合性視角。本文用“人類學轉向”或“文化轉向”,來標志新時期以來我國新文科發展大趨勢,四位人文學科不同專業的專家及其著作——李澤厚《說巫史傳說》、楊伯達《巫玉之光》、蕭兵《玄鳥之聲:藝術發生學史論》和王振復《中國巫文化人類學》,即是“人類學轉向”現象在文史哲藝和文博考古學科中的代表。
文化自覺與華夏文明根性探尋
巫史問題、巫玉問題和廣義的巫文化問題,是新時期以來文科研究的新亮點。哲學學科的李澤厚、文物考古學科的楊伯達、中文學科的蕭兵和王振復,在共同的問題意識驅動下,拓展各自的研究方向。他們的人類學轉向路徑可被概括為:李澤厚的“巫文化視角與中國思想史視角的融合”,楊伯達的“巫文化視角與中國特色的玉文化研究的融合”,蕭兵的“巫文化視角與文藝起源研究的融合”,王振復的“巫文化視角與中國文化關聯性的理論研究”。
(一)李澤厚:巫史
李澤厚早年研康德哲學,后成為當代影響力廣泛的思想史和美學研究名家,晚年時關注點轉移到康德最看不起的非理性的巫術方面。他希望通過對巫史傳統的認識,找到中國文化有別于西方文化的特性所在,相繼寫出《說巫史傳統》(1999)、《論語今讀》(1998)和《由巫到禮釋禮歸仁》(2015)。他意識到,中國思想傳統沒有產生過類似西方人上帝的觀念,也不存在類似西方形而上學的思辨哲學等。儒家的仁學,其側重點在現世社會的人情。“情本體”本來就“在倫常日用之中”,沒有過多的玄秘。他關注作為原始宗教的巫術,如何先轉化為周禮,隨后又在禮崩樂壞語境中再度轉化為儒學,希望借此梳理出儒學思想內蘊的宗教性品格。
《說巫史傳統》指出,所有原始民族都以巫的宗教實踐為特色,但對西方文明而言,其巫術后來明顯分化升級,一方面變成科學,另一方面變成宗教。從希臘到近代,哲學思辨總是和自然科學結合在一起的;由巫史傳統催生出的中國思想,不同于西方純粹的形而上思辨傳統,而是信仰、情感和理性糅合在一起的華夏傳統。
李澤厚的這些觀點,比亦步亦趨跟隨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而大講中國古代思想如何實現“軸心突破”的余英時等高明。在挪用西方哲學理論模式方面,首先要清醒地洞察本土國情的實際。只有這樣,才可以避免混淆中西文明的不同語境。但是,因為缺乏一個本土神話學視角的語境化理解和詮釋,華夏的信仰世界的存在,也就被“由巫到禮”的進化論理論模式,事先解構掉了。文學人類學派對此已經做出本土立場之質疑:若不能從每個文明特有的神話信仰觀念入手,就無法有效理解該文明的核心觀念,包括宇宙觀、價值觀和生命觀。
神話觀念決定論,指每一個文明的文化原編碼始于其特有的神話信仰和觀念。李澤厚在反駁中國古代思想“突破”或“超越”時,認為古代思想與原始部落思想一樣,具有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特點,這樣的判斷在理論上能夠說得通,但是對于認識中華文化的特殊性方面則很不利,似乎與認識中國文化根性的初衷背道而馳,也容易落入殖民時代以來某些西方人類學家(如《原始思維》的作者列維—布留爾)將中國傳統等同于原始思維傳統的做法。這方面的認識關鍵,不在于如何強調非西方文明社會的普遍性和共同性;而在于像人類學家逐個解讀部落社會那樣,找出每一種文化自己特有的神話信仰和文化編碼邏輯。
(二)楊伯達:巫玉
如果說李澤厚是從“道”的立場看待華夏巫史傳統,那么楊伯達的《巫玉之光》則要將巫史這個文化尋根視角完全應用到對上古之“器”的研究。他提出,文物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器物挖掘、器物形制源流和玉石材質鑒別方面,需要引入人文關懷和信仰驅動的文化解釋學研究視角。楊伯達和李澤厚一樣,主要通過借鑒美國華裔人類學家張光直的著作,開啟自己的人類學轉向之旅。
《巫玉之光》卷首的導言副標題是“以‘巫書’釋巫玉”,所謂巫書是指《山海經》。他認為“玉神物也”這句話最重要,指出了玉的獨特功能。他對玉神物這一要領作出三點解釋:(1)玉是神靈寄托之物體或外殼;(2)玉是神之享物;(3)玉是通神之神物,玉本身即是神(“物神”)。楊伯達提出,華夏國家玉禮器的直接源頭,就是史前宗教所崇拜的對象——玉神器。他認識到的玉文化另一個重要的宗教性內涵,便是“巫以玉事神”。李澤厚對巫史的關注焦點在于從巫到史的演進,以及巫術禮儀的理性化改造方面,而楊伯達則要將人們的目光引向先于文明國家的史前時代。書中提出玉文化發展三段論,也是參照人類學的進化論模型而來,他命名為“巫玉—王玉—民玉”。而巫玉作為玉文化的開端階段,其文化基因的意義非同一般。
楊伯達晚年有兩部巨著問世,即《中國史前玉文化》和《中國史前玉器史》。這兩部書都將研究的范圍聚焦到“中國史前”,因為這正是充分體現玉文化發展三階段中的初始階段,即巫玉階段。唯有在這個時期里,前文明國家的巫教社會特質,才表現得最為充分。
以河南靈寶西坡21世紀新發現仰韶文化大墓隨葬玄玉玉鉞為標志,一個比夏王朝還要早一千多年的中原玉文化曙光期,從距今五千五百年一直延續到距今四千年。這就是文學人類學團隊完成的上海市社會科學特別委托項目“玉成中國”系列著作的第一部《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的成果。可以說,楊伯達先生開辟的史前中國玉文化史體系研究,不僅在文學人類學派這里得到繼承和發揚,而且從巫玉理論再出發,更進一步提升為重新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整體理論系統。
從一萬年的超長時段看,中國統一的歷程先后經歷過三個大的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為玉文化的統一,這也是玉石神話信仰及以玉祭神禮儀行為的文化認同過程,完成于距今四千年之際;第二階段的統一是以甲骨文為首的漢字書寫符號的統一,完成于距今三千年的商周時期;第三階段的統一才是秦帝國的軍事和行政版圖的統一。由此可見,人類學轉向帶來的中國歷史認識的大變革,既包含歷史深度方面的變革,也包含百年中國考古的系列新成果。
源于李澤厚《美的歷程》和《說巫史傳統》的華夏文明傳統大反思,到楊伯達《巫玉之光》和《中國史前玉器史》,再到文學人類學派的《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和《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這場學術的接力賽已經持續數十年,目前仍然在緊張地進行之中。
(三)蕭兵:巫儺
蕭兵早期著作《楚辭與神話》(1987),就包括《巫咸為太陽神巫考》《黃帝為璜玉之神考》《西王母以猿猴為圖騰考》等內容。在20世紀90年代李學勤主編的“長江文明叢書”中,蕭兵貢獻了一部專研巫儺文化專著,題為《儺蠟之風》(1996)。90年代初,李澤厚先生大膽收錄蕭兵的著作《楚辭文化》,并納入他主編的“美學叢書”。
2019年,蕭兵推出煌煌三卷《玄鳥之聲:藝術發生學史論》,是研究藝術起源的理論性著作,提出“藝術發生于學習及其成果的展演”命題,為已經眾說紛紜的藝術起源大討論,再添一種假說。人類學轉向在他這里,似乎是與生俱來的優勢。他本人的學術興趣不是在學院派的課程里培育出來的。在1949年以來的中國高校中,文史哲藝術專業內部一般不會有師資去開設文化人類學的課程或傳授相關知識,而國學的文史研究傳統自身中也并不包含巫文化的內容。若不是學者自發的持久努力,文學人類學或歷史人類學等新興交叉學科都不可能在舊有的學科格局中涌現出來。
(四)王振復:巫文化
與蕭兵同屬于中文專業的王振復,在2020年出版的《中國巫文化人類學》中,聲稱是“以人類學關于巫學的理念治學”。這一傾向開始于其早期著作《巫術: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他要從原始“信文化”入手展開,總括人類史前文化共性為“三維動態結構”說,即神話、圖騰、巫術的三足鼎立格局,并以此作為宗教文化之母。從學術史視角看,王振復的“三維動態結構”說,可以視為本土學者對國際上人類學研究史與宗教史學方面已有的代表性觀點的再整合。
在將此三維結構論框架運用到中國文化研究時,作者強調巫性,將其視為中國文化的原始人文根性作用所在。巫性的社會行為形態,表現為拜神與降神、媚神與瀆神的背反與合一。他辨析中國文化的神的觀念,認為其中蘊含著鬼與氣的意識成分,因而與西方宗教的上帝觀截然不同。他尚未涉及的,是從巫術信仰到拜物教信仰的本土宗教衍生與進階過程。在此種學術空缺的意識作用下,筆者嘗試撰寫《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將一般化的巫文化理論與巫玉理論,提升到中國史前國教信仰的高度,從中梳理演進變化的脈絡和規則。
王振復新著發前人所未發之處,是巫性文化與中國風水學說的內在關聯研究。他認為中國巫文化的基本思維方式為類比思維。類比發生在自然環境與人居環境之間,自然而然會產生出神話的風水觀。他還指出,風水文化作為中國巫文化,在人與環境之關系上是對于自然神靈與命理的一種迷信,但風水理論與實踐中蘊含了一些樸素的生態環境意識。這也是具有當下意義的研究主題。
從比較文明史的對照看,所有的文明古國無一例外,都是在濃重的神靈信仰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氛圍下催生出的。這就構成一般而言的文明共性:文明不是伴隨理性和科學而來的,而是伴隨信仰和神話而來的。不過,關鍵的難題在于,如何細致入微地區分不同文明的神話信仰之特點,尤其是確認和聚焦到唯獨本土文明擁有而其他文明所無的文化特質方面。竊以為玉石神話信仰驅動的玉文化一萬年持久發展,就是這樣一個方面。而這也恰恰是一百年來的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研究完全忽略的。
討論與總結:新文科的創新引領
通過回顧四位本土人文學者的研究道路轉型,可以表明新文科的先驅性探索和嘗試,早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學界就已經存在,并且以某種不約而同的方式在文科各個專業領域中展開。正是人類學轉向,給大家帶來對學科本位視野的突破效應。交叉學科與傳統學科相比,在創新引領方面具有理所當然的優勢,但是交叉學科的倡導者也自然面對比常規學科的學者們更大的學術阻力和現實困難。
20世紀后期以來,交叉學科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出來,諸如文學社會學或藝術社會學,還有政治人類學、法律人類學、經濟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似乎人文社科中的所有學科都可以和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發生交叉,滋生出新學科。
唯有打破原有學科是不可侵犯的本位主義成見,創新引領的作用方可達到新文科實踐者的自覺意識。自西學東漸以來,學科劃分問題是最常體現西方觀點的場合。本土文化自覺的時代要求,正在改變原有的學科設置,也促進著本土學人走出學科本位局限,與時俱進地補習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如分子生物學和基因理論等。文學人類學派希望將史前文化與華夏文明史傳統對接成一個不間斷的文化編碼再編碼整體,其溯源性的深度認識程度達到一萬年的超長時段,這樣能給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全程研究打開新思路。
過去五十年以來,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經歷文化人類學輻射性影響并完成學術范式轉向的同時,文化人類學自身也經歷了非常巨大的學術轉型,即從早期進化論學派的效法自然科學模式,轉到逐個地認識和解讀特定文化的文化闡釋學方向。更加具有改變三觀作用的邊緣學科效應,是來自體質人類學或稱分子生物學的最新進展,從人類基因組的大數據方面重新看待人類文化和種族、族群分布源流的全新知識體,正在形成和完善之中。一個能夠真正兌現文理交叉、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叉融合的新時代正在到來。新文科的早期先驅實踐者們所集中關注的巫術或巫文化問題,也在方興未艾的薩滿文化研究大格局中獲得知識更新與理論提升的契機。這將是文科學者接納數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以來的超長時段相關新知識,從而再造基于大歷史、大傳統觀念的研究范式之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