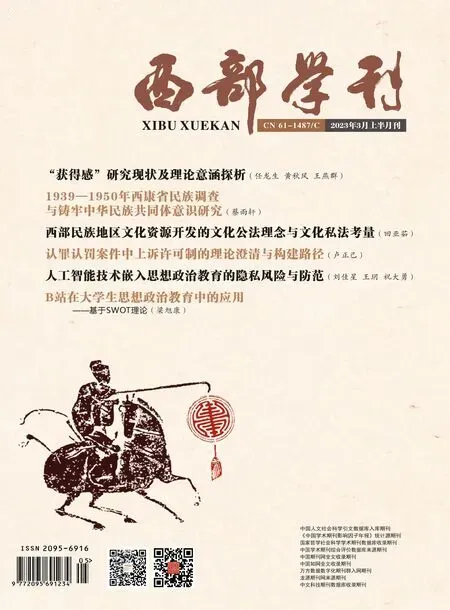1939—1950年西康省民族調查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
蔡雨軒
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各民族通過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加深了民族情感,逐步形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識,因而研究各族人民交流交往的關系史能夠看出中華民族共同體逐漸形成并不斷被鑄牢的過程。1939—1950年西康省民族調查是對特定歷史時期民族關系史的真實呈現,打破了漢族與西康省少數民族之間交流交往的壁壘,試圖將少數民族作為一個主體,平等地納入到國家政治話語中,于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各方面加強了西康省少數民族與其他各民族的認同感,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著意義深遠的影響。
目前學界對西康省民族調查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之間的聯系尚缺乏必要的研究,現有成果或側重于將西康省民族調查本身介于歷史脈絡的梳理和參與調查的個體或學術團體的研究,如曹春梅[1]的研究細列了民國時期參與西康省民族調查的考察者的不同類型、原因及考察影響;李沛容[2]從任乃強個人學術發展史的角度,探索任乃強在“中華國民之一體”影響下,對川康等邊疆地區民族觀的形成與轉變;張學強、李東東[3]分析梁歐第對西南地區邊疆教育方面研究的意義。或側重于民國時期介于整體歷史政治背景影響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發展過程表述,如俞祖華[4]介紹了民國歷史階段在歷史、政治、文化方面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成長和增強的過程;朱亞峰[5]以民族關系為中心,介紹不同時期中華民族關系的特征以及民族關系模式作用下,中華民族統一政治體形態的發展變化。本文從這一特定的民族學人類學實踐活動——西康省民族調查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出發,揭示其歷史意義與現實價值。
一、西康省民族調查的歷史背景
西康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其長期處于相對封閉的狀態,以致民國之前國人對其了解甚少。最早提出建立西康省的清末川滇邊務大臣傅嵩炑在《西康建省記》中記載:“西康,古、藏、衛三區之一也,東自打箭爐起,西至丹達山止,計三千余里。”[6]這里的西康主要包括大渡河以西,西藏丹達山以東地區,指傳統意義上的康屬地區,1939年西康建省后的區域還兼有雅屬和寧屬地區。西康地區地理上位于四川盆地西部、青藏高原東部的康藏高原,高原、山地構成其地貌的主要類型,山脈和河流呈南北縱貫態勢[7]。正是因為地形險峻、河流縱橫、氣候復雜,導致交通不便,阻礙了西康地區與外界的交流,其社會發展一直處于緩慢狀態,形成了相對獨特的民風民俗、社會形態。
歷史積累的多重矛盾使西康地區一直存在民族問題。從清末到民國初期因政局動蕩、戰爭頻繁,造成西康地區少數民族在中央政權中處于政治上被邊緣、情感上被疏離的狀態。清朝前期對西康地區的統治沿襲了前朝的土司制,管理相對松散;清末時期,西方列強將魔爪伸向我國邊疆地區,西康地區作為川藏交界地帶,也被西方列強所覬覦。清政府為維護邊疆穩定,派駐藏幫辦大臣治理西康地區,卻發生了“巴塘之亂”①,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等被殺。清政府派趙爾豐平定叛亂,改土歸流[8],延續至民國時期。民國成立后各地混戰,西康地區既有陳遐齡、劉成勛、劉文輝、劉湘等軍閥叛亂割據,又有在英殖民影響下的康藏之戰。此時西康地區千瘡百孔,民族問題更加尖銳。
1939年西康省正式成立,劉文輝擔任主席,政局相對穩定,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民族關系得到一定程度緩和。劉文輝受過新式教育,重視“文治教化”,期望發展“新西康”。他總結趙爾豐治理西康地區失敗的原因:“偏重武力,操之過急,是其一;忽視康藏人民之心理、宗教風俗習慣,沒有在康民精神上生根,是其二。”[9]因而在施政措施上,一方面,劉文輝誠邀各方面專家學者前往西康省考察,并給考察團隊、個人提供相應支持,以了解民情,出謀劃策,為西康省發展探索道路;另一方面,他深知西康省少數民族受宗教等影響根深蒂固,施政困難,便創辦報紙雜志等媒體,用以影響輿論、啟發民智,聯系民族情感[10]。這些施政措施既為學者們到西康省進行民族調查提供了便利,也為他們提供了可發表調查成果的學術陣地,客觀上推動了西康省民族調查的開展。
全面抗戰爆發后,與川、滇、青、藏四省接壤,作為陪都重慶大后方的西康地區,成為漢藏交流的必經之路,連接中印、中越、中蘇的交通線[11],承擔著為抗戰前線提供政治、經濟、軍事保障的責任,“邊地變腹地”,西康省具有重要的國防戰略意義,其民族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到該地區的穩定。這一時期,戰區大批高校內遷至西南地區,昆明接納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南開大學,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接納了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組成了華西“五大學”,兩處都為抗戰時期的學術“圣地”。因便利的地理位置,學者會聚,加之守護邊疆、民族統一思想的推動,學政兩界密切關注邊疆地區,“邊疆學”“邊政學”“民族學”興起,對西康省進行調查、研究和開發備受重視。
從西康省民族調查的歷史背景中可以看出,雖然惡劣的地理環境阻礙了西康省各民族與外界的交流,歷史積累的多重矛盾激化了西康省的民族問題,曾一度弱化民族共同體的情感聯系,但劉文輝的“文治”施政策略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民族關系,由抗戰帶來的外部危機激發了中華民族本就血濃于水的“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深層理念,在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共赴未來的“共同體”思想影響下,政府、學者等多主體參與者開始投入到西康省多方面、多訴求的民族調查中,主客觀上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西康省民族調查的內容及特點
西康省民族調查是指1939—1950年間,由政府為主要倡導者,學者、少數民族精英等多主體自覺參與,在原西康省存在時間的范圍內進行的一系列社會民族調查活動。調查內容涉及廣泛,涵蓋歷史、地理、生物、藝術等多學科,尤其在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家的參與下,各民族權利平等、文化相對論等思想逐漸在此調查中得到體現。對多元文化的研究將長期游離于國家知識體系之外的西康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納入到了中華民族理論敘述體系中,政府官員、學者等各行業人士努力踐行經世致用的思想為西康省民族發展建言獻策,在思想、文化、經濟建設等多方面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覺醒。
(一)堅持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進行調查研究
民國前歷代中原王朝對邊地少數民族的態度常帶著固有的歧視和偏見,即使調查與研究也是站在“統治”的角度,未能將其平等地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體系中,由此使西康地區給外界的刻板印象是貧窮落寞的山野鄉村,西康地區少數民族則是野蠻兇殘的代名詞,民族形象被“污名化”,嚴重影響著民族間的關系。民國時期到西康省參與民族調查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們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與各少數民族民眾平等地交往交流,通過實地調查成果反映出真實的西康省民族形象,傳達民族平等思想,以化解彼此間的隔閡。

林耀華的調查經歷讓我們看到,以往對西康省少數民族的形象描繪存在著謬誤和偏差,民族形象的展現關系到民族情感的維系,而西康省民族調查是其他民族與西康省少數民族一次平等的交流互動,只有在平等交流的基礎上,各民族才有共赴未來的決心。
(二)堅持以民族多元文化的角度進行調查研究
民國前西康地區的民族文化研究處于一個未開發狀態,而民國時期一批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民族學家等展開了西康省少數民族文化的多角度調查研究,保護西康省少數民族的文化多樣性,讓各民族認識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強了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

民族文化方面,宗教是西康各民族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了民眾思想教化的重要任務,更影響著政策的實施和經濟的發展。李安宅曾說:“宗教在邊疆的勢力較在內地為大,故欲建設邊疆,在文化一方面應以宗教為對象:因為宗教在邊疆不但常與政治經濟密切聯系,而且常是唯一的教育。”[22]李安宅對康藏地區佛教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他于1944年、1945年對西康考察后發表論文《德格之歷史與人口》[23]《薩迦派喇嘛教》[24],還有馬長壽寫的《缽教源流》[25]、任乃強的《喇嘛教與西康政治》[26]等都詳細介紹了西康佛教各教派的歷史。與西康省的藏族信仰佛教不同,彝族等少數民族信仰原始宗教,陳宗祥在《倮儸的宗教》[27]中介紹了倮倮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觀念、祭祀儀式等,在《西康栗粟水田民族之圖騰制度》[28]中介紹了傈僳族、水田族中與圖騰制度相關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祭祀等風俗。
物質文化遺產方面,隨著抗戰后國立中央博物院開始向四川等地區南遷文物,國立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們將重點放在了西南地區的研究和文物搜集上。國立中央博物院于1938年冬至1939年春派遣中英庚款委員會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資助的川康考察團,由馬長壽帶領,進行第三次考察,歷時四個月,主要在西康省越巂東部尼帝、斯補、埃絨三土司區域,共搜集了12箱文物和標本[26];凌純聲帶領的川康民族考察團于1941年主要考察了川康地區的藏族、羌族、彝族,也搜集了相關的民族文物和用品[29]229-230。
這些學者對西康各民族歷史文化的調查考證,促進了其他各族民眾與西康省少數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讓各族民眾在國家危亡時期認識到民族文化遺產的博大精深、民族文化的“多元一體”,有助于樹立民族自信心,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三)堅持以踐行“經世致用”的思想進行調查研究
西康省民族調查涉及多主體多領域,參與調查者秉持著“經世致用”的思想關注民族地區存在的問題,為西康省民族地區發展建言獻策。一方面國民政府已經由“統治”思想轉型為一定程度的“建設”與“發展”的萌芽意識,國民政府出于處理民族關系、邊疆事務及加強國防的需要設立專門的調查機構,例如蒙藏委員會調査室、邊疆行政設計委員會等側重考察少數民族民生政情,促進邊疆地區經濟開發建設;另一方面戰時身處西南地區的學者、行業精英切實接觸到邊疆地區社會發展的問題,他們在政治目的之外,希望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為西康少數民族發展作出貢獻,因而不少人利用政府、學校、基金會、企業等各種渠道籌集考察經費,開展西康地區民族調查,涉及多學科、多角度的調查研究。
社會經濟發展方面,調查涉及人口分布、家庭情況、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與分配,以及自然資源轉化等,是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的重要引擎,是加強交融至關重要的因素。西康省川康科學考察團經濟組的吳文暉在考察后與朱鑒華合作撰寫了《西康人口問題》[30]《西康土地問題》[31]兩篇文章,分別列出了西康省雅屬、寧屬、康屬地區的人口分布、宗族信仰、種族、男女比例、家庭經濟、受教育程度、土地利用與分配等情況,并指出存在的問題,供邊疆設計者思考。柯象峰[32]有法國里昂大學社會經濟系專業背景,在西康民族的調查研究方面更多地從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的角度入手,詳細分析了西康居民人口分布與變遷、家庭生活、經濟政治情況、教育發展,提出“因俗為治”“因時因地制宜”和“執簡馭繁”的社會治理原則,制定了西康地方的“土地政策大綱”“貿易政策大綱”以及生產、教育等政策大綱。畢業于暨南大學的謝天沙[33]以一位工程師的理性態度,不僅記錄了游歷沿線的地形方位、風土人情、政治設施、工業產業等調查資料,更設想如何將康藏豐沛富饒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生產力,如利用好高原地區的風能發電、化解高原堿質泥土后筑修公路等。
文化風俗方面,西康省少數民族的歷史地理、人文物產、人情風俗調查,使西康省少數民族地區與外界有了交流溝通渠道,增進相互了解,更為民族關系史的梳理、民族形象的展示提供大量理論與實踐的支持。作為實干者的段公爽只身前往西康地區辦報,用報紙開化民眾,并在《入康記》[34]中以半日記半游記的形式記錄了辦報過程的所見所聞。林耀華于1944、1945年暑假由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接受美國羅氏基金會及哈佛燕京學社的專款資助進行川、康邊境及康北地區的調查[29]223-224,發表了《康北藏民的社會狀況》《川康邊界的嘉戎土司》《川康嘉戎的家族與婚姻》[35]等論文。在李安宅推動下,1942年由華西協和大學成立的華西邊疆研究所,以華西地區少數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成為研究西康地區少數民族的重要機構,李安宅任副所長主持工作,成員有任乃強、劉立千、于式玉、玉文華、馮漢驥、謝國安、羅榮宗、蔣旨昂、鄭德坤、葛維漢等[36]。華西邊疆研究所一度缺少經費,李安宅就利用國民黨的雜志《康導月刊》,蒙藏委員會的雜志《邊政公論》發表華西邊疆研究所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甚至利用國民黨單位職務獲得考察的便利。學者陳宗祥[37]就曾受李安宅推薦于1944年到馬邊“邊民生活指導所”從事為期三年的邊民指導工作,并于1945—1947年曾橫越大涼山進行民族宗教、社會組織等方面的田野調查,發表了《橫越大涼山》[38]等論著。
三、西康省民族調查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義
民國時期,為更好地發展西康地區建立了統一行政建制,并在此基礎上為制定該地區的發展規劃進行了全方位的實地調查,以圖構建地方性的、較為全面的涉及各民族社會文化的知識體系。西康省民族調查不僅促進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治理者對該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現狀的了解,也為后來的民族識別、社會歷史調查奠定了基礎,更為現代國家建設初步積累一定的實踐經驗。
(一)承認各民族平等地位,初步在實踐中探索“民族國家”政治理念
民國前的政權對少數民族的統治大都采取武力打壓、文化同化等政治措施,使其依附于中央王朝,這讓少數民族的平等地位長期無法被承認和實現。民國時期學界、政界第一次積極探索“民族國家”的政治理念,重視各少數民族的權利,讓少數民族社會開始萌發對民族平等權利的想象和追求。
1939年在邊疆危機的影響下,傅斯年提醒當時主編《邊疆周刊》的顧頡剛,他認為應該謹慎使用“邊疆”“民族”這兩個詞,防止有心之人“巧立民族之名,以招分化之實”[39]。顧頡剛接受了傅斯年的建議,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主張“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再析出什么民族——從今以后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么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40]。受此觀點影響,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41]中表示“中華民族是多數宗族融合而成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意在弱化“民族”概念,強化“國家”概念。吳文藻、費孝通憑借深厚的人類學知識積累及長期的田野調查經驗,對此表示不贊同。吳文藻認為:“今日吾國之邊疆,種族宗教復雜,語言文字歧異,經濟水準不齊,文化程度不等,乃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欲鏟除各民族間互相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來隔閡的感情,亟須在根本上扶植邊地人民,改善邊民生活,啟發邊民知識,闡明‘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曉示‘中華民族完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真義,能如是,則思想可以統一,組織可以健全,畛域可以化除,團結可以實現,國力既充,邊圉自固。”[40]費孝通指出:國家和民族不是一回事,不必否認中國境內有不同民族的存在。國家內部發生民族間的分裂,并非各民族不能共生,根本原因在于各民族間政治上的不平等[39]。
吳文藻、費孝通對于“民族國家”的構想意在強調,要關注各民族種族、宗教、語言、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性,增強各民族的情感認同,在經濟發展、社會民生、知識傳播等方面給予少數民族幫助,從而實現各民族思想、組織的團結統一,建設多元民族為主體的國家。盡管“民族國家”的構想受到了當時其他一些學者和官員的批評,但這一思想在西康省民族調查中因該區域特殊社會環境而得到了初步實踐。特別是參與調查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學者大都受到了“構建民族國家”這一理念的影響,他們支持尊重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的主體地位,注重收集地方的歷史文化資料、解釋少數民族的污名形象、關注地方社會民生發展,并且希望在權利平等的框架下將各民族納入到民族國家的敘述體系中。他們的實踐理念超越了傳統的“統治”“教化”和“獵奇”等思想,對于構建“民族國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政治、情感上增進了各少數民族對于民族“共同體”的理解和認可。
(二)探索各民族良性互動路徑,初步在實踐中促進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
由于長期以來地方政治沖突、文化差異顯著、經濟社會發展脫節、歷史敘述與社會輿論片面化等原因,導致西康省各民族間存在較大隔閡,始終無法形成持續性的良好互動路徑。例如在家支林立的涼山彝區,漢族、彝族作為主要世居民族長期以來不乏矛盾和沖突。在林耀華進入彝區調查時,也時刻承擔著可能被當地彝民擄去當“娃子”的風險[14]21。由此,探索各民族良性互動的路徑,將成為建立“民族國家”尤為重要的前提。在西康省民族調查期間,各民族的良性互動首先由官方和學者自上而下、由外向內的行動來引領,正如前文所述對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平等權利的關注。同時,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良性互動并非只是政府和學者單方面的要求,少數民族社會渴望通過融入中央政權來解決自身面臨的困境,特別是少數民族精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因此積極參與到探索各民族良性互動路徑之中。
從西康省民族調查資料中可以看出,當時西康省一些地區深受少數民族政權的壓迫,對漢族地區有著向往和憧憬。李安宅在《云霓之望》[42]中寫道,尚在拉薩政治范圍內的西康藏民“望漢官設治,誠如大旱之望云霓”,當地人更是流行一句話“壞的漢官也勝似好的藏官,好的藏官也不如壞的漢官”。可見西康藏族對于歸屬中央政權的渴望。藏學家楊質夫在《夥爾三十九族之調查研究》[43]中表達了黟爾三十九部備受徭役壓迫的痛苦和渴望早日歸漢的愿望。
在漢族地區受過新式教育的涼山彝族領袖嶺光電、長期扎根于涼山彝區工作的毛筠如以及來此調查的學者們都帶來了很多涼山以外的信息,影響著彝族對漢族的認知與判斷。在這些人的努力下,民國時期的涼山彝區在一定程度上向漢族地區學習、進行改革,促進了彝漢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嶺光電為涼山彝族土司,后家族衰弱,來到漢族地區接受教育,于1933年考入國民政府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后擔任軍政職務。由于從小生活在大涼山彝區,嶺光電對彝民的生產生活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又因接受了新式教育,開化了思想,了解了涼山以外的世界,他深知彝區的閉塞導致彝漢關系有很深的壁壘,也使彝族各種陋習積弊已久,彝民需要開化、彝區需要開放。為了讓涼山彝民了解外面的世界,嶺光電興辦學校等公共事業,支持電影的推廣,讓深山中的彝民通過教育增長學識,自立自強。為了化解彝漢間的矛盾,讓漢族地區人民對涼山彝區有更深入地了解,嶺光電曾翻譯過彝族經典歌謠、故事,發表過一些論文,1943年他整理12篇與彝族相關論文編輯成《倮情述論》[44]。這些論著既記錄了涼山彝區過去與現在的各個方面,也有很多是對于彝族現狀與發展的思考。與作為客體到西康調查、把彝族等少數民族作為“他者”的漢族學者的視角不同,嶺光電的文章以敘述“自我”方式展示了彝族社會風貌,促進了外界對彝族的了解。這也表明,少數民族政治文化精英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與中央政權及外界進行有效互動。
可以看到,在政府、學者和少數民族精英的共同努力下,西康省民族調查是參與者在“民族國家”思想影響下不斷探索各民族良性互動路徑的過程。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西康省民族調查是政府關注域內各民族互動狀況的第一次嘗試,是知識分子們集中進行邊疆少數民族研究的學術實踐,同時也是少數民族精英渴望獲得民族權利、發展機會而與外界進行的良性互動。通過西康省民族調查,我們看到多主體之間相對平等的互動成為可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被認識并鑄牢。
(三)積累各民族識別經驗,初步在實踐中為民族政策制定、民族研究奠定基礎
歷史上最早進入西康地區進行系統社會調查的是西方人,其中不乏以游歷、探險為名的侵略活動,而民國時期的西康省民族調查是為中國自主進行社會調查邁出的重要一步,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礎。這一時期對西康省彝族、藏族、羌族等民族的研究,為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識別積累了經驗,也為民族政策制定、民族研究奠定了基礎。
調查形成的對西康省各民族的初步認識,為今后進行民族調查的實施、民族政策的制定積累了寶貴的經驗。1950年進行的民族識別和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即是針對當時民族狀況不清、族群認同混亂、少數民族社會性質不明確、民族地區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局面,為保障民族政策有效實施,發展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事業,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而進行的調查研究[45]。期間,民族學家們承擔了主要的調查工作,在民國時期進行西康省民族調查的林耀華、陳宗祥等專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都繼續參與到政府組織的民族大調查工作中,而民國時期的調查成果則起到了很大的助力作用。例如,曾經參與西康省民族調查的學者們更會注意到少數民族名稱的來源、意義,少數民族群眾對本民族稱謂的態度的重要性,因而在民族識別過程中提出盡可能遵從“名從主人”的原則。這些調查者中尤其是人類學、民族學家們通過調查發現了西康省各少數民族文化、宗教、語言的差異性,并進行相應的研究分析,影響著后來參與者將共同語言、共同心理素質、共同地域這三個特征作為民族識別的依據。他們對由于歷史發展進程的不同造成民族階級屬性的差異有了初步的了解,促進了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時少數民族階級情況的順利劃分及之后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實施。此外,他們意識到民族政策對于“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政策、加快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建設政策等都是對“民族國家”政治理念進一步的實踐,這說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四、結語
由于歷史原因,西康省少數民族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知曾受到一定的沖擊,但在全面抗戰特殊的歷史背景下,西康省民族調查重新喚起了當地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和認同。西康省民族調查對西康省少數民族形象的重新表述、對當地民眾生計生活的關注以及對當地社會發展的現實意義,使西康省少數民族逐漸融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道路中來。盡管新中國成立后西康省不復存在,但西康省民族調查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民族識別、民族政策制定等方面。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過程中,不僅是意識形態,如思想開化等問題,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一體化尤為重要,民國時期的西康省民族調查在開始關注少數民族生計、生存、發展等實際問題中,逐步產生了帶領各少數民族一起進步的萌芽,各民族共同參與國家建設,共享國家發展成果,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以鑄牢的基礎條件。
注 釋:
①“巴塘之亂”是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初,在川邊地區發生的暴亂,主謀者是巴塘土司與丁林寺上層。巴塘土司與丁林寺喇嘛聚眾焚燒法國天主教堂,殺死兩名法國傳教士,并打死清政府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及其隨員百余人。事發后,四川總督錫良、成都將軍綽哈布奏派四川提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剿辦”。六月,馬、趙率軍擊敗巴塘、里塘土司軍隊,打死里塘土司和桑披寺喇嘛,并將巴塘正、副土司正法,平定巴塘、里塘。隨后,馬維騏回川,趙爾豐留任爐邊善后督辦,處理巴塘、里塘改土歸流事宜,并繼續征戰鄉城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