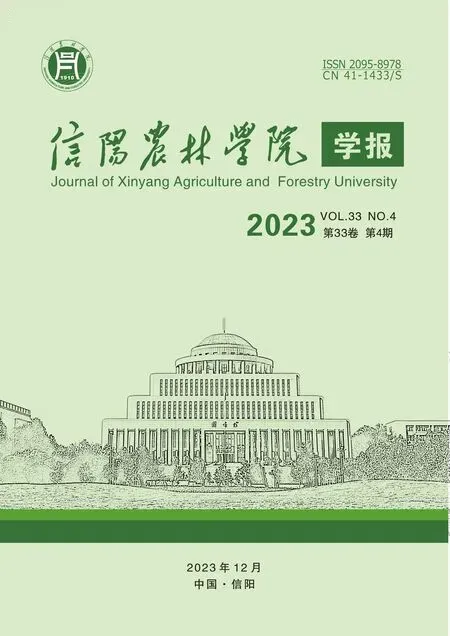書寫鄉土中國的新氣象
——讀喬葉《寶水》與付秀瑩《野望》
梁玉潔,馬騰驤
(1.信陽農林學院 茶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2.信陽農林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 信陽 464000)
百年中國現代文學中,鄉土文學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救亡、建設、改革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承擔起了書寫中國和記錄時代的重要責任。在新的社會面貌下,如何對中國式鄉土現代化的偉大變革進行有分量的文學賦形,這之于當代作家是個不小的挑戰。喬葉的《寶水》和付秀瑩的《野望》就直面了這一時代命題,她們從村莊這一基礎單位出發,通過個體敘事和鄉村新變刻畫當代中國滄桑巨變的深刻履痕。本文以這兩部新近面世的長篇小說為例,分析作家們如何呈現了當代鄉土的新氣象,并由此觀照新時代鄉土的總體樣貌和精神氣象。
1 返鄉:發現新的鄉村風景
對于從故土走向現代都市的知識分子而言,“返鄉”常成為反復書寫的母題和敘述模式。同為70后女作家,喬葉和付秀瑩的人生軌跡極為相似:農村出生,縣城讀書,在省會乃至首都工作安家,以農村老家為原點,生命軌跡的外延不斷擴展。喬葉和付秀瑩在創作各自的長篇小說時,一方面繼承了傳統的返鄉敘述話語,一方面因為人生經歷,都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獨特的返鄉主體,以在場的敘述展現了中國鄉村的生命力和包容度。
1.1 轉變焦點,發現鄉村的包容和闊達
《寶水》中地青萍患有嚴重的失眠癥。失眠癥是現代都市生活中常見的一種病癥,多與生活狀態和心理有關,地青萍生活富足、工作輕松,失眠多是心理因素。進入城市生活后,相繼面臨父親、奶奶、丈夫的離世,她像無根的浮萍,沒有依托,夜夜難寐。一次偶然的機會,她發現鄉下可以治好失眠,于是果斷回去,在一年的返鄉生活中,她“視覺的焦點和重心發生變化”[1]58,對老家的態度由逃避轉變為接納。
地青萍視覺的焦點和重心發生變化主要見于兩組鏡像關系。第一對關系是寶水村和福田莊。地青萍返鄉了,但沒有回老家福田莊,她本能地拒絕福田莊,歸根究底是以奶奶和父親為代表的農村處世觀與其本人所持的城市價值觀發生了分歧。奶奶的人生信條是“人情似鋸,你來我去”“維人”,她也的確以智慧和能力維系住了家族的穩定,待兒子扎根城市,她便將維系家族的繩“套”在了兒子身上,千絲萬縷的繩越套越多,終于在父親借車給同村人結婚的路上車禍身亡而斷裂了。奶奶的處世哲學成為地青萍厭惡福田莊的根源,她以為這種恨意會隨著奶奶的去世消失,卻不想折磨到了她的睡夢中。寶水村的生活,使她不自覺想起福田莊的幸福童年,在寶水村人情往來中的游刃有余,不得不說得益于奶奶身傳于她的維人哲學。“寶水如鏡”,寶水村就像一面鏡子折射了福田莊,也照見了地青萍內心深處對福田莊的依戀。奶奶與九奶是第二對鏡像關系,也是觸發地青萍真正讀懂鄉村的重要紐帶。在寶水村,她第一次見到九奶,就覺得九奶的臉、做派像極了奶奶;與九奶“扯云話”的時光里,她拼湊出了奶奶少女時的模樣,完成了對奶奶的精神畫像;與九奶同吃同住,發現九奶的氣息也像極了奶奶,她不自覺地把九奶當成自己的奶奶,在她身上傾注了對奶奶未盡的孝心。在九奶的遺言中,她終于知道了讓自己無數次夢魘的奶奶的遺言:回來就好。謎團打開,她完成了自我救贖。在兩組鏡像關系中,地青萍從認為“所謂老家,就是這么一個地方啊”[1]19到“老家意味的,是親人”[1]330,而深刻理解了老家的意義。
鄉村不會言語,它一直都在那里,對鄉村的態度,取決于人的心境。再次返鄉,地青萍重新理解了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生活邏輯,內心的矛盾糾纏得到釋懷。《寶水》是一場精神返鄉之旅,她意外地發現了鄉村的包容和闊達。
1.2 全景畫卷,呈現鄉村的生命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鄉土文學書寫,較為頻繁地流露出對鄉土終結命運的憂思,這的確與中國農村潰敗、空心化的現實有關,但并不代表鄉村就是一派絕望的景觀,那些未曾離開的人始終與鄉土命運與共。所以,付秀瑩是可貴的,她沒有居高臨下的姿態,而是隱身在主人公翠臺的身上,本真地從一個農村婦女的視角全景描繪了熱氣騰騰的新時代鄉村生活畫卷。
如果《野望》是一部電影,鏡頭就是始終圍繞著翠臺的,“吃罷早飯,翠臺到她爹那院里去”[2]1,而后就是一鏡到底的長鏡頭:耀宗家人頭攢動的衛生院、衛生院對面秋保超市、超市旁邊新蓋的村委會大樓、大樓前面建國媳婦的燒餅攤子。翠臺腳步和眼睛關涉到的地方幾乎涵蓋了芳村醫療、經濟、政治、社交的全部場所,在這些活動場域,流動著不同的人物和故事,都帶有生活的溫度和肌理,這是鄉村秩序穩固恒常的狀態。芳村中的物象也順應四時的變化,呈現出飽滿豐盈的生長姿態。冬日陽光薄金一樣淡淡灑下照得人懶洋洋;居連上種著棗樹、槐樹,雜草茂盛,空氣中一股子潮濕的泥土腥味兒和著莊稼地的草木青氣……自然物象群不僅裝點了故事的自然背景,也凸顯了鄉土生活的秩序和生氣。
芳村的生命力還體現在常態生活中的變態事件,變中涌動著一種尋求出路的迫切需求。翠臺的生活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兒子大坡與媳婦愛梨鬧矛盾,愛梨連夜回娘家從小寒住到了臘月底,翠臺托人請了四回,每請一次內心就愈發焦灼,但在人前,為了維持家庭的體面和安穩,她還是該拉家常拉家常,該辦年貨辦年貨。愛梨被接回家,翠臺的生活似乎平靜了一些,緊接著妹夫投資被騙,廠子快辦不下去了,翠臺非但幫不上忙,還欠著妹妹家的錢,只能指望丈夫根來養的豬賣了錢才有辦法。不料,養的豬一夜之間鬧瘟疫死光了,不僅沒了經濟來源,根來也心事重重。兩代人的家庭矛盾、農村傳統經濟模式的不穩定與低效能帶來的生存危機,幾乎是芳村家庭都面臨的問題,每一家都在平凡瑣屑的生活中手忙腳亂地應對。“變動—應變—常態”的過程中,鄉村的人和物都在與時代的互動中醞釀新的可能。
2 造境:點亮鄉村傳統美學的光彩
中國鄉村已然步入城鎮化的軌道,全球化、現代化的人文風景幾乎已經滲透到鄉村大地的每個角落,與此同時,鄉村中具有地域色彩、民間色彩的民俗文化也正在流逝[3]。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喬葉和付秀瑩,將傳統文化元素注入小說的血脈和根系,又以鮮活的方言俗語活躍了鄉村的表情,點染了中國鄉村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
2.1 傳統的重量
“一部好的長篇必須有一個好的有機結構,以求在相對精小的空間中貯藏起較大的思想容量和藝術容量。”[4]《寶水》和《野望》采用了“四季”和“二十四節氣”結構小說,在始于冬終于冬的四時集序中完成一個井然有序的輪回。《野望》以二十四節氣命名章節,形成了以“節氣注解語—節氣古詩詞—生活場景”為固定模式的每章結構:
春分
《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
踏莎行·魚霽風光
[北宋]歐陽修
雨霽風光,春分天氣。千花百卉爭明媚。畫梁新燕一雙雙,玉籠鸚鵡愁孤睡。
薜荔依墻,莓苔滿地。青樓幾處歌聲麗。驀然舊事心上來,無言斂皺眉山翠。
春分了,天氣漸漸暖起來。草木萬物都生發了,空氣里濕漉漉甜絲絲的……算來算去,越算心里越煩惱……閑得人心慌[2]142。
每章古詩詞的選擇并非簡單的對號入座,詩詞的基調往往與故事氛圍有內在的一致性。春天,自然界萬物復蘇,但這個家庭卻沒有生氣:翠臺家養豬,豬肉價格一直往下掉;村里青壯年都在忙活,兒子兒媳卻無業,花錢還不節制,如此種種正是“舊事心上來”。付秀瑩深諳節氣就是鄉村人的生活節奏和精神原點,節氣關聯著他們的收成、溫飽,指導著行為處事和生活秩序。她以節氣和傳統文化架構小說,打通了進入中國鄉村的路徑,提供了解開鄉村文化的密碼,這種精心和耐心正體現了作家還原一個傳統文化積淀深厚的鄉村面貌的用心良苦。小說的名字“野望”與唐代詩人杜甫、王績的古詩《野望》題目相同,這種并非刻意的一致,“大約是傳統這個東西太強大了,它早已經滲透到你的文化血脈深處,默默滋養潤物無聲”[5]。跨越時空的作家們,都在“野”而“望”,看見的風景已是滄海桑田,但對家國民眾的深沉情感是相似的,這就是作家對深藏在精神血脈中的傳統文化的自覺體味與認同。
《寶水》分為“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章,每章均勻分布30節,共120節,也時常可見作家對節氣、時令相關生活的描寫,如驚蟄吃懶龍(菜蟒)、正月挖茵陳、三月三薺菜煮雞蛋等,都表明了節氣對鄉村人生活的深刻影響。相比節氣,小說中更引人注意的是作家對鄉村風俗習慣和口耳相傳的念詞、唱詞等的熟悉。蓋房子上梁時要送主家面包或剛出鍋的饅頭,取一個發字,上梁要選陽氣正盛、陰氣全無的吉時,請太公、祭梁(澆梁和上梁)、撒梁,每一步都有隆重莊嚴的念詞。這樣繁雜的流程反映了土地、房屋之于鄉村人的重要意義,傳統的自然經濟使鄉村人依附于土地,土地也帶給了他們歸屬感,人與土地的黏連造就了中國人深刻的鄉土觀念。小說中舞獅子喊彩的情景也十分熱鬧,鑼鼓班和舞獅兄弟走過村里的每一家,依著家中的情況都有一套唱詞,家中有喜就唱得熱鬧喜慶、有喪就唱得悲慟蒼涼,整個隊伍配合得行云流水,每一戶村人都感受到了社群的親密團結。小曹結婚時,鋪床環節最要緊的還是念詞,只有八句,大英還與時俱進,把時興的詞融進去,舊俗新禮竟和諧有趣。九奶是村里行走的典故和風俗集,她被大英逗著唱時令菜名兒曲子,節奏韻律雖完全變形,卻讓人牽腸掛肚。九奶去世后,吊孝的人絡繹不絕,村里安排抬著九奶巡山,選定吉時,由孫子老原摔瓦盆扛幡,徐先兒高喊“八仙各守一方—抬重各在其位—起靈”,巡山正式開始。巡山不走回頭路,走過西掌喊四句詞,到了中掌又喊四句,下棺前還需至親躺進墓坑暖房,埋棺前眾人撒土……九奶配享巡山,不只是因為年紀和貢獻,她仁厚如地母的氣質,代表著傳統的鄉土精神,她是鄉村凝聚力的體現。
在鄉村,蓋房子、結婚、喪葬、農事活動等都有相關的風俗習慣或行事規則,并形成了約定俗成的鄉村秩序,人們在共同體中遵守秩序并享受秩序帶來的安定,這些傳統文化就是鄉村賴以存在的根基。需要補充的是,兩部小說都描寫了鄉村迷信現象,《野望》中小別扭媳婦善跳大神,被無助的人們視為最后的救命稻草;《寶水》中趙先兒鋪個卦攤兒,說命看宅相面滔滔不絕。迷信固然是鄉村傳統文化中蒙昧的一面,但也側面反映了鄉村傳統文化的厚重綿長。
2.2 流淌的語言
兩部小說雖都有明確的時間線索,但推動小說的卻是一種強大的語言力量,在充滿鄉野氣息的語言流中,細碎的生活、纏繞的人情、綿密的事理全部敞開來,一種久違的生活體驗撲面而來。兩位作家憑借對地方生活和語言系統的熟悉,喚醒了方言的生命力。
評論家陸梅認為《寶水》是“三成書面語、七成方言土語”,喬葉完全同意這一說法[6]。小說120個標題,有近30個是以方言詞條作為標題,如“維”“悠”“扯云話”“里格楞”“得濟”等,由此引出對人物、故事以及鄉村典故的講述,頗有周立波《山鄉巨變》、韓少功《馬橋詞典》“詞典體”的形式。“悠”是閑庭信步的意思,在放松、無事的情況下,慢悠悠地晃蕩在鄉村各處,呈現了心境和環境融為一體的和諧。“扯云話”是聊天的意思,但又非聊正事,而是無邊無際、天馬行空般隨意聊下去,話頭越扯越多、越扯越遠,沒有目的,也不追求意義。標題之外,小說中還有大量的鄉諺、俚語、俗話、童謠,展現了豫北鄉村獨特的語言樣貌,更凸顯了地域滋養的人物性格和精神脈絡。
《野望》中的語言具有充沛的生命力和細膩的美感,付秀瑩善于調配各種感官體驗,搭配貼切的語言,打磨小說的細節,使我們感同身受。
“這個季節,天短,黑夜來得就快些。也不知道是霧,還是霾,從四面八方聚攏來,慢慢籠罩了整個村莊。路燈卻遲遲才亮起來,是那種蒼白的燈光,好像是一只一只眼睛,在茫茫的暮色中明明滅滅。田野變得模糊了,天空中那些橫七豎八的電線,也沒了痕跡。誰家的狗叫起來,懶洋洋的,叫了幾聲,覺得無趣,也就罷了。有小孩子在放鞭炮,噼啪一聲,噼啪又一聲,噼啪,又一聲,猶猶豫豫的,是試探的意思,也有那么一點不甘心。”[2]39
意象雖稍顯低沉,但生活氣息絲毫不弱,作家調動了翠臺視覺、聽覺、觸覺、情緒全方位的感知,描繪了大寒傍晚人景交融的場景。翠臺本就因愛梨回娘家,三請四請不回來,兒子卻沒心沒肺而惱恨到流淚,此時站在門外見夜色漸漸籠罩,內心更加孤獨無助。斷斷續續的噼啪聲,就仿佛愛梨娘家不肯輕易妥協的態度,任她再有心勁,也只能焦慮又期盼。付秀瑩這段描寫頗有魯迅遺風,用極其細膩的筆觸雕刻出了日常生活的褶皺和人性的共通點。除了極富故事感和情緒力的語言,小說中只要人物互動,方言就無處不在,“叫他們笑話去!都是添言不添錢的。誰家能說一輩子在崗上?誰就沒有跌在洼地的時候?”[2]76稠密的方言,不需要解釋,就能明白意思,并以此照見人物的脾性,人與話緊密相融,有一種人在話中、話見人心的閱讀體驗。
一般而言,描寫鄉土的小說總會有“國罵”“屎尿體”等粗鄙的方言,但在這兩部小說中幾乎沒有,鄉村生態純潔純真。所以,方言在這里不僅是一種聲音、一種語言,更是作家體察當下鄉村生活的一種立場和視角。
3 建設:呼之欲出的新鄉土想象與鄉村變革
在中國村莊的地圖上,并不能一比一找到“寶水村”和“芳村”,他們是作家新鄉土想象的產物,但也是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寶水村是喬葉以焦作的一斗水村的地理形態,融合信陽郝堂村和焦作大南坡村的生活實踐創造出來的[7];芳村是付秀瑩對故鄉的一萬種想象和記憶的承載裝置,實際上它們彷佛是每一個中國的鄉村。《寶水》《野望》用文學想象的方式參與當下中國的鄉村建設,并試圖提供豐富多樣的實踐方案,也正因如此,喬葉和付秀瑩的鄉土書寫擴大了新世紀鄉土文學的格局。
寶水村走美麗鄉村道路,除了自然條件成熟,還有賴于國家政策資金扶持、鄉建團隊的專業指導、領導的重視和鄉村基層組織的實干。孟胡子“是一個順應時代潮流、扎根鄉村干實事、具有時代精神特質的新人形象”[8],他不是鄉村基層干部,也不是農村新人代表,作為寶水村美麗鄉村項目的規劃師,非體制的靈活身份以及對鄉村規則的熟悉使他在與政府、村民的往來中較少局限。孟胡子從不以優越的姿態批判或教育村民,更多是建設性的指導,從鄉容鄉貌上規劃每一家民宿的院墻、瓷磚、指示牌;在垃圾治理、廁所、收費問題上詳細解釋和引導,以現代管理制度幫助村民擺脫小農意識、顧全大局。孟胡子的鄉村規劃始終重視發揮村民的主體性,就是希望即使自己或閔縣長離開,鄉村仍能自主運轉。孟胡子是鄉村外來者,他打造了寶水村人和城里人理想的生活面貌;大英是在村者,她守護和鞏固了寶水村的發展和穩定;小曹是返鄉者,他享受并參與村莊的建設,他們與村莊都有不同的連接,但都在這里找到了價值并賦予了鄉村新的意義。
“各地農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條件有別,所開辟的生財之道必定多種多樣,因而形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模式”[9]。《野望》中芳村是冀北一個平原村,付秀瑩沒有程式化地將鄉村旅游作為鄉建的法寶,而是尊重自然生態,讓芳村順勢走產業發展道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農村實行了以包產到戶為主要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增強了個體發家致富的積極性,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的市場經濟時代,這種獨立分散的小規模經營由于缺乏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生存空間不斷縮小。小說中大全、增志、團聚等各自經營的皮革廠因為資金、污染等問題面臨破產;根來等個人養豬場遭遇豬瘟,全軍覆沒。獨立經營看似自由靈活,一旦風險來襲,對整個家庭就是滅頂之災。如何解決村民分散經營中的困難,50年代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提供了一個有效參考,不同的是,“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僅包括勞動者的勞動聯合,還包括勞動與資本、技術、管理等聯合,聯合的目的是實現個體的發展”[10]。發達帶著根來等人發展公司加農戶的新型規模化養殖模式,背靠大公司,把零散的農戶養殖聯合起來;縣里建了產業區,將對增志等的小廠子進行統一管理;香羅經營的超市開啟了加盟連鎖的模式。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給了芳村人新的出路,也煥發了鄉村新的生機。
寶水村主打旅游致富,芳村依靠產業振興,在差異化轉型的道路上,現代智識資源的注入使鄉村舊貌換新顏,而作家們重點關注的還是如何激發鄉村內部的強韌生命力,真正實現鄉村振興。“村景再美,美的芯兒還是人”[1]483,只有革新鄉村人的經濟觀念、審美觀念、價值觀念等,才能使村莊即使沒有外在的支持,也能“斷了輸血自造血,真正做到自力更生且生生不息”[1]162,這也是兩部小說進一步關心的問題。喬葉在《寶水》的閃光之一就是塑造了“美的芯兒”——鄉村女性雪梅的形象。雪梅同丈夫經營民宿,她善良、有原則、素質高,具有鄉村傳統女性的美好品行,更重要的是,她具有符合新時代的意識觀念。雪梅的審美天分是地青萍和孟胡子認可的,她喜好插花、熱愛繪畫,民宿的布置具有超出同村人的高級感。食藥監管局抽檢民宿的食品安全,本村的民宿只有雪梅家過關,因為她不貪便宜買來路不明的干貨,憑良心、講原則。《野望》中翠臺的孩子大坡和二妞是新時代典型的鄉村青年代表,大坡學業無成、工作無著,在父母的操持下娶妻生子,婚后一家三口繼續啃老,在經歷父親養豬失利、家庭沒有經濟來源后,他意識到家庭責任開始變得勤勞務實。二妞在城里讀書,翠臺希望她留在城市吃國家飯,二妞卻要回來建設鄉村,她是屬于新時代獨有的新人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青年要進城才能改變命運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識,而現在,二妞這樣的農村青年選擇建設鄉村已成為一種趨勢:喜針在北京念了博士的外甥回縣里工作、鎮里新來的博士生張書記、來村里掛職的郝主任、在村里辦畫畫培訓班的四川美院畢業生,大批返鄉者或下鄉的年輕干部投身鄉村建設,他們是芳村的一道風景,也是新時代鄉村變革跳動的脈搏和翻騰的血液,正是他們,鄉土想象才有極大可能成為現實。
“芳村這地方,向來講究這個。”“芳村這地方有個風俗。”“(寶水)村里就是這”,鄉村有自成一套的傳統和秩序,它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體系,唯其不變,才凝聚人心、涵養情感,才使中國鄉土穩固恒常。喬葉和付秀瑩在《寶水》和《野望》中,都將鄉村作為敘述的主體,活躍傳統文化的基因,運用貼近土地的語言,以地方色彩、民俗畫卷、鄉村新顏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的守常與新變,建構了新鄉土小說的文學形態,耐心地完成了當代作家書寫鄉土中國新故事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