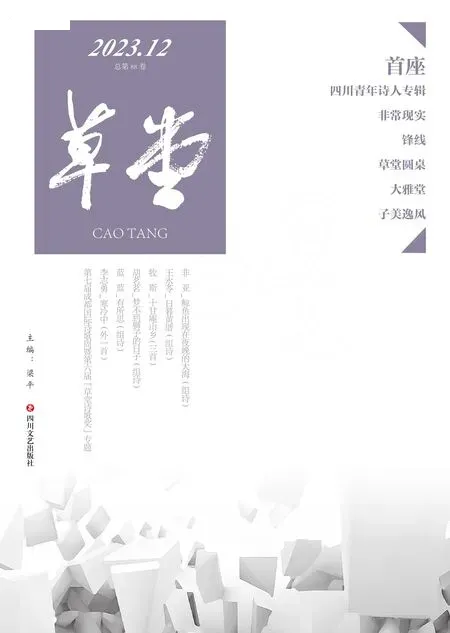緘默的愉悅
朵 漁
緘默的愉悅,就是從震耳欲聾的現場抽身出來,緊閉嘴巴,但有一種戲劇式的內心獨白。緘默有一雙敏感的耳朵和一個微微上揚的譏誚的嘴巴。緘默者帶著對外界深深的失望,降低體溫,如一條冬眠的蛇。只有體溫低于周圍環境才能將內心的火焰慢慢熄滅,以便在普遍的狂熱中保持一種旁觀者的心安理得。緘默是關上院門不再與鄰里來往,不再與人同呼吸共命運,獨自建立一個人的城邦,其中的快感不足與外人道也。
我們現在不缺會說話的嘴巴,所有的嘴巴都在言說——科技也給每張嘴巴都配上了民主的裝備。言說的嘴巴,包括震耳欲聾的腹誹,都在向著一個空無的耳朵訴說——但無人聽。言說者自己漸漸擁有了一雙幻聽的耳朵,自我之耳——它只能聽懂繭房里的甜言蜜語。如果沒有傾聽的耳朵,言說的意義又是什么?也許只是參與一場公共戲劇。朝向空無的言說帶來一種成功的眩暈效應,仿佛在一個龐大的劇場中,沒有觀眾,所有人都涌上了舞臺,每個人都言說著自己的臺詞——公共的、私語的、腹誹的——既不去傾聽他人的言說,也沒有現場的耳朵。仿佛言說就是這場戲劇的必要情節,無關觀眾,沒有導演。
此時,詩人退場了,讓出了舞臺的一角。詩人閉上了嘴巴,以便讓世界安靜一點。詩人閉上了嘴巴,卻無法停息內心的獨白——這無法停息的聲音,正是詩。詩人緊閉嘴巴,嘴角卻流露出難以掩飾的悲哀。悲哀的表情最能與緘默相合,大悲讓緘默者的嘴唇閉得更緊。緘默仿佛一個偉大的深淵,可以盛下一個悲哀之海。這緘默里有一個風平浪靜的表面,和一個浪濤暗涌的底里。這緘默之淵的底部是一個敞開的傷口,它可以盛得下一切悲哀。
我常在這種緘默的背景里構想藍藍的詩人形象。 她把自己的位置騰空,撤出人群、劇場、主席臺,撤出市場、街巷和客廳,回到一個人黑暗的房間,拉上窗簾,此刻,一個詩人的內心獨白和著肖斯塔科維奇的旋律響起。她像尼采教授那樣跳起濕婆之舞,雙手不由自主地做起了指揮。她指揮著內心的旋律漸漸響起—— 一首詩也在黑暗中被她寫下。
她有時像祖母般身材龐大的阿赫馬托娃,當她從探視的隊列里抽身回來,從一張包裹著魚的報紙中看到自己的厄運已定,此時,她的緘默之唇微微顫抖起來—— 一首偉大的詩篇在命運中降臨。
她有時像熱烈而又脆弱的茨維塔耶娃,當她從一場失望的愛的歷險中回過神來,形銷骨立,但不再尖叫,不再寄希望于虛幻的愛,她從敞開的傷口中剝開自身的珍珠,一首詩代替了她最后的哭泣。
緘默者從未真正放棄說,或者說緘默者說得更多,她只是說與自己聽,有一雙能夠傾聽自己內心言說的耳朵。當她開口說話,聲音刺耳,她知道那不是詩。當她從緊閉的雙唇中發出聲音,那才是詩,仿佛從未說出,但早已被自己聽到。至于他人是否聽到,這關詩和詩人何事?他人又是誰?他人就是無人,詩的讀者也是無人。詩是如石頭般的存在之物,有誰去讀一塊石頭嗎?陽明先生讀竹,可曾讀出個所以然?他最終悟出世界之存在如那巖中花樹,獨自明滅。
從這里,我開始閱讀藍藍的《有所思1》,因為我覺得她這首詩從一開始就省略了我上面所寫的那些話。“但那不一樣的是”,開頭就是一個“但”,一個緘默者吞下了“但”之前的所有鋪墊。“但”之后,詩人要開口說話了。她首先說出的是一個生存真相:“生活在水底的人”,為何要去水底生活?也許是緘默者的自我撤離或隱藏,水底就是一個緘默之淵。“應該浮上來”,為什么?因為要“換氣”,要讓自己重新沉浸于生活的表面。我們是否會疑惑于生活在水底的人為何長不出自己的鰭?為何要浮出水面換氣?這是詩人的宿命之所在,還是歷代士大夫那種“處江湖之遠”的天命之所寄?換氣,呼吸,繼續相信愛,這一個個命令式,仿佛換氣般的急迫,不言自明的真理。“即使是”在波浪上種稻子,在陽光的影子里畫草圖——無論現實如何荒誕,都不能擊破詩人那使命的夢想,不容置疑的夢想,哪怕秉承一種注定要失敗的命運。換氣,但不是吐泡泡,說廢話。“哪怕被迫待在沉船里”,“哪怕”其實已經很可怕,處處可怕,但這個詞被詩人轉換成一個輕盈的轉折連詞,一切“怕”都全然不顧了。“被迫”,事實上,我們可以想象沉船的事實嗎?有多少命運的小舟在時代風浪中沉沒?這些皆不堪講,詩人也用沉默留白。總之,還是要“說”,“用各種方式說話”。是命運,還是責任?這個命令式無疑來自詩的使命,是詩命令詩人:說。如何說?“用各種方式說”。這里面既有說的急迫,也有說的技藝——詩的偉大技藝。你可以獨自發明新語言,也可以改造舊文明,“新的拼音,新的蘇美爾語,新的甲骨文”,詩的秘密心臟可以盛納這一切。
詩的技藝是否會退化為一種“技藝之癮”?斷然不會,因為還有“五億萬噸黑暗的壓力”,這是詩的壓艙之石,既來自外部,也已被內化為責任。退一步說,如果你感受不到這“黑暗的壓力”,“或者至少”,詩人給出了最后的選擇——“或者至少,抱緊內心的傷口,/在沉默里分泌你幽亮的珍珠”。“或者”是一種選擇,“至少”是一個底線。“傷口”是詩人的天賦,詩人就是以他赤裸的心臟和黏液質的觸須面對世界的;“傷口”是武器,也是最后的庇護所。內心沒有傷口的詩人,在厄運面前將無路可退,無處可逃。但“傷口”并非一個悲哀的舒適區,并非沉默之淵,而是一個子宮、一個港口、一片田地。在那里,你可以獨自孕育“你幽亮的珍珠”。這最后的悲哀的果實,也許是塵世最終的救贖。
在這里出現了一個“你”——“你幽亮的珍珠”,說明詩人寫到了這里,內心終于出現了一個對話者“你”,是“我和你”在這首詩中對話。這是一種對孤獨共同體的召喚,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是熟人,也是陌生人。這首詩因此并不渴望讀者,因為一切交流已在詩中獨自完成,“你”就是我唯一的讀者和對話者,“你”心知了,“我”便肚明了。
事實上,這首詩的題目《有所思1》就已經點明了,它首先是“我和我”的內心獨白。“有所思,在遠道”,一種遙遠的亙古的呼應,時空更拉深了孤獨感。“思”即不言,或緘默之言,內心轟鳴著一種只有自己能夠聽懂的聲音。這種緘默的愉悅會漸變為詩人的舒適區,孤獨漸變為孤立,詩的變異也由此而來。詩人任何時候都需要警惕舒適區,包括孤獨的舒適區。布考斯基說他“不以孤獨為榮,但以此維生”,此言甚佳。因此,詩人在最后邀來一個“你”與“我”對話,這也是一種向他者的開敞。
當詩人告別水底的生活,重新回到世界上,又該如何自處?或者說,又該以什么作為生命的錨定之物?“每天臨近黃昏/在附近的森林公園奔走。//高大的楊樹和矮一點的柳樹、槐樹/以及果子掉落在地上的海棠、黑棗/被游人摘光了的山楂、柿子——//在秋風中搖曳葉子,迎著陽光/低處是大片的野蘆葦、矢車菊/紫色的桔梗花,無名的野草鋪展向遠處”(《有所思2》)。詩人給出的答案是:接近自然,接近物,哪怕只是接近那些美好的名字——柳樹、槐樹、黑棗、海棠、山楂、柿子、野蘆葦、矢車菊、桔梗花、無名的野草和陽光。這些現實之物,這些美好的名字,皆可安頓“我”的痛苦和疑惑。這些現實不虛的力量,讓一切愛和期許都擁有了重力。“寫詩也是這樣——/屏住呼吸,傾聽萬物的窸窣”(《深夜來客》)。但畢竟詩人的天性是“有所思,在遠道”,這些美好之物只是短暫的安慰和駐留,我的心最終還是要“朝著特洛伊的方向——”。
遠和近,現實與虛無,緘默與言說,讓詩人永遠無法擺脫內心的交戰,只能在“痛切的淚水中盤作一團”(勒內·夏爾語)。這千古之惑,遠大于現實中的“刀與書”之惑,或“敘拉古之惑”:“人在痛苦中一把抓住的語言/卻在謊言里喪失了”,“敘拉古雄偉的城門日夜洞開,/進出著眾多精明和蠢笨的天才”(《敘拉古之惑》)!現實之惑尚可言說,尚可批判,內心之惑最難將息。它是“我和我”的不斷反詰與確認,是“我和你”的無窮大(“我和你”之辨即存在之辨),更是“我和他”的相互映照。在《深夜來客》中,便出現了一個不安的陌生人:“他”。“他”既是一個陌生的他者,也可能是“我”的對立面:“而我從不害怕/面對和我一樣的人”。更現實一些講,“他”也可能就是弗羅斯特所面對的“林中岔路”——最終“他”選擇了做物欲之賊,得到了他想要的紙幣,而“我”得到了詩。但這是可以選擇的嗎?也許命運就是如此,你根本就別無選擇。“也許多少年后在某個地方,/我將輕聲嘆息把往事回顧,/一片樹林里分出兩條路,/而我選了人跡更少的一條,/因此走出了這迥異的旅途”(弗羅斯特《未選擇的路》,顧子欣譯)。弗羅斯特對自己的人生選擇感嘆再三,最終認同了詩人的宿命。藍藍則向那翻身走向大街的陌生人,致以詩的美好祝福:
——祝你春節快樂,陌生人
愿你走上寂靜的大街時
使你高興的不是那沓薄薄的紙幣
而是城市停下的渦輪機,是變暖的夜風
槐樹,鄉間土路的車轍
以及掛在瓦松上破曉時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