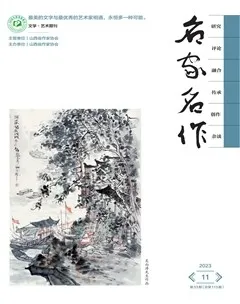論俞振飛的昆曲藝術對李漁“登場之道”的繼承和發展
宋心媛
李漁(1611—1680),字謫凡,號天徒。后改名漁,號笠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學家、戲劇作家、戲劇理論家。其著作《閑情偶寄》中的《詞曲部》和《演習部》講述的“登場之道”,關于表演和編導的一系列經驗總結不僅滋養了清代以來的劇作家和戲劇表演藝人,而且他在戲劇舞臺上的多重身份啟迪了后輩戲曲人對于戲劇的多樣性的探索和實踐。俞振飛(1902—1993),當代杰出的京昆藝術大師,在昆劇表演上轉益多師、博采眾長;在書法、繪畫、詩詞等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除過和程硯秋、梅蘭芳等京昆藝術大師合作以外,俞振飛有過在暨南大學教學的相關經歷,同時潛心將自己在不同階段表演不同劇目的舞臺經驗和編劇經驗整理成文字。這些文字是俞振飛在無數次的舞臺實踐當中提煉、深化和總結出來的,是昆劇藝術不可多得的一筆財富。
目前,學界對李漁和俞振飛兩位戲劇大師都有相當的研究。對李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閑情偶寄》戲劇理論、李漁本人的創作以及演劇實踐等,很少有人注意到李漁的戲劇理論對后代昆劇表演藝術的指導性意義,并進行詳細的對比分析;對于俞振飛的研究集中在昆劇表演方面,對其吸納前輩藝人的演藝經驗的總結較少。本文將從“曲唱”“編導”“情感格調”等方面分析俞振飛對李漁“登場之道”的繼承和發展。
一、俞振飛對李漁“曲唱”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昆曲的歌唱藝術在昆劇表演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李漁在《演習部·授曲第三》中談到了演員應當如何唱曲的問題。首先,演唱者需要解明曲意、了解曲情(即曲中的情節)。“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中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意之所在,則唱出口時,儼然此種神情,問者是問,答者是答,悲者黯然魂銷而不致反有喜色,歡者怡然自得而不見稍有瘁容。且其聲音齒頰之間,各種俱有分別,此所謂曲情是也。”在李漁的觀念中,“曲情”包含唱腔曲調之情和戲劇情節的雙重寓意,要求演唱者必須“得其意而后唱”,在演唱時專注于曲情的表達,“務求酷肖”以期達到“感人心、動人神”的效果。在昆劇舞臺上,即便實際演出時改編本和折子戲居多,演員也應從完整的文本入手設身處地地考察人物在特定時空的處境和心情,并且要將自己的生命體驗也投入其中,這樣才不至于“脫離人物”。戲劇本身就是一種生命活動,是人類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唱曲者力圖做到“曲盡人情”。
其次,“調熟字音”和“字忌模糊”指出了演員在表演時發聲吐字的技巧。李漁提出了“教曲必須審音”。在注重曲情表達的同時,也同樣注重演唱時字音的清晰和字意的明確,要求演唱者掌握“調平仄、辨陰陽”,曲文的每個字都要注意“出口”“收音”“余音”,認清唱腔中每一個字的“頭、腹、尾”,力求歸韻收音清晰、準確。演唱者須凈其齒頰,學習規范的咬字方法,做到“字字分明”;在音正聲純之后,再進行唱腔和板式、節奏、氣息等方面的訓練和加工,這是一個需要不斷積累、長期訓練的過程。最后將情、字、演三者相相合,形成一個精細講究的曲唱體系,并根據具體的情節、人物加以改造和潤色。在后世的舞臺實踐當中,曲唱的精細度和靈活度都有很大的提高,對于曲唱者的基本要求始終不離李漁所指。
再次,我國戲曲發源于民間,在形成和演變的過程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藝術風格,演員演唱昆曲時難免受到方言的影響。李漁在《演習部·脫套第五》中對戲劇表演中方言的運用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即作方言,亦隨地轉。”即方言的運用必須注意到受眾群體的地方性,建立在觀眾理解和接受的基礎上為塑造人物性格服務。我國戲曲演唱行當分明,各個行當分工明確,且在演唱方式和表演規范上都有各自的特點。李漁總結出了曲唱方面的普適性要求,并且提出了從曲情出發的基本立足點,其曲唱理論大多是各個行當普遍適用的綱領性要訣。對于各個行當的具體要求和規范沒有進行更精細的論述,只是用“曲盡人情”中的“人情”指出了行當塑造和人物表現的基本準則,還需后人在實踐的過程中加以補充和細化。
和李漁的曲唱理論相比,俞振飛對于曲唱理論的梳理更具系統性,且專精于昆曲巾生行當的曲唱方法,形成了鮮明的風格,實踐性高、實用性強。俞振飛的父親俞粟廬是清末著名的清曲家,昆曲正宗“葉派唱口”的傳人,有著“江南曲圣”的美譽。俞振飛以其父“字、音、氣、節”理論的闡釋為核心,在融匯傳統曲論精華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舞臺經驗,將“字、音、氣、節”理論具體化。所謂“字”,就是要講究四聲、陰陽、出字、收尾、雙聲疊韻等;所謂“音”,是指發聲部位、音色、音量等;所謂“氣”,就是運用丹田來送氣、呼吸以及氣口之間的轉換;所謂“節”,指的是節奏的快慢、松緊以及各種定腔的規格等。這一點在俞振飛的《習曲要解》中已經有了系統的總結和闡述。俞振飛所說的唱曲“講究”,即咬字、發音、運氣、行腔等技巧必須依合法度。他進一步提到了如何“適度”把握唱曲的法度問題:如果“不講究”,就會在演唱過程中出現字音模糊、荒腔走板等問題,曲唱的失色勢必影響舞臺形象的呈現,演出效果也會大打折扣;如果“太講究”,則成了為咬字而咬字、為做腔而做腔,過分強調出字和歸韻,使字音不夠完整連貫,過分強調運腔和轉喉等技巧性的方法,使昆曲腔調不夠圓和流轉而顯得矯揉造作。與李漁的“曲情”觀相似,俞振飛認為習曲的要點是“有情”——所有的演唱經驗和曲唱技巧都是為了塑造舞臺人物服務的,任何時候都不能脫離具體的人物進行沒有根據的創造和發揮。唱曲應該營造特殊的戲劇化的語境以及各種貼合人物的復雜感情,是對于書面描寫人物的再一次開掘。
在方言土語對于昆曲曲唱的影響方面,俞振飛同樣也有所承襲。昆曲演唱總體秉持中州韻,具有部分吳地語音特征,演唱南北曲時字音有所差異。他說:“昆劇和京劇的唱、念,用的都是中州韻。”且重視演唱音韻的同時,應該強調對字音的規范,使昆山腔的演唱有章可循;摒除土音,使昆山腔演唱語音具有一定的通適性,能夠走出地域聲腔因方言之間的障礙所產生的流播限制,能夠在更廣的地域有更豐富的受眾群體。這一點同樣繼承了李漁的觀點,從觀眾的接受視角出發,并且和戲曲延續和發展的內在規律相吻合。
二、俞振飛對李漁“編導”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在選劇方面,一個好的劇本在“結構”“詞采”“音律”“格局”等方面都有細致的講究。部分昆曲劇本直接來源于《六十種曲》或其他明清傳奇作品,多為長篇巨著。隨著唱詞節奏的放慢以及表演藝術的日益細膩,演出時長過長,需要去蕪存菁,選取其中一些精彩的折子戲進行演出。“縮長為短”改變了昆山腔傳奇劇本的形式。劇本是戲劇舞臺上各個角色一同搬演故事的底本,是由創作者產生、由導演和演員進行二次加工而完成的。而在舞臺上搬演的劇本沒有固定的成熟形態,一個幾近完美的劇本是在舞臺演出的實踐中逐步改進下漸趨完善的。劇本的靈活性和可變性也對導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演習部》中的《選劇第一》《變調第二》闡述了導演對劇本“二次加工”的方法,使“案頭文字”變成“場上之曲”;《授曲第三》《教白第四》談如何教育演員和指導排戲;《脫套第五》涉及的服裝、伴奏等許多問題,也就是除了劇本和演員表演之外對于舞美、音樂、燈光、道具以及服裝等一系列因素的有機組合。新時代的昆劇藝人和文人的聯系十分緊密,同時自身也注重文化素養的提高,在某種程度上使導演、演員二者的身份合二為一。即便昆劇演員沒有完全擔綱導演這一職務,演員與導演對于表演形式、舞臺呈現等方面的交流也是十分緊密的,團隊分工的精細化促進了演員從更多角度進行思考和再創作。
俞振飛參與了昆劇《墻頭馬上》編、導、演的全過程,新的劇本是依照元雜劇《墻頭馬上》改編的。原故事脫胎于白居易的樂府詩《井底引銀瓶》,元雜劇拋棄了樂府詩“止淫奔”的教化作用,將原本因為頑固的封建制度釀成的悲劇改編為諷刺封建禮教的喜劇劇目,正面肯定了男女主人公對于真情的追求和對禮法的反抗。昆劇《墻頭馬上》的劇本經過演員、導演、編劇等多次協商修改,成為1959 年的演出本。俞振飛認為人物是戲劇表演的核心,所有的情節關目都必須在塑造裴少俊和李倩君兩個正面、積極的人物形象的過程中完成。在實際編排、導演的過程中,一開始為了加強這出戲的喜劇效果,在劇本中加入了很多“插科打諢”的部分,后來發現并不恰當。《閑情偶寄·詞曲部下·科諢第五》:“若是,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于此。”戲曲中的科諢必須是具有審美意味的。想要“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就應“全在此處留神”。如何加工形成適當的對白、科諢,就必須先做好戲曲人物的定位。同時“戒淫褻”“忌俗惡”也是昆劇表演中需要遵循的,要避免過分追求喜劇效果而使戲劇趨于庸俗下流。俞振飛認為,不能夠把裴少俊定位成風流浪子、輕薄兒郎,而是應該將其塑造成一個在封建家庭中成長起來、長期受到思想上的約束和禁錮,但不失對于真善美的追求的本性的青年。他對于李倩君的愛情是忠貞篤定的,但是受成長環境的影響養成了懦弱的性格。在找準了人物定位之后,就應該時刻圍繞人物定位反過來剖析劇本,從而設計出與人物形象相貼合的臺步、服裝、砌末等。
《變調第二》中的“變舊成新”,是處理舊劇本或舊的表演形式的一般原則。所謂“仍其體質,變其豐姿”,即不改變原劇文本的主體,以示對原著的基本尊重;而為了適應新的審美需要,對原著的枝節部分可以根據舞臺表演規律進行改動,以收獲更好的表演效果。李漁還提到了對“缺略不全之事,刺謬難解之情”也應該進行適當的修正。
俞振飛吸納了李漁“變舊成新”的觀念,在編導方面最典型的實踐當屬與梅蘭芳合作演出的昆劇《斷橋》。昆劇《斷橋》的原劇本參考清方成培的《雷峰塔傳奇》。這一本的人物情感比較模糊,沒有很鮮明的愛憎,削弱了戲劇沖突的激烈程度。通過對原劇本的分析,俞振飛等人一致認為問題較多地出現在許仙這一人物對待夫妻感情的態度上,表面上是寫佛教戰勝了異端,實際上是封建勢力戰勝了民間的反封建力量。在新觀眾的眼中,原本的許仙已不符合時代對人物的要求。因此,俞振飛將許仙這個人物的心理復雜化、曲折化,有對夫妻關系的留戀、得知真相后的悔恨、對于法海迷惑人心的怨恨,以及難以面對白娘子的羞愧、不敢面對小青的膽怯等,充滿了人情倫理的矛盾沖突,顯得真實而立體。人物的基調確定了,隨之也涉及了形式的問題。《斷橋》經過了幾代人的琢磨,表演技巧完整,藝術程式謹嚴,對于改革應當采取“積極而又審慎、大膽而不魯莽的態度”。在念白和唱詞中突出許仙的動搖,采用一波三折的手法來描寫許仙內心的糾結。在表演身段方面,俞振飛認為將許仙性格懦弱、動搖的一面體現出來的同時應該突出他溫柔多情的一面,這樣對于表現他和白娘子之間的愛情主題會更加有益。論行當,在原劇本中許仙屬于巾生應工,但由于角色的特殊性,他的許多動作都接近窮生。俞振飛等人將這一類動作做了一些調整,大體改為巾生的路子來演。
三、俞振飛對李漁“情感格調”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在情感表達方面,李漁的劇作崇尚“戒諷刺”“重機趣”。所謂“戒諷刺”,即反對不講道德,任意諷刺;“重機趣”則提倡戲劇作品的風趣幽默。李漁希望戲劇作品能夠成為娛樂大眾、放松身心的一種手段。《笠翁傳奇十種》中的大部分作品能夠在迂回曲折的情節中,反映出主人公對于人間真情的大膽向往和勇敢追求,在張揚人性、解放個性方面如同春風化雨一般感染著觀眾。對觀眾來說,情感始終能夠跟隨場上人物起伏跌宕,從中感知到積極振奮的力量,從而獲得良好的戲劇效果。
在俞振飛演出的昆劇劇目中,《玉簪記·琴挑》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玉簪記》是明人高濂所作,故事內容是道姑陳妙常和書生潘必正沖破封建禮教的樊籠,相識相戀并定下終身之事。《琴挑》這一出戲是兩個主要人物的對手戲。劇本中,曲子只有一支【懶畫眉】、一支【朝元歌】以及五支【前腔】組成,白口比較松散。為了突出特定情境下少男少女之間隱秘幽微的情思,除了昆劇的唱腔以外,還需通過念白的語氣、聲調、節奏等方面推敲出不同的處理方式,使各人的“情”得以深化、共同的“情”得以彰顯,帶給觀眾一種朦朧溫馨的氛圍。俞振飛的高足岳美緹在傳承《琴挑》時有言:俞老師那種不刻意表現身段而突出表演人物感情的特點,后來我才漸漸懂得,這是一切手段都融合于藝術之中,這就是“蜜成花不見”的藝術境界。這一突出“情”的過程,也是使這出戲成為詩、情、畫三者結晶的過程。
“情”的抒發和“意”的表現是昆劇舞臺表演藝術的目的,而“情意”的表現又必須借助戲曲演員所掌握的一整套表演程式為手段。而演員必須深入生活、體驗角色,通過醞釀內心感情、增加生活經驗和表演經驗的方式增加自身表演的素材。真正的舞臺表演是演員內心對“情”的感悟、對人物的感悟的外化,不但有人物本身的情感,還有演員自己從角色身上生發的感想和體悟。觀眾所接收到的不僅僅是演員和角色所帶來的情感的交疊,同時在“接受”方面,還存在觀眾在演員表演的過程中所激發的自我感悟。因此,戲劇所表達的情感由于劇本的變化、演員的不同和觀眾的接受度的差異等,同一部戲劇作品可以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情感內涵。一部成熟的戲劇作品,是圍繞著“情”來展開情節、塑造人物、呈現角色的,并將戲劇程式融化在人物表現中,從而達到“曲盡人情”的最終目的。
所謂格調,清代陳以剛等人輯《國朝詩品》中有言“梅村歌行以初唐格調,發杜、韓之沉郁,寫元、白之纏綿,合眾美而成一家”,這里的格調更偏向于“風格”,指的是作品給人的一種整體感受。昆劇表演要保證全劇積極健康的格調。李漁在《閑情偶寄》中強調,在追求戲劇效果的同時,應避免庸俗、下流,或是一味地為了取悅觀眾而有意制造不合情理的情節或者帶有惡趣味的橋段。觀眾可在喜劇情節陶冶情操、愉悅身心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催人向上、提高審美。
昆曲的格調是由戲劇內容、戲劇表現形式以及藝術技巧組合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也可以說是一部成熟的昆劇作品呈現在舞臺上時帶給觀眾健康、高雅的人文情懷。論及格調問題時,俞振飛談到昆曲《奇雙會·寫狀》這出戲一直受觀眾歡迎的原因。首先,《奇雙會》的劇本能夠感動人。這出戲的情節是圍繞冤案展開的,但是它的三折重頭戲著重表現的都是父女、夫妻、姐弟、翁婿之間在平反的過程當中深厚且誠摯的感情,全劇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其次,這出戲用喜劇的手法展開悲劇的敘事,李奇被冤幾乎屈死,事件本身具有很大的悲劇性,但劇作者卻用喜劇的手法來處理其中的“寫狀”“三拉”兩折戲,用微小且精妙的細節,不僅反映了苦盡甘來的新婚夫妻之間的相敬如賓、濃情蜜意,而且也各自彰顯了他們二人獨立、鮮活的人物形象。結構嚴謹、語言精練。插科打諢生動自然,大段念白和與念白相對應的科介都詳盡、到位。因此,這個戲的“格調”也外化成為影響情緒、感化內心的一種強烈共鳴。
戲劇的格調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不能脫離審美范疇。且這種美必須和真結合起來,如身段必須具有真實感,但又不能失去藝術性和技術性。如果過分突出技術,那么真實感就會大打折扣;如果完全符合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舉動,又無法達到舞臺藝術的要求。身段是外表的,需要內在的配合,“欲發之狀,先動其心”,內心表演的過程也就是情緒醞釀的過程。《明心鑒》中有言“要將關目作家常,宛若古人一樣”。除此之外,演員在練功時應時刻思考如何訓練才能達到美的要求,思考程式和人物是否貼合等問題,及時積累藝術經驗,做出藝術總結。
四、結語
李漁和俞振飛兩位大家在戲曲方面造詣精深,除了自身的天賦和各自的從藝經歷之外,昆劇發展的外部環境也促使他們在搬演時不斷思考、總結經驗,以探索舞臺表演的規律。李漁認為戲曲具有教育功能、認知功能和娛樂功能,李漁是奔著廣大民眾喜聞樂見這一目的去探索創作和舞臺的表演規律的。俞振飛所處的時代跨越了昆劇興衰起伏的許多時期,作為非職業演員“下海”成為專門的京昆表演藝人,俞振飛兼有的多重身份讓他能夠打開視野,破除局限。在適應當下社會審美需求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觀眾對戲曲舞臺的感知能力和審美水平,將戲劇藝術推向新的高峰。和李漁致力于著書立說相似,俞振飛在其弟子及其他戲曲史家的協作下,整理完成了《振飛曲譜》《俞振飛藝術論集》《訪歐散記》等著作。他們二人勾連了戲劇創作與表演之間的橋梁,促進戲曲文本和舞臺呈現緊密相連,也讓后世從事戲劇藝術的研究者進行從劇本到舞臺、從編導到表演等多向度的考察,也促進了更多像他們一樣多重身份的戲劇家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