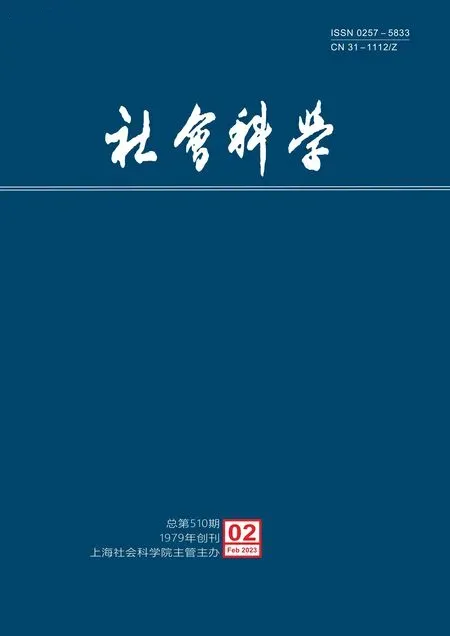“非制”的王言:明代中旨的政治文化考察
唐佳紅
關于明代中旨是否構成一項具有制度特性的體系,是一個頗值得討論的問題。①中旨類文書在明代史料中有許多不同的稱謂。本文在未涉及具體詞義論析的語境中,將此類文書總稱為中旨。另有加引號的 “中旨”一詞系特指。最為學者所注目的明代傳奉官制度,是皇帝以自出政令介入國家人事安排的一種方式,似已成為一套有別于外廷政務運作的獨特體制,②相關研究參見谷光隆:《成化時代の伝奉官について》,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1955 年,《史林》第38 號;土屋悠子:《明 代の太醫院院使とその伝奉授官》,東京:中央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2 年,《人文研紀要》第74 號;方志遠:《“傳奉官” 與明成化時代》,《歷史研究》2007 年第1 期;劉小朦:《皇明異典:明中期傳奉醫官的身份、遷轉與政治文化》,《歷史研究》 2017 年第3 期。其中通常被稱為“內傳”的文書實即中旨。作為一種體現皇權意志的特殊文書政治,舉凡政治、軍事、人事、司法等領域都可以看到中旨參與其間,與官僚組織所據以運轉的制度規定不同,其具有較強的皇權色彩。對明代士大夫而言,“中旨”在多數場景下被視為內閣之權伸張與否的關鍵,中晚明以來,亦成為明代士大夫據以詆訶閣臣、宦官乃至距難皇帝的政治話語與伸張道統的理念工具。
目前對明代中旨問題的討論散見于明代政治文書、中樞體制、政治制度等領域的研究中,論者多將中旨置于君主專制的視野中加以認識,給讀者留下了其作為皇權任意插手政務的工具的粗略印象,未對其作出深入探討。①相關研究參見王其榘:《明代內閣制度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144 頁;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第25 頁;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第84—86 頁; 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第45—46、54 頁;李渡:《明代皇權政治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第129 頁;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年,第93、 277 頁;方志遠:《明代內閣的票擬制度》,《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4 期;趙軼峰:《票擬制度 與明代政治》,《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 年第2 期;王劍:《密疏的非常制參與與明代的皇權決策》,《吉林 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 年第3 期。李福君在所著《明代皇帝文書研究》中辟有一小節“內批與中旨”專論此題,其將中旨視為明代皇帝文書制度的一種“異化”,所論發明有限,對中旨性質的判斷亦未盡善。②李福君:《明代皇帝文書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204—211 頁。王曉明初步梳理了明代中旨的類別、使用等問題,但對史料的處理尚多限于排比,析義亦未詳盡,值得進一步檢討。③王曉明:《明代中旨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近年馬子木注意到中旨之類的名目“由于從未形成制度,明人已不完全清楚此類文書的劃分與適用范圍”,④馬子木:《重塑綱紀:東林與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135 頁。這是一個具有啟發性的認識,然而正因其力求廓正中旨含義,使其未能充分意識到中旨之稱作為明人政治觀念的一種表達,本身就具有主觀性和模糊性。綜合現有研究來看,學者多拘于對中旨不甚精確的“制度性”總結,忽視了中旨實為明人使用的一種政治話語而非文書類型,未能進一步展示其在明代政治中的運行實態。
本文試從前人較少措意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視角出發,跳出以往制度史研究的窠臼,探討“中旨”作為政治話語,其含義在各個群體之間的不同闡釋及其與時政之關系,在明代政治的特殊背景下,更可成為透視明代政治文化中內外公私、祖制觀念以及君臣關系等諸多理念內在張力的窗口。
一、名與實:“中旨”含義析疑
以往學者常將中旨與內批并舉,對其理解受到唐宋之內降、御筆等詔令文書的影響,將明代的中旨與內批視為違反詔書草擬、頒宣程序的“異化”“非制”之旨。李福君對明代中旨的定義具有一定代表性:“中旨和內批指的是奏章不由內閣票擬、詔令不由內閣草擬,徑由內廷批發,且不經六科駁正,直接交付相關部門施行。”⑤李福君:《明代皇帝文書研究》,第204 頁。另如方志遠也認為:“皇帝詔令之草擬、各部門所上奏疏之批答,如不由內閣票 擬,即為中旨、內批。”方志遠:《明代國家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第56 頁。學者對中旨、內批的定義應與明代內閣輔政與秘書的兩重職能相關,⑥例如,譚天星即將內閣的出令權歸納為“票擬批答”和“草擬詔旨”兩項。參見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第43、49 頁。不妨先繞開內閣出現之前明代中樞機構的具體運作情況,先對明中后期內閣以文書參與國家決策的主要方式稍作梳理,以便展開。
按明制,內閣的主要文書職責,其一是奉圣意視草,其稿本經皇帝核準、六科封駁始得發各部院,各衙接旨后還需覆奏方可施行。⑦覆奏是確定于宣德以后的定例,宣德元年詔:“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明宣宗實錄》卷19, 宣德元年七月己亥,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年校印本(下引明代歷朝《實錄》皆為這一版本),第498 頁。 關于明代詔令文書行移的程序規則,參見李福君:《明代皇帝文書研究》,第120—187 頁。所謂中旨,即應由內閣草擬之各類詔誥敕諭,⑧明代詔令的類型,參見陳時龍:《明代詔令的類型及舉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編:《明史研究論叢》 第8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作為“朝廷之命”,是國家頒布政令的最主要形式,明初中央發布的各類重大政治決策,一般均以詔令的形式發出。⑨參見萬明:《明初政治新探——以詔令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編:《明史研究論叢》第9 輯,北 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年。其二,內閣得協助皇帝處理章疏,作為經閣議擬、皇帝核準的對章奏疏議所批復的處理意見,沿唐宋之舊稱為批答,其也具有圣旨王言的權威,在明代的政務運作中一般直稱“旨”。⑩明人范泓云:“判其章奏曰批答,又云內批,本朝稱旨。”范泓輯:《典籍便覽》卷5《政事部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 部第17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第712 頁下欄。今存明人疏鈔,疏后批答起首皆稱圣旨、有旨、旨意等,是符合歷 史實際的。明人最常稱徑出禁中的旨意為“中旨”或“內批”,以名稱而言應即源此。
總之,前人基于對明代中樞文書政治的這種認識,將內批和中旨分別視為不經過內閣票擬、六科抄發而徑由禁中下發執行的詔令或批答,強調其不經內閣議擬、六科抄發的非制度性特點,這種看法或容再議。
首先,明人對于中旨或內批的區分,并無十分嚴格的標準,其內容也遠遠超越詔旨與批答兩種文書形式,試舉數例言之。明代文書體系中存在一些使用相對便捷的詔敕文書,如手詔、手諭、手敕,①關于明代的手敕,可參見馬子木的《明代手敕考》,《歷史檔案》2021 年第4 期。該文認為,“相較于屢為士大夫詬病的內批、 中旨,手敕具有更多的合法性”。但即便是這類制作、頒布程序較為“透明”的旨意文書,間或仍不免受到如內批、中旨一 樣的指責,這更加提醒我們注意中旨內涵的廣泛包容性。多出自御筆,既非批答,又非由詞臣視草之詔令,然亦被稱為“中旨”或“內批”。如正德十三年,蔣冕上疏云:“內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手敕、旨意,撰擬進呈,然后行之于外,此祖宗舊制。近奉手敕……而皆徑自內批,不關內閣,命下之后,諫者盈廷。”②《明武宗實錄》卷164,正德十三年七月甲寅,第3177—3188 頁。蔣冕此言顯然是將手敕視為敕之一種加以申述,實手敕出 自御筆者亦多有之。參見李福君:《明代皇帝文書研究》,第120—127 頁。萬歷十二年玉牒撰成,神宗以手敕褒獎諸臣,王錫爵等復旨云:“特降中旨,加恩大小執事諸臣,以示鄭重。而又徑自下部發行,不關臣等,此無非欲臣等之必受耳。”③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歷起居注》,萬歷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1193 頁。另外,即便在制度上不必經內閣票擬、六科抄發的秘密文書,亦被稱為中旨、內批。試舉一例,嘉靖二年,明世宗強取刑部見監人犯李陽鳳等人至鎮撫司鞫問,刑部尚書林俊疏云:“嘉靖二年閏四月十六日,該校尉陳賢赍捧駕帖,該太監崔文題,為分豁妄捏虛詞陷害良善代伸私忿事奉欽依……”④林俊:《見素集奏議》卷6《企寢內降以正法守疏》,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1 輯第68 冊,合肥:黃山書社2013 年, 第512 頁上欄。駕帖在明初只是某類用于差遣近臣的敕諭的指稱,其制度內涵較為模糊。在明中后期廠衛日益涉入刑事事務以后,始漸專用于錦衣衛奉旨緝捕,然而錦衣衛奉詔參與刑事,在制度上已由祖制確認無需內閣票擬,⑤明后期形成的對駕帖的各類規定,備載于萬歷《明會典》,然明末汪文言以駕帖被逮入詔獄,駕帖“不令閣知,不從閣票”竟 然成為楊漣批判魏忠賢的主要理由之一。參見楊漣:《楊忠烈公文集》卷2《疏· 為逆珰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 無日無天、大負圣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即《二十四大罪疏》),《續修四庫全書》集部 第137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61 頁下欄。這體現了“中旨”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其含義的擴張。成化、弘治時王恕等人以“旨意必經于六科”為名,將六科簽批駕帖制為定例。在此過程中,駕帖是被視為一種不合司法程序的“中旨”來加以制衡的,六科封駁詔旨的職能在此過程中得到了特別強調。⑥參見唐佳紅:《明代駕帖制度考論》,《安徽史學》2022 年第5 期。此道駕帖并不合于弘治以來的慣例,其時刑部及科道對此抗疏尤切,抗論諸臣均稱之為“內降”“中旨”“內批”。⑦參見唐佳紅:《詔法之爭與嘉靖初年政治——以李陽鳳案為中心的考察》,《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 5 期。由以上所舉可知,中旨與內批之稱不僅不限于詔旨或批答,在具體指涉上亦無確切含義,似是以其“非制”性而言對此類旨意的通稱。
再看正式詔書是否也可能被視為“中旨”。嘉靖三年七月,明世宗詔去章圣皇太后“本生”之稱,并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左順門事件爆發,毛紀以邇來一切政事斷自宸衷稱:“如近者大禮之議、平臺召對、司禮傳諭,不知其幾,似乎商確矣,而皆斷自圣心。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何可否之有?至于昨日笞罰廷臣,動至數百,乃祖宗以來所未有者,亦朝廷之大事也,皆出于中批,臣等不得與聞。”⑧毛紀:《辭榮錄》之《再陳懇悃乞允退休以全晚節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59 冊,第483 頁下欄。此疏為《明世宗 實錄》及陳子龍《明經世文編》收入時皆作“朝廷之大事也,皆出于中旨”,或反映了嘉靖以后“中旨”之稱取代“內批”的 趨勢。此處所謂“中批”,顯非所謂不由內閣票擬的奏疏批答,而是代指皇帝對于一切重大政務皆得獨斷的“旨意”,內閣已經無法履行其參預機務的職責。毛紀上疏之前,已頒布的《改稱章圣皇太后為圣母詔》⑨《皇明詔令》卷19《今圣上皇帝》,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布政使司刊本。未經閣議而直敕禮部詔告天下,⑩《明世宗實錄》卷41,嘉靖三年七月乙亥,第1041 頁。是具有立法意義的正式詔書,但仍被楊廷和、毛紀等反對者斥為中旨、內批。可見無論手敕、駕帖還是正式告知天下的詔旨,均可被稱為中旨、內批。據此可以認為,中旨、內批等名目是外延并不明確的籠統“概念”,而非專指批答或詔令。
考察這兩個詞的具體使用語境,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明人意識中內批和中旨在明代文書程序中的“位序”。排除旨意由內閣下行以后的情況,以下兩例展示了旨意在內閣與皇帝(或言宦官)之間往還的過程。弘治八年,大學士徐溥等云:“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于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茍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①《明孝宗實錄》卷107,弘治八年十二月甲寅,第1952 頁。其經內閣接到旨意后,“其合理者”付外,否則封還,但無論何者皆稱“中旨”。正德年間及嘉靖初,內閣楊廷和、費宏、石珤均曾多次封還“御批”,《今獻備遺》在石珤的傳記中載:“上謂珤非通儒,珤又三封內批,忤旨。”②項篤壽:《今獻備遺》卷40《石珤》,《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43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 年,第 213 頁下欄。此所謂“內批”即皇帝“御批”,當是由禁中下發但經內閣會議封還的旨意。在此類旨意的制作與傳達過程中,內閣起到了封駁可否的作用,而所謂中旨實為圣意下達內閣但尚未付外施行之時的泛稱。
王曉明糾駁前人,認為中旨之特征不在于是否經六科封駁,而在于內閣是否參與擬議,③王曉明:《明代中旨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 年,第2 頁。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明人對內閣參與票擬旨意的職權的合理認知。但按照明代的文書程序,六科封駁乃至行政部門會議、覆奏職能的制度化趨勢也很難被忽視,尤其是在明后期科道、六部與內閣鼎立的格局下,閣擬旨意也難以賦予“中旨”以絕對的權威合法性。前文的辨析提示我們,中旨作為一種時人辨別政治決策所由出的“概念”而非可以從制度上予以確認的正式文書,基于某項特定標準來判斷其性質恐未能盡其義。張治安指出,內閣票擬可徑出閣臣意見,也可由皇帝以御帖或口諭的方式指示內閣票擬內容,閣臣對于皇帝旨意,可依閣議選擇執奏封還或接受下發,對于前一種情況,皇帝和內閣均可依己意更改票擬內容,但皇帝對決議能否發部仍擁有最終決定權,其間批答往還可視為一種君臣議政的形式。④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77—98 頁。以此而言,所謂中旨可以視為全然斷自宸衷,主要內容未經內監、閣臣、科臣或任何個人改易、處理或影響,直接付外執行的皇帝“親裁”。學者多注意到明人議論中對中旨內批的否定與批判,將之視為侵奪國家機構權能的“非制”行為,同時內監等以此“中假”謀私之議也史不絕書。但如果圣裁盡善而閣臣無可“匡正”,或在更多時候是內閣為上意所屈,無力盡到糾駁之責,旨意下達部院是否仍會被視為中旨?又或在另一種情況下,居于外廷和皇帝之間的宦官或閣臣得以專權,外廷如何確認所受旨意是中旨還是票擬批答?這是一個極具現實性的問題。
萬歷二十一年,三王并封實起自王錫爵議擬,外廷猶疑之間,或口稱中旨宸斷,或“眾疑閣票”未當,對此莫衷一是。實際上,對內閣而言,批答是徑出圣裁還是由閣臣票擬,抑或君臣合議,多數時候都可以得到確認。⑤此言“多數時候”,蓋因即使是地處密勿的內閣,也因其與皇帝之間仍有宦官遮攔其中,間或也難以判斷旨意究竟是“中旨” 還是“中假”。如天啟四年,外廷頻攻魏忠賢矯擅中旨,葉向高上疏云:“諸所論列,如中旨之頻傳、大臣之擯斥、言官之被 逐、章奏之停留,凡屬此類雖皆引以為圣裁,然九閽沉沉,何處可問?即臣等地近密勿,亦未信其盡出宸斷與否,況外廷遠 隔,能不猜疑。”葉向高:《續綸扉奏草》卷14《論魏忠賢事情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第689 頁下欄。然而對于科道尤其是遠離“密勿禁地”的部院而言,因無論是閣臣票擬還是徑出上意,批答中均題明“旨”,外廷無從判斷此“旨”之所由,因而很難明確決議是出自皇帝、閣臣還是內監,進而區分中旨或閣票。諸如“凡有章奏悉出內批,不知果上皇親批歟?抑奸臣擅權歟”⑥譚希思:《皇明大政纂要》卷24,景泰元年四月條,國家圖書館藏明抄本。“今日諭旨之下輔臣總政之,云此果皇上之所自出乎?抑亦閣中之所票擬乎”⑦錢一本:《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吳亮輯:《萬歷疏鈔》卷4《政本類》,《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8 冊,第243 頁上欄。的言論遍見于史籍。嘉靖時給事中吳時來的言論,表達了外官對中樞決策不透明的疑慮:“自七月以來,批答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于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于外也?又安知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⑧吳時來:《保泰九札疏》,孫旬輯:《皇明疏鈔》卷6《君道六》,《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63 冊,第410 頁上欄。可見,內外的身份差別是制約外廷官員和士論理解中樞決策合理性的關鍵,天啟時李應升的觀點更可說明這一點:“邇來章疏,此亦曰中旨,彼亦曰中旨,群情未暢。臣竊怪之,夫所謂中旨者,必其纖毫無與于外廷而突從內降者也。由今觀之,大有不盡然者。”①李應升:《落落齋遺集》卷2《直剖積疑之根、共消相傾之習、以彰主權、以彰圣德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50 冊, 第84 頁上欄。此番言論的背景是彼時內閣附于魏忠賢,外廷“諸臣之疑,非疑其從內出,而疑其從外入者”。這段話實已否定了凡經內閣議擬的旨意即非中旨的認識。在明后期黨爭加劇的背景下,不同群體對“中旨”爭訟紛紜的現象相當常見,這提示我們中旨與閣票之分在時人眼中并不明確,明代外廷對國家決策形成機制有著一種“他者”認知,即對于內閣參與之批答、詔旨,科部外臣也未必能認清其是否系中旨,或言其主觀上是否視之為中旨。史料中大量對中旨的指摘言論,掩蓋了中旨作為一種以士大夫政治理念為基準的主觀認知而非特定文書形式的特征。
要之,明代的“中旨”在文獻中的含義十分駁雜,并不限于是否經六科駁正,在明代中樞體制與派系背景下,或亦不限于是否經內閣票擬,即對于批或旨之分亦不甚嚴格。在特定的環境中,乃至具有具體指涉的文書如駕帖、口諭、②參見《萬歷邸抄》,萬歷二十六年二月,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 年,第1123 頁。手敕,也被明臣視為中旨。基于上文的討論,可以將明代的中旨以內外兩層的方式定義為:第一,中旨是對皇帝旨意或“觀念”的廣義指稱,無論正式頒宣的詔令還是非正式的文書、口旨、手書,均系“如綸如絲”的王言。在此意義上,中旨體現著皇帝旨意的至高法理權威,這是由君主專制制度本身予以確認的。③王曉明將此一意義上的中旨視為“普遍意義上的中旨”,認為其缺乏作為與閣票相對應的“中旨”的關聯性,不代表其“非 制”,因此未予關注。筆者將會說明,正是由于中旨在明代政治體制中擁有的這種至高的合法性,進而才展現出明中后期士 大夫對中旨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以及隨之而來的被外廷用于對抗內閣、宦官的多重意義。以往學者由于過于關注“中 旨”一詞在明人言論中的負面色彩,因此未能注意到這一點。第二,以內閣機構對中樞決策的參與和外廷(主要是六科)的封駁職能而言,中旨之稱則隱含著未經內閣議擬、六科封駁乃至外廷會議等被視為政治決議所由出的公共程序的承認,在“慎命令”思想的影響下,其“非制度性”是一個隱藏推論。此兩種性質造成了中旨在明代文獻中的復雜含義和為明人所賦予的迥異色彩。
二、內與外:中旨與閣票的再認識
前文言及明人對中旨的復雜認知,很大程度上來自明代內、外廷之分野,如以明人對此類“王言”的稱謂而言,與“中旨”“內批”涵義相同或相近者,又或稱為“內降”“內傳”“內敕”“中批”“內旨”“內帖”等。體其文義,強調旨意所由之為“內”“中”,與“外”相區別,其政治權威源自其切近中宸的特殊地位。即如學者所言:“如手敕、御札、內批、中旨等,從名目來看,均與皇帝個人的關系較為密切。”④馬子木:《重塑綱紀:東林與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135 頁。考察“中旨”與“內批”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出現的頻率,可以使我們更易于把握中旨、票擬與明代中樞權力演變之間的聯系,詳見下表:

表1 “中旨”“內批”在明代歷朝《實錄》中出現的次數及其語境統計表⑤《明實錄》與明代數量龐大的其他各類史料不同,具有即時性(即當時人記當時事而非出于后代追述)的特點,體例、取材 大體一致,且紀事起止幾乎縱貫有明一代,較之其他史料更具有統計意義。表1 以皇帝實錄起止斷限,景泰帝附于英宗,光 宗附于熹宗,《崇禎實錄》紀事止于崇禎五年。
基于明代《實錄》中“中旨”與“內批”二詞使用的語境,本文將二者數據合并后分為“抗疏”與“紀事”再行統計,表中“抗疏”一欄指《實錄》摘述臣僚疏言直接批判“中旨”“內批”的內容,而“紀事”則表示“中旨”“內批”只用于史臣敘述史事,前者表現出時人強烈的政治訴求,后者則可視為《實錄》修撰者暗示旨意徑自獨斷的“春秋筆法”。這兩個指標,可間接反映中旨在時人觀念中的爭議性質與時政形勢。茲請對該表所提供的幾點信息略作闡釋:第一,正統以前,涉及旨意下達,在《實錄》中僅稱“諭”“旨”“詔”“命”等,一般不以“內”“中”稱之。自正統以后,中旨、內批的說法始漸見于《實錄》。正統朝一般被認為是內閣大致形成、票擬制度發軔的時代,蓋自此時宦官復阻間于皇帝與傳統文官之間,中監、內閣與六科、部院的內外分野在體制上成為事實,“中旨”之稱始具與外廷相對的意義。第二,以正嘉為界,在此之前“內批”一詞較“中旨”使用為廣,此后則“中旨”的使用成為“主流”,尤自萬歷以來,“中旨”之稱幾乎完全取代“內批”。對此的解釋是,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主要涉及近幸乞旨傳奉,旨意多出批答;而嘉靖以后朝議寢弛成為常態,皇帝愈依賴以文書與外廷交流,“中旨”一詞以名義而言包容性較廣,更具宸斷意味。以上文我們對中旨的定義,其政治意涵可直接由“中旨”來表達,這導致了晚明人對中旨的歧異理解。第三,與嘉靖以前《實錄》僅以“內批”指示傳奉授官并于其中暗寓褒貶不同,嘉靖以后外廷關于“中旨”的激辯時見于朝堂,反映了晚明權力格局下宦官、內閣、部院、科道數股勢力的政治角力,對“中旨非中旨”的批評,也隱含著晚明人意圖重現明初面賜上裁的努力,對中旨的觀察可以成為理解晚明士大夫“重光祖制”這一思想進路的途徑。
依據張自成將明朝分為宦官與官僚兩套體制的“雙軌制”理論,李伯重將司禮監等皇帝近幸定義為“外朝”之外的“內廷”,①李伯重:《明代后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中華文史論叢》2019 年第1 期。換言之,在他看來“外朝”應是包括內閣在內的所有官僚機構及其組織,也即為學者所習稱的“文官集團”,其說在一定程度上呈現了研究者眼中明代政治體制的顯著特征。但這種籠統劃分在明代復雜的現實政治中是否具有實際意義,則仍須斟酌,尤其是聯想到學士之職最初只是備職為皇帝顧問的近侍人員,②《大明律》對近侍官的定義,清楚表明明初學士、經筵之臣與宦官一樣,均是皇帝邇密近臣而非朝臣:“內官是有職名者,內 使不在內。近侍人員謂給事中、尚寶等官、錦衣衛官校之類、如內閣經筵等親近之臣皆是。”劉惟謙等:《大明律》卷2《職 制· 交結近侍官員》,《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6 冊,第538 頁上欄。使我們更難遽斷內閣的內外歸屬。
不妨看看幾例明代內監、科部、閣臣對“內廷”這一概念的不同使用環境。天啟四年,楊漣上《二十四大罪疏》彈劾閹黨,魏忠賢陰結內閣學士魏廣微、顧秉謙等人鎮壓東林,劉若愚《酌中志》載其時魏忠賢“求助于外廷”。③劉若愚:《酌中志》卷24《黑頭爰立紀略附》,《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1 冊,第243 頁上欄。同書又記:“南樂魏相公(廣微)于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④劉若愚:《酌中志》卷11《外廷線索紀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1 冊,第108 頁下欄。同為魏廣微內閣,前者視為“外廷”而后則非之。對科官而言,魏大中云:“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福、制生殺,一殺王安以立威于內廷,一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等諸臣以立威于外廷。”⑤魏大中:《題為合詞請納憲臣之忠以除逆珰疏》,金日升輯:《頌天臚筆》卷6《贈蔭二》,《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39 冊, 第292 頁上欄。按此疏在魏氏文集中收入,“內廷”“外廷”二詞作“內”“外”。魏大中:《藏密齋集》卷8《奏疏》,沈乃文 主編:《明別集叢刊》第5 輯第21 冊,第92 頁下欄。王安為司禮太監,劉一燝系閣臣,周嘉謨、王紀系吏刑兩部尚書,似在魏大中看來閣部一體均系“外廷”,這也是當時科部府院臣僚的普遍認識。然自魏廣微結于魏忠賢,閣臣被時人詆為“魏家閣老”,⑥吳應箕:《兩朝剝復錄》卷3,天啟六年七月條,《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1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 年,第638 頁上欄。內閣已然不為外廷所接納,胡敬辰稱其時魏忠賢“用內廷攻外廷之異已者,而外廷盛于玄黃”。⑦胡敬辰:《周蓼洲先生傳》,鄭元勛輯:《媚幽閣文娛二集》卷1,《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72 冊,第420 頁下欄。內閣已被視為“內廷”以區別于當時反對閹宦的外廷諸君子。就內閣的特殊地位而言,其與外廷的區別自不待言,即如沈德符所說:“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語。”⑧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7《內閣密揭》,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第198 頁。所謂禁密,即指內閣。可見內、外廷之稱,在明人看來實系一種以關系親疏與派系身份為參照的區分。
事實上,即對閣臣自身而言,其不僅不自視為外廷,更始終維持與“外廷”“卿寺科部”的距離,這方面的記載遍見于當時閣臣文集、起居注等文獻。⑨對于內閣這種超然于內外廷的自我認知,近來已有學者申說,參見李小波:《明代內閣密揭制度考析》,《歷史研究》2021 年 第6 期。王錫爵甚至曾言“閣臣受心膂之托,于外廷疏而于皇上親近者”。①王錫爵:《王文肅公文集》卷32《因事陳言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8 冊,第14 頁上欄。閣臣自視為超越內外廷的群體,一方面是欲維持其公正自處的形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晚明的內外矛盾和門戶畛域下,他們很難以外廷全體代表的身份行動。宦官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出現,使得無論內閣、六部、科道還是府院,均可被視為一體,而由宦官所傳旨意自然可被稱為“中旨”;但如果排除宦官群體,在所謂“外朝”文官內部亦有鮮明的分野,對于部院科道而言,內閣便具有“內朝”的身份,②歷來學者都注意到內閣這種定位模糊、職權矛盾的特點,例如譚天星稱內閣“既備顧問,又預機務,既掌經筵,又主票擬, 集各種職能于一身,給人一種既非顧問型,也非決策型,也非秘書型的感覺,這實際上是內閣角色矛盾發展的反映”。譚天 星:《明代內閣政治》,第74 頁。城地孝更將內閣在前后期的兩種角色稱為“顧問團”和“行政府”,參見城地孝:《長城と 北京の朝政——明代內閣政治の展開》,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社2012 年,第125 頁。部院科道之視內閣,如內閣之視內監。這種較之外廷更加切近皇帝的特殊地位,賦予了內閣超越“內外大小臣工”的權力,換言之,晚明閣臣據以影響政治的密揭言事的職權,本就依賴與“徑出于上裁”的中旨之間的直接交流。③參見王劍:《明代密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陳永福:《萬暦黨爭における密掲制度と情報格差—王 錫爵內閣と東林黨との對立を中心に—》,《中國史學》第22 卷,2012 年。前引沈德符之言,正是為閣臣密疏言事的超然權力而發。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旨”作為一種話語隨這種內外之分而展現出較大的解釋空間。
有學者認為明代文書政治中多道程序“過濾”了皇權意志,④陳時龍:《論明代內閣的票擬——以泰昌、天啟初年的內閣為例》,《史林》2017 年第3 期。而這種過濾,也造成了明人對內、外廷的復雜認知。圍繞皇帝構成的權力差序格局導致了政治信任的分層,亦令外廷無法對內閣持有較深的身份認同,至有恢復國初部院諸臣直接與皇帝面議政事之制,以杜絕內閣與宦官交結者:“自今凡御內朝批本及一切政事,必敕內閣及該科都給事中、該衙門官同至御前面議可否,裁自圣心行之,蓋必有學士則內臣不得以自專,有都給事中則學士內臣不得以聲勢相倚。”⑤《明孝宗實錄》卷11,弘治元年二月乙未朔,第238 頁。外官對所謂中旨、內批權威性的強調,同時也傳達著外朝臣工對內外溝通的孔道是否“壅蔽”的質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內閣的定位是溝通內外的中介,而非傳統意義上的作為外朝之首的“宰相”,即如申時行所言:“臣等因鑒前人覆轍,一應事體,上則稟皇上之獨斷,下則付外廷之公論。”⑥申時行:《召對錄》,萬歷十八年正月甲辰條,《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49 冊,第544 頁下欄。基于這個理由,賀凱甚至稱: “對他們(六部)來說,大學士似乎在外廷是沒有根基的人,只是充當內廷的代表和傳聲筒(Spokesmen)。”參見牟復禮、 崔瑞德主編:《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第1 章《明代政府》(賀凱執筆),張書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第71 頁。在申時行看來,內閣不過是肩負著調燮內外的職責,絕不敢以宰相自視。
天啟元年,御史易應昌疏云:“近日中旨屢宣,群情疑惑,皇上之魁柄未嘗旁屬也,天下人竊竊焉,疑其為旁屬之漸也;閣臣之行徑未嘗中通也,天下人竊竊焉,疑其有中通之息也。愿盡罷中旨,還票擬于閣臣。”⑦《明熹宗實錄》卷5,天啟元年正月丁亥,第243 頁。諸如“旁屬”“旁落”的擔憂,往往被視為中旨的主要弊端,原因在于中旨并非“王言”的直接表達,⑧如鄧繼曾言:“近日中旨,多戾皇言。”鄧繼曾:《為乞審綸音以光圣治事》,張鹵輯:《皇明嘉隆疏抄》卷4《命令》,《四庫 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2 冊,第437 頁下欄。而有可能成為被宦官乃至閣臣利用的“中假”。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正嘉之際,士林盛傳內閣原有內閣得旨及閣臣條旨之底稿曰“絲綸簿”,后為宦官所奪,遂使政權旁落,類似的政治流言在外廷甚囂塵上,但往往使得閣臣深感不知所云。⑨孫繼芳:《磯園稗史》卷3,《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70 冊,第567 頁;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8《內閣· 絲綸簿》, 第222—223 頁。“絲綸”之名,即取《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之意,明人設想的作為條旨原稿的“絲綸簿”,被視為較傳達外廷的中旨更“純粹”的“王言”,可供外廷“逐日對同”下達旨意,實際集中體現著外臣對“王言”為中官旁竊的憂懼。這種謹慎多數時候并非出于對內閣的不信任,其用意或更在約束宦官。⑩在明代的現實政治中,權柄實際旁落的可能性是比較低的,約束宦官的目的仍是勸止皇帝“謀及褻近,徑從內批”,維持文 官與皇帝“共治”的理政格局。參見夏言:《夏桂洲先生文集》卷12《奏疏· 請遵祖訓以端政本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第74 冊,第552 頁下欄。由此,在“面議”不可能恢復的情況下,內閣較之宦官仍更易取信于外廷,訴諸內閣拾遺補闕的職能便成為外廷唯一的選擇。
出于防弊的目的,外廷仍多選擇支持內閣票旨、反對中旨徑下,強調內閣在決策形成機制中的參與,以防止宦官乘隙干政。因有“閣票急于內票”①《明熹宗實錄》卷3,泰昌元年十一月丁亥,第145 頁。“盡罷中旨,還票擬于閣臣”②《明熹宗實錄》卷5,天啟元年正月丁亥,第244 頁。“朝廷大政,必由內閣、六部,而以公論付臺諫,勿令徑從中出”③《明武宗實錄》卷14,正德元年六月乙卯,第418 頁。的諸多言論,乃至稱“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④吳時來:《保泰九札疏》,孫旬輯:《皇明疏鈔》卷6《君道六》,第410 頁上欄。外廷之所以倚重內閣,無非以其可以盡到宰輔之公責。在此,內閣、六部、科道才是“朝廷大政”所以施之于萬民的合法途徑,內閣集議(閣票)則多被視為中旨獲得政治“合法性”的必經程序。外廷科部在支持內閣時,對傳達于近侍的旨意往往采取批判態度,學者將中旨視為皇權擴張、侵奪國家機構權能的“非制”行為,即是基于這個事實。此時外廷與內閣同進退,共同抵抗以內監為代表的近幸勢力,將中旨、內批與票擬對舉,強調其“非制”的負面意義,因此有“所謂中旨者,謂不由臣等票擬,徑從中出”⑤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歷起居注》,萬歷四十四年七月,第3284 頁。之類的說法,這是明代內外廷之分與閣權形成以后士大夫自我意識伸張的結果。
盡管外廷力主內閣擁有輔政之權,然并不意味著他們支持內閣權力的無限制擴張,尤其是閣臣與內監交結,無論在道德還是法理上都無法容于“公論”,即明人所謂“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⑥馮應京:《皇明經世實用編》卷2《乾集二· 祖訓首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67 冊,第19 頁下欄。關于明人對權 臣的認識與闡釋,參見李佳:《明代中樞政體的演進與反思——以“權臣論”為視角》,《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2 期。一旦票擬批答不孚人望,外廷必疑內閣交結或依附內監,可能釀成權臣或權宦之禍,則往往反過來強調中旨的至高權威,借中旨對抗閣臣或宦官,票擬約束中旨的“合法性”也便不復存在了。相應的,中旨則被視為有效對抗權臣的制度依據,強調“宜法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經宸斷”。⑦譚希思:《皇明大政纂要》卷24,景泰元年八月條。隆萬之際張居正當閣,對內交結馮保,對外“自專自擅”,亦多借中旨名義清洗言路,在此時勢下,內閣已無法維持其外廷士大夫代表的身份。隆慶初年,駱問禮疏云:“面奏請旨,則其權常在朝廷;票之內閣,則其權屬之內閣;又且傳遞于宮闈,又將入于宮闈。在內閣治亂半入宮闈,未有不亂者矣,而在內閣者,入宮闈之漸也。”⑧駱問禮:《萬一樓集》卷31《奏議· 論中官為喉論三》,《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174 冊,第303 頁下欄。對于駱問禮而言,無論政權是在內閣還是在傳遞旨意的“宮闈”,都是權柄旁落的現象。因此圣意直達行政部門所經行的程序越簡,則圣意愈不易被旁竊,政權也愈得其正,宦官、內閣在此同被視為政柄旁落、言路壅蔽的肇因。
張居正之后,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等繼任閣臣皆出自張居正舉薦,屢屢受到利用票擬僭竊中旨、侵凌六部的指責,仍不得不借“票擬必經御覽,凡處分必奉宸斷”以洗“專擅部臣”的污名,抵抗言路和清議。⑨《明神宗實錄》卷148,萬歷十二年四月丁未朔,第2752 頁。明代外廷對閣票的肯定,根本出發點不在于肯定“票擬”,而是基于外朝士大夫對內閣匡正君主之失、避免內監專權的信任。對于內閣附于內監的情況,清人崔邁有精辟論述:“內閣之票擬必決于太監之批紅,是內閣且寄權于太監矣。蓋天下雖以宰相待閣臣,而宰相之上又有司禮秉筆太監以承上而臨下,閣臣視以為固然而不怪;沿之既久,而閣臣遂為太監之私人。”⑩崔邁:《尚友堂文集》卷下《明論》,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內監的權力主要來自傳達旨意與批紅,天啟初,阮大鋮等后來被目為閹黨者多以中旨升用,時人對此屢有指摘,閹黨李魯生竟直言:“中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哉?”?吳應箕:《兩朝剝復錄》卷1,天啟四年十二月條,第606 頁上欄。顯然,正是中旨直接源自皇權的事實支撐著他的言論,即使反對中旨最激切的科道官,也只能借“壅蔽”“旁落”來立論,無法否認其作為王言象征的權威。天啟間反對魏忠賢專權的言官,正是以當時內閣依附于魏忠賢,往往強調“中旨”之出于宸斷的“純粹性”,其中不容輔臣、宦官干涉,如有閣臣借票擬之責奪君主本意,則中旨亦“非中旨也”,這正是前引李應升立論的基點。
賀凱指出“中旨”一詞的含義為:“任何形式的聲明都是由皇帝或其內部代理人發起的,而不是皇帝對相關機構提交的建議的回應。”①Charles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an Francisc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89.賀凱對中旨的定義不全然適用于明代的情形,但卻敏銳地指出了中旨有可能來自其“代理人”而非皇帝本人的事實。論者多以為閣票與中旨之間是判然兩分、互不相容的關系,未意識到明代政治觀念中的內外之別,是由內監與內閣、科道、部院之間復雜的權力關系所決定的,是一種隨時政變化的相對觀念與身份調適。晚明君主深居九重,經由宦官傳達旨意,以內閣代行政權,而自嘉靖以來,內閣與宦官交結幾乎成為一種慣例,上下暌隔與政權旁落的憂慮,使得中旨在晚明被賦予有別于明中期的特殊含義。相較于明中期士大夫主要論及中旨與近幸相關的“非制”,因正德、嘉靖以來閣臣與司禮監的合作成為慣例,伴隨著權臣、權宦相繼出現,外廷日益感到內閣已經無法代表外廷與皇帝接觸。言路“搖唇鼓舌”,閣部與科道之爭愈發激烈,部分外廷士大夫轉而維護中旨的權威性與純粹性,強調其是既不經宦官攀求、也不受權臣意志左右的“王言”,這是自萬歷以來中旨之爭的主要論題之一。
三、法祖與法后王:中旨話語與晚明政爭
如前所述,內閣的內外之別不甚清晰,明人對中旨的認識也多隨明代臣僚的政治訴求而變化,是一種基于士大夫集體價值判斷的“可塑性”認識,欲了解這種認識的根源,則必須先理解對中旨“合法”抑或“非制”之判斷的源流所自。
嘉靖二年,世宗命內閣草擬派遣織造局太監前往江南提督織造的敕書,楊廷和等人以其為內批拒絕草詔,世宗遂越過內閣,徑自“御筆親批”差官前去,使內閣大感驚愕:“前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我祖宗朝諸所批答,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有擅自改擬、營求御批以濟其私者,新政以來不曾明正其罪,遂令此輩小人敢于復蹈覆轍,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壞祖宗之法度哉?”②楊廷和:《楊文忠三錄· 題奏后錄》卷2《請停止織造第二疏》,《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5 輯史部第23 冊,重慶:西南師范 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463 頁上欄。類似楊廷和這樣將內閣參預旨意批答視為“祖制”的說法常見于明人議論。值得注意的是,世宗派遣內監前往江南五府監督織造,正是依“成化、弘治年間例”,③《明世宗實錄》卷34,嘉靖二年十二月庚戌,第868 頁。而內閣拒絕草詔的理由則是:“陛下謂織造是累朝事例,臣等考諸洪武、永樂,下迨天順,并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④楊廷和:《楊文忠三錄· 題奏后錄》卷2《請停止織造第二疏》,《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5 輯史部第23 冊,第463 頁上欄。楊廷和等人以為此例并非起自洪武、永樂時代,而是成化、弘治朝的“不美之政”,因此否認其系祖制。如以此種政治溯源來定義合法性,則明臣對票擬批答制度的論述亦不免遇到相同的困境:內閣票擬批答即是祖制否?抑或中旨御批是否也是祖制的規定?在此有必要對這個問題加以檢視。
洪武廢相以后,皇帝親理庶務,處理章奏或出宸斷或與群臣面議處置,殆至宣德以后外廷與皇帝之間日漸暌隔,面議之法不行,大臣參與議政之權則轉為內閣代替皇帝票擬批答。作為處理日常政務最常用的旨意下達方式,中旨在明代文書政治中占據著最主要的地位。成書于嘉靖初期的《翰林記》《殿閣詞林記》等書詳細記載了這段歷史,并且成為明人對明代中樞體制演變的經典敘述。⑤參見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9《傳旨條旨》,《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254 冊,第356 頁下欄。此節在明后 期多為明人援引,體現著時人對中央決策制度演變的普遍認識,也是后來學者討論明代票擬制度的經典文獻。但此類說法 其實在成化、弘治時期已然成為明人對早期章奏批答制度的經典記憶,如弘治元年南京戶部主事盧錦言:“太祖高皇帝每御 大政,悉從府部官面奏區處,又召近臣如學士詹同、給事中吳去疾等相與講明,太宗皇帝能體此意,凡事皆于晚朝以盡委曲, 又命學士胡廣等七人俱入內閣,與論政事。近來批本,學士在閣下者只聞內臣傳說,不得面陳所見,其府部官亦不得面奏區 處,故恩柄不覺下移。”《明孝宗實錄》卷11,弘治元年二月乙未朔,第238 頁。因此,我們看到明人在論及內閣票擬之權時,多引洪武時期面奏取旨之制,因無上下壅蔽之患,亦無皇權旁落之憂,中旨之稱并不具有實際意義。在面議之法廢棄以后,閣議作為一種替代方式出現,其目的在于保證皇帝旨意得以承行。由此,支持票擬者以內閣票擬批答作為防范宦官挾私致使“政柄旁落”的必要程序,而反對內閣者則上追明初“面奏取旨”的美意,強調中旨直達群臣以防“壅蔽”而保持其合法性,這是明人反對內閣權力擴張的祖制依據,因而造成了雙方在制度溯源上對票擬制度合法性產生不同理解。
另一方面,即以中旨全面參與政治,也并非是明中期以來的“不美之政”。以中旨授官為例,王天有、方志遠等人以傳奉授官一詞在《明實錄》中首見于天順八年,①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第78—79 頁;方志遠:《“傳奉官”與明成化時代》,《歷史研究》2007 年第1 期。以之為明代傳奉授官之始。然此已是傳奉授官日漸冗濫,“傳奉官”成為明人所熟知的概念之時,而非中旨升授官員的起點。無論文武職官還是醫戶雜流,憑借特旨傳升躋于朝堂之例在洪武、永樂時期已多有之,②關于傳奉授官在明初的情況,可參見趙晶:《明代傳奉授官制度變遷考論》,《故宮學刊》2019 年第1 期;劉小朦:《皇明異 典:明中期傳奉醫官的身份、遷轉與政治文化》,《歷史研究》2017 年第3 期。宣德時還特別對中旨除授官員加以規范:“今后凡中官傳旨除授官員,不問職之大小、有敕無敕,俱要覆奏明白,然后施行。”③《明宣宗實錄》卷45,宣德三年七月庚申,第1102 頁。此時專門規定中旨升授需經覆奏,當是對宣德元年中旨覆奏例的補充。可見當時傳奉授官已非罕事。在太祖欽定的《諸司職掌》中有諸多條例特注“特旨升授,不拘此限”,可視為中旨授官的祖制依據。與“中旨”之名強調其“非制”的特征不同,“特旨”所以名,蓋以其非常制而特許之,但二者并無本質差異。如正德《明會典》載:“國初選用人才,不拘一途……隨才授用,多出親擢,其后始定銓選之法。”④正德《明會典》卷2《吏部一· 官制· 推升》,東京:汲古書院1989 年,第47 頁下欄。此處對中旨的覆奏規定,當是對宣 德元年中旨覆奏例的強調。中旨授官恰是一種合于“祖宗之法”的行為,而在成化以來視“中旨”“內批”為非法,反而是基于內閣制度化、銓選之法逐漸完善以后的“后王之法”立論。葉向高曾言:“中旨內批,誠非美事,然自臣未入閣時已有,非始自今日。”⑤葉向高:《綸扉奏草》卷20《乞休第三十八疏》,第258 頁上欄。以此而言,中旨不特不始于萬歷,而且是與有明一代相始終的體制性問題。
黃宗羲在討論明代相權之演變時,曾描述閣臣與宦官對“祖宗之法”的不同闡釋與實踐,⑥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置相》,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 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9 頁。恰到好處地揭示了在明代,尤其是在晚明事必法祖的環境下,祖制作為一種“工具性話語”為各方所利用的政治現象。⑦關于對“祖制”的工具化解釋,可參見解揚:《話語與制度:祖制與晚明政治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年,第28—82 頁。前文已經論及,正是基于對“中旨”在制度溯源中的這兩種“錯位理解”,皇帝、宦官、閣臣、科官、部臣各以其所需解釋“中旨”,中旨也成為了各種政治群體角力的重要政治話語。天啟中,魏廣微當閣交結魏忠賢傾軋外廷,使得“部院一空”,楊漣在給浙江巡撫王洽的信中說:“此事固中旨傳奉,而教猱使鬼,實南樂(魏廣微)為政而主此行。”⑧楊漣:《楊忠烈公文集》卷5《書· 又與王蔥岳》,第203 頁上欄。按劉若愚載:“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溫旨, 皆昆山(顧秉謙)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考,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敕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 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考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擬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也。”劉若愚:《酌中志》 卷11《外廷線索紀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1 冊,第109 頁上欄。據此,當時批答、詔誥出自閣臣票擬或視草, 實非一般意義上的“中旨”。當時謝升甚至致書魏廣微勸其“停止中旨”。⑨劉若愚:《酌中志》卷11《外廷線索紀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1 冊,第108 頁下欄。可見,即批答明題“有旨”,內閣也不免因見疑與宦官交結或自逞私意而遭到訾議,被外廷詆為“旁竊中旨”。即如給事中王志道言:“中旨屢諭,群臣猶半疑非上意;票擬已下,輔臣或間推為內批;章奏已抄發,或經月未見題覆;題覆已經歲,或中外未見行事……今廷臣所舌敝而爭者,非中旨哉。”⑩《明熹宗實錄》卷6,天啟元年二月甲寅,第290 頁。明中后期內閣與宦官相倚的趨勢與內閣權威的形成,使得外廷對內閣的憂慮日深,中旨與閣票的討論則成為了朝臣執論的焦點。
部臣借中旨排詆內閣的現象,早在正德間已現其端,其時吏部尚書王瓊與楊廷和互不相能,王瓊以閣權太重,言及國初旨意下達之情云:“(國初)群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旨意批寫本后,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于本面發出之事乎?”?王瓊:《學士官制議》,張瀚輯:《皇明疏議輯略》卷10《史職》,《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71 冊,第693 頁下欄。王瓊此論,與當時局勢密切相關,其時武宗深疾內閣掣肘,王瓊等人逢迎上意,與武宗交往“多取中旨,不關內閣”,?《明史》卷198《王瓊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第5233 頁。因此對楊廷和內閣借票擬干涉外廷政務不以為然。
正嘉以來閣權膨脹,權侵六部,乃至出現了對皇權有所威脅的權臣。然張居正之后,繼任閣臣多循默自守,對內則曲意茍容,即或票擬也多“節奉明旨”,內閣呈現出內轉的趨向,難以盡到宰輔之責。①晚明內閣權力伸張無過于嘉靖、隆慶及萬歷初年,萬歷十九年趙志皋云:“試觀今日之閣臣,與二十年以前之閣臣,其勢之 輕重何如哉?”因請“以威福歸朝廷,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趙志皋:《內閣奏題稿》卷1《題正人心、定國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3 冊,第642 頁下欄。其所謂“朝廷”,蓋指內閣,彼時較之二十年前即張居正主閣的時代, 其時閣權較隆萬之際自然不逮,但權力仍遠躡乎科部之上。閣權循默的另一面是,內閣對外廷黨爭的卷入日深,閣部分合不定,并與言路對抗,閣臣頻罹權臣之譏。趙南星稱其時“上深居頤養,內外隔絕,內閣為太倉王公錫爵、蘭溪趙公志皋、新建張公位,用人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為江陵之事而欲權歸于己,稍有識者莫不離逖自疏”。②趙南星:《味檗齋文集》卷11《墓志銘·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孫清簡公墓志銘》,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4 輯第29 冊,第291 頁上欄。在晚明內閣與外廷科部的齟齬中,中旨作為政治話語的作用愈加凸顯。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京察前夕,御史史孟麟疏云:“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③史孟麟:《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吳亮輯:《萬歷疏鈔》卷10《言路》,《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8 冊,第 486 頁上欄。其時閣部關系激于門戶之爭,而中旨超越門戶,遂不免成為外廷“與政府相持”的主要話語。萬歷二十五年,葉夢熊、呂坤諸臣因遭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劾舉,被旨解職,科臣劉道亨等人疏論此由大學士張位銜恨呂坤,私下授意戴構陷呂坤,而內閣順勢借中旨擬其革職。④其實在戴士衡疏論呂坤等人之前,呂坤已屢次乞休,并獲準致仕。此事始末可參見解揚:《萬歷封貢之敗與君臣關系的惡 化——以呂坤(1536—1618)萬歷二十五年被迫致仕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09 年第2 期。面對外議洶洶,張位上疏自辯云:“臣思士衡疏中所論有五人焉,當發票之初,臣擬吏部知道,此舊體也。當去當留,銓衡自有定論,臣不能以愛憎而增減一字者也。至于坤疏發票之時,臣擬照舊供職,不待吏部之留而輒留之,此亦優禮大臣之體,宜爾也,臣未嘗有薄于坤也。若夫前疏既已發科,而又復追還不下,后疏閣票擬留,而內批回籍調理,則圣意淵微,非臣所能揣摸;圣心獨斷,非臣所能參預。外廷不知閣事,必有漫謂臣之得以置其力者。”⑤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歷起居注》,萬歷二十五年八月,第1476 頁。神宗不得不出面親承“此系朕心獨斷,難以強留”。⑥南炳文、吳彥玲輯校:《輯校萬歷起居注》,萬歷二十五年八月,第1477 頁。在當時的背景下,張位力圖擴張閣權,與呂坤、孫丕揚諸臣不善,外廷則借票擬出自內閣私意而非上意為由加以抵制,中旨在此處被賦予了一種超越閣議的對政治決策的最終解釋權,成為科道官對抗閣議的重要理據。
應當說,劉道亨懷疑張位借中旨芟夷異黨并非毫無理由。中旨在法理上雖往往與外廷捍格,但在制度上仍舊對朝政事務具有最高解釋力,內閣所擁有的票擬職權為閣臣借中旨之名行伐異之實開了方便之門,萬歷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時吏部尚書孫丕揚在葉向高的支持下參劾御史金明時“倡言要挾,嚇逃考察”,⑦《明神宗實錄》卷481,萬歷三十九年三月乙巳,第9056—9057 頁。金明時隨即以言辭不謹例被旨“冠帶閑住”,⑧《萬歷邸抄》,萬歷三十九年三月,第1829 頁。因孫丕揚題本后明題圣旨處分,刑部主事秦聚奎認為神宗倚信孫丕揚,駁“凡疏論重大事情即取旨”,⑨秦聚奎:《為舍死報國事》,周念祖輯:《萬歷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2,《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35 冊,第252 頁下欄。亦被旨革職。此次京察中,神宗對孫丕揚表現出較大的支持,時人一般不以為處置昆宣黨人的旨意是經首輔葉向高票擬的,當時論者謂其所被嚴旨“皆不由票擬”,以中旨視之。⑩張延登:《內降之旨宜停溯流窮源以補部臣之疏》,周念祖輯:《萬歷辛亥京察記事始末》卷7,《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435 冊,第592 頁上欄。按周念祖所輯《萬歷辛亥京察記事始末》所收錄的奏疏表明,當時為京察中受到貶斥者申辯的言官, 普遍將中旨不謹作為主要的論題。這份奏疏匯編因出于為京察翻案的特殊目的,可能無法反映當時的整體情況。參見黃友灝、 黃澈:《明萬歷朝京察申辯禁令下士大夫鳴冤的新方式——以〈萬歷辛亥京察記事始末〉的成書歷史為例》,《學術研究》2020 年第11 期。但因此也便于觀察中旨作為一種群體話語的使用情況。直到萬歷四十一年十月,兵部主事劉定國參劾吏部尚書趙煥交結內官矯出中旨,斥逐湯兆京、周起元、孫居相等人,吏科給事中張延登借機追論辛亥京察中諸人被旨革職之事,并請“敕諭輔臣查前后明旨果何人所擬”。?張延登:《內降之旨宜停溯流窮源以補部臣之疏》,第592 頁下欄。葉向高為平息外廷科部爭論,親承金明時之去實由其本人“擬以閑住”,“未嘗從中出”,并稱:“即煥之疏,有經臣擬者,有圣裁者,臣以為此皆皇上眷禮大臣之盛心,所當將順,何必執爭?惟是事關政幾,經由六部、九卿而后行者,則無問宮府,無論大小,當盡發臣等擬議,擬議不當,則皇上裁示,容臣等再擬。如仍不當,則言官糾駁,如此則光明正大,人無可疑,揆之政體,似當如此。”①葉向高:《綸扉奏草》卷22《剖明內旨疏》,《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37 冊,第307 頁下欄。葉向高對外臣對中樞決策之爭論的評價,折射出“中旨”“內批”在明代政治文化語境中的復雜面向,這不禁使人想到萬歷十九年錢一本疏論申時行“專權”的言論:“每于嫌怨所在,必以出自圣斷為擬,然則其余之為時行斷,勿問之矣。皇上斷者不能十之一,時行斷者且逾十之九矣。皇上斷謂之圣旨,時行斷亦謂之圣旨,習矣不察,蓋不特權侔陛下,而更過之矣。”②錢一本:《敬陳論相大義以正朝綱疏》,吳亮輯:《萬歷疏鈔》卷4,《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58 冊,第244 頁。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如以黨派身份而言,科官錢一本與閣臣葉向高均被視為東林,然而二人卻因當時身份與立場相異而分別使用了含義相矛盾的“中旨”與“票擬”,這種隨時政形勢而變化的認知使得外廷可借此反對宦官、閣臣,而后者亦得借此凌轢外廷。
晚明的閣部之爭,外廷以吏部卷入最深,③關于晚明吏部與內閣的關系,可參見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第92—114 頁;城井隆志:《萬暦二十年代の吏部と黨爭》, 《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13 卷,福岡:九州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1984 年;趙樹國、閆福新:《閣部制衡:明代吏部侍 郎政治角色演變探析》,《東岳論叢》2020 年第9 期。因吏部歷來被視為六部之首,職掌用人大權,在晚明閣權伸張的背景下,內閣對吏部人事權的侵奪造成了內閣與外廷關系的緊張。陳建述及正統以來閣權膨脹的情形說:“景泰而后,始令吏部會推,而實亦司禮監與內閣陰主其柄。用人之得失,隨監閣之賢否也。”④陳建著,錢茂偉點校:《皇明通紀》卷6,永樂六年四月,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第445 頁。可以說以外廷立場而言,基于內閣與中官、皇帝在政治圈層中的特殊關系,內閣的選任權是在中旨的支持下形成的。⑤皇帝親擢大臣,一般稱為“特簡”或“特旨簡授”,而不以中旨名之。參見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41 頁。這在制 度上也是對太祖祖制的依循。李小波特別指出,“特簡”一詞即指代任命不經廷推徑自上命,參見李小波:《明代會議制度研 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 年,第161 頁。試以閣臣簡用為線索,在內閣與外廷關系的視角下,探討明中旨作為一種話語是如何被使用的。
明代會推制度在成化、弘治時大致形成,但朝廷大員尤其是閣臣仍多由特旨點用,⑥參見張治安:《明代政治制度研究》,第1—39 頁;李小波:《明代會議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 年,第156— 162 頁;郭培貴、鄭欣:《明代閣臣選拔方式的階段特點及其成因與效果》,《文史》2021 年第2 期。這種出于中旨的任命方式,多為閣臣援引古例支持。⑦參見李小波:《明代會議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 年,第160—161 頁。內閣之所以支持“特簡”,而對廷 推不甚熱心,蓋因皇帝特簡亦多征求內閣意見,閣臣得以此推薦自己中意的人選,從而間接掌控中樞人選,謝國楨因此形容 其為閣臣“衣缽相傳”。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第23 頁。迨至嘉靖朝世宗乾綱獨斷,以特旨簡授閣臣成為制度定例,終世宗一朝,閣臣皆出欽點,⑧嘉靖《吏部職掌》載:“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多系特旨簡用。其有命下廷推者,本部請應該與推官赴闕會推。”李默刪定: 《吏部職掌· 文選四· 開設科· 會推大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 冊,第69 頁。此銓選則例雖未否認九卿廷推 的合理性,但據學者統計,萬歷十九年廷推定制化以前,任命閣臣78 次,其出廷推者僅11 次,參見黃友灝:《明萬歷朝閣 臣廷推的定制化及其影響》,《中國史研究》2022 年第3 期。可見此閣臣任命仍裁奪于中旨,這很大程度上是因內閣的特殊 地位使然。對此沈德符稱:“輔臣以中旨入閣,雖先朝皆有之,唯世宗朝為多,而臣下不敢議。”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9《內閣· 太宰推內閣》,第259 頁。《明世宗實錄》卷38,嘉靖三年四月戊戌,第950 頁。倘稍留意前文的統計,便會發現世宗臨御四十五年,其《實錄》中關于中旨的記錄卻不到10 例,反而是使用較正式的“特旨”的頻率超過歷朝,正可見在皇帝攬權意識較強的時代,對中旨的反對聲音因“旁落”之議無從立言,反而漸歸沉寂。
泰昌元年十月,上諭吏部尚書孫如游入閣,引起外廷震動。③《明熹宗實錄》卷2,泰昌元年十月壬戌,第90 頁。時御史左光斗、賈繼春等人相繼言:“孫如游突從內傳,大駭聽聞。輔弼非傳奉之官,臺鼎非夤緣之地,乞收回成命,以塞幸門。”④《明熹宗實錄》卷2,泰昌元年十月乙丑,第101 頁。戶科給事中王繼曾則稱:“祖宗建置閣臣,職專票擬,杜絕內降,以防旁竊。今目以內降為固然也。”⑤《明熹宗實錄》卷8,天啟元年三月戊申,第371 頁。盡管熹宗多次強調孫如游系“出朕親裁”,⑥《明熹宗實錄》卷2,泰昌元年十月乙丑,第101 頁;卷3,泰昌元年十一月庚辰,第136 頁。孫如游仍因無力抵抗清議,于次年屢次乞休而去職。當時輿論之非議孫之入閣,無非因其在立儲、移宮諸事上深得帝心,外廷又詆其入閣非由廷推,疑其攀求內降。以時人而言,皆以為孫如游入閣之議全出中旨,似內閣全然無與,然核諸《泰昌天啟起居注》可知,此議實出于內閣諸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人親自票擬,并專門強調“其前諭札,已經吏部咨行本官,抄傳中外”。⑦南炳文等校注:《校正泰昌天啟起居注》卷2,泰昌元年十月七日、泰昌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 第39—40 頁。科道在此刻意忽略閣票與中旨對舉的含義,將二者的界限模糊化,以外廷立場直視其為“內降”加以批判,以保持外廷對閣臣選任的參與。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事件中,熹宗特旨諭孫如游入閣正是以“累朝簡用閣臣,俱憑宸斷”的祖宗故事,⑧《明實錄附錄·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卷1,天啟元年正月十三日,第14 頁。但此類“先王”祖制,并未取得如萬歷時由文官們確立的“后王”制度那般為士大夫所承認的地位。萬歷四十一年,葉向高曾言:“所謂祖制者,《祖訓》也,《會典》也,累朝之功令也。”⑨葉向高:《綸扉奏草》卷20《請減福藩莊田疏》,第252 頁。迨至天啟三年,工部尚書姚思仁甚至說:“皇上與內外臣工所共守者,《大明會典》一書耳。”⑩《明熹宗實錄》卷30,天啟三年正月辛丑,第1505 頁。寄寓著萬歷以后文臣理想設計的《明會典》被視為君臣共守的新“祖制”。造成這種局面的緣由在于,宣德以后皇帝在現實政治中的缺位,使得明前期“君臣面議”“親賜裁決”行政體制難以為繼,因此,畫一、公開的《明會典》便成為晚明部分士大夫借以伸張“公論”的制度依托,而“中旨”則因多少仍保留著明初行政體制“親裁”的祖制意味而受到另一部分希圖上意者的擁護,這也是晚明政治撕裂的一大誘因。
余 論
關注明代政治文化的學者,對明代政治體制的“雙軌”特性印象深刻,在“以文書治天下”的明代,中旨作為皇帝以文書或非文書的形式下達的政令,是皇權意志影響、支配官僚組織的主要方式。以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的觀點來看,傳統中國的體制是一種融合了韋伯式科層制和君主制的官僚君主制(bureaucratic monarchy),?參見孔飛力:《叫魂:1768 年的中國妖術大恐慌》,陳兼、劉昶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 年。因此論者很容易將明人對中旨的批判視為受到晚明以來伸張的公與私、君主與國體等辯證理論的支持,?相關研究可參見溝口雄三:《中國的公與私》,鄭靜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第5—44 頁;《中國前 近代思想的曲折與展開》,龔賴譯,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1 年,第51—73 頁。其中所體現的是制度理性對行政人格化的抵抗,以及傳統士文化中的“道統”與“政統”的張力。然若細繹明人對“中旨”的使用環境、申論策略和制度溯源,即會發現并不盡然,中旨作為一種“話語”,始終為各個政治群體不同程度地利用以進行政治實踐。
盡管宦官與文臣的權力來源均為皇權,但相對于作為家奴嬖幸的內監,傳統士大夫在人格上相對獨立,他們在認同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系的前提下,同時秉承著“以道事君”的理念進行政治實踐,由此顯示出“中旨政治”與士大夫政治不相容的一面。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皇帝仍舊是明代官僚體制的中心和頂點,明中期以后,皇權的行使日益依賴于層級化的文書行政,中旨仍代表了皇帝對國家政務的最高裁決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閣部還是科道,其對中旨或詆或佞,亦無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上取諸圣裁,下行之群臣,防止政權“旁落”或內外“壅蔽”。這也是明初“面奏取旨”體制成為政治典范的思想基底。從這個角度而言,明代士大夫之拒斥“中旨”,并非純出于道統意識之指導而抗拒皇帝專斷,也是拒斥宦官、內閣等諸多“代言者”橫亙于君臣之間造成的內外懸隔,并且多少寄寓著“得君行道”“君臣一體”的政治理想。尤自嘉靖以來,君主意志的表達意愿有增無減,與之相反的是皇帝視朝日稀,朝參議政體系逐漸崩解,①展龍:《“儀”與“朝”:明代朝參議政及其淪失的歷史考察》,《河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2 年第3 期。反借以宦官、閣臣為中介的中旨、內批指導政治,在公私觀念日漸發皇的晚明,愈加無法取信外廷、統合“公論”。萬歷初,馮琦在給孫湛明的信中說到:“大略今之所苦,在上與下隔絕,而內復有隔;中與外乖離,而外復自離。故上無所施其調停,而下但增其排擊。上安得無輕外廷?外廷之說何從入乎?”②馮琦:《宗伯集》卷81《書牘· 答孫湛明少參》,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4 輯第58 冊,第151 頁上欄。這恰如其分地展現了明朝中樞在重重阻隔之下內外離心的政治現實,且與時政及士大夫理想之間的沖突密切相關。而這種內外懸隔,正是以中旨為中心的文書行政所造成的。
被稱為“王權主義學派”的學者盡管不否認傳統儒家文化中存在制約君權的因素,但傾向于認為古代中國是一個“權力宰制理性”、以王權為中心的權力體系。③葛荃:《權力宰制理性——士人、傳統政治文化與中國社會》,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關于“王權主義學派”(或稱 “劉澤華學派”)的主要思想,可參見李振宏:《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文史哲》2013 年第4 期;《王權主 義歷史觀的有效性及其證成》,《天津社會科學》2015 年第2 期;《在矛盾中陳述歷史:王權主義學派方法論思想研究》,《河 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5 期。對此張分田認為士人限制君主的行動始終以“尊君”為依歸,“無論維護道義的士人與時君、時政有多大沖突,都不具有在理論上否定君主制度的意義”。④張分田:《從民本思想看帝王觀念的文化范式》,《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1 期。這種認識多可見于明后期外廷士大夫言行中。以此而言,似乎可以認為明清之際勃興的激切的反君主專制思想,可能并不能呈現晚明以來政治文化的全部面向,也非晚明政治思想進路的自然延伸。⑤關于晚明政治權威的重建,學者指出:“萬歷年間東林秩序化構想的主張之一,即是皇帝不時臨朝召對,實現‘君臣一體’ 的理想狀態,并在太阿獨持與恭己而治間維持微妙的平衡……東林期望的是對明初面賜裁決體制的回復,思宗意不在此,試 圖調適文書行政與面賜裁決兩種決策機制,建立一套以皇帝本人為中心的皇權運作體系。”參見馬子木:《重塑綱紀:東林 與晚明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 年,第266 頁。這正說明晚明批判“中旨”最力的東林士 大夫所期望的并不是約束皇權,而是期望皇權從禁中“走向前臺”,直接臨朝。“中旨”批判性質在晚明的這種轉變,值得 留意。本文提供的一個解釋是,因常朝議政、君主面決的決策渠道淪失,而監閣體制并不能徹底填補這一權力真空,遂造成中樞權威在中晚明的失落,正統以來形成的“旨由閣票”制度因決策程序的不透明而為外廷所非議,晚明士大夫對國初面賜裁決體制的進向,復展現于對弘治朝孝宗“日勤召對”的追慕,這也是訴諸“祖制”的一種現實訴求,⑥櫻井俊郎提供了一個晚明圍繞常朝與召對問題具體討論的案例,參見櫻井俊郎:《隆慶初年の奏疏問題:視朝· 召対を巡る 議論》,《人文學論集》第21 號,2003 年。其目的在于否定“中旨”體制,實現君臣一體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