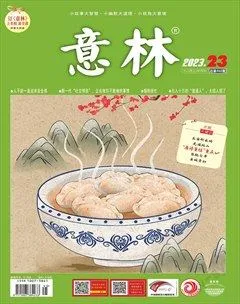沒有姐姐漂亮的我,陷入“容貌自卑”的十二年
silver moonlight
我在醫院醫美科候診時,遇到了一位不太常見的病人——一位大概才上初一的小男孩,坐在不遠處。護士詢問時,我聽到坐在他身旁的母親說:“小孩長青春痘,非要我過來陪他看一看。”護士調侃:“哎喲,這么小就懂得愛美呀?”
小男孩耿直地回答:“我覺得這樣不好看,我就想治好。”底氣十足的聲音響徹走廊。時間一下子將我的記憶拉回到十年前,而他正好成為我的對照組。如果年幼時自己可以再選擇一次,我一定會像這位小男孩,在容貌最自卑焦慮的時刻勇敢地去面對。
我從小就長著連心眉。小時候我的兩條眉毛就長得直順且茂密,但旺盛的毛發不受控制一路蔓延到了眉心,架起一座稀疏的小橋,通向另一側眉毛。
起初我也沒有意識到這種“異于常人”的眉毛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多大影響。但小學一年級入學不久,我就毫不意外地收到“原始人”“大猩猩”這類侮辱性外號,但那時候班里絕大多數同學,都被分到了一個略帶侮辱性的外號。我雖然內心不滿,可是一想到許多同學也在和我承受同樣的外號之苦,再去向老師告狀,只會顯得小題大做或者遭到孤立,我就默默忍下了這份惡意。
直到三年級時,我才真正因為它感受到強烈的“被排斥感”。那天體育課下課后,我身邊兩個玩得最好的死黨,忽然走到我身邊說:“××,你還是把眉心的毛剃一下吧,你這樣長得很奇怪,我們都不好意思跟你走一起。”聽到最好的朋友說這句話時,我當下覺得羞愧不已,也正是因為連她們都這么說,才是最絕望的。
放學回到家后我大哭不已,把自己關進廁所,一邊淚流滿面,一邊拿起媽媽桌面常放的小鑷子,一根一根地把眉心幾簇突兀的眉毛拔掉。拔眉毛的過程非常疼,我能看到鉗出的眉毛底部有粗黑的結實長根,告訴我它們不想走。
那一年,我年僅9歲。
解決了眉毛問題,我的容貌自卑這件事暫時被擱置了一段時間。但另一輪容貌自卑就像水缸里壓不住的水瓢,在一次次議論中還是在我心底生出——因為我的嘴太凸了。

《仙劍奇俠傳1》里劉亦菲的絕美側顏,也被搬到網絡上成為檢驗美女的標準:從鼻尖放一手指,能碰到下巴而不碰到嘴唇,就是頜面標準的完美側臉。那時我們幾個好朋友都做了這個測試,她們都能符合標準,而我的食指首先碰到的,永遠都是嘴唇。直到后來網絡更發達了,我才明白自己得到的是“凸面型頜面+下巴后縮”的顏值土氣大禮包。
初一時我就萌生了正畸的念頭。在我的要求之下媽媽帶我去了她常去的口腔醫院。在經歷拍片、檢查、診斷后,醫生說我確實有些凸嘴,并給出了一套整牙方案,價值4萬元。
聽到要花幾萬元時,媽媽的情緒反應比想象中還要大。
她當場開啟對峙模式,提高了音量對醫生發出N連問:“4萬元啊?這也太多了!”“就不能便宜些嗎?”2011年家里經濟剛剛好轉一些,但4萬元對我家來說還是一筆巨款,媽媽跟我說家里拿不出這筆錢,我自然也無力去堅持,尷尬地與醫生四目相對,最后悻悻地從醫院離開。自此我把精力都用在了學習上,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大學。
到了大學,我的感情之路屢屢不順,我總是有意無意將其歸為自己的顏值問題。但故事到這里,我并沒像童話里的灰姑娘,也沒有女巫,替我來一場舞會前的華麗變身——因為自卑的種子已深深扎根在自己心中,我抑郁的傾向也變得嚴重。我曾多次去過大學的心理咨詢室就診,從咨詢師口中明白自己是那個“配得感”極低的人。“不配”這個信念一直與我心中積極的想法打架,讓我活成了一個擰巴的人。
從小我和姐姐就像是一對相互競爭的選手。我和她的年紀只相差一歲半,有姐妹之名,無姐妹之實。姐姐長相周正,性格外向活潑,一直以來都更得爸媽和親戚朋友喜愛,而我就像姐姐這棵大樹下的陰影,長相怪異,性格內向,我曾試圖用學習成績好來獲取父母關注,但最后發現比起關注我,父母還是更愿意關注姐姐。
我一邊覺得自己努力了也不配得到關愛與重視,一邊又堅定認為父母的差異對待源于自己的外貌性格,既然抓到問題根源就該直擊痛處。觀念兩相對沖,我原地踏步。加上彼時熱播的《甄嬛傳》里,甄嬛那句“以色侍他人,能得幾時好”的金句早已深入人心,我早早把“反容貌焦慮”當成一件時尚單品佩戴在身上,卻忘了具體情況該具體分析。如果容貌自卑就是自己的病因,并且不難解決,那再裝作沒看見、繞過這個原因解決問題時,無異于走進一間房間,而明目張膽地忽視房間里的那頭“大象”。
其實當年如果能早點想明白,成年后對我負責的方式是早點直面內心的矛盾,自己解決、不做過多內耗,人能成長得更快。
后來我在父母的安排下,見過一個相親對象,男生近乎沉默地和我吃過一頓飯后消失無影,這更讓我確信是自己的顏值問題,終于下定決心重新去正畸。而母親見我年紀不小,又經歷相親失敗,終于忍不住直白地說:“你應該早點去箍牙的。”我反駁道:“初中時我就想做,是因為你說太貴才不做的。”
“我哪里說過太貴不做了?我沒說過。”
媽媽幽幽地說出這句話時,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二年前她大聲和醫生對峙的場景,那一記寫著“都怪你”的回旋鏢從那天飛出,在我十幾年后回頭時,以猝不及防的方式正中我心口。年幼時選擇對父母經濟的諒解,卻成了成年后刺痛自己最深的那把刀。
我在當天就迅速掛了醫院口腔科的號安排做正畸,這也是我第一次由心萌生勇氣去面對自己的缺陷。
媽媽的遺忘,與我當年不夠堅定的“自私”,才使得始于童年的容貌自卑拖到成年才解決。成長過程中,我感受到了異樣的相貌給自己帶來的不自信,也共情到了容貌自卑的女性群體,她們心里的悲傷。
女性追求美、不想吃外貌的虧這件事并沒什么錯,錯的是不問前提就粗暴地將這種行為歸類為“服美役”,或者直接將這群女性定義為“助長女性被剝削的幫兇”。當一個社會里任何人都有追求美的自由,也有不迎合美的自由,居于其中的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而我相信,這一天終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