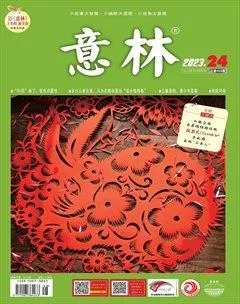挺拔之姿
晉人普遍有好竹之癖,打開魏晉史冊,一群生機勃勃我行我素的人就涌了出來,在山陰道上的竹林深處,放浪形骸,快然自足,得大自在。
竹被稱為四君子之一,它在四君子中是最為清俊的,竹子從筍尖出土就開始了筆直向上的里程,追慕光明,從而略去了許多天下擾攘。竹子作為人格氣節(jié)的象征是有道理的。屈原的《離騷》充滿香草的芳香,可惜,他寫的都是湘沅澤畔之物。他一定離竹林很遠吧,要不,他一定會以孤竹自況,向楚懷王表示自己砥節(jié)立行的井渫之潔和安窮樂志卓然自異于俗常的格調(diào)——以竹子作為喻體,會勝過那些優(yōu)柔的香草,也會使屈原風(fēng)骨遒勁,不至于最終絕望而自沉汨羅。當(dāng)然,竹子在我眼中也有一些孤高兀傲的意味。爭相軒邈,思逐風(fēng)云,都像梁山好漢單干時那般獨標奇崛。相比于王維在夜間的竹林里又是彈琴又是長嘯,弄得一片喧嘩,我則以為竹下獨坐靜聽風(fēng)來會更與竹默契。李白就是這般靜靜地坐在敬亭山上的。竹是清肅之物,鄭板橋曾在《蘭竹石圖》上題寫了“各適其天,各全其性”,認為它是循自然之道的。如果它是一個人,一定是心懷素淡,性喜蕭散,有一些不可犯之色。每一個人的內(nèi)心都會有一個位置來安放一竿竹子,或者一片竹林。所謂風(fēng)骨,就是內(nèi)在的支撐。
一個人愛竹,在他筆下會有哪一些流露呢?真要用兩個字描述,那就是“清”和“簡”了。庾子山在《小園賦》中有不少數(shù)字,不過最讓人欣賞的是“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讀到此處,清出來了,簡也出來了。
我是在農(nóng)耕兄弟的老房舍里大量的竹器中看到竹子之力的,力透到尋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緊緊地箍住了一家人的生活、一個村子的生活,不使失散。漸漸地,在竹林環(huán)繞中的人們也有了堅韌和忍耐。盡管我離開那里很久了,還是固執(zhí)地認為他們就是一片會行走的竹子。
回到城里看到的更多是與園林建筑相匹配的纖纖細竹,優(yōu)雅而有骨感。進入古色古香的庭院,玩味鐘鼎彝器、瓦甓青花,又翻動圖籍殘紙。忽然有一縷淡淡的流逝感浮了上來——日子是越發(fā)小巧婉約起來了。算算此時,是農(nóng)歷的六月七月之交,時晴時雨,山野在潮濕中,無數(shù)的竹鞭在奮力吮吸,竹節(jié)爭先向上,風(fēng)雅鼓蕩,場面奇崛,整座山嶺充盈著大氣與生機,讓熱烈的陽光照徹。
(本文入選2017年高考天津卷,文章有刪減)
朱以撒,現(xiàn)為福建師范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福建省書法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顧問,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任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學(xué)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書法篆刻展覽評委、中國書法蘭亭獎評委、全國書學(xué)研討會評委。2009年被評為“中國書壇年度人物”,2014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評為首批“福建省文化名家”,2022年被福建省政府聘為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意林》:您是先寫書法,后寫文章,寫作對您意味著什么?
朱以撒:1995年我開始寫點散文遣興。此前一直傾心傾力于書法創(chuàng)作與研究。直到這個時候,突然覺得很需要以文學(xué)語言表達個人的感受。這種來自個人的需要成為我寫作的樂趣。既然是個人感受的表達,真實肯定要放在首位。如果一個人持有精湛的文學(xué)技巧,能夠充分地表達,著實可喜,甚至讓人羨慕。如果不能充分表達,過程中打了折扣或者產(chǎn)生偏頗,只要基于真情實感,也甚可自慰。因為技巧可以在長久的磨煉中逐漸遞進、優(yōu)化,而個人感受,如果一開始就沾惹上刻意、矯飾的習(xí)氣,形成慣性,那才是難以捩轉(zhuǎn)的。
《意林》:寫作和書法都貼近學(xué)生,您對此有什么樣的建議?
朱以撒:每一個活動都要設(shè)置一些規(guī)矩,然后依規(guī)矩而行。就像參展,參與展覽就是給自己設(shè)立一個指標,這個指標要是實現(xiàn)了,也算是參與者最大的欣慰。對寫字的人來說,自由程度那么高,可以這么寫,也可以那么寫,全在自己一念間,自適其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