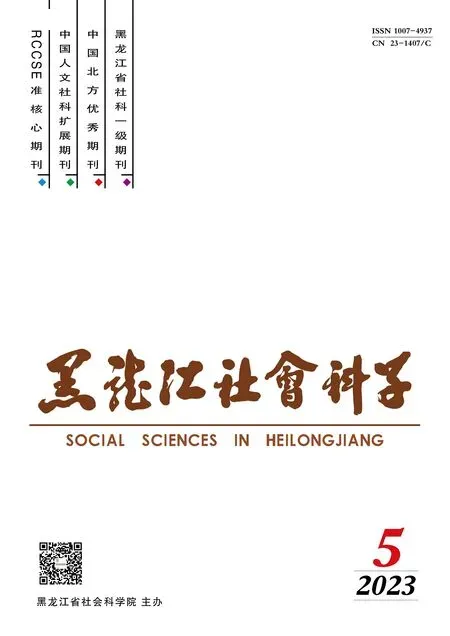新時代網絡輿論生態及其輿情治理
唐魁玉,趙峻宏
(哈爾濱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與法學學院, 哈爾濱 150001)
隨著信息時代的飛速發展,互聯網技術的進步給人類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但它往往也會伴隨著風險一同出現[1]。因此,在當今互聯網技術與人類社會高度同步的情況下,網絡技術的發展與應用成為網絡輿情轉變為社會公共安全事件的潛在根源。人們所面對的網絡輿論生態異常復雜。與此同時,網絡空間也存在著虛假新聞、謠言、網絡暴力,以及網民肆意釋放的極端情緒,而這些情緒成為影響網絡輿論的重大變量。至此,復雜無序的網絡輿論生態逐漸催生出種種“后真相”現象,在網絡空間中人們失去全面真實的判斷力,情緒共鳴成了網絡輿論的主要導向,在“后真相”時代里誰掌握了大眾情緒誰就能成為“事實真相”的言說者,這對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正常輿論的沖擊不可小覷。
當今網絡輿論空間所處的“后真相”時代特征,使得網絡輿論空間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種“價值共識”,以此來減少不良網絡輿情的發生。誠然,網絡輿情中的暴力事件是極端平民化在網絡世界的另一種表現,它看似為大眾發聲、強調人民的價值和理想,實則利用網絡世界中言論自由的開放性、輿論交流匿名化的特點,迅速成為社會輿論的放大器。網絡輿情之所以亂象不止,是因為它本質上存在一定的民粹性,倘若處理得不好,就會導致網絡秩序的無序化。
在“后真相”時代里,人們開始根據自己的立場有選擇性地相信事件的真相或者根本拒絕相信真相。“后真相”現象通過模糊情感與事實真相的邊界使真相異化,從而導致網絡輿論空間無法建立起社會基本共識。極個別人可以輕易利用網民情緒撕裂社會,這無疑加劇了網絡環境的復雜性,給網絡輿情治理帶來了新的課題與挑戰。
本文試圖從“后真相”現象切入,深入剖析互聯網輿論生態中頻繁出現的網絡輿情事件成因,探討“后真相”時代下頻發的網絡輿情亂象給網絡輿論生態帶來的危害,進而有針對性地提出網絡輿情治理的應對之策。只有這樣,才能不斷提高人們辨別與思考公共事件真實性的能力,進而使新時期網絡輿論空間得以良性發展。
一、“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論生成及演化邏輯
(一)何謂“后真相”時代?
“后真相”(post-truth)這一概念早在1992年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被美國學者斯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提出,并用“后真相世界”一詞批判美國政府以操控輿論的方式刻意隱瞞真相,使民眾不能辨別事實真相,生活在不正常的輿論生態中[2]。此后,也有學者運用“后真相”一詞但并未在學界產生較大反響。直到21世紀初,美國傳播學學者拉爾夫·凱伊斯(Ralph Keyes)重新闡釋了“后真相”時代的概念,指出“后真相”是一種模棱兩可的陳述,介于真相與謊言之間,模糊人們情感與事實的邊界,這將成為未來一種全新的真實觀[3]。“后真相”現象相比網絡中單純的虛假編造信息更為復雜,它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并未完全拋棄事實,往往真相被混雜在既不完全客觀也不完全虛構的信息之中,這種似是而非、真假難辨的狀態定義為“第三種陳述”。當今網絡社交平臺中存在著大量的第三種陳述,誠然,如今我們所處的網絡輿論生態可被稱為“后真相”時代。
從結構上分析“后真相”時代的特性,主要可分為兩個方面。首先,互聯網信息膨脹使得人們認知更為多元化,經過“后真相”的粉飾,公共事件的“客觀事實”逐漸被隱藏在背后。如果說公共事件的真相只有一個,民眾在清楚事件真相的前提下進行的自由交流與探討是可以達成意見共識的,與此同時網絡輿論生態也會得以良性發展。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言論自由的失序發展,使得人們在認知多元化的同時變得更為主觀,探討輿論事件更傾向個人主觀性判斷。“客觀事實”與意見共識不再重要,如何在網絡中捍衛自己的判斷成為人們進行輿論交流的首要任務。當真相缺少了唯一性、失去了統一性時,真相也同樣缺少了科學性與準確性[4]。
其次,網絡社交平臺、新媒體的迅猛發展與民眾使用網絡頻率的增加,加速了公共輿論話語權的分化。傳統大眾媒體,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新媒體已經變成重要的輿論“場域”,在其發揮作用的網絡空間中逐漸形成了人人手中都有的“麥克風”、人人都可以擁有話語權的局面。平民大眾與新興媒體成為公共輿論的主流社交媒介,如微博、抖音等新興社交平臺以追求平等、提倡言論自由、去中心化、多元化、匿名屬性等特點迅速成為輿論交流的中心地帶。網絡社交技術的日益發展、輿論社交平臺用戶的增多不僅給網民評價和討論公共事件帶來便捷,更激發了人們的表現欲與表演欲,在此環境下第三種陳述油然而生。因此,可以說放任網絡社交平臺無序發展是“后真相”時代到來的必然結果。
(二)“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論生態邏輯
“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論生態,具有特定的運行及生態邏輯。從宏觀層面上看,“后真相”現象是借助網絡輿論的復雜性,創造民眾情感和道德的共鳴以此凌駕事實真相之上。但有學者認為,倘若“后真相”現象的出現對民眾理解當下網絡輿論環境產生了癥候學意義,其所表現的就不應該只是某一事件及其背后的結果,而必須指認出當今社會的歷史性存在所產生的巨大變化,即“后真相”的本質是后共識[5]。然而,造成“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生態的邏輯混亂必然包括網絡公共性邏輯混亂和價值取向邏輯混亂。
第一,網絡公共性邏輯混亂造成網絡輿論邊界模糊,誘發網絡輿論空間“自由言論”的失控,造成社會對立情緒,使得重建網絡輿論秩序成為重要議題。現今,網絡技術飛速發展,數字通信技術與現實世界高度嵌入網絡輿論之中,這對現實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哈貝馬斯認為,公共輿論是指“公民對社會公共問題進行自由、平等的辯論與交流,并進行理性探討從而達成共識的過程;如果公民沒有批判意識而進行相互交流,即使輿論具有公共潛力也不可能轉化成一種公共輿論,長此以往,網絡輿論領域逐漸成為和公共權力機關直接抗衡的第二場域。”[6]數字通信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可以隨時隨地參與到網絡輿論之中,網絡化的輿論“場域”改變了以往的信息傳播與交流模式,促使網絡媒介的公共性進一步加強。然而,自媒體的興起一定程度上是從精英手中“搶奪”走了輿論話語權,網絡輿論“場域”成為普通網民交流互動的全新場域。網絡的進一步普及增加了網絡輿論的公共性,網民可以“自由”地對公共事件進行隨意評論,為網民提供了大規模交流互動平臺的同時,也時刻考驗著政府網絡治理的水平。
第二,網絡價值取向邏輯的混亂是資本集團合謀技術賦權、社會行動以此曲解價值取向,從而使自然情感被工具化[7]。以往在互聯網Web2.0時代網絡輿論話語掌握在社會精英手中(如網絡新聞、“博客”這種只能看的傳播形式),網民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和內容以及傳播后的影響力非常有限。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Web3.0時代微博、抖音、“微信”等網絡社交平臺以言論自由、去中心化、信息多元化的特點成為公共輿論聚集的主要場所。網民通過發布文字、圖片、視頻的方式參與到公共事件的傳播及討論中,其中不乏一些無責任意識的偏激言論,以及對公共事件斷章取義、虛假編造的失真信息。尤其在后真相時代,人們在網絡輿論空間評論與探討的公共事件很可能一開始就是帶有情緒傾向的信息或已經扭曲事實的虛假信息。一些自媒體為博取眼球吸引流量刻意制造具有爭議、情緒導向強的公共輿論,從而致使網絡輿論環境愈發復雜。人們在網絡社交平臺無法了解公共事件的真實情況,網絡輿論已經不存在通過理性探討以此達成意見共識的過程,人們在復雜的網絡空間中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此時,充斥著極端情緒和意見傾向的網絡輿論變成了“武器”對當事人進行攻擊,導致網絡輿情事件頻發。網絡的力量從虛擬走向現實直接對現實社會造成影響,輿論的失序與網絡價值取向的曲解成為當前網絡輿論的主要問題。事實上,網絡輿論空間經過多年失序性的演化,已逐漸進入到“后真相”時代。
二、網絡輿論中“后真相”的現象化表征
從“后真相”時代形成的主要原因不難看出,網絡世界正處于“后真相”“后秩序”“后共識”的環境下,真相淹沒在無限擴大的言論自由中難以呈現和還原。真相變得不再重要,無邊界的言論自由加速網絡輿論空間失序,人們情緒宣泄大于尋求事件真相,網絡輿論交流難以達成共識,真實不等于真相。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曾指出:“真相的本質就是一種共識,它直接反映事件的因果性與整體性,因此,其正確性在于建立在主觀認知和客觀事實之間,凡是真相必是真實,但當真實的外延大于真相時則不然。”[8]既然真實不等于真相,那么真相的本質又是什么?如果從認識論上看真相其本質就是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主觀與客觀各執一詞的爭論,那么真相就變成了一個偽命題。因此,諸多哲學家通過探討后更傾向于認為真相是對特定事物主客觀的普遍共識,顯然真相是沒有統一標準的,在理論層面也并不牢靠,這樣“后真相”這一真假參半、模糊事實的現象在互聯網世界更容易使網民產生分歧,從而形成輿論漩渦。
(一)網絡輿論情緒先行,引發認同的異化
在一定意義上,“后真相”時代也可以被稱為主觀化時代,真相被弱化、情緒先行成為輿論認同的風向標。網絡輿論生態中民眾面對公共事件的真相是失真的,與此同時網絡空間也逐漸難以達成基本共識。誠然,人們通過數字通訊工具可以隨時隨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這種不加思考與斟酌的評論是極具情緒化和感覺化的。當交流本身的目的不再是探討分析社會事實、真實不再重要、基本共識不復存在,抒發情緒和得到認同便成為人們在網絡輿論空間交流的首要目的。不思考、不聽勸、不理性反而變成了社會事件評論的主要風向。當今網絡空間中人人手中都有“麥克風”,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對公共事件發泄極端情緒言論、散布流言緋聞、編造曲解甚至杜撰事實,從而博取認同、獲得流量成為“后真相”時代的主要特點。誠然,獲取大眾情感認同成為某個社會事件的意見領袖以此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被認同感,這種情感上的“快感”無形中催生了一批“無目的”的民粹主義者。正如學者鄒詩鵬所言:“網絡世界中的‘后真相’時代,這種負面輿論聚集狀態的復雜性與無序性,其本質是網絡民粹主義。”[9]網絡輿論從理性討論進而達成共識變為尋找、聚集相同情緒的主觀認同,尋求真實、判斷對錯、理性批判不再是網絡輿論的基本共識。人們從各執己見互相勸說變為只尋求情緒先行和只追尋主觀認同,這種非理性輿論已然成為網絡空間的主流價值觀。吳曉明教授認為,網絡世界中“后真相”和民粹主義都是時代性的階段產物,它是一種無限制的主觀性,可以理解為“壞的主觀性”,這種錯誤的主觀性隱含在主體性哲學形而上學中,其合乎邏輯是必然的結果[10]。但隨著網絡輿論對現實社會的影響愈發強烈,壞的主觀性往往很容易成為群體性共識。這種認同上的異化往往是對統治階層、精英集團的失望,從而對政府制度產生懷疑,甚至怨恨。個體存在壞的主觀性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微乎其微,但是網絡社交平臺的興起以及民眾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失望,致使網絡空間可以迅速聚集起眾多擁有相同壞的主觀的網民,他們使輿論成為武器,并且使網絡空間淪為輿論的“修羅場”。
(二)網絡言論符號化,造成無邊界的言論自由成為網絡輿情
“后真相”時代失序的自由言論反而使言論愈發不自由,輿論化身為“暴力”的符號從而形成網絡輿情。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曾提出“場域理論”,他認為社會的構成是由各種相互競爭的“場域”構成的,而個人作為影響“場域”形成的主要成分,人的心智構成是呈現為更加具有形成性的“習慣”[11]。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提供的數據:截至2023年3月,我國網民中20歲以下用戶達到2.6億,青少年占全部網絡使用用戶的18.7%[12]。數據表示在“網絡場域”中青少年用戶往往心智尚不成熟、未接受高等教育、情緒波動大,其對“網絡場域”的構成造成直接影響。青少年在網絡空間中花費大量時間所獲取知識的信息來源過于碎片化、多元化,然而青少年缺乏知識體系構建與思維判斷訓練左右了心智構成的“習慣”。盲目的言論自由則成為那些心智尚不成熟、不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少年網民們的武器。只要高喊“要尊重我言論自由的權力”就可以不假思索、不負責任地對公共事件進行過激評論,這種言論往往具有較強的情緒傾向。久而久之網絡空間中出現了“反諷”“整活”“狗頭表情保命”的網絡語言,這種青年化的網絡語言加速了“后真相”現象的發展,直接導致真實信息進一步模棱兩可,促使更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參與到對網絡輿論評論的跟風當中。
在網絡輿論體系中,情感與理性作為左右個人言論導向的理論范式一直被視為相互排斥、相互競爭的關系。勒龐從情感分析的角度指出:人在群體當中個體智力與道德以極快的速度消亡,個人的情感本能交集取代了理性判斷,個體在群體當中會變得異常偏執、盲從、狂躁,本能般地喪失邏輯與判斷能力,只有極端情緒才能使他們產生共鳴[13]。意見領袖們正是利用了網絡社交中群體化特性,高舉言論自由大旗、使用強硬語言輸出極端情緒、絕不訴諸理性。此時,無限制的自由言論已變成網絡輿論中暴力的“符號”,捍衛自由的權力成為非理性與極端言論的保護傘。至此,失序的自由言論成為法不責眾的代名詞,也是網絡世界中大眾默認的共識。哪怕所謂的自由言論是虛假的、具有人身攻擊性的,只要情緒得以發泄人們便不在乎其行為對當事人的傷害。久而久之失序的自由言論成為網絡場域中的“符號暴力”,意指使用者并不想知道自己已經臣屬于符號權力,甚至其行為與使用符號權力者的想法不謀而合,在此功能特性下遭受“符號暴力”的人們毫不知情,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稱之為“溫柔的暴力”[14]。在網絡空間里,互聯網語言無形中構成了“符號暴力”,這種行為是群體合謀參與后賦予的暴力由“網絡場域”機制決定的。即使行為者擁有認知與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要在網絡中交流就會隨波逐流產生網絡暴力。符號暴力是網絡場域中的本能機制,當網絡輿情發生時,每一個參與者在潛移默化之中都對符號暴力機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行為人不會意識到自己參與到了網絡暴力之中,即使意識到了自己可能是施暴者也不會對被施暴者心存愧疚,只會“安慰”自己剛剛的行為是個人自由言論的表達。
無序的自由言論成為符號暴力的代名詞,區別于直白的網絡暴力,自由言論者認為在網絡世界無邊界地發表自己的言論是個人表達自由的權力,肆意地抒發觀點是自由言論權力的表現,即使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也渾然不知。如果說“后真相”時代造就了虛假的真相,那么失序的自由言論則經常呈現為不自知的網絡暴力。倫理學家密爾曾在《論自由》中說明:“一切思想與意指應該被允許自由發表,但不能超出公平討論的界限,需要從方式上有所節制。”[15]如何給言論表達設定出合理的邊界,逐漸成為網絡治理的難題。針對人們在網絡空間中的過度情緒宣泄,如何正確引導網絡輿論及其走向和重建網絡秩序已迫在眉睫。“后真相”時代中的話語表達看似內容更為多元,實則并非如此。而且,毫無邊界和限定的表達也是不可以的。
(三)數字時代技術發展加速社會進程,群體基本共識消亡
數字時代下,數字化技術對社會的加速致使原有傳統共識消亡。網絡空間中,“后真相”時代本質是模糊真相并且難以達成理性共識,那么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是什么呢?歸根結底是技術發展導致的傳統集體共識不再被人們熟知。網絡空間中集體性共識消亡是社會異化的另一種映射。學者拉爾·耶基(Rahel Jaeggi)指出:異化是社會中缺乏關系的關系,異化并不是沒有關系,異化本就是一種關系,是有缺陷的關系[16]。“異化關系”成為現代社會批判理論中傳統共識改變的新形態,“異化關系”是社會加速發展的產物,可理解為一種人與世界之間的冷漠化、沒有回應、本能地不顧及他人以及靜默不理會的關系。“異化關系”直接影響了青少年的價值觀,社會關系的冷漠導致網絡世界傳統共識的崩塌。
當今令諸多學者不能理解的是,在關注網絡輿情問題時原本可以通過基本共識就能避免的輿情事件怎么就突然變成了網絡暴力?直到德國社會學理論家哈特穆特·羅薩通過對社會加速后產生的新異化現象的研究,才解釋了社會基本共識消亡后產生“異化關系”的原因。主要表現為以下幾點:其一,社會加速后人與空間的關系異化,人們無法與所居住、生活的環境建立起熟悉的親密關系(“家”的概念從溫馨的港灣變為物質性極強的社會細胞),這種歸屬感的缺失使空間成為沒有意義且沒有回憶的“沉默空間”;其二,社會加速后人與時間關系的異化,人們習慣了接受碎片化信息,看似獲取的信息更為豐富和多元,實則逐漸喪失了對人生歷程中內在經驗的感知(比如旅游時忙于拍照打卡,照片和紀念品成為記錄時間和回憶的載體,而不是好好享受的美好時間和旅途中的風景);其三,社會加速人與自己的行動關系的異化,人們每天機械式地生活逐漸忘記了什么是自己想做的(即使看似人們自愿做的事情),人們開始忽略自己的想法,自己想做什么變得不再重要,社會想讓你做什么逐漸成為我們的生活準則,我們看似自愿“刷短視頻”、買“快消品”,其實放棄了原本想讀的書,想關心的人[17]。羅薩認為,社會中“新異化”的產生是社會加速破壞了人與自身、人與世界之間原有的共鳴關系,直接造成了人與世界之間冷漠、疏離的異化關系。當今,過快的生活節奏和海量的碎片信息,誘使人們寧愿把所有空閑時間浪費在網絡之中,也不愿意重新關注自己、關注生活。人們迷失在失序的網絡空間變得越發冷漠、越發不愿意思考,迎合多數人、隨波逐流地宣泄情緒成為人們網上沖浪的首要目的。這也是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網絡輿情之中的原因,即使人們知道自己在網絡世界對他人進行了言語施暴也不會有任何負罪感。
社會加速無形之中影響了青少年的價值觀和生活習慣,原本通過周邊熟悉的鄰里親朋就可以建立的基本共識不復存在。共識的缺失使人們越來越難得到培養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事件真相的能力。總之,社會基本共識的缺失是造成“后真相”現象復雜的原因之一。人們正在經歷社會對個人思維意志的洗腦,我想要什么、想成為怎樣的人,生活的意義是什么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社會想讓你成為什么樣的人、資本需要你成為什么樣的人。
三、“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情治理路徑
“后真相”的形成是數字技術發展與社會互動的結果。意見領袖通過模糊事件真相,制造網絡輿情,并借助“后真相”現象破壞網絡秩序以此影響現實社會。網絡中真相問題本質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的本質又是社會問題。社會加速發展導致社會缺乏共識就難以建立經驗事實的真相。社會共識缺失直接導致網絡秩序混亂,只有一個社會秩序才能夠產生出人們可以接受的普遍后果,滿足人們的公平感和必要的社會共識,“后真相”現象才能被克服[5]。因此,“后真相”時代的網絡輿情看似是網絡輿論問題,實則是社會問題。努力將改善民生和保障公平相結合,普及傳統社會共識與建立理性的網絡價值觀是解決網絡輿情滋生的根本方法。除此之外,消除“后真相”現象需要通過完善相關法規將言論自由設定界限,加強網絡道德教育提升思維判斷力、重新建立網絡秩序控制話語權,形成社會共識。從政府、社會和網絡“三位一體”進行協同治理,進而探討符合當下“后真相”時代網絡輿情治理的新路徑。
(一)政府層面:完善網絡安全法,給言論自由設定界限
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言論自由也需要設置邊界,這是需要良法善治作為運行基礎的。習近平同志在《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滋養人心、滋養社會,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為廣大網民特別是青少年營造一個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18]實際上,我國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針對網絡輿情治理的行動。中央網信辦多次部署開展“清朗”行動,對網絡輿情開展了專項治理行動。主要聚焦網絡輿情易發多發、影響力大的18家網絡平臺(包括“微博”“知乎”“抖音”等),并通過建立完善的網絡監管識別系統、實時監控保護、溯源追究法律責任等措施進行全鏈條治理。其一,建立健全的識別預警機制,通過細化網絡輿論分類及時預警具有網絡輿情傾向性問題;其二,建立健全的個人隱私保護機制,通過建立快速舉報、取證通道及時對受網絡暴力人群進行救助保護;其三,嚴防網絡輿情信息傳播擴散,通過對信息傳播方式的監控及時處理網絡不良評論;其四,加大對違法違規賬號、機構平臺的處罰力度,對有煽動性質的平臺及相關賬號進行法律追責;其五,強化警示曝光和正向引導,推動權威機構和專業人士友善評論、理性發聲[19]。從各項新增的媒介法規與治理辦法可以看出我國對整治網絡輿情的決心,顯示評論者IP地址無形中給言論自由設置了邊界,一些帶有惡意輿論傾向的評論在被顯示國外IP地址后其評論的影響力大大減弱。給言論自由設置邊界,讓網民意識到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逐漸引導人們在網絡社交中理性評論。
(二)社會層面:加強網絡道德教育,提升思維判斷力
互聯網是現實社會的再映射,更是個人思想道德的“放大器”。社會加速發展,青少年的成長中分數成為評判一個人能否成功的唯一標準,學校與家長逐漸忽視對青少年責任意識、法律素養和邏輯判斷能力的培養。網絡道德教育的提升主要源自學校和大眾傳媒的持續教育,但目前這兩方面逐漸成為“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生態中輿情發生的天然土壤。青少年一邊在學校里接受主流思想教育,一邊在網絡中“抱團取暖”滋生出種種大眾文化意識。這種情形導致了許多青少年知行不夠統一,缺少了對社會中多元文化的真正理解、認知與包容。如何處理好“一元主導”和“多元化發展”的關系,這需要學校和家長共同協作完成,培養新一代青少年正確的思想道德觀是解決網絡輿情亂象的根本任務。首先,學校應該強調思想道德品質的重要性,改善青少年的社會化環境,使青少年從小就意識到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是一個人難能可貴的優點;其次,家長應該加強對孩子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教育。父母永遠是孩子最好的老師,通過家長給予的思想啟蒙教育,讓青少年從小耳濡目染形成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意識,更有助于孩子今后的成長。我們認為,理性是啟蒙的第一要義,更是發揮思維判斷力與行使社會責任感的重要路徑。面對復雜多變的網絡輿情環境,只有保持理性判斷和高度的責任意識,才能快速有效地分辨出事件的真偽,從而進行理性討論[20]。最后,媒體應該承擔起更多的繼續教育責任,加強主流媒體的影響力和內容多元化,增加符合青少年興趣的愛國教育內容。要讓網民意識到在行使公民權利的同時,還需要履行相應的公民義務。如何探尋出主流媒體繼續教育的正確方式是疏導網民負面情緒、辨別信息真假的關鍵,社會層面只有通過學校、家長、主流媒體多方面配合才能在潛移默化之中培養出青少年正確的道德素養和思維判斷能力,這是有效治理“后真相”時代網絡輿情亂象的根本方法。
(三)網絡層面:強化主流媒體公信力,掌握網絡話語權
“后真相”時代看似通過模糊事件的真相來影響輿論、制造輿情,實則是網絡世界中具有公信力的媒體受到一定削弱,網民無處獲取公共事件真相的權威信息。因此,在網絡空間討論社會問題時,有些人就會主觀臆斷,把個人意見和情緒宣泄在網絡之中。誠然,網絡媒體權威性的缺失,加之我國正處于高風險社會時期,社會潛在問題不斷顯現,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從而導致網絡輿情事件頻發。個別網絡輿論人利用“法不責眾”的特點踐踏媒介法律規則,并不失時機地搶奪話語權。因此,應在互聯網中培養積極正面的意見領袖與加強主流媒體公信力相結合,重新掌控網絡話語權,化解網絡輿情風險。實際上,在網絡輿論生態中出現的網絡輿情事件就是別有用心的人發表帶有非理性情緒的評論,以此吸引網民參與非理性的討論,影響輿情導向。由此可見,意見領袖對于輿論風向的引導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因此,應該通過積極正面的網絡意見領袖的動員功能,利用培養出來的意見領袖增加主流媒體公信力,建立政府與人民理性溝通的橋梁,以此達到治理“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生態中輿情亂象的目的。其一,在互聯網中培養體制內積極正面的意見領袖,與此同時吸收網絡中具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網紅”,利用其一定的“名人效應”促成積極正面的輿論共識和價值引導。其二,必須加大官方網絡平臺多元化建設,搭建富有活力的可以理性溝通的實名制虛擬社區。提供社會重大問題交流討論專項論壇,使公眾可以表達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讓不同階層、不同利益群體可以進行理性交流;鼓勵體制內培養的意見領袖和政府官員參與到討論之中,積極發聲弘揚正能量,合理引導網民意見從而提升主流媒體公信力,搭建政府與人民溝通的網絡橋梁,以此鞏固民心。其三,建立針對具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的硬性監管機制、定期溝通交流、明確社會重大事件討論的“紅線”,引導建立積極正面的網絡共識。對于具有煽動和發表不良言論的海外IP和意見領袖應第一時間進行“封號”,根據具體情況進行法律追責。其四,主流媒體應積極弘揚正能量,同時秉承實事求是的態度避免過分夸大和誤導性宣傳。只有官方媒體做到嚴于律己,實事求是地掌握宣傳尺度才能逐步提升網絡公信力。其五,主流媒體應與網絡意見領袖一道,定期舉辦社會問題討論會。鼓勵網民積極參與提出問題,官方提供合理解答,在疏導網民情緒的同時達到教育與宣傳相結合的作用。在網絡輿情事件發生前預先與網民溝通建立正向的社會共識,防患于未然。通過建立具有公信力的主流媒介進而形成擬態環境,讓民眾在潛移默化中理解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此有效疏導“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生態中的網絡輿情亂象,從而凈化網絡環境、化解網絡輿情風險,最終把握住文明和健康的網絡意識形態及其方向。
結 論
當前,由于網絡空間的復雜性,致使網絡輿情事件頻出。“后真相”時代網絡輿論生態下產生的輿情亂象映射了我國在社會轉型期間,社會日益增多的矛盾與分歧。對于社會轉型期間的網絡治理必須擺脫原有經驗主義的局限性,與時俱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加快社會層面改革速度,改善民生與加強網絡輿情防范、疏導情緒、管控監管相結合。重視網絡輿情對現實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完善網絡安全法規建設給言論自由設定邊界,鼓勵理性討論社會問題;加強網絡道德教育提升網民思維判斷能力,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面對公共輿情事件首先秉持懷疑的態度,進而減少“后真相”現象的出現;不遺余力地強化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將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加以融合,掌握正面積極的網絡話語權,搭建民眾意見反饋平臺,盡力疏導民眾負面情緒,加強網絡治理水平,從而提高政府形象來化解問題、聚集民心。各級政府只有在網絡輿論中及時提供事實真相及其信息,建立理性共識倡導民眾理性討論社會問題,并尋找出符合社會規范和社會寬容原則的平衡點,才能卓有成效地對網絡輿情進行社會治理和國家治理。中國式的現代化有賴于文明、健康的網絡輿論環境以及數字經濟的雙重支持和保障,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