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 糕
◇任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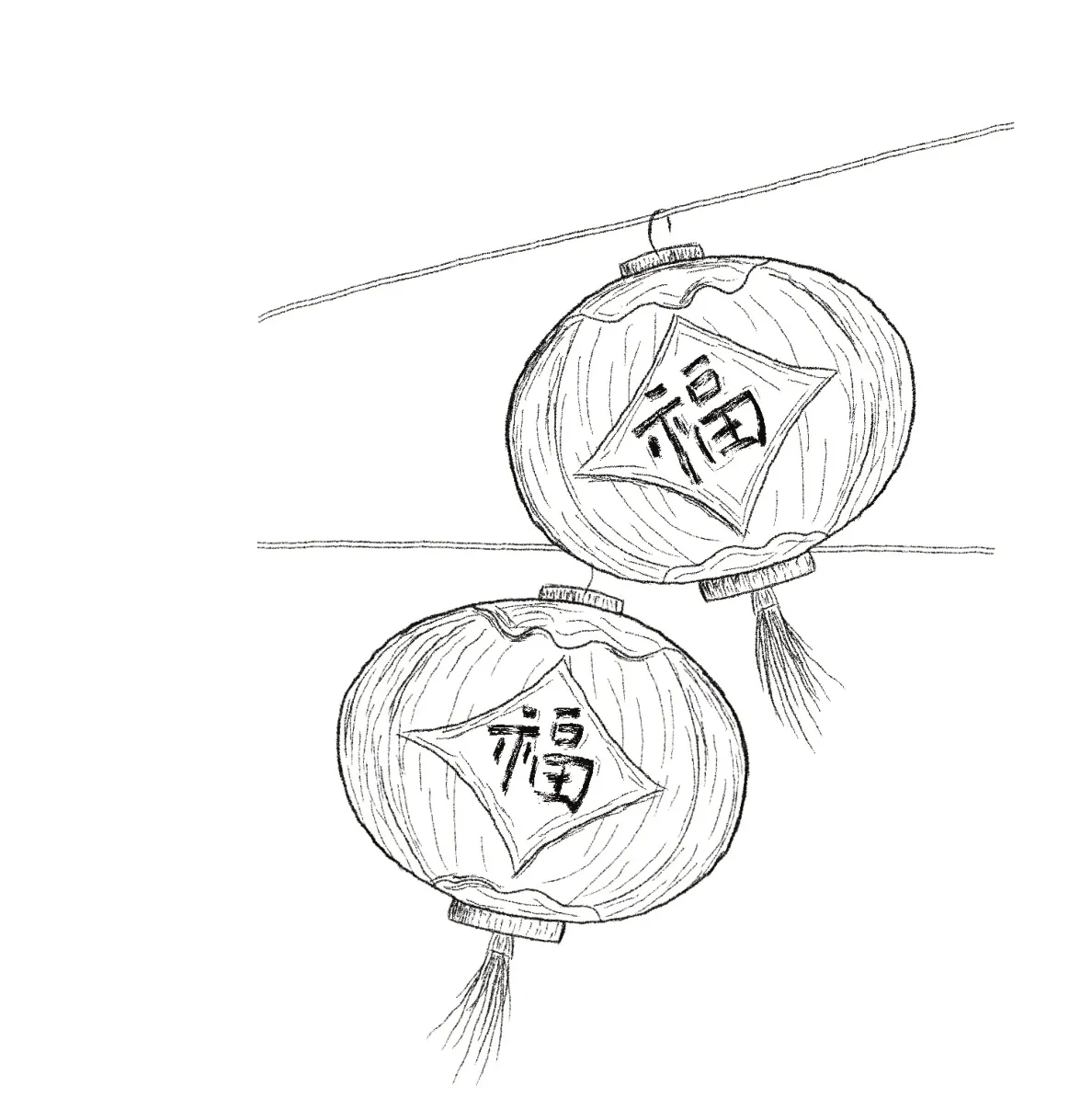
每到過年,總有一些記憶泛起,涌在心頭,我也為此寫下過一些思念的文字,掃家、寫對、看燈等等,今天寫寫吃糕。
平定有過年吃糕的習俗。
一盤黃澄澄、熱騰騰的糕,置于年夜的飯桌上,不是主角,勝似主角。“趁熱!趁熱吃!”趁熱夾一筷,軟糯甜香,彈牙可口,為口福,也為來年的幸福。
莊戶人家的自留地里,大多會預留一塊“條條”地,即使是荒地,重新耕種,或者新墾,反正不用多少投入的那種。等大多農作物都已耕種在地,抽空或順路在預留地里撒下種子,除去間苗,幾乎不再打理;秋天收獲了,這便是黍,平定也叫糜黍、糜子。這種作物抗旱、耐貧瘠,產量還不低。它不管在多么荒蕪的土地里生長,去了外皮的果實卻粒粒晶瑩,像極了玲瓏剔透的小珍珠。上碾、去殼,仿佛一個個黃色的小圓球,這才是真正的果實——黃米。黃米比小米稍大,顏色稍淡,是蒸糕的主料。
“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年。”過了臘八,年就真的近了。大人、小孩都各有事做,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年的喜慶、新的希望。臘月二十前后,母親提前把黃米泡上,泡發(fā)的黃米浸在水桶里,水面沒過黃米,泛著一個個乳黃色的夢。母親囑咐我們看著點石碾的情況,我們被過年的激動和期盼慫恿著,都十分樂意當這個勤務兵。弟兄仨輪流從家到碾窯,從碾窯到家,有時候隔著院墻,有時候站在窯頂,一遍又一遍向母親匯報“偵查”的結果。事實是,那幾天,石碾已忙得不可開交,常常是這家的還沒碾完,那家就早早排上了號。磨道里的小毛驢戴著眼罩,不緊不慢地圍著碾臺轉圈。碾墻上的人們不厭其煩地享受著這熱鬧的場面。終于輪到我們家碾米,要是不借用鄰居家的毛驢,我們仨就是推碾的幫手。母親一會兒用笤帚把碾壓出磨盤的黃米掃在碾磙下,一會兒用粗籮收攏了碾碎的黃米去篩面。時間一圈一圈流逝,米香一股一股散發(fā)而來,我們對糕的盼望一陣比一陣強烈。
母親是遠近鄰居中蒸糕的好手。她蒸的糕,軟而不瀉,筋而不硬。鮮香的黃米面躺在簸籮里。煮好的紅小豆、眉豆粒和大紅棗,顆粒飽滿,光澤耀眼。爐火正旺,坨六鍋里的水正幸福地翻滾著白色的水花。案板、瓷盆、籠床(蒸糕的砂制品,扁圓柱狀,無蓋,底鏤空、布滿錢幣大小的孔洞,類似現在的蒸屜)都已清洗,正煥發(fā)著嶄新的容貌。我們跟在母親身后,進進出出,欣喜若狂。母親告訴我們,古話說,蒸糕的時候,不能有生人,要不糕就蒸不好了。我們都不是生人,卻都擔心糕因為我們的搗亂而蒸不好。弟兄仨溫馴地聽從古話的教導,卻并不走遠,在院子里坐立不安,心煩意亂。
母親嫻熟地把摻了紅小豆、眉豆粒的黃米面握在手心,輕輕擠成一個小團,一個一個緊密地鋪進籠床里。她把鋪滿一層小面團的籠床坐在鍋沿上,嫻熟地用黃米面把籠床和鍋沿的縫隙封嚴。籠床里氤氳著白色的水汽,水汽彌漫在熱氣騰騰的廚房里。母親用小碗盛了黃米面均勻地撒在籠床里,又抓了一把大紅棗撒在上面。她嫻熟地一邊把握火候,一邊掌握著籠床里水汽的大小。我們在院子里追逐、嬉戲,院子里升騰著棗糕的濃郁的香氣。
中午飯,照例就是一碗新鮮的糕。就算沒有菜蔬,我們個個也吃得津津有味。我想,幸福就是那一碗糕,它采用最普通甚至最廉價的食材,綴以日常的苦樂酸甜,經歷生活的淬煉和時間的打磨,最終得以傳承和延續(xù)。
有了糕的日子,從此就多了一份選擇。蒸好的糕放涼、定型后,母親把它分切成小塊,手掌一般大小、薄厚。除開送給舅舅、姑姑家的和春節(jié)、元宵節(jié)吃的,其余的就凍在院子里的墻角。我們在外面玩累了,跑回家,掀開鐵鍋,拿兩塊兒放在爐火邊,慢慢等著火口的熱度將冷凍的糕塊兒喚醒,烤熱,直至外皮焦脆、內里軟糯。性急的我們常常一邊烤,一邊吃,吃完烤完,烤完吃完,哪里等得到外焦內糯。也常常是你吃了我烤的,我吃了你烤的,弟兄仨誰也說不清,辯不明。找母親評理,母親對我們說,不管誰烤,就多烤幾塊兒。
爭搶著吃糕的日子,甜蜜而幸福,卻再也一去不返。
今天,糕已成為我們的家常便飯。兒女喜事,吃喜糕;親友聚會,吃炸糕;變換口味,吃餡糕……自己做,超市買,還有專門的店鋪出售。每到飯時,樓下常會有“棗——糕——棗——糕”的叫賣聲不絕于耳。中國人都愛吃糕,雖然地域不同,做法各異,但“糕”“高”諧音,吃的是香甜,聽的是高興,寄予的是人們對生活“節(jié)節(jié)高、步步高、年年高”的美好愿望。
又快過年,我對母親說,該泡黃米、蒸糕了。母親說,臘八不是才吃了糕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