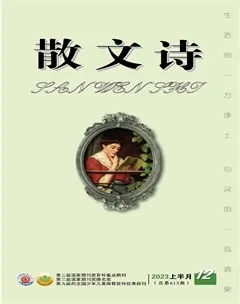逆流而行
◎王武臣
初 像
從一場雪中窺探黎明, 有基因的古老流向, 是另一部古籍的某個章節, 引申的人左手持劍, 或提筆寫詩, 在歷史的流動中,落下一行行燃燒的文字。 那是一脈相承的傳統, 視而不見的隔代人, 因為某種習慣而對峙, 隱忍的冬天, 演繹著繪聲繪色的故事。
一樣的凜冽, 一樣的寒涼。 左手持劍的人, 用右手刻畫命運的契約, 劍是意象, 雪是詩, 它們相互摩擦, 形同鋸齒, 時間飄逸在細小的緩沖區, 揮劍的定義, 總是劈空, 一劍斬斷汩汩作響的臺詞。
流蘇被風擦傷, 掂在手里的涼亭結滿冰霜, 左手寫的字形同虛設, 單調的命運從亭檐緩緩滴落, 從此相信一滴湖水, 相信氤氳的水汽能帶來飽滿的思想。 少年的作文里, 清清晰晰刻畫著這些景象, 諸如楠竹長在青云之上, 門前的桂花樹落滿明朝的寒霜, 火爐前, 他是如何煮沸一盆水, 潑出床前明月的白光的。
月色染白了大地, 那些煌煌塵世的詩意部分。 歷史的腰身,拇指輕捻著變瘦、 喑啞的文字, 在少年手中被擦得锃亮。 一陣揉搓之后, 春天即興而來, 種子乘著風長大, 所有的果實, 竟會為它們新生的骨肉悲傷。 就像那一年, 故事在手指縫隙流淌, 流動的光陰存在敘事性, 唯獨僅存的詩, 被月夜彎折在石橋上。
疾速的馬蹄踏碎了陶俑和酒, 跑出一路曲曲折折的月光, 光之盡頭, 無人乘坐的木蘭舟被擱淺, 河流有隱忍的弧度, 曲線盡頭是一張灰白色的紙, 滿屏的春風降維在此, 記錄著角落里的聲之嚶嚶, 命之煌煌, 人生的初像。
逆 流
為了讓右手有適應的角度, 他把虛構叫虛構, 把寫實叫寫實。瞬間掉頭的風向, 在一泓湖水上擱淺, 把往年的春天依次疊加,搖曳在河岸生生不息的嫩枝上。
抬起手, 春光有母性, 溫婉的呼喚隨風降臨, 右手的文學概述和左手的卡頓慢放, 都接納著明凈通透的佛塔、 遠山、 閑云,以及漢字重新排列組合、 流淌于基因的久違詩行。
所有的快樂源于習慣, 豐盈的美學是一種闡述, 文末的煙波在城南, 情緒在城北, 他在城市中央。 左手掬一彎下弦月, 右手是羅紋般的恍惚哲學, 我們, 我和他, 適應著相同的過往。
開始用右手寫詩, 但左手抓住的時間, 才能讓飛翔的想象力變得更加飽滿。
不由自主, 融化輕風的詞匯是純音, 為保持純粹, 舊年代的氣息開始彌漫, 鮮活的事物學會了左右逢源。 即便如此, 他的左手仍是一片荒島, 每動一下, 落日就下沉一點, 零零碎碎的白灰落在眼角, 變成流星閃過的淡綠色霉斑。
巷子里, 時過境遷的舊庭院門前, 兩座古老的石獅, 啃嚙著時間長大, 它們時而仰天長嘯, 從身上抖落寫意的碎片; 時而在陽光下暴曬血肉風骨, 接近神性的披身讓它們活靈活現, 經久的筆意山重水復, 劃除蒼勁的留白, 又寫出新的留白。
巷子外, 詞義鋪墊好放學的路, 流出暮色爍爍的靜水, 兌現的世界充滿裂痕。 藏在書夾的落日, 每天都在男孩體內搖晃, 晃著晃著, 就晃出了一個寫滿秘密的春天。 那是左手的誤區, 在飄零而下的往事間隙, 插上了寫滿舊夢的明信片。
僅剩的光陰也在逆流, 仿佛一曲倒放的流行歌, 他右手拿著掃把做的吉他, 左手擦了擦西邊的天空, 下午重新亮了起來, 光線照進體內, 歌詞唱到了昨天, 春風的含義被染上不同色彩, 變成了懷舊的語言和棄用的習慣。
重 逢
左手有群山, 也有游弋不到的海岸。
四十多年來, 這個心懷流水的人, 按捺著右側的曲解, 尋覓左手抓住的光線, 用內在的觸覺, 把手心的掌紋與大地接壤, 與天穹貫通。
忽左忽右的風暴望不到盡頭, 變幻的世事沒有諧音, 一切都詞不達意, 一切也完好如初。 他懷疑他的奔跑, 又重塑那些奔跑, 柔軟的風繞過兩側, 吹散的標點開始硌腳, 在青苔遍布的青磚地面, 碾出一道道裂痕。
裂痕里, 母親的訓導不絕于耳, 泥土顏色鋪陳著少年底色,他依舊用右手寫作, 用左手取出陳年舊霧, 那些回憶柔軟、 松弛, 像藝術品。 每當此刻, 他會躺于沙發上, 任清寂的日子在陣痛的文本漲潮, 明月表面涌出沸騰后的樂音, 以及完美造物者安靜的睡眠。
后來, 他用右手拆散過很多文字, 演講稿、 論文、 總結、 工作匯報……那些文章的細枝末節會盛開璀璨煙火, 那些創作經驗繽紛多姿, 那些苦苦熬掉的深夜隱含著感恩和仁慈。 文字的清香, 從春風吹過盛夏, 又從頭頂染白深秋的雪。 偶爾, 停在某一章的青石被藤蔓纏蔽, 再被古老的時光照徹。 那些文學性闡述的肉身, 從鏡像里緩緩走出, 他們對視: 一個緘口不言, 一個淚流滿面。
他問, 如何截取一節時光的骨頭, 才能在另一種情景下重生?每次新建一個文本, 就是新建一片天, 風會吹來古老的動詞, 用文字的不同姿態, 和另一個自己重逢, 觸摸未竟之詞的冷暖。
尋 找
落單的時辰從天而降, 停在小人書前, 雙手捧起的光線開始抽象, 老鷹從手影戲脫身而出, 在天空薄得像一首詩, 那些倒裝句的詩, 一行一行飄進水泥陽臺, 落在他經常遠眺的石階上。
斷續詩意的下午, 鋪展著暖暖的日光, 手洗的校服蜷進紅邊白底的陶瓷盆, 搓衣板斜杵在執拗的身體上, 那是一個人的春天, 遮擋著淺藍色窗簾的光線。 風是明媚的藍, 在思想側身, 如倒影, 無比斑斕。 他的左手, 握住過往, 慢慢漏掉的時間像風沙, 翻轉的沙漏有“滴答答” 的走針聲。
那些年, 他手捧武俠書, 蹲坐在青春的臺階上, 快速翻閱的故事跌宕, 顯著的事物漸漸起伏, 那些情情愛愛的心跳過程, 無法從人物抒情角度闡述, 有文藝之大美。
淺見薄識, 陋室白丁, 視贗品為珍寶。
從拐角, 虛構了一場曠世孤獨, 周伯通左右手互搏術, 在兩首律詩里平仄通韻, 專研、 模仿。 后來, 他用左手練出了一個新的他, 右手理性的他和左手思想的他, 對飲, 搏擊, 擁抱, 鼓勵。 于是, 他安排左手的工具包, 在車間里進進出出, 安排右手的紙和筆, 寫出桃花島, 寫出一條大船, 寫出一次又一次宿命遠航的長帆。
那是老北京冰棍走俏的炎炎夏天, 他和他們, 以及她和他們,把身體內干癟的大海拴在用舊的船舷。 站在大汗淋漓的甲板中心, 平添一場暴雨, 漲潮的文字溢出繁瑣無用之詞。 他們拋錨投出的纜繩, 至今沒找到出海的港灣。
聽 雨
用左手觸摸春風, 日子逐漸豐盈, 手臂布滿的陳舊雨水, 順著語境滑落。 靈魂埋伏在這場雨中很多年, 歲月的尖刺扎著腳,淅瀝瀝的水汽困住往事, 像耳鳴, 習慣日復一日, 似無終止。
用哪一種敘述, 能描寫好形形色色的路人? 他們擦身而過,日漸蒼老, 青春的留白更加從容, 雨沒有停, 時間, 清澈見底。
剪刀手, 千篇一律的笑, 照片傻里傻氣。 柳枝在舒緩的岸邊涌出未傾盡的綠, 瘦削的詞匯毫無張力, 潮濕的連詞累贅著臃腫的文本, 吹來一個午后, 又帶走一個午后, 像莊嚴的儀式, 主語開始退潮, 輪番而下, 一浪接著一浪, 以倒退的形式, 洗凈了繁瑣纏身的無用文章。
拾起消失的街道、 舊衣服、 門前的白楊, 生命忽然遼闊, 清澈的目光在身側, 擠進熒光的年少之門。 在門口, 他一次次用文本重建春天, 建好就刪, 刪了再建, 直到歲月模糊, 時光舒緩,仿佛墜落的靈魂在谷底, 牽起一根凋零的藤蔓。 上爬的骨骼酸疼, 時間的脫臼聲, 響徹了整座空山。
遠行前, 他說, 唯有闖蕩可補償疏忽的時光, 這所謂的現實,正好消解那些充沛的想象, 就像他起身, 左手, 拽著人生的宿命奔跑, 右手, 擰緊自己的凡塵和異鄉。 那場雨一直下到昨晚, 在年輪中心, 一遍一遍, 浸泡出內心的雜質。
每次回到那里, 沒有落日的夏天, 都會在他體內, 長出新的枝丫。
妥 協
試圖鉆進身體的深處, 尋找那棵菩提。 河流是回憶的綠, 在東岸至高點, 染亮久違的時光之種。
左手捧來清風, 在耳畔吹走了紙上的名字, 他的人間開始失重, 全身的骨肉被重復放空, 懷疑的世界暗了又亮, 亮了又暗。體內霉斑變成朵朵浪花, 宜人的光線透過枝枝葉葉, 絲絲縷縷,穿過古老行蹤的夢。
每當此刻, 走散之人會從某些舊址陸續走回, 他們敘舊, 互相指認歷史, 一串串翻新的腳印被風鈴踏亂, 疼到骨子里的, 是前年的肩傷, 在老照片落下的病根。
他右手扶著酸痛的文字, 站在熒光的年少之門, 懷疑, 走形的身材能裝下多少斐然之詩?
光是紙的底色, 紙是他的空白, 他把自己降維在筆尖, 緊緊握著——吹走的名字。
只有思考時, 用舊的思想才會從窗外吹回, 像那些聯系不上收件人的信件, 以虛構印戳蓋上的詩, 每一行都歷經了世態炎涼, 每一首都飽含了雷電風霜。
妥協之人漂洋過海, 沿著來路返回, 身上的光陰一把一把剝落, 順著腳下的河流, 流淌向宿命的方向。 春天的盛開, 需要回到青春的皸裂之前, 補上一些舊時光。
他沒有太多時間, 要捱過每一個隱忍的夜晚, 把僅剩的一絲暖陽, 掛在有空發呆的地方。
從泥土中成長、 輾軋、 淬煉的文字, 碎成硌手硌腳的符號,詩意, 裝載著失而復得的童年。 兩次揮手告別, 在起點和終點,修繕彼此的時空秩序, 誠意和謊言。
妥協的人孤懸在生活之上, 信守著未經歷的霜雪, 眺望的目光在體內延展, 閑散的歲月有春夏的昨日、 秋冬的明天。
完 成
右手筆力千鈞, 左手輕描淡寫, 力透紙背的河流走向, 有一葉命運的輕帆, 它緩緩穿過運河, 周游在縮小視覺的天空下。 時間越來越慢, 文字變得潮濕, 無法一行行透過歷史的宣紙, 抵達密藏在隱晦現場的修辭。
心里的仿古建筑令人眩暈, 臺詞的錯覺無法確認春天的暖。他試圖完成一個句式, 再承接下一個句式, 古老的空間有人帶來消息, 那些止于柔風的思想, 在花香中盛開。
為完成這段敘事, 他丟下很多生活, 抽出柳枝的句子重疊起斑斕的說辭, 站在清透的湖水前, 隔岸觀望, 隱秘的內容, 正順著明清的房檐向下流淌。
這是心中所愿嗎? 他慢慢翻開古籍, 一段不屬于自己的年代撲面而來。
陽光半遮掩, 還算明媚, 他調整好情緒, 行走在矜持的青石道上, 試圖把這條路的所有避諱, 洗凈在春水融化的禱詞前。
許多個他, 早已遍布這場春天所有的背影, 在他的面前, 那些蜚言和行人的春風大致相當。
而最后一場對峙, 情節被嚴重刪減, 像某人送的舊鋼筆, 常常用筆尖, 剔除時間螺紋里的灰。
沉浸在竹林的深吻中, 詩人稿紙上的夢境, 正汩汩冒著熱氣。交流的內容無從想起, 唯獨她裊娜的坐姿, 多年未變, 纖纖玉手提筆, 緩緩寫下, 春的上部……
那個字娟秀, 后面的每個字都聞風起舞, 像那年手舞足蹈的我們, 牽著手奔跑, 跑進下一個春天。
字落在信紙上, 字揉進紙簍里, 字飛越獨立思想的另一端。熱情的靈魂在時光之門關閉前——
他猛回頭, 名字安詳, 書還在枕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