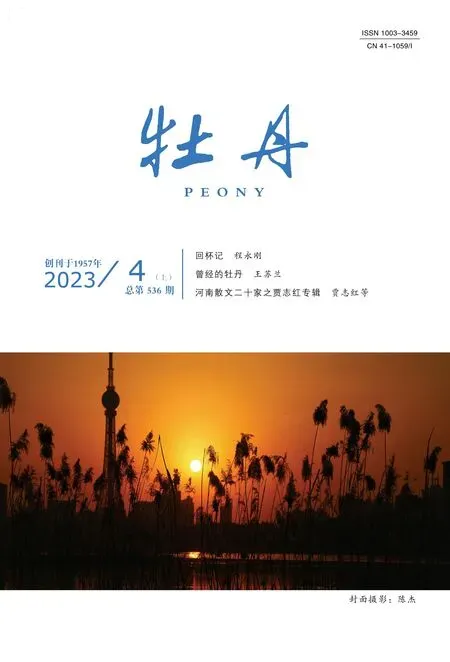我讀陳文東
紫藤晴兒
對(duì)我而言,無論寫什么,首先是從語言出發(fā),語言如同一個(gè)作家的氣質(zhì)。
在讀了陳文東一系列的散文之后,新發(fā)現(xiàn)令我喟嘆,以至于會(huì)顛覆我一直所崇拜的博爾赫斯的神秘時(shí)空,《車站》《窯》讓我會(huì)覺得那個(gè)二十多年前的時(shí)空同樣的神秘。文章所散發(fā)的時(shí)間感,并非是需要我沿著光陰后退,而是需要我用靈魂去飛越,去追趕,才能跟得上那些玄妙。
還有一部分是寫人物的,如《鄉(xiāng)下的伯父》《笑呵呵的姥姥》《王二爺王老師》,從現(xiàn)實(shí)的意義進(jìn)行記敘,窺見生命中永存的溫度,語言又回到一種原生態(tài)的樸實(shí)和干凈,文本所散發(fā)的自然情感會(huì)讓每一個(gè)讀者從中獲取內(nèi)心的一種缺失,它具有普世性的色彩。從容于兩種不同的寫作形式在同一個(gè)時(shí)期,所有的經(jīng)驗(yàn)空間,現(xiàn)實(shí)精神,個(gè)人體驗(yàn),以及語言視界都是我需要學(xué)習(xí)的,我讀到的和領(lǐng)會(huì)到的一如寫作的旨?xì)w,讓我同時(shí)獲得了思想緯度和一種精神勢(shì)能。
《車站》開頭就像佩索阿的詩(shī),“那條路沒有了,早已經(jīng)沒有了。”在有意識(shí)或無識(shí)之中生發(fā)出來的語言。標(biāo)題車站和路不知道是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建立關(guān)系。但僅這樣的開頭,就足以取勝。它不是個(gè)人意義的路而是“從眾意義”的發(fā)聲。語言的密碼也在一點(diǎn)點(diǎn)地布置,以路為時(shí)空展開的張力,也在以弱小擴(kuò)張著它的縱身密度。這其中加入了許多詩(shī)性的語言,重疊和彰顯著詩(shī)意的天空。《車站》以現(xiàn)實(shí)的抵抗和挖掘,打通了一條精神通道,車站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超越時(shí)空的精神共同體。趨向于無限高度的終極關(guān)懷。我想意義之中的車站是隱喻了一個(gè)時(shí)代的車站,它在時(shí)間中延伸著民族的發(fā)展力量和文化元素,用思辨的結(jié)尾,拓展了車站的終極意義。
《窯》同樣以詩(shī)性的開篇,抽離于現(xiàn)實(shí)和想象之中,感官之中既是大我也是無我。“在雨聲中睡去,從雨聲中醒來。”讓我一再確認(rèn)了散文可以與詩(shī)歌有關(guān),從此也有了寫散文動(dòng)力。語言的秘境充溢著詩(shī)歌的濃郁,并在時(shí)間和空間中大幅度的跳躍。“那一年我15 歲,還從未走出過生我養(yǎng)我的那一片一望無際、坦蕩如砥的平原……據(jù)縣志記載,這塊曾經(jīng)是古莘國(guó)、古毫國(guó)的土地上,原是有著幾座風(fēng)景秀麗的小山的,可它們似乎都隨著歷史的煙云消散無跡了……”無疑這是一種超越常規(guī)的散文寫作,我原來以為只有詩(shī)歌可以天馬行空。超越空間的搭建,通常都在擴(kuò)張著精神的堡壘,這是我理解的,而《窯》是一個(gè)精神的偌大堡壘,不受時(shí)間限制,但受空間的影響。這篇文章里面也有很接地氣的敘述和描寫,同樣增加了語言的幽靜和沉穩(wěn)。
作家是一種責(zé)任,勃洛克在《詩(shī)人的使命》中寫道:“詩(shī)人的職責(zé)要求于詩(shī)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了揭開外部表面的覆蓋,開掘精神的深處,詩(shī)人必須擯棄世俗世界的一切羈絆。”透過詩(shī)人的使命仿佛這一切都是在為陳為東而設(shè)定的,“我告訴自己說沒有什么可怕的,沒有山林中才有的猛獸,沒有神情暗淡的陌生人,只不過是一個(gè)荒涼的土堆……撥開一叢茂盛的紫荊和蘆葦,鉆進(jìn)破敗的窯膛中。”感嘆之中又退回了時(shí)間的遠(yuǎn)處。但近處是他站在回憶之中,又深陷于時(shí)間的陌生感。在時(shí)間、空間中轉(zhuǎn)換著一個(gè)《窯》的神秘之境,讓讀者也向往跳進(jìn)去。幽寂之中是神秘的通道在此打開,在時(shí)間和空間中有形無形地穿越,一如這也是小鎮(zhèn)馬孔多。從下雨到雨停了正是沿著時(shí)間的線條和空間構(gòu)筑擴(kuò)建著宇宙般的精神時(shí)空,內(nèi)部的世界完整著一座窯的無限精神圖譜和跨越時(shí)空的限囿。
《鄉(xiāng)下的伯父》《笑呵呵的姥姥》《王二爺王老師》是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展開的記敘或陳述,語言凝練又樸實(shí),這是兩種決然不同的風(fēng)格。以線性的敘述抓住人物特點(diǎn),又以情感的緯度展開畫面感,以一種生活的效力和語言的深度凝視并呈現(xiàn),我竟然分不出哪一種寫法更好,我更喜歡。這個(gè)看似簡(jiǎn)單,就如朱自清的《背影》,那些細(xì)膩的描寫具有吸附人心的力量。而每一個(gè)動(dòng)作就像一個(gè)強(qiáng)大的磁場(chǎng),它的強(qiáng)度足以顛覆著一顆孤高之心。這是親情的正本,是生命的本源回歸。特別感動(dòng)于那些細(xì)節(jié)“他多次向我要寫滿了墨跡的演算本子卷煙抽,那煙葉末子是他自個(gè)兒烤的煙葉,用他粗大的手指碾碎的。白白的煙霧從他嘴里冒出來,可嗆人了。那時(shí)候我就想:他有那么多的紙為什么還要向我要?……”畫面感超強(qiáng),而內(nèi)心的情愫又自然而然。好文章也應(yīng)該是這樣的獲取人性關(guān)懷。“伯父就是這樣一個(gè)鄉(xiāng)下人。”所有的特指都拉近了讀者和伯父的距離,伯父也應(yīng)該是每個(gè)人的伯父。一個(gè)年代的伯父縮影。《笑呵呵的姥姥》的敘事力量也來自于情感,但又不止于情感,同時(shí)也可以延伸于一個(gè)時(shí)代的感應(yīng)。“在我的印象中,姥姥是個(gè)不太幸福的人。“姥姥是個(gè)如今已經(jīng)很少見到的小腳女人”,小腳姥姥那是一個(gè)封建社會(huì)的回響,雖然只是裹腳,但現(xiàn)實(shí)之中的傷痛一定特別深刻。我小時(shí)候也見過村子里的老太太,腳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的感覺。這種暗傷具有時(shí)代性、時(shí)效性。在矛盾中對(duì)立又統(tǒng)一于姥姥的笑,笑呵呵的姥姥,是最完美不過的姥姥了。姥姥的寬慰和悲憫之心也人人可見。所以無論是伯父,還是姥姥他們離開了塵世有多久了,他們依然活著。以永存的溫度。溫暖著現(xiàn)實(shí)的疏漏和孤單,我們都需要一個(gè)伯父,一個(gè)姥姥,隔著時(shí)空寒暄。這也是我們的情感意識(shí)和精神共識(shí)。
縱觀這些散文所散發(fā)出來的文學(xué)氣息,除了嘆服,我還有欽佩。兩種出色的寫作技巧或手法同時(shí)集中在一個(gè)時(shí)期,一個(gè)人身上,還有語言的嚴(yán)謹(jǐn)和得當(dāng),——除了贊美我也不會(huì)說別的了。如果春天所有的花朵都是用來贊美的,那么我就要送上一個(gè)春天的最好起始。“我的職業(yè)就是,贊美崇高,為此上帝教我語言,還讓我的心充滿感激。”請(qǐng)讓我引用大詩(shī)人荷爾德林的話,“信仰神圣事物的,自有那自身神圣的人。”為此我也想借著春天看到燦爛和繁茂于不同的時(shí)期的另一個(gè)精神出口或神圣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