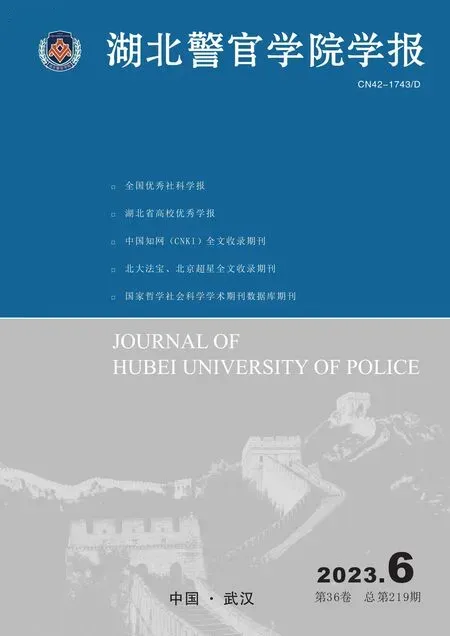基于市域治安問題防控路徑的思考
劉瑾澤,趙 欣
(1.上海公安學(xué)院,上海 200137;2.上海理工大學(xué),上海 200093)
近年來,隨著我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的深入推進(jìn),社會(huì)觀念、社會(huì)心理、社會(huì)行為產(chǎn)生了復(fù)雜而深刻的改變,一系列社會(huì)變革所帶來的物質(zhì)層面的設(shè)施建設(shè)、新技術(shù)應(yīng)用以及非物質(zhì)層面的觀念更新、文化沖突等在客觀上也引起了治安實(shí)體的激烈變化。治安主體履職質(zhì)效低下和治安規(guī)范調(diào)整滯后的現(xiàn)狀使得乏力的治安服務(wù)供給無法滿足現(xiàn)代城市社會(huì)的多元需求,市域治安實(shí)踐中的矛盾愈加凸顯。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高速發(fā)展,截至2021 年,我國(guó)城鎮(zhèn)化率達(dá)64.72%①關(guān)于我國(guó)城鎮(zhèn)化率的數(shù)據(jù)來源及擴(kuò)展信息,參見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2023 年2 月9 日訪問。,城市已經(jīng)成為人口流動(dòng)頻繁、思想文化交匯碰撞、資源要素高度集約、社會(huì)系統(tǒng)高速運(yùn)轉(zhuǎn)的空間區(qū)域。城市社會(huì)群體結(jié)構(gòu)、社會(huì)組織架構(gòu)、社會(huì)關(guān)系以及社會(huì)事務(wù)的復(fù)雜性決定了市域治安工作的復(fù)雜性。相較于鄉(xiāng)村治安問題,市域治安問題在宏觀上涉及的人員范圍更廣、隱含的矛盾糾紛更復(fù)雜、違法手段的形式更多元、事件與案件的發(fā)生情境更多樣,涵括了經(jīng)濟(jì)利益糾紛、情感糾紛、醫(yī)患矛盾糾紛、征地拆遷糾紛、危險(xiǎn)物品管理、特種行業(yè)管理等方面所引發(fā)的一系列治安事件與案件,反映了我國(guó)城市社會(huì)轉(zhuǎn)型過程中的“陣痛”。
社會(huì)基礎(chǔ)秩序決定著治安秩序狀況,治安秩序狀況反映著社會(huì)關(guān)系的協(xié)調(diào)程度。根據(jù)烏爾里希·貝克的“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理論,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大幅提升必將帶來不斷攀升的社會(huì)風(fēng)險(xiǎn)[1]。因此,市域治安實(shí)踐活動(dòng)不能脫離城市社會(huì)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樣態(tài),要增強(qiáng)市域治安防控工作的系統(tǒng)性和綜合性,審查市域治安問題產(chǎn)生的深層次社會(huì)原因,將社會(huì)治理同治安秩序維護(hù)進(jìn)行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以強(qiáng)化市域治安實(shí)踐的柔性、彈性和韌性,減少資源浪費(fèi),提升工作質(zhì)效。
一、當(dāng)前我國(guó)市域治安問題產(chǎn)生的新挑戰(zhàn)
(一)治安失序的擴(kuò)散與躍遷
在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深入發(fā)展的背景下,城市經(jīng)濟(jì)與社會(huì)建設(shè)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以往高速、粗放的發(fā)展模式下,同時(shí)產(chǎn)生了發(fā)展失衡、物欲橫流、價(jià)值混亂、信仰喪失等負(fù)面效應(yīng),傳統(tǒng)治安問題與新型治安問題相互交織,市域治安秩序紊亂的“慣性”在短期內(nèi)難以“剎車”,“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傳統(tǒng)治安實(shí)踐模式在應(yīng)對(duì)當(dāng)前市域治安問題時(shí)已經(jīng)力所不逮。
我國(guó)城市社會(huì)目前面臨著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一方面,城市中既有白領(lǐng)精英人群,同時(shí)也有大量社會(huì)地位較低的務(wù)工人群,階層之間的實(shí)力差距較大;另一方面,我國(guó)中產(chǎn)階級(jí)群體規(guī)模的占比不高,社會(huì)分配仍存在不合理之處。羅伯特·默頓的緊張理論,又稱文化失范理論,能深刻揭示我國(guó)“金字塔”型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所面臨的現(xiàn)實(shí)風(fēng)險(xiǎn)。由于城市社會(huì)中存在較大規(guī)模的低階層社會(huì)成員,其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的保障程度較低,比如經(jīng)常面臨的風(fēng)險(xiǎn)有經(jīng)營(yíng)不善或失業(yè)、“五險(xiǎn)一金”等社會(huì)保障不到位、工作條件差、人際交往危險(xiǎn)易遭侵害等諸多問題,使他們?nèi)狈ψ宰鸶泻蜌w屬感。低階層社會(huì)成員因缺乏獲取正當(dāng)與合法權(quán)益的機(jī)會(huì)和途徑,極易滋生怨恨、嫉妒、抑郁、焦慮、暴躁等負(fù)面情緒,加之在低自尊感和低歸屬感的影響下,他們?nèi)菀變A向于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不法利益。這些不法利益既有常見的物質(zhì)性內(nèi)容,又有“造成影響”、“獲得關(guān)注”、“發(fā)泄不滿”等精神性內(nèi)容,但最終都會(huì)造成擾亂市域治安秩序的后果。
與此同時(shí),由于多元文化與價(jià)值觀念在城市社會(huì)中相互碰撞,其中關(guān)于“秩序與自由”的價(jià)值沖突導(dǎo)致了公眾對(duì)治安實(shí)踐的認(rèn)識(shí)分化,使現(xiàn)實(shí)中具體的治安實(shí)踐屢遭質(zhì)疑和爭(zhēng)議。這種認(rèn)識(shí)分化不僅存在于治安主體和被管理對(duì)象之間,還廣泛存在于社會(huì)成員的群體內(nèi)部。例如,對(duì)于民警的盤查工作,有的市民對(duì)此表示理解和支持,而有的市民則產(chǎn)生抱怨、厭惡和抵觸情緒。社會(huì)成員之間文化和價(jià)值觀念的差異使其對(duì)社會(huì)事件的理解不盡相同,容易形成觀點(diǎn)對(duì)立,引發(fā)“網(wǎng)絡(luò)罵戰(zhàn)”,甚至發(fā)展為“線下沖突”。由于現(xiàn)代信息網(wǎng)絡(luò)幾乎不受時(shí)空制約,治安輿情擴(kuò)散迅速,甚至可能發(fā)生治安事件與案件跨地域聯(lián)動(dòng)的“躍遷效應(yīng)”,進(jìn)而對(duì)其他地區(qū)的治安秩序造成破壞。
(二)基層組織的退行與失能
基層組織既指以公安派出所為代表的國(guó)家基層治安主體,也指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huì)等基層社會(huì)治安主體;既指街道辦事處等基層政府派出機(jī)構(gòu),也指以居民委員會(huì)為代表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基層組織與民眾接觸的廣度和深度遠(yuǎn)超其他層面的社會(huì)組織和國(guó)家機(jī)關(guān),基層組織履職質(zhì)效的良好與否能夠廣泛影響市域治安秩序狀況。
基層組織在治安秩序維護(hù)乃至社會(huì)治理中發(fā)揮著基礎(chǔ)性、決定性作用,但目前其存在工作方式退行、職責(zé)履行失能的問題。第一,基層組織與人民群眾的聯(lián)系不夠緊密,調(diào)查研究工作不到位。例如,當(dāng)前居民委員會(huì)陷入自治組織和行政組織的雙重角色之中,在組織形式、身份意識(shí)、服務(wù)意識(shí)上存在偏差。行政權(quán)力的滲透使居民委員會(huì)身份變質(zhì),導(dǎo)致居民在參與社區(qū)事務(wù)中的話語權(quán)喪失[2],造成社區(qū)矛盾得不到及時(shí)發(fā)現(xiàn)、溝通和化解,矛盾的積壓使社區(qū)治安隱藏著不穩(wěn)定因素。第二,各類基層組織之間常態(tài)化溝通協(xié)作機(jī)制不暢通,形成“治安信息孤島”。公安派出所、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huì)、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huì)在進(jìn)行治安秩序維護(hù)和社會(huì)治理活動(dòng)中往往各自為戰(zhàn),直到問題凸顯才被動(dòng)地進(jìn)行溝通和尋求解決之策,缺乏對(duì)治安風(fēng)險(xiǎn)隱患的識(shí)別和預(yù)警,對(duì)市域治安問題的預(yù)見性不足。第三,基層組織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不適應(yīng)社會(huì)治理的現(xiàn)代化要求。自由和秩序兩者是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其中一方若逾越合理限度,則必然導(dǎo)致另一方的價(jià)值被侵蝕,進(jìn)而造成“自由—秩序”的價(jià)值失衡[3]。維護(hù)治安秩序從根本上講是為了保障絕大多數(shù)社會(huì)成員的自由,但現(xiàn)實(shí)中一些基層組織片面強(qiáng)調(diào)治安秩序穩(wěn)定,其治安實(shí)踐和社會(huì)治理行為超越了應(yīng)然邊界,形成了“一刀切”的工作方式,侵犯了民眾的合理自由與合法權(quán)利,極易引起他們的抵抗并產(chǎn)生治安輿情。第四,基層組織工作人員素質(zhì)不高、履職不力、能力不足。作為維護(hù)治安秩序一線力量的基層組織工作人員在開展具體工作時(shí),常發(fā)生精神懈怠、推諉逃避、處置不當(dāng)、溝通不善等情況,往往被民眾當(dāng)作對(duì)立面而遭受輿論攻擊,導(dǎo)致基層組織公信力被削弱,在開展治安實(shí)踐時(shí)易受到各方質(zhì)疑、阻礙和對(duì)抗。
二、市域治安問題成因的多維剖析
(一)沖突:廣泛存在的社會(huì)現(xiàn)象
由于當(dāng)前城市社會(huì)系統(tǒng)未必能夠按照預(yù)期目標(biāo)運(yùn)行,從而導(dǎo)致各類社會(huì)沖突存在其社會(huì)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社會(huì)沖突論的視角來看,沖突具有保障社會(huì)連續(xù)性、避免社會(huì)僵化、促進(jìn)社會(huì)整合的正面作用,但市域治安問題則是社會(huì)沖突的一種負(fù)面效應(yīng)。社會(huì)學(xué)意義上的沖突既包含不同社會(huì)階層之間的經(jīng)濟(jì)沖突或分配沖突,也包含異質(zhì)文化之間的文化沖突。城市社會(huì)沖突既是物質(zhì)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其沖突的維度相較于鄉(xiāng)村社會(huì)而言更加豐富。
我國(guó)現(xiàn)代化社會(huì)治理正在有序推進(jìn),但其仍存在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水平不相適應(yīng)的方面。其一,社會(huì)治理主體仍以政府機(jī)構(gòu)為主。地方政府基于對(duì)城市社會(huì)矛盾復(fù)雜性等現(xiàn)實(shí)因素的考量,對(duì)其他社會(huì)主體參與社會(huì)治理始終存有不完全信任的態(tài)度,在社會(huì)治理事務(wù)中放權(quán)不徹底、管理不適時(shí)、服務(wù)不周到,過度強(qiáng)調(diào)全過程監(jiān)管,對(duì)其他社會(huì)主體的專業(yè)化治理過程施加負(fù)面干擾,陷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治理困境。其二,完善的社會(huì)治理制度體系尚未形成。現(xiàn)行社會(huì)治理制度體系的責(zé)任和監(jiān)督機(jī)制不清,時(shí)常會(huì)形成制度運(yùn)行“空轉(zhuǎn)”的局面。其三,隨著“市民社會(huì)”興起,市民的權(quán)利意識(shí)高漲,但他們對(duì)公民意識(shí)的認(rèn)識(shí)仍不全面。市民對(duì)參與社會(huì)治理的責(zé)任和義務(wù)往往采取漠視和逃避態(tài)度,這是因?yàn)樗麄內(nèi)狈Α肮蚕砩鐣?huì)治理成果”的獲得感,因而對(duì)地方政府包攬社會(huì)治理的現(xiàn)狀抱以“不合作”的消極態(tài)度。
當(dāng)城市社會(huì)缺乏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臺(tái),同時(shí)市民又缺少自治和自助渠道時(shí),在矛盾沖突事件中就容易出現(xiàn)市民同以公安機(jī)關(guān)為代表的國(guó)家治安主體發(fā)生直接碰撞的情形,進(jìn)而導(dǎo)致市域治安問題產(chǎn)生。奧斯丁·西奧多·特克的權(quán)力沖突理論認(rèn)為,社會(huì)秩序建立在強(qiáng)勢(shì)社會(huì)主體對(duì)于一致性和強(qiáng)制性的平衡之上[4]。當(dāng)前無論是在市域治安實(shí)踐還是社會(huì)治理方面,地方政府及其公安機(jī)關(guān)作為強(qiáng)勢(shì)社會(huì)主體,對(duì)社會(huì)治理的權(quán)利義務(wù)分配缺乏思考,導(dǎo)致強(qiáng)勢(shì)社會(huì)主體介入社會(huì)治理的邊界模糊,進(jìn)而引發(fā)民眾與強(qiáng)勢(shì)社會(huì)主體之間的沖突。比如擾亂治安秩序的行為人可能在事前缺乏暢通的表達(dá)訴求、協(xié)調(diào)利益、保障權(quán)益的渠道,在自認(rèn)為相關(guān)利益遭受侵害后,其往往會(huì)轉(zhuǎn)而通過以非法方式進(jìn)行“維權(quán)”。
異質(zhì)文化之間的文化沖突不同于前述沖突。文化沖突不僅是索爾斯坦·塞林的文化沖突理論所認(rèn)為的社會(huì)主流文化同從屬文化之間的沖突,其還存在于實(shí)力相近、地位對(duì)等的社會(huì)主體之間。有時(shí),沖突的雙方并無顯著的實(shí)力和地位差距,只因在“文化觀念”、“價(jià)值判斷”、“行為模式”、“對(duì)某一社會(huì)現(xiàn)象或事件的認(rèn)識(shí)”等方面存在差異且無法調(diào)和,進(jìn)而發(fā)生文化沖突。例如,江蘇揚(yáng)州一女孩身著cosplay 服裝乘坐公交車,被一老年乘客持續(xù)謾罵的事件,就體現(xiàn)了雙方之間的文化沖突對(duì)公共安全秩序造成的不良影響。這種發(fā)生于平等社會(huì)主體之間的“文化沖突”也是導(dǎo)致市域治安問題產(chǎn)生的深層次原因。
(二)情境:犯因性因素交織的社會(huì)環(huán)境
犯因性是指可以誘發(fā)違法犯罪心理、提供違法犯罪機(jī)會(huì)或條件且具有互動(dòng)性的各種情境因素的性質(zhì)體現(xiàn)。米爾頓·巴倫的犯因性社會(huì)理論認(rèn)為社會(huì)及其文化中蘊(yùn)含著的犯因性因素——片面追求成功和地位的價(jià)值觀、抗拒權(quán)威、盛行欺騙的文化環(huán)境等,容易導(dǎo)致治安或犯罪問題的產(chǎn)生[5]。從宏觀的犯因性社會(huì)視角來看,城市社會(huì)中犯因性因素的增加會(huì)導(dǎo)致市域治安問題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上升。
隨著傳媒和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信息交互和文化傳播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高速且頻繁地運(yùn)行著。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深刻影響現(xiàn)實(shí)社會(huì)人類活動(dòng)的空間[6]。當(dāng)前,由于監(jiān)管力度不足、干預(yù)措施滯后、治理效能低下等現(xiàn)實(shí)困境制約,網(wǎng)絡(luò)空間極易成為城市社會(huì)生活的“陰暗角落”。民眾常用的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中藏匿著大量諸如散播功利主義價(jià)值觀、煽動(dòng)社會(huì)對(duì)立等各種有害信息,這些信息快速地交互和傳播于民眾之間,導(dǎo)致社會(huì)的犯因性因素不斷得到確認(rèn)和強(qiáng)化,受其影響的社會(huì)成員逐漸形成小團(tuán)體,并不斷吸納新成員加入,極易成為影響社會(huì)治安的不穩(wěn)定因素,加之城市公共空間中也存在諸多犯因性因素,有違法犯罪傾向的人受其影響后,就可能實(shí)施危害社會(huì)治安秩序的行為。例如,一些城市有部分區(qū)域存在社會(huì)治理的缺位,出現(xiàn)市容和衛(wèi)生狀況不佳、基礎(chǔ)設(shè)施損壞卻無人及時(shí)維修等狀況,這都會(huì)形成“破窗效應(yīng)”,給潛在的違法犯罪分子以“該地區(qū)權(quán)力真空、無人監(jiān)管”的心理暗示,降低了其違法犯罪的風(fēng)險(xiǎn)成本預(yù)判,進(jìn)而促使他們選擇實(shí)施危害社會(huì)治安秩序的行為。
(三)控制:人際關(guān)系的淡化和萎縮
社會(huì)原子化使人際關(guān)系的紐帶斷裂、分化、萎縮,社會(huì)關(guān)系朝著非人格化方向退化。一方面,在城市人口廣泛流動(dòng)的社會(huì)背景下,城市擁有規(guī)模龐大的外來常住人口。以上海市為例,截至2021 年末,本地常住人口為2489.43 萬人,其中外來常住人口高達(dá)1031.99 萬人①關(guān)于上海市常住人口的數(shù)據(jù)來源及擴(kuò)展信息,參見http://www.stats.gov.cn/sj/ndsj/2022/indexch.htm,2023 年2 月9 日訪問。。多數(shù)外來常住人口只身前往城市謀生,脫離了其原生家庭和原屬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在快節(jié)奏的生活和巨大的工作負(fù)荷壓力下,他們極易被邊緣化,形成缺乏歸屬感的“外群體”。另一方面,由于受當(dāng)前“獨(dú)居文化”、“單身文化”、“孤獨(dú)文化”等思潮的影響,許多城市居民缺乏與他人形成社會(huì)聯(lián)系的積極性,鄰里關(guān)系淡漠、朋友寥寥無幾、很少參加社交活動(dòng)的現(xiàn)象普遍存在于青年市民群體之中。人際關(guān)系淡化和萎縮結(jié)果的社會(huì)心理機(jī)制仍很復(fù)雜,當(dāng)前社會(huì)群體結(jié)構(gòu)和社會(huì)組織架構(gòu)的變化迫使相關(guān)人群走向了這一結(jié)果。他們內(nèi)心對(duì)人際關(guān)系的淡化和萎縮實(shí)際上處于一種類似于回避型依戀的緊張狀態(tài),而這種積壓于內(nèi)心的緊張最終會(huì)以各種形式爆發(fā)和釋壓,由此可能會(huì)引發(fā)各類市域治安問題。
社會(huì)原子化將會(huì)導(dǎo)致社會(huì)聯(lián)系的萎縮,社會(huì)聯(lián)系的萎縮將會(huì)引起社會(huì)控制的削弱,社會(huì)控制的削弱將會(huì)造成違法犯罪威懾遏制力量的衰退。特拉維斯·赫希的社會(huì)控制理論認(rèn)為,人之所以沒有實(shí)施違法犯罪行為,不僅是出于對(duì)該行為本身風(fēng)險(xiǎn)和成本的顧慮,同時(shí)還出于對(duì)實(shí)施該行為后可能會(huì)導(dǎo)致其社會(huì)聯(lián)系遭受損失的顧慮[7]。社會(huì)聯(lián)系就是個(gè)體的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和社會(huì)組織關(guān)系,包括與親人、朋友、鄰里、同學(xué)、同事、學(xué)校、雇主、工作單位、社團(tuán)組織等方面的聯(lián)系。市場(chǎng)化改革以來,人們的集體意識(shí)逐漸衰弱,相較于單一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下單位制和街居制的社會(huì)管理模式,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體制下現(xiàn)代城市社會(huì)各單位對(duì)其成員的控制力大幅下降,社會(huì)組織架構(gòu)的變化導(dǎo)致了社會(huì)控制被削弱。各單位對(duì)員工的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越不力,則單位對(duì)員工的控制力就越低,大量的市域治安問題肇事者屬于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較低的群體。總之,當(dāng)前市域治安問題頻發(f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huì)聯(lián)系的萎縮等問題導(dǎo)致了社會(huì)控制的削弱。
三、市域治安問題防控路徑的優(yōu)化
市域治安問題防控是一項(xiàng)系統(tǒng)性、綜合性工程,既要依靠治安主體發(fā)揮治安秩序維護(hù)的主導(dǎo)作用,又要依托基層組織發(fā)揮現(xiàn)代化社會(huì)治理的根本作用。市域治安問題的產(chǎn)生和頻發(fā)有其社會(huì)根源的深層次原因,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系統(tǒng)觀念、堅(jiān)持“三治融合、四防并舉”理念,將完善社會(huì)治理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與維護(hù)治安秩序的終極目的相融合,從整體層面思考和規(guī)劃市域治安問題防控路徑的優(yōu)化。
(一)緩和社會(huì)緊張,化解社會(huì)對(duì)立
緩和社會(huì)緊張是避免市域治安問題產(chǎn)生的治本之策,既要從客觀上提升弱勢(shì)社會(huì)成員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地位,又要從主觀層面化解其內(nèi)心的緊張狀態(tài)。首先,要建立健全重點(diǎn)覆蓋弱勢(shì)社會(huì)成員的社會(huì)保障體系。社會(huì)治理主體應(yīng)當(dāng)協(xié)同有關(guān)部門想方設(shè)法提高弱勢(shì)社會(huì)成員的物質(zhì)報(bào)酬,并為其提供獲得更多合法利益的渠道。公安機(jī)關(guān)要協(xié)同其他基層組織做好調(diào)查研究工作,在對(duì)市域治安問題進(jìn)行常態(tài)化統(tǒng)計(jì)的基礎(chǔ)上分析其人口統(tǒng)計(jì)學(xué)特征,并深挖導(dǎo)致問題產(chǎn)生的宏觀社會(huì)原因,以治安秩序維護(hù)為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提出完善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建議。其次,在城市管理的相關(guān)決策活動(dòng)中,要善于考量后續(xù)的銜接舉措,對(duì)利益攸關(guān)者做出妥善合理的安排。例如,2023 年2 月實(shí)施的《上海市住房租賃條例》以立法形式明確禁止將住房用于群租。對(duì)此,政府部門則要考慮原租戶的居住需求,并給予相關(guān)政策幫扶。再者,要加強(qiáng)社會(huì)心理服務(wù)體系建設(shè),打造“心防”工程。在社區(qū)、企業(yè)、工廠、學(xué)校等基層單位設(shè)立心理健康和精神衛(wèi)生服務(wù)機(jī)構(gòu),推進(jìn)服務(wù)的網(wǎng)絡(luò)化和全覆蓋;同時(shí),加強(qiáng)隊(duì)伍建設(shè),招募具備社會(huì)學(xué)、心理學(xué)、犯罪學(xué)等專業(yè)知識(shí)背景的社會(huì)工作者,面向基層單位提供心理咨詢服務(wù),開展心理輔導(dǎo)和治療,以及進(jìn)行心理健康宣傳教育。最后,要對(duì)大眾傳媒中存在的“急功近利”、“拜金主義”、“唯利是圖”等消極價(jià)值觀內(nèi)容進(jìn)行限制,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廣泛宣傳和諧包容、理性平和的正能量?jī)r(jià)值觀內(nèi)容,提高對(duì)自食其力勞動(dòng)者的社會(huì)評(píng)價(jià),增強(qiáng)他們對(duì)自身的職業(yè)認(rèn)同感。
化解社會(huì)對(duì)立是減少市域治安問題發(fā)生的有效途徑。一方面,要完善分配制度,通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努力形成“橄欖型”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另一方面,社會(huì)治理主體應(yīng)當(dāng)持續(xù)發(fā)揮引導(dǎo)作用,并積極同文化部門進(jìn)行協(xié)作,提供交流平臺(tái),主動(dòng)發(fā)聲引導(dǎo),鼓勵(lì)社會(huì)參與,促進(jìn)城市社會(huì)中多元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dòng)與改良融合,進(jìn)而有效推動(dòng)世界多元文化同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文化之間的交流與適應(yīng)。同時(shí),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要注重化解不同文化價(jià)值理念之間的沖突與對(duì)立,及時(shí)阻斷相關(guān)各類矛盾的傳播和擴(kuò)散,努力促進(jìn)多元社會(huì)治理主體共建共治共享和諧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的形成。
(二)貫徹“零容忍”處置理念,治安行為精細(xì)化運(yùn)作
“零容忍”處置理念體現(xiàn)的是有利于填補(bǔ)社會(huì)治理漏洞,有利于提升市域治安問題防控的綜合性和系統(tǒng)性,進(jìn)而有利于保障治安秩序維護(hù)目的實(shí)現(xiàn)的治理思維。20 世紀(jì)90 年代,紐約市警察局開展的“零容忍”警務(wù),在短期內(nèi)迅速扭轉(zhuǎn)了本市治安秩序混亂的局面,隨后“零容忍”警務(wù)策略被全球各地廣泛借鑒并獲得普遍成功。社會(huì)治理也需要借鑒“零容忍”處置理念的警務(wù)經(jīng)驗(yàn),以“治早治小”、“防微杜漸”的工作模式將社會(huì)失序遏制在萌芽階段,以此防范“破窗效應(yīng)”。社會(huì)治理主體要在城市市容衛(wèi)生、環(huán)境保護(hù)、工商管理、交易消費(fèi)、社區(qū)管理、建設(shè)開發(fā)、網(wǎng)絡(luò)治理等方面建立社會(huì)治理快速反應(yīng)機(jī)制,對(duì)相關(guān)領(lǐng)域中的破壞行為實(shí)施“零容忍”策略,對(duì)細(xì)微的破壞行為進(jìn)行及時(shí)干預(yù),適當(dāng)增加懲處力度,進(jìn)而不斷消除城市社會(huì)生活中的犯因性,最終通過營(yíng)造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為優(yōu)化治安治理創(chuàng)造條件。同時(shí),還要持續(xù)加強(qiáng)社會(huì)治理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推進(jìn)前沿技術(shù)在社會(huì)治理中的應(yīng)用,以實(shí)現(xiàn)“嗅探敏銳、數(shù)據(jù)共享、實(shí)時(shí)交互、協(xié)同配合”的智能化社會(huì)治理愿景,推動(dòng)社會(huì)治理向社會(huì)“智”理轉(zhuǎn)型,用科技為“零容忍”處置理念的社會(huì)治理賦能。
治安行為是聯(lián)結(jié)治安主體、治安規(guī)范和治安實(shí)體的中樞,也是治安秩序結(jié)構(gòu)中的核心要素[8]。提升治安行為效能有利于修復(fù)治安秩序結(jié)構(gòu),而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的路徑是治安行為精細(xì)化運(yùn)作。治安行為精細(xì)化內(nèi)涵不僅要求治安行為不應(yīng)過分介入社會(huì)生活,還要求對(duì)治安行為本身加以優(yōu)化和完善,使治安行為的運(yùn)作既精準(zhǔn)又細(xì)致。一方面,要為治安行為劃定合理邊界,使公安機(jī)關(guān)減少參與非警務(wù)活動(dòng)。通過優(yōu)化空間治理,為治安行為的介入設(shè)限,既要平衡秩序與自由的關(guān)系,又要保障治理張力和社會(huì)活力,以促進(jìn)治安秩序的再生產(chǎn)[9]。另一方面,公安機(jī)關(guān)進(jìn)行治安實(shí)踐活動(dòng)時(shí),要落實(shí)責(zé)任和監(jiān)督機(jī)制,強(qiáng)化預(yù)案編制和各警種、各部門的協(xié)調(diào)聯(lián)動(dòng),實(shí)施分類管理、分級(jí)處置,對(duì)日常的治安秩序維護(hù)和突發(fā)的治安事件與案件的處置進(jìn)行流程再造,提升工作質(zhì)效和應(yīng)急處突能力。公安機(jī)關(guān)要聯(lián)合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針對(duì)市域轄區(qū)范圍內(nèi)的治安秩序狀況進(jìn)行調(diào)研和評(píng)估,及時(shí)掌握治安實(shí)體產(chǎn)生的新變化、新形式,通過事前預(yù)防和預(yù)警、事中控制、處置、報(bào)告、輿情管控、事后治安秩序重建等工作流程,開展多方位、全過程的治安實(shí)踐。
(三)理順基層治理邏輯,提升基層治理質(zhì)效
市域治安問題防控與社會(huì)治理重心在于維護(hù)基層穩(wěn)定,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huì)治理格局是理順基層治理邏輯,提升基層治理質(zhì)效的動(dòng)力保障。
首先,要理順政府與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之間的關(guān)系。在基層治理中,政府要對(duì)非必要管控領(lǐng)域和非核心安全領(lǐng)域放權(quán),發(fā)揮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的專業(yè)化優(yōu)勢(shì),推進(jìn)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的依法自治。政府的角色應(yīng)當(dāng)由主導(dǎo)向負(fù)責(zé)轉(zhuǎn)變[10],對(duì)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輔之以必要的人力、物力、財(cái)力支持,政府不必參與或監(jiān)控基層治理的各個(gè)環(huán)節(jié),而是要建立基層治理考核評(píng)估機(jī)制,注重對(duì)治理質(zhì)效結(jié)果的評(píng)價(jià)。政府要通過宣傳教育提升市民的公民意識(shí),鼓勵(lì)他們參加各類社會(huì)治理組織,同時(shí)鼓勵(lì)其他社會(huì)治理主體廣泛搜集民意,引導(dǎo)市民為基層治理建言獻(xiàn)策,并要以社會(huì)治理成果之“共享”反向促進(jìn)社會(huì)治理之“共建”和“共治”。
其次,要理順基層組織之間的關(guān)系。對(duì)屬于市域治安問題范疇內(nèi)的防控工作,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以公安機(jī)關(guān)為核心,通過創(chuàng)新合作方式推進(jìn)社會(huì)治安防控體系建設(shè)的寬度和廣度[11]。公安機(jī)關(guān)對(duì)基層治理中可能存在的影響市域治安秩序的因素要向其他基層組織進(jìn)行通報(bào)并尋求協(xié)同解決之策;其他基層組織發(fā)現(xiàn)可能影響市域治安秩序的情況后也應(yīng)及時(shí)將相關(guān)信息報(bào)至公安機(jī)關(guān)。公安派出所、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huì)、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huì)之間要建立常態(tài)化治安信息共享機(jī)制,通過搭建治安信息共享平臺(tái),強(qiáng)化各方溝通協(xié)作;同時(shí)要推行治安隱患排查和治安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機(jī)制,持續(xù)推進(jìn)治安預(yù)警關(guān)口前移。
最后,基層治理要兼顧線上和線下同步運(yùn)行。社會(huì)治理主體要加強(qiáng)對(duì)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內(nèi)容的審核監(jiān)督,暢通民眾的舉報(bào)渠道。尤其要對(duì)傳播極端功利主義等錯(cuò)誤價(jià)值觀的各種負(fù)面信息、虛假信息、煽動(dòng)性信息等內(nèi)容及時(shí)進(jìn)行清理,同時(shí)采取適當(dāng)措施削弱網(wǎng)絡(luò)空間中的“匿名化”效應(yīng),持續(xù)加強(qiáng)對(duì)擾亂網(wǎng)絡(luò)傳播秩序行為的懲處力度。社會(huì)治理主體應(yīng)當(dāng)重視自身在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中話語權(quán)的體現(xiàn),通過自主設(shè)立社交媒體賬號(hào)或培育扶持合作賬號(hào)等方式積極發(fā)聲,打破“沉默的螺旋”以正本清源,不斷消除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的犯因性。
(四)構(gòu)建親密社會(huì),強(qiáng)化社會(huì)控制
基層組織要在增進(jìn)市民人際關(guān)系、修復(fù)社會(huì)聯(lián)系、構(gòu)建親密社會(huì)、強(qiáng)化社會(huì)控制等方面發(fā)揮組織引領(lǐng)作用,同時(shí)各基層組織之間也要積極協(xié)同配合,共同織密市域社會(huì)人際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公安派出所和治安保衛(wèi)委員會(huì)要在各自的管轄范圍內(nèi)對(duì)市域治安問題背后隱藏的市民人際關(guān)系矛盾糾紛產(chǎn)生的深層次原因進(jìn)行挖掘,掌握和分析轄區(qū)民眾的人際關(guān)系基本情況,并及時(shí)將相關(guān)問題反映給轄區(qū)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huì),為其開展工作提供信息支撐。
基層組織要在管轄范圍內(nèi)為市民設(shè)定共同的價(jià)值目標(biāo)、創(chuàng)造共同的體驗(yàn)經(jīng)歷,使他們共享社會(huì)服務(wù)及治理成果。首先,基層組織要在市民中開展宣傳教育。選擇社區(qū)內(nèi)人際關(guān)系和諧的典型事例,利用豐富多樣的宣傳和推廣方式,消解“獨(dú)居文化”、“單身文化”、“孤獨(dú)文化”等帶來的負(fù)面影響,營(yíng)造親密和諧的社會(huì)氛圍。其次,基層組織要在社區(qū)內(nèi)積極開發(fā)各種類型的“鄰里守望”項(xiàng)目,并以項(xiàng)目為平臺(tái),建立社區(qū)志愿者隊(duì)伍。要掌握社區(qū)內(nèi)獨(dú)居老人、獨(dú)居青年、留守少年兒童、單親家庭、經(jīng)濟(jì)困難家庭、失業(yè)者、殘疾人等弱勢(shì)人員的基本情況和現(xiàn)實(shí)困境,發(fā)動(dòng)社區(qū)內(nèi)的普通民眾、社區(qū)志愿者、基層組織等一起對(duì)弱勢(shì)人員進(jìn)行幫扶,開展經(jīng)常性走訪慰問,并鼓勵(lì)他們參與社區(qū)事務(wù)和活動(dòng)。再者,基層組織要增強(qiáng)對(duì)社區(qū)民眾矛盾糾紛的化解工作能力,優(yōu)化調(diào)解流程。要善于組織發(fā)動(dòng)社區(qū)民眾共同聘請(qǐng)退休法官、退休基層干部、律師等人士擔(dān)任調(diào)解員,吸收熱心民眾參與矛盾糾紛調(diào)解過程,以強(qiáng)化調(diào)解的專業(yè)性、民主性和公信力,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最后,基層組織要廣泛開展豐富多樣的文化活動(dòng)和社交活動(dòng),為促進(jìn)市民和諧人際關(guān)系的形成搭建平臺(tái)。同時(shí),各社會(huì)治理主體也要加強(qiáng)對(duì)企事業(yè)等單位的勞動(dòng)保障監(jiān)督,多措并舉維護(hù)勞動(dòng)者的合法權(quán)益,以持續(xù)增強(qiáng)企事業(yè)等單位的社會(huì)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