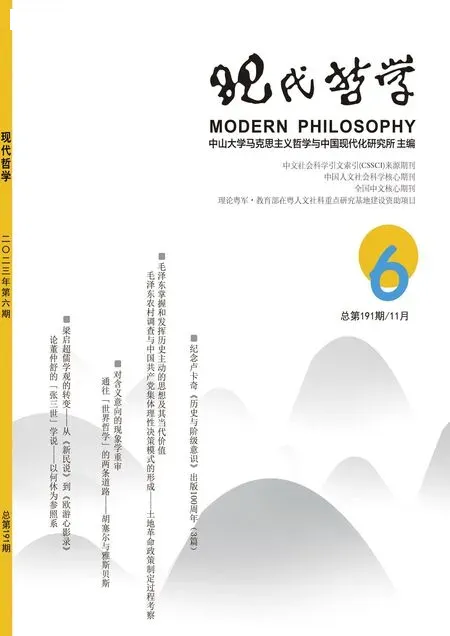杜預“體元”說探源
——兼論《左傳》與《公羊》的元年之爭
劉禹彤
一、引言:唐人的疑問
《春秋》經文以“元年春王正月”為開端,杜預注曰:“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1)[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清嘉慶刻本影印)第1冊,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5頁。杜氏以《春秋》為史記大綱,《左傳》為史實詳目。因此,“元年春王正月”六個字中,年、春、王、月四字皆史官記事通例,唯獨“元”與“正”寓含《春秋》特筆。杜預認為不言“一年一月”而言“元年正月”,是希望人君即位能做到“體元以居正”。唐代之后史書于新君即位之際,常美其辭曰“體元居正”。但“體元”的含義究竟是什么,成為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科舉考試明經一科的考題:
問:褒貶之書,宣父約于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于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鄒氏、夾氏,學既不傳,尸子、沈子,復為何者?鄙夫未達,有佇嘉言。(2)[清]徐松撰、孟二冬補正:《登科記考補正》中冊,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第574頁。
此時士人應試明經科,義理皆據《五經正義》。孔穎達主持的《五經正義》于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年)編成,后經多位學士校訂增損,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正式頒行。杜預以“體元”注解《春秋》之元,孔穎達《左傳正義》釋曰“與元同體”,語焉而不詳,顯然不孚眾望。因此,在孔穎達之后近二百年(803年)的官方考題還發出了“經有體元,且無訓說”的疑難。我們看不到唐朝考生的回答,歷朝紛解亦難得其要。本文試圖探究的正是這道科舉考題。
二、宋儒的回答:體元即體仁
胡安國《春秋》學多有得于程頤,程頤《春秋傳》沒有直接釋“元”之義,但伊川在注《周易》時,提出以“體仁”解釋“體元”。《易·乾》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程頤注曰:“體法于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3)[宋]程頤撰、王孝魚點校:《周易程氏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頁。“體”即效法之義,“體元”即效法仁道。程頤以元解仁,從屬于以儒家仁義禮智對應《乾卦》元亨利貞的基本邏輯,然而,不僅《周易》有元,《春秋》亦有元,六經之間存在統一性,于是勾連《周易》與《春秋》的解釋得到宋儒的廣泛認可。胡安國《春秋傳》最早據此提出對“體元”的系統見解: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于正矣。(4)[宋]胡安國撰、錢偉強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頁,標點有改動。
為了證明程頤以仁解元的合理性,胡安國用了巧妙的論證結構。《胡傳》短短二百字的注解依次征引了程頤、杜預、孟子、董仲舒四家的說法。首先,與胡安國時代最為接近的程頤強調《春秋》是圣人之用,胡安國開頭便直指《春秋》之元是“人君之用”,《周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天之用”,“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地之用”。《春秋》言人,《周易》言天地,共同窮盡了天地人三才之用。接下來,《胡傳》正式進入杜預“體元”說的訓解。程頤認為“體”是效法之義,但按照胡安國的邏輯,人君與宰相分屬“體元”與“調元”之職,“體元”是體,“調元”是用,即區分了元的體和用兩個維度。“體元”之體即“體用”之體。胡安國強調整部《春秋》是人君之用,而《春秋》之體在元,明體而達用,元之體可以統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君之用。
換言之,胡安國理解的“體元”是“以元為體”。那么,“元”該如何解釋?胡安國指出,“元即仁也,仁,人心也”。程頤早已指出“體元”與“體仁”互通,胡安國的推進乃是引入孟子以仁為人心所固有之善端的觀點,鞏固元與仁之間的關系。董仲舒對仁的看法異于孟子,孟子以仁為人心,但董仲舒言“仁者,天之心也”(5)[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62頁。,將孟子拉回“人心”的仁重新推向“天心”。《胡傳》序言繞過董仲舒與何休,指出孟子才可謂得《春秋》真傳。在“元即仁也,仁,人心也”的解釋中,董仲舒的天命圣人與建國立教問題,被胡安國內化成道德人心問題。
最后,胡安國為了證明自己的解釋并不脫離傳統《春秋》學脈絡,援引了董仲舒《天人三策》。《胡傳》所謂“《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一于正矣”,幾乎是程頤和董仲舒原話的拼接,首句“《春秋》深明其用”是程頤的觀點,“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莫不一于正”出自董仲舒《天人三策》。以漢代首席《春秋》經師董仲舒作結,胡安國的整個論證看似繼承了傳統,但思想內涵已完全不同于董仲舒,也不同于杜預。
宋儒對《春秋》學的關注有其側重點,比如孫復等宋初學者關注尊王問題,二程以降的《春秋》學關注王霸義利之辨。宋儒普遍繞過漢儒,轉而將孟子思想作為《春秋》綱領。因此,直到宋代才正式出現了孟子傳《春秋》的論調。《孟子·公孫丑上》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道行仁,霸道假仁,王霸的分界線在于王者有仁心,而霸者徒有仁表。因此,仁與不仁是胡安國研習《春秋》時的判教標準。為了讓“仁”成為最高的標準,最簡便的做法就是將之作為《春秋》開門見山的第一要旨,即將“仁”與“元”進行義理上的整合。胡安國反復強調“元即仁”:
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建立萬法,酬酢萬事,帥馭萬夫,統理萬國,皆此心之用也。堯、舜、禹以天下相授,堯所以命舜,舜亦以命禹,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周公稱乃考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故一心定而萬物服矣。(6)[宋]胡安國撰、錢偉強點校:《春秋胡氏傳》,第37-38頁。
漢代公羊家眼中的《春秋》是孔子寄法后世的虛擬王朝,《春秋》之元是天命降祚于新王改元立教的標志。因此,改元不是人心問題,而是天命與政教的問題。但在宋儒看來,改元已是遙遠的故事。南宋王應麟言:“戰國而下,此義不明。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后元,始變謂一為元之制。漢文十有六年,惑方士說,改后元年,景帝因之,壬辰改中元,戊戌改后元,猶未以號紀年也。武帝則因事建號,歷代襲沿,《春秋》之義不明久矣。”(7)[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68頁。從歷史實際來看,漢武帝之后的帝王在位期間皆可隨意改元。改元早已在歷史進程中喪失了天命的含義,宋人不得不更新對“元”的認識,才能讓《春秋》免于束之高閣的宿命。因此,胡安國在將“元”理解為“仁”之后,還必須破除“元”與“天命”的關聯。《胡傳》曰:“《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于天,以義立命,不委于命,而宇宙在其手者也。”(8)[宋]胡安國撰、錢偉強點校:《春秋胡氏傳》,第397頁。“不任于天”“不委于命”,胡安國認為人可以通過能動性屹立于天地之間,而不需要被動地仰賴天命。
換言之,宋儒開啟了不任天命、但任人心的《春秋》學。胡安國《春秋傳》序言開頭便說:“《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9)同上,第1頁。胡安國越過兩漢魏晉的今古文《春秋》學,遙指發明人心的孟子才可謂得《春秋》真傳。胡安國之后,《春秋》“傳心”成為宋人的普遍認識,胡安國之侄胡寅繼承《胡傳》以人心為歸的基本思路而加以細化:
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于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妄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赗,邪心也;祭伯來,貳心也;益師卒而不日,慢心也;仁則無是矣。(10)[宋]胡寅撰、劉依平注解:《讀史管見》下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1071頁。
三代的更迭不是天命的轉移,而是仁心的得失。仁貫穿古今,成為宋儒遙契三代精神的線索或曰道統。胡寅先通過造字法認定“元”與“仁”本是一字,元既然是人心之仁,繼而區分出仁心的對立面——妄心、賊心、貳心、慢心。《春秋》作為“傳心之要典”所要保住的是仁心,而所應破除的就是妄心、賊心、貳心與慢心,《春秋》完全成為一部修養心性之學。總之,胡安國的“體元”是“以仁為體”,胡寅的解讀實際上是進一步“以心為體”。
宋儒對“體元”的改造,使得杜預遺留的問題第一次得到系統解釋,直至晚清依然有學者遙相呼應。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引用王應麟的說法:“《春秋》書元年,人君之元,即乾坤之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眾非元后何戴?后體元則仁覆天下也。”(11)[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67頁。在董仲舒等漢儒看來,“元”是國君的元年,新君改元然后施行政教,因此,元與眾庶不產生直接關聯。但在宋人王應麟看來,元不需要以圣王為中介,而是直接與天下蒼生相關;眾人雖然不是作為元后的天子,但不代表眾人與元無關;天子體元即體仁,體仁便可使仁覆天下之人。經過宋人的努力,漢人縹緲的天命落實并收束進以仁為核心的人心修養體系中,其優點是使元具備了徹上徹下的主導性。但與此同時,《春秋》學作為仁學的下屬,逐漸喪失了獨立的品格。
三、“體元”說疑云
在宋儒之前,唐人多雜糅杜預《左氏》學“體元”說與兩漢《公羊》義理。如《舊唐書》所載,唐肅宗時的一道詔書稱:“欽若昊天,定時成歲,《春秋》五始,義在體元,惟以紀年,更無潤色。”(12)[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262頁。《春秋》五始本為《公羊》家言,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五個開端,作為從天道至王道的層層相扣,勾勒“大一統”的邏輯線索。杜預既然想成一家之言,必然反對《公羊》的元年釋義,因此沒有直接采用《公羊》的五始說。但唐肅宗詔書所言“《春秋》五始,義在體元”,將《公羊》“五始”的根本意義嫁接到杜預“體元”說之中。
初唐長孫無忌也參與了《五經正義》的修訂工作,他對“體元”的理解顯然也雜糅了《公羊》的受命改元說。《通典》記載長孫無忌之言曰:“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有舊章。”(13)[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223頁。長孫無忌認為,唐高祖李淵作為開國皇帝有“體元居正”之功,但他顯然不甚明了杜預“體元居正”之義,將《公羊》家的“受命改元”和《左氏》家杜預的“體元居正”混而為一。有唐一代,始終沒有學者對杜預“體元”說提出恰當解釋,直到宋人給出了“體仁”的回答。
朱子對《胡傳》已頗有微詞,但元朝以《胡傳》取士,直到晚明才遭到士林拒斥。王夫之《春秋家說》認為必須先肅清《胡傳》,方可言《春秋》。至清乾隆年間,《胡傳》乃在官方廢除。明末清初對胡安國的反思從對“體元”的解釋開始。黃宗羲認為,胡安國所謂的“體元”與“調元”皆附會之辭。(14)[清]黃宗羲撰、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14頁。王夫之也認為將“體元”解釋成“體仁”,更多是宋儒懸于《春秋》元年之上的空帽,實屬強言而立義:

王夫之反對宋儒《春秋》學以“仁”解“元”的傳統,若國君即位第一年言元年,元代表“以仁體元”,是否意味著第二年、第三年就不再需要體仁?王船山的反駁隸屬對程朱理學的整體反思,即警惕宋儒眼中的天與人“各有畛而不相貫”。仁應當貫穿始終,不能只是高懸于《春秋》開頭的“元年”之上。實際上,《春秋》之“元”在王夫之看來無實義,若強行賦予《春秋》之元以特殊或深刻的義理,反而容易導致元與萬物的截斷,或曰天與人的分隔。值得注意的是,胡安國所謂《周易》乾元、坤元與《春秋》之元三者并立,分別代表天地人三才之用。然而,在王夫之對胡安國的復述中,“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春秋》之元與《周易》乾坤之元已經合而為一。換言之,胡安國認為《春秋》之元與《周易》乾坤之元相互獨立,歷代《春秋》學者皆重視起首之“元”,不會輕易將《春秋》之元與《周易》乾坤之元等量齊觀,否則難免破壞其中一經的獨立性,而更有可能是以《春秋》為《周易》的附屬。在更為服膺《易》學的王夫之眼中,《春秋》之元即隸屬于《周易》元亨利貞之元。
在船山之前,已有宋儒試圖會通《春秋》之元與《周易》之元。明末諸儒指責以“體仁”解“體元”實屬疊床架屋之后,《易》學的視角重新為杜預的“體元”說提供了活力。清朝匯通《周易》乾元與《春秋》之元逐漸成為解釋主流,認為《春秋》開頭所體貼的正是《周易》元亨利貞之道。比如《周易·乾·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曹元弼釋曰:“‘首出庶物’二句,人君體元成既濟之事。”(16)[清]曹元弼撰、吳小峰整理:《周易集解補釋》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頁。《周易》無“體元”一詞,在杜預之后,“體元”才流行開來。乾卦為首,萬物創生,曹元弼認為乾首即要求人君體元。《易·系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曹元弼釋曰:“《易》隱初入微,元之神也。知幾其神,圣人體元之神也。”(17)[清]曹元弼撰、吳小峰整理:《周易集解補釋》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47頁。在曹元弼看來,“體元”一詞可以脫離《春秋》而成為一個普遍概念,人君與圣人皆應“體元”。曹元弼的“體”不再是程頤的“效法”之體,也不是胡安國眼中的“體用”之體,而是“體會”之體,人君與圣人應當能夠體會元之精妙。
晚明以降,學者對宋儒以“體仁”解“體元”破而不立,后續即使《左傳》學者也沒有提出對“體元”的見解。清代乾嘉考據之學興起后,學者不斷回溯兩漢之學,《左傳》學也以追蹤杜預之前的賈逵、服虔為尚,劉文淇《春秋左傳舊注疏證》、洪亮吉《春秋左傳詁》等著作皆未討論杜預“體元”說。此外,清代《公羊》學復興之后,討論的核心回到了“元”本身。晚清《公羊》家更關心孔子法的普遍性,比如康有為試圖會通《春秋》之元與《易》之元有更明確的問題意識,即證明孔子之道有一個形而上的“元”作為總攝與歸依。(18)[清]康有為撰、樓字烈整理:《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24頁。康有為列舉《易》“大哉乾元,乃統天”、何休“元者,氣也”、易緯“太初為氣之始”、春秋緯“太一含元,布精乃生陰陽”,以及《易》“太極生兩儀”等說法,認為這些說法共同表明“孔子之道,運本于元,以統天地”。熊十力也直言“《春秋》與《大易》相表里。《易》首建乾元,明萬化之原也。而《春秋》以元統天,與《易》同旨”。(19)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3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019頁。同時,熊十力再次回歸被晚明學者拋棄的宋代解釋,重新提出“元”就是“仁”:“三統原是一統,一者仁也。《春秋》始于元,元即仁。雖隨世改制,而皆本仁以為治。”(20)同上,第1049頁。熊十力重拾宋儒的解釋,但問題意識與宋儒不同。在熊氏看來,舊內圣可以開出新外王的核心在于“仁”。“元”作為新朝改制的標志,內圣的核心“仁”在這一“隨時改制”的過程中,依然可以為新治統提供源源不竭的能量。因此,熊十力眼中的“體元”即“本仁”,以另一種方式回歸了宋儒以仁解元的傳統。
綜上可見,唐宋到明清乃至近代的解釋史幾經兜轉,依然沒有澄清唐人提出的問題。我們只有回到杜預及其能夠獲取的漢代思想資源,才能廓清“體元”說的本來面目。
四、西漢開元與東漢體元
不少學者認為杜預“體元”說來自董仲舒,比如中唐的劉蕡曾上疏曰:“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21)[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第15冊,第5068頁。日本的竹添光鴻也認為,杜預的“體元居正”繼承的是董仲舒。竹添光鴻的證據是董仲舒《對策》言:“《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敢一于正。”竹添光鴻指出,杜預“體元居正”蓋本于此。(22)[日]竹添光鴻:《左傳會箋》,于景祥、劉海松整理,沈陽:遼海出版社,2008年,第4頁。“居正”說的確可謂繼承了董仲舒這段話中反復強調的“正”,但“體元”之“體”從何可見?董仲舒論新王受命改制,改元即改制的首要任務。杜預有意與《公羊》家立異,斷非沿用董仲舒此說。
“體元”一詞非杜預首創,依目前可見,杜預之前有兩篇文獻提到“體元”,一是《易緯》,二是班固《東都賦》。《易緯·乾鑿度》曰:“生曰象,又假生曰寓,化象物邪,象正體元。”(23)[清]趙在翰輯,鐘肇鵬、蕭文郁點校:《七緯》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24頁。大意謂萬物由象而生,“象正體元”應是一個主謂詞組,象可正則體可元。《易緯》這段話前后有闕,殆與杜預“體元”關系甚微。那么,杜預之前完整可考的“體元”說還剩班固的《東都賦》。
班固以《漢書》奠定其史家地位,以《白虎通》集兩漢經說大成,又以《兩都賦》聞名天下,位列《文選》之首。因此,《兩都賦》作為經史大家班固的代表作,不能單純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加以解讀。《毛傳》所謂“升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漢賦是《詩經》六義“風雅頌賦比興”之賦的發展。劉勰《文心雕龍·詮賦》稱贊以京都賦為代表的漢大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體國經野”語出《周官》,后多用于指稱經世之學,可見漢大賦與漢代經學有同轍之誼。并且,班固《兩都賦》的創作本身便帶有強烈的經世意圖。《兩都賦》即《西都賦》和《東都賦》的合稱。其創作動機是東漢遷都洛陽之后,部分國人懷念西都長安,欲復西漢之舊。《兩都賦》對比西都長安和東都洛陽,以糾時人心態:長安和洛陽的對比不止是兩座都城的較量,更是西漢與東漢不同精神氣象的呈現;時人思長安不只是思念長安的繁華,而是王莽之后人心思漢的延續;人心思漢也不只是對一個朝代的懷念,而是對“漢德”的歸依;(24)《后漢書·盧芳傳》曰:“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后漢書·馮衍傳》曰:“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參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05頁;《后漢書》第4冊,第963頁。)漢德不僅僅是漢代之德,更是唐堯以來圣王相傳,又經孔子《春秋》總成的最高德性。然而,漢祚中缺,東漢再受命,如何界定東漢與西漢的關系,不僅是東漢帝王的問題,還是班固《兩都賦》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光武)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蕩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25)[清]高步瀛撰,沈玉成、曹道衡點校:《文選李注義疏》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4-162頁。
班固為我們理解“體元”之義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西漢“開元”、東漢“體元”。東漢必須符合漢德的召喚,才能得天下之心。因此,除了《兩都賦》之外,班固還“作《典引篇》,述敘漢德”(26)[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第5冊,第1375頁。。與班固同時的儒生也多有歌頌漢德之文。班固的父親班彪曾言:“百姓謳吟,思仰漢德。”(27)同上,第1323頁。東漢士人與百姓皆心慕漢德,“漢德”成為聯結西漢與東漢的精神紐帶。那么,如何將這條精神紐帶落實到政治層面?東漢政權自稱“更受命”,即不以開創性的王朝自任,而是對前朝的繼承與中興。東漢的創立不是為了尋求新突破,而是要盡快恢復被擾亂的舊秩序。因此,班固提出了東漢再受命的另一種表述:西漢“開元”,東漢繼承漢德而稱“體元”,即“系唐統,接漢緒”,與西漢之元同體。
可見,班固“體元”之體來自《公羊》學的“繼體守文”之體。《公羊》文九年傳言:“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繼文王之體,即在血脈與精神上繼承文王;守文王之法度,即在制度與文為上繼承文王。繼體守文是對受命王之后每一代王者的要求。光武帝的確是漢室血脈,故可稱得上繼體。因此,班固稱東漢“體元”而立,符合東漢再受命的自我定位,并且順應了時人對漢德的忠心。但東漢不止是對西漢的繼承,實際上,班固認為東漢是“繼體而不守文”的王朝,《東都賦》稱光武帝“體元立制”,體元即繼西漢之體,立制即創東漢之制: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28)[清]高步瀛撰,沈玉成、曹道衡點校:《文選李注義疏》第1冊,第218-219頁。
時人皆歌頌漢德,但班固認為鮮有人真懂漢德。漢德不是“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將經書倒背如流也無與于漢德,因為漢德在于溫堯之故而知漢之新。東漢與西漢的不同在于東漢敢于“知新”,更敢于將經義落實到現實政治中。《西都賦》只贊美長安城的金碧輝煌,“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珰”;《東都賦》全篇展現的則是東漢禮制的完備,“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最后班固以三雍之詩作結,即《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三雍是重要的經學制度設計,班固用“體元立制”重新定義漢德,東漢在繼承西漢的血脈之后,經學與漢制有了更實際的結合,真正落實了唐堯至孔子孕育的漢德。《兩都賦》將漢德與西漢剝離開來,漢德不僅屬于西漢,因為漢德的實質是堯道。“元”即“漢德”,西漢開元可以算漢德的開端;但東漢體元,繼漢德之體,與堯道融為一體,成為漢德的“中興”。
可見,杜預注《春秋》“元年春王正月”曰“體元以居正”,極可能是取班固《東都賦》所代表的東漢“體元”之義與《公羊傳》之“大居正”合成一新詞。同時,班固的“體元”說可以成為杜預突破兩漢《春秋》學“元年”解釋的方便法門。
五、杜預與“繼體改元”
即便我們難以斷言杜預直接繼承了班固的西漢“開元”與東漢“體元”說,但以“體元”為“繼體改元”在杜預的整體思路中也完全成立。兩漢《春秋》學以《公羊》學為主導,《左氏》學也分享了很多《公羊》學的基本預判。因此,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指責兩漢《左氏》家“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29)[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1冊,第57頁。,認為賈逵、服虔等《左氏》先師自亂家法,表明自己“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即打算徹底與兩漢《公羊》學立異。唯其如此,《左傳》才能成為真正獨立的解釋系統。杜預《左傳》學的獨立,正是以解釋《春秋》第一個字“元”為開端。
許慎《五經異義》沒有記載《公羊》與《左傳》關于“元年”的爭議,表明直到東漢中后期,《左氏》的元年釋義都不足與《公羊》抗衡。比如,賈逵《左氏長義》只是指責《公羊》讬魯隱公為受命王,以元年為新王受命元年是名不正言不順,但并沒有提出《左氏》自己的元年釋義。晚于杜預的徐彥《公羊疏》第一次明確指出了《公羊》與《左傳》元年釋義的尖銳對立:
若《左氏》之義,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讬王于魯,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30)[漢]何休注、[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頁。
《公羊》家認為《春秋》讬王于魯,即讬魯隱公為新王即位改元。然而,杜預認為元年是魯隱公的元年,而王正月是周平王的正月。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于祖廟,于每月初一告朔朝廟,領受周天子的歷法和政令。新任天子或諸侯于正月即位,同時改稱元年。這樣一來,《春秋》所有諸侯國的新君即位改稱元年都吻合歷史傳統。杜預所謂新君即位“體元居正”,此“體元”即“繼體守文”之“體”,繼體有兩層含義,一是繼承始受命先祖之體,二是繼承先考之體,新君即位同時繼承受命先祖與先考之體。在杜預看來,新任天子與諸侯都是繼體君,皆可改元,故稱“體元”。
班固認為東漢繼承西漢之體,故稱“體元”,杜預將之用于解釋《春秋》之“元年”,元不是新王之元年,而是繼體君之元年,不僅提出了《左氏》自己的元年釋義,還第一次有力攻擊了《公羊》的“王魯”說。杜預深知,一旦擊破王魯說,將會動搖《公羊》學的根基。魯隱公只是歷史上一個普通的諸侯,還是寄寓了《春秋》之法的新王?《公羊》家預設“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因為只有王者才有資格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春秋》假讬魯國承擔起天下化首的重任,只有讬王于魯,《春秋》大一統的義理才有歸依。“王魯”與“大一統”實質上都是孔子的立法,杜預“體元”說所要反駁的正是孔子立法這件事本身。
杜預既然認為元年是繼體君之元年,而非受命王之元年,那么孔子的身份就發生了偏轉。如果《春秋》沒有讬新王受命于魯,魯隱公只是魯國漫長歷史中的一個諸侯,那么《春秋》就只是周代歷史長卷中的一頁,作為魯史之《春秋》自然是周公之法的延續,何來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之說?杜預《春秋序》引一家之言孔子為素王、左丘明是素臣,并未加反駁,表明他不反對孔子是素王,但他眼中的“孔子素王”更像一個比喻:孔子不是《公羊》家眼中創作《春秋》的真素王,而是孔子繼承周公之志修《春秋》,就像素王一般。杜預《春秋序》言:“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31)[清]阮元校刻:《阮刻春秋左傳注疏》第1冊,第36頁。孔子是周公遺制的傳承者,而不是新王之法的開創者,就像魯隱公是周禮盡在之魯的傳承者,是繼體中興的“體元”者,而不是垂法將來的“開元”者。
孔穎達不明杜預“體元”之義,故雜引《公羊》和《周易》為之解。《左傳正義》曰:“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32)同上,第118-119頁。“氣之本”和“善之長”皆有違杜義。首先看“氣之本”,董仲舒已提到“元氣”一詞,但不以元氣解元,以元為“元氣”始于何休。何休在《公羊》家內部第一次正式引入《易》學“卦氣”說來解釋《春秋》之“元”(33)參見廬鳴東:《何休“卦氣說”窺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例釋》,《東華漢學》2004年第2期。徐復觀也承認《春秋》元氣說是《易》學的滲入,但認為肇始于董仲舒。徐復觀的觀點已遭到周桂鈿等學者的反駁,以元氣解元是何休開啟的傳統。(參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2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28-329頁。),將《春秋》之元視為創生天地的源頭。杜預以《春秋》為魯史舊文,絕非一套理論構想,因此“體元”不會是何休“元氣”論設想的宇宙創生論,而只是現實國君更迭的繼體之元。此外,杜預有意與《公羊》家立異,自然不會直接采用何休的“元氣”說。因此,孔穎達以“元者,氣之本”解釋“體元”,與杜預之意南轅北轍。
其次,孔穎達以“善之長”釋“元”,采自《周易·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34)[唐]李鼎祚撰、王豐先點校:《周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頁。《左傳正義》多剿襲二劉之說,但劉炫《春秋規過》明確反對杜預“體元居正”以及《公羊》家的元年釋義,認為“元”除了“始”之外別無他意。可見,此處以“氣之本,善之長”來解釋“元”可能就是孔穎達諸人的理解。孔穎達不明杜預“體元”為繼體之義,故據元氣論和《易傳》賦予元在宇宙論和道德論中的最高地位,最終與杜預之義南轅北轍。
然而,孔穎達這一違背杜預的解釋卻意外接續了劉歆以《易》學比附《春秋》學的傳統。劉歆初年本治《易》學,后領校秘書時發掘《左氏》,據《漢書·楚元王傳》載,劉歆之前的《左氏》只有字義訓詁之學,但劉歆之后《左氏》學“章句義理備焉”。(35)[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67頁。劉歆的《左氏》學著作沒有流傳下來,但從《三統歷》可推知劉歆《左氏》學的研究思路:
(《春秋》)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于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于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啟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兇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余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36)[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第4冊,第981-983頁。
劉歆認為《易》與《春秋》分別代表天、人之道,實質上是認為《春秋》學缺乏終極的基礎,只講人道而不講天道。因此,劉歆認為《春秋》之“元”可比附《易》之“太極”,取“春秋”為名符合《易》兩儀之中,三統符合《易》三極之統,并通過《易》學為《春秋》學搭建起一個形而上或宇宙論的開端。接著,劉歆引《左傳》的龜筮之法為例,占卜求的是天象與天數,但通過天象和天數才可知人事的吉兇禍福,暗示《春秋》的創作本身就以《周易》為模板。比如,《春秋》之“元”加上春秋、三統、四時共有十端,以五乘十恰好符合《周易》大衍之數五十的要求。可見,劉歆開啟了以《周易》天學籠罩《春秋》人學的傳統。
這一以《易》學解釋《春秋》學的脈絡,還可追溯至劉歆與董仲舒之爭。近現代學者普遍承認,董仲舒哲學的核心是天,但即便董仲舒《公羊》學如此重視天的維度,我們也看不到董仲舒直接以善于言天的《易》學作為《春秋》學的理論基點。《春秋繁露·玉杯》排列六經之序曰“《易》《春秋》明其知”,二者功能相通,皆明知之學。《春秋繁露·精華》說《春秋》“其辭體天之微”,如果善于查驗,那么《春秋》可謂“無物不在”“天下盡矣”。(37)[清]蘇輿撰、鐘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第96-97頁。董仲舒認為《易》與《春秋》有相通之處,《春秋》本身便兼包天人,非劉歆眼中互補式的以《周易》提攜《春秋》,而是互明式的《易》與《春秋》志同道合。因此,直接以《易》學比附《春秋》不是董仲舒《公羊》學的傳統路徑,而是源于劉歆《左氏》學的新傳統。
劉歆以《周易》比附《春秋》,對此后的《春秋》學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不僅《左氏》學受到劉歆的影響,何休以源于《易》學的“元氣”釋“元”,或許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劉歆的啟發。但劉歆首先以《易》名家,兩漢《公羊》《穀梁》或是《左氏》專經學者皆未完全照搬劉歆的思路,因為《春秋》經師首先會承認《春秋》本身的義理系統和解經路徑。何休以“元氣”解釋“元”,與其說是《易》學的引入,不如說是借用《易》學資源來搭建《公羊》自身的理論框架。杜預一心證明《左傳》具有獨立的解釋系統,自然也不甘于附庸《周易》。因此,杜預沒有沿用任何一家的元年釋義,轉而吸納了“開元”與“體元”的張力,在對抗《公羊》元年釋義的同時,也是自立門戶的標志。
《春秋》是一套“開元”的斷裂性法度,抑或“體元”的延續性法度?《公羊》與《左傳》在此產生分歧。《公羊》截斷眾流的新王期待秩序的開新,《左氏》承前啟后的中興苦心于文明的延續。杜預認為《春秋》魯隱公是繼體之君,而非受命之王,“元年”不是一套素王之法的開端,不包含宇宙論或道德論的建構。因此,杜預以中興的“體元”對抗《公羊》新王的“開元”。杜預尚有漢人專經博士成一家之言的余風,即在貫通一經義理始末的前提下對具體經文作出貼合全局的理解,而不是直接通過以經解經,在表面上實現每一條經文解釋最大限度的合理化。杜預“體元”說基于對《春秋》學的整體把握,孔穎達對“體元”的解釋則糅合了看似相關的不同經文。不過,孔穎達引《周易》解釋杜預“體元”說,雖然歪曲了杜預的思路,恰恰發揚了劉歆的傳統。換言之,孔穎達接續了《春秋》之元在董何與杜預之外的第三條解釋路徑。此后宋儒以仁釋元,某種意義上推進的恰是劉歆《春秋》學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