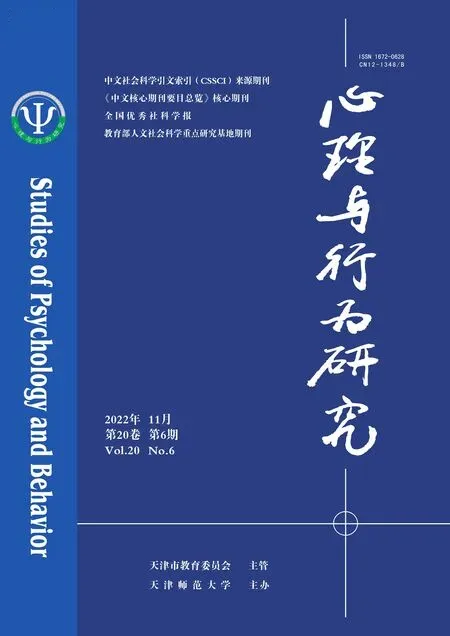父親婚姻滿意度對1~3歲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的鏈式中介作用 *
何慧華 陳迎新 蔣 琴 姜 露
(上海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上海 200234)
1 引言
根據家庭系統理論,父子關系屬于親子關系網絡,和父親養育以及父母關系相互作用,共同影響兒童發展(Christopher et al., 2015)。近十年來關于父母關系、父子依戀、父親參與的研究證明,父親與幼兒的問題行為、認知水平、社會-情緒能力發展等都關系密切(Cano et al., 2019; Zhang et al., 2021)。“三孩”政策背景下,父親越來越被期待參與到嬰幼兒的日常照護和高質量陪伴中,以有效緩解雙職工家庭母親的養育壓力。因此,進一步理解父親在家庭養育和促進兒童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實踐意義。
社會-情緒能力是指個體有效應用必要知識、技能和態度從而識別和管理情緒,建立關系,解決人際問題,做出適當行為的社會性和情緒能力(Wang et al., 2019)。Carter等人(2003)提出了嬰幼兒階段的社會-情緒能力模型,包括依從性、注意力、模仿或游戲、求精動機、移情和親社會同伴關系六個維度。在個體發展早期,社會-情緒能力的發展可能存在年齡和性別差異,甚至交互作用,比如,出生第一年的女孩比男孩會表現出更強的社會取向反應(Barbu et al., 2011)。雖然先行研究未能就年齡與性別差異達成共識,但關于家庭養育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結論較為一致。作為家庭系統的子系統,夫妻關系可以直接預測嬰幼兒的心理適應和社會-情緒能力(Abuhammad et al., 2020)。作為夫妻關系的關鍵因子,婚姻滿意度是夫妻雙方對夫妻關系的主觀反饋與評價(Bernier et al., 2014)。若夫妻對雙方關系的主觀評價較低,則會產生敵意、憤怒情緒和情感疏遠等問題,從而導致兒童出現抑郁、適應不良、社會退縮等問題行為(Qian et al., 2020)。尤其對新手父母來說,婚姻滿意度會在嬰幼兒出生早期呈下降趨勢(McCoy et al., 2013),導致婚姻沖突的增加,并進一步對兒童的同伴關系(Lindsey et al., 2009)、問題解決和親社會行為等社會-情緒能力產生消極影響(McCoy et al., 2009)。以往研究多關注婚姻沖突這一消極方面(梁宗保 等, 2016),但包含積極和消極評價的婚姻滿意度更能綜合地反映婚姻質量。近二十年來關于父子子系統的研究均發現,即使父親可能不是家庭中親子關系的主要構建者和養育行為的主要實施者,但作為構建父母關系的一方主體,其對婚姻滿意度的評價也可能直接影響嬰幼兒的社會-情緒能力。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父親婚姻滿意度正向預測嬰幼兒的社會-情緒能力。
生態系統理論指出,親子依戀是影響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重要因子。Bowlby(1978)將親子依戀界定為兒童早期與依戀對象(如父親、母親等)間形成的穩定情感聯系。精神分析理論與社會學習理論均強調嬰幼兒與父母的依戀是個體早期社會化和社會-情緒能力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王紅艷, 王冰, 2006)。但父子依戀的構建方式和作用均與母子依戀有所不同,對嬰幼兒的發展具有獨特的貢獻(邢學瑋 等, 2014; Brown & Cox,2020)。首先,在建構方式上,父親與幼兒的游戲互動更具刺激性和不可預測性,父親更加支持幼兒的冒險和探索行為,因此嬰幼兒也能和父親構建起安全依戀(Fernandes et al., 2020)。其次,雖然母子依戀對幼兒獲得積極的自我認知有更大的影響,但父子依戀能更準確地預測幼兒的行為問題(Veríssimo et al., 2011)。另外,嬰幼兒在12個月和18個月時的父子依戀可能影響其5歲時的同伴關系;早期具有安全父子依戀的嬰幼兒,后期在游戲中產生的消極情緒較少,同伴關系也更好(李曉巍, 魏曉宇, 2017)。同時,在婚姻滿意度較高的家庭中,高水平的父母安全依戀預示著同樣高水平的親子安全依戀(Qian et al., 2020),父親的婚姻滿意度會通過父子安全依戀影響幼兒的心理適應能力(周柳伶 等, 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2:父子依戀在父親婚姻滿意度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中介作用。
父親參與是父親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認知、情感與行為等多維度的卷入(Hawkins et al., 2002)。家庭系統理論認為,婚姻滿意度不僅會影響父母關系子系統,也可能影響家庭成員參與教養的行為表現(Lui et al., 2020)。比如,父親對婚姻滿意度的下降預示著父親較少參與父母養育決策過程和執行養育任務(Christopher et al., 2015)。Kwok等人(2013)對2~6歲兒童的父親研究發現,婚姻滿意度是父親參與的重要預測因素。父親參與會顯著影響其子女的認知和非認知領域的發展,父親參與的頻率、方式和質量均能顯著預測兒童早期的認知能力、社會-情緒能力、游戲水平以及入學后的學業成就(李原, 2011; Boldt et al., 2014)。由此可見,父親婚姻滿意度能通過提升父親參與教養的水平進而作用于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發展。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3: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中介作用。
雖然先行研究從不同視角探究了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對幼兒發展的影響,但兩者聯合作用于嬰幼兒發展的機制尚未明確。大部分研究強調,父親依戀和父親參與的關系取決于父親參與的數量和質量兩者的作用,也與具體的參與行為和家庭、社會背景關系密切(Brown et al., 2018)。高水平的父親參與意味著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的投入,可以為構建高質量的父子依戀提供途徑。依戀關系也可以預測父親的養育行為(張印平 等,2015)。親子依戀安全性高的幼兒與父母關系更為親密,父母也能夠從高質量的親子依戀中體驗到積極的情緒和養育效能感,從而更積極地參與養育活動(Rueger et al., 2011),即高質量的父子關系可能是父親積極參與教養的情感基礎之一;另一個情感基礎則來源于和母親的婚姻關系,高質量的婚姻關系和親子關系是父親積極參與教養的預測因子(沈欣 等, 2022; Mo et al., 2021)。已有研究探討了父子依戀、父親參與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關系,但較少有研究將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兩個變量同時納入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關系中。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1~3歲的低齡嬰幼兒,與其互動較多的可能是母親和祖輩,所以父子子系統的機制很可能是關系在先,行為在后,即父子之間先建立情感聯結,形成較為安全的依戀關系,從而使得父親參與的水平逐步提升。因此,本研究將反映父子關系的父子依戀作為第一個中介變量,將反映養育行為的父親參與作為第二個中介變量,提出假設4: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以上研究假設,構建一個鏈式中介模型(見圖1),考察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機制。

圖 1 鏈式中介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法,選取上海市某早教機構的1~3歲嬰幼兒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共發放、回收問卷230份,回收率100.00%,其中有效問卷212份,有效率92.17%。嬰幼兒的平均月齡為27.81(SD=5.52),其中男孩114名(53.77%),女孩98名(46.23%)。嬰幼兒父親年齡為30~40歲,其中31歲以下38名(17.92%),31~34歲87名(41.04%),35~38歲56名(26.42%),39歲及以上31名(14.62%);學歷以本科為主,122名(57.55%),大專或高職及以下51名(24.06%),碩士及以上39名(18.40%)。參與本研究的主要為社會經濟地位中等偏上的家庭,家庭月收入10000元及以下的占14.15%,10000~15000元的占18.87%,15000~0000元的占25.47%,20000元以上的占41.51%。
2.2 研究工具
2.2.1 父親婚姻質量滿意度問卷
采用Olson婚姻質量問卷中的婚姻滿意度分量表(李凌江, 楊德森, 1999)。量表包含10個項目,由父親報告。采用5點計分,“1”表示“確實不是這樣”,“5”表示“確實是這樣”,得分越高代表父親的婚姻滿意度越高。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9。
2.2.2 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問卷
采用12~36月齡嬰幼兒情緒社會性評估量表(張建端, 2008)中的“能力域”子領域考察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共35個項目,包含依從性、注意力、模仿或游戲、求精動機、移情和親社會同伴關系6個子維度,由母親報告。采用三級計分,“0”表示“不符合或偶爾符合”,“1”表示“有時符合”,“2”表示“經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越高。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0。
2.2.3 父親參與問卷
采用Hawkins等人(2002)編制、尹霞云(2012)修訂的父親參與問卷考察嬰幼兒父親參與水平。共26個項目,由父親報告。問卷包含4個維度:支持規劃維度(8個項目)、日常照顧維度(9個項目)、鼓勵表揚維度(5個項目)和管教約束維度(4個項目)。采用6點計分,“0”表示“完全不符合”,“6”表示“非常符合”。4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7~0.94,總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8。
2.2.4 父子依戀與母子依戀問卷
采用洪佩佩(2008)修訂的幼兒依戀問卷考察父子與母子依戀。共31個項目,包含依戀-探索(13個項目)、交互順暢性(11個項目)和社交活躍性(7個項目)三個分量表。采用7點計分,完全符合第一項行為計7分,比較符合計6分,有點符合計5分;完全符合第二項行為計1分,比較符合第二項行為計2分,有點符合計3分;項目所描述的情景從未發生或幼兒的行為表現不在項目描述范圍內,計4分。問卷由父母親分別填寫,父子依戀和母子依戀問卷總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70、0.72。
2.3 研究程序
研究者利用周末嬰幼兒及其父母到早教機構參加親子活動的時間發放紙質問卷。問卷采用匿名方式,由父親、母親分開填寫。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周浩, 龍立榮, 2004)。結果表明,父親問卷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16個,其中第一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32.42%,小于40%的臨界標準,母親問卷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22個,第一因子的變異解釋率為12.81%,低于40%的臨界標準。因此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父親婚姻滿意度、父親參與、父子依戀、母子依戀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兩兩顯著正相關;嬰幼兒月齡和性別均與父子依戀、父親參與和社會-情緒能力無關(見表1)。
3.3 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關系及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運用SPSS22.0中的PROCESS插件進行鏈式中介(Model 6)檢驗。由于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嬰幼兒月齡和性別均與父子依戀、父親參與和社會-情緒能力無關,而母子依戀與父子依戀、父親參與和社會-情緒能力均相關,因此將母子依戀作為控制變量,分析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直接效應、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的中介效應。見表2。
結果顯示,父親婚姻滿意度顯著正向預測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β=0.31,p<0.001)、父子依戀(β=0.21,p<0.001)和父親參與(β=0.46,p<0.001),父子依戀顯著正向預測父親參與(β=0.22,p<0.001)。將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共同納入回歸方程后,父親婚姻滿意度(β=0.09,p>0.05)和父子依戀(β=0.02,p>0.05)均無法顯著預測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只有父親參與能夠顯著預測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β=0.42,p<0.001)。這表明在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中,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起完全中介效應。
進一步分析顯示,總中介效應值為0.221,由三條路徑的間接效應組成:間接效應1,父親婚姻滿意度→父子依戀→社會-情緒能力,置信區間包含0,說明該路徑的間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2,父親婚姻滿意度→父親參與→社會-情緒能力,該路徑的間接效應顯著;間接效應3,父親婚姻滿意度→父子依戀→父親參與→社會-情緒能力,該路徑的間接效應顯著(見表3)。以上結果表明,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的假設成立(見圖2)。三個間接效應分別占總效應的1.60%、62.58%、6.39%,總間接效應占總效應的70.57%。

圖 2 鏈式中介檢驗模型

表 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結果

表 2 各變量的回歸關系分析

表 3 中介效應分析
4 討論
4.1 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直接效應
本研究發現,父親婚姻滿意度和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顯著正相關,且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具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大部分研究結果一致(梁宗保 等, 2016; McCoy et al., 2013)。父親在婚姻關系中體驗到的沖突、壓力和疲勞,會遷移到父親對幼兒消極情緒的反應方式中,從而導致幼兒的焦慮、害羞、退縮等內化行為問題,攻擊、違紀等外化行為問題,以及同伴沖突、低社交能力、低學業成就等適應不良問題;而和諧婚姻關系所帶來的積極家庭環境能夠在父親履行家庭養育責任中提供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楊青青, 李曉巍, 2018)。婚姻滿意度較高的父親更傾向于積極解決問題,為嬰幼兒提供正向示范,嬰幼兒則在模仿的過程中發展社會-情緒能力。
4.2 父親參與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父親婚姻滿意度通過父親參與的單獨中介作用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產生影響。這一結果支持了以往研究(李曉巍, 魏曉宇, 2017;Lui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1)。家庭系統理論的“溢出假說”認為,家庭是由相互影響的子系統組成,在一個系統中產生的情感可能在另一個系統中表現和表達(Cox & Paley, 1997)。雖然婚姻關系從屬于夫妻子系統,但在家庭壓力視角的溢出機制觀點中,夫妻子系統內的情緒和行為也會遷移到父母子系統中(Erel & Burman, 1995)。因此,反映婚姻關系和質量的婚姻滿意度也可能是導致父親參與家庭養育的關鍵因素之一。高水平的婚姻滿意度能激發父親參與家庭養育的主動性,能夠從緩解母親育兒壓力、承擔家庭育兒職責的角度出發,積極參與嬰幼兒早期的生活照護、陪伴游戲等養育活動,而這類養育活動能夠及時并適當地對嬰幼兒的需求做出反應,嬰幼兒在父親的支持和接受下自由表達和討論情緒,這就構成了嬰幼兒獲得適應性情緒調節技能的基礎(Fearon & Belsky, 2004)。因此,父親婚姻滿意度通過父親參與影響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模型路徑具有合理性。
4.3 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的鏈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中起鏈式中介作用。以往研究表明,享有支持性婚姻關系的父母,在家庭中更愿意表達積極情緒,更有可能與子女構建起安全的高質量依戀關系,從而也更有能力以敏感與合作方式參與家庭養育(楊青青, 李曉巍, 2018)。而沖突性的婚姻關系則可能導致父母消耗心理和情感資源,在處理婚姻矛盾中不自覺地暴躁和不耐煩,無法在情感上與子女構建安全依戀,從而對養育參與的頻率和質量造成消極影響(Bernier et al., 2014)。在父親參與模型中,高質量的安全依戀可以通過高水平的父親參與為嬰幼兒早期提供社會交往、情緒理解和表達等行為示范提升其社會-情緒能力(Fernandes et al.,2020; Mo et al., 2021)。因此,父親婚姻滿意度通過父子依戀→父親參與繼而影響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模型路徑具有合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兩個中介變量后,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直接作用不顯著,表明父親婚姻滿意度作為遠端環境變量,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的影響需要通過父子建立安全依戀關系以及父親高頻率參與教養的“橋梁”作用才能達成。本研究中,父子依戀的單獨中介作用沒有發揮。產生這一結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對象為城市1~3歲嬰幼兒家庭,這一階段的嬰幼兒往往由祖輩在家養育,且和父親相比,母親承擔了更多的照護責任(宋雅婷, 李曉巍, 2020)。因此,父子依戀尚未能發揮出重要作用。而父親參與作為直接與嬰幼兒互動的教養實踐,其作用比較明顯(Brown et al.,2018)。另外,在祖輩共同養育的背景下,可能母子依戀和父子依戀對兒童的社會性發展都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嬰幼兒與教養人所構建的多重依戀關系既存在一致性,也有差異,因此可以相互補充或者疊加,共同作用于兒童社會性發展(邢淑芬 等, 2016)。今后可以進一步探討合作養育背景下父子、母子、祖孫等多重依戀關系的聯合效應。
綜上,本研究證實了父親婚姻滿意度對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產生的積極作用,高水平的婚姻滿意度可以通過外溢效應作用于高質量父子關系的構建,從而驅動父親積極參與早期教養,助力于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發展。本研究也拓展了父子依戀與父親養育行為關系的解釋,被婚姻關系所影響的父子關系也是父親參與的預測因素。新生兒出生后疊加祖輩參與教養產生的復雜性,婚姻關系往往容易被忽略,夫妻雙方應共同努力夯實婚姻關系這一家庭功能的重要情感基礎。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的樣本主要來源于城市家庭,且樣本量不大,未來可擴大取樣范圍和數量,進一步探討不同城市、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城鄉差異。其次,本研究所采用的父親參與測量工具主要考察父親參與的頻次,未來研究可以結合觀察法,考察父親參與質量的作用。再次,母親婚姻滿意度和母親參與,以及祖輩參與和祖輩-父輩共同養育等因素也可能是影響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中介關系的重要因素,未來可以納入到模型中加以驗證。
5 結論
(1)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呈顯著正相關;(2)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中介作用;(3)父子依戀和父親參與在父親婚姻滿意度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間起鏈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