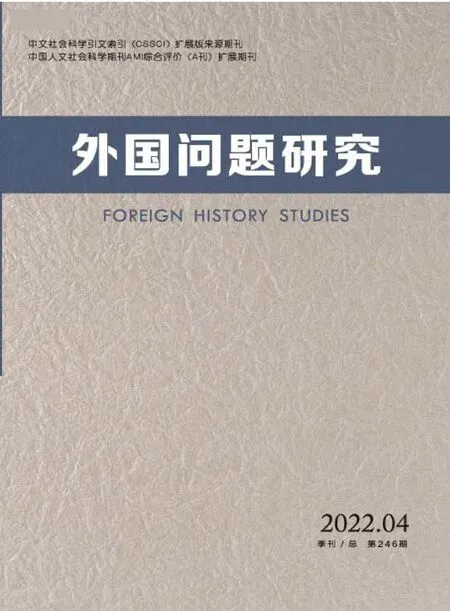“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歷史教科書的變遷
谷麗偉
(東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歷史上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的覬覦由來已久,甲午戰爭清軍陸、海戰皆敗,在《馬關條約》的談判中,日方除了索要巨額軍費賠償,還要求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附屬島嶼。由于三國干涉,日本被迫將遼東半島有價償還,這令當時身在旅順的德富蘇峰“憤懣無比”,“捧了一把旅順港外的沙礫,用手絹包起來”,當作日本“僅剩的一點遼東的版圖”帶走。(1)德富蘇峰:《中國漫游記 七十八日游記》,劉紅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82頁。其后日俄戰爭爆發,最終締結《樸茨茅斯和約》,約定俄國將旅順口、大連灣并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讓與日本,南滿鐵路及支線、附屬地也歸日本經營,“出兵一百萬,糜款十五億”,(2)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東京:緑蔭書房、2005年、第39頁。日本終于攫取到垂涎已久的特權和利益。
為了經營南滿,1906年日本撤銷各地軍政署,改關東總督為關東都督,掌管旅、大租借地。同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成立,經營包括南滿鐵路及其支線礦、農、林等東北的重要產業,假股份公司之名,行政府機關之實。此后,日本不斷謀求擴大勢力范圍并進行殖民滲透,在修筑鐵路以控制東北經濟命脈、鼓動日人移居東北的同時,如何對勢力范圍內的中國人加強殖民化宣傳與教化,以扶植親日勢力,也被提上日程。作為日本在東北的主要行政機關,關東廳與滿鐵在原有學校的基礎上,不斷修復、擴建公學堂,(3)“關東州”及滿鐵為居住在東北地區的日本兒童開設的小學稱“尋常小學”,所用教科書與日本國內一致,“公學堂”指日本殖民當局針對中國人在城鎮開辦的初等教育機構。設立中、高等教育機構,以收容中國學生,堂長人選自不必說,“教員也盡量聘用日人”。(4)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大連:大連文教社、1935年、第118頁。對于“關東州”、滿鐵附屬地各級教育的基本情況、特點及影響,其他學者有宏觀性的研究,(5)謝忠宇:《滿鐵附屬地學校教育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9年;劉振生:《近代東北人留學日本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但在關乎歷史的細節處,論述尚顯籠統與模糊,有學者就認為,“‘滿鐵’附屬地公學校的教學科目、教材和課時安排與‘關東州’的公學堂基本相同”,(6)劉振生:《近代東北人留學日本史》,第75頁。顯然未慮及九一八事變前“關東州”與滿鐵附屬地所面臨的不同形勢。本文即以“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所用歷史教科書的變遷為視角,考察日本當局如何根據中日關系以及兩地的局勢變化來調整其殖民教育策略,進而揭露日本試圖切斷東北與其他地區的淵源、將中國東北歷史與日本歷史嫁接的企圖。
一、九一八事變前“關東州”公學堂的歷史教科書
日俄戰爭之后,以旅順、大連為中心的“關東州”被日本視作“準殖民地”,“如同臺灣、朝鮮的感覺”,(7)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巖波書店編:『巖波講座教育科學第十冊』、東京:巖波書店、1932年、第23頁。因與清政府簽有《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域內環境相對簡單,“在白仁長官(‘關東州’都督府首任民政部長白仁武)時代已實行純然的同化政策,公學堂唱‘君之代’,施行日本式訓練”。(8)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3頁。1916年,關東廳設立旅順師范學堂,(9)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93頁。目的是為公學堂培養符合日本殖民當局意愿的中國教員。在公學堂的科目設置上,為避免激化當地人的民族情緒,1906年3月“關東州”民政署民政長官石塚英藏氏發布《“關東州”公學堂規則》,第一條“生活必需的智識技能”止于漢文、算術兩科,缺少地理、歷史、理科等日常生活最必要的科目。(10)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19頁。1915年3月修改公學堂規則,廢除六年學制,分置初、高等科,修業年限分別為四年、二年,并于高等科教科目中加入理科、地理,(11)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21頁。歷史科仍付闕如。1920年、1922年分別有“朝鮮教育令”“臺灣教育令”改革,“臺灣”、朝鮮開始增設課程“日本歷史的大要”,直接將臺灣、朝鮮人視作日本國民,講授與日本內地學校相同的日本史。在這一背景下,1923年3月,公學堂規則第三次修改,首次于高等科中加入歷史科目。(12)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21頁。
歷史既被列為正科,由于中華民國發行的歷史教科書不符合“關東州”及滿鐵的教育方針,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遂著手編輯教科書,1923年10月發行《公學堂歷史教科書》(稿本)卷二;1925年發行《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一;1930年發行《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二;1932年3、4月分別發行修訂版《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一、卷二。卷一為中文版的中國史(附日譯文),卷二為日文版的日本史。公學堂高等科第一學年講授“中國歷史的大要”,由中國教員擔任,第二學年講授“日本歷史的大要”,由日本教員擔任,每周與地理科共占三個小時。
《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一(1925)大致遵循民國歷史教科書的敘事脈絡,從中國太古時代講起,直到清朝滅亡、民國建立,但有意增加女真、契丹人的分量,凸顯女真族三次建立獨立政權的事跡,如第十二課上代滿洲、第十六課渤海、第二十課金、第二十九課清之興起。至于金朝滅亡的原因,在于“自遷都燕京后,百官皆學漢字,衣漢服,風尚日趨靡弱,惟在滿洲金人率質樸”。(1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8頁。不止如此,在“渤海”一課中,除了提到渤海國與唐朝修和交通,“夙遣朝貢使于唐”,還專文述及渤海國與日本的歷史淵源,“與日本屢次修交,以取其文化……其使日本者亦多長詩文之才”,(1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5頁。意在為日本當局宣揚的“日滿提攜”提供歷史依據。另一方面,日本也為其在南滿具有特殊權益的帝國主義立場辯護,稱甲午戰爭是“清廷派兵朝鮮,有所違于《天津條約》,遂與日本啟釁”,在日俄戰爭中,俄國占據東北,在鴨綠江沿岸修筑炮臺,“足以危東亞之局,固為所不忍默視”。(1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38—39頁。
1932年3月發行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一與1925年版內容基本相同,但文體從文言變成了白話文,可能是“被日語學習占據太多時間,中國學生的國文水平降低難以理解文言的緣故”。(1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東京:緑蔭書房、2005年、第212頁。事實的確如此,據1906年“‘關東州’公學堂規則”第一條,“公學堂以教授中國人子弟日語、施以德育以及傳授生活必需的智識技能為宗旨”,(17)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19頁。將教授中國兒童日語當作教育上的最要緊事。1917年,深谷松濤、古川狄風兄弟踏查“關東州”,留宿村莊時,便不止一次遇到學習假名并能夠靈活使用日語的兒童。(18)深谷松濤、古川狄風:《滿蒙探險記》,楊鳳秋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44頁。1922年4月創立的大連西崗子公學堂,初等科四年期間中國文、日本語每周講授時數分別為八九九九、六六七八,高等科兩年皆為七,(19)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44、145頁。日語學習時間所占比重逐年增加。
《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一(1925)若隱若現、煞費苦心地試圖切斷“滿洲”與中國的歷史淵源,1923年《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二(稿本)“日本歷史的大要”則與之相唱和,大幅宣揚日本建國的神話與歷代天皇的“仁德功業”,意在潛移默化地將日本的“皇國史觀”植根于學生心中。
1930年修訂發行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二同樣以關于天皇的記述為中心,但與1923年的稿本相比增加了明治以降的現代史比重,對于明治維新前夕日本國內尊王攘夷論的盛行、甲午戰爭前清日在朝鮮的角力等皆有明文敘述。時隔七年,新版之所以作此改動,據日本學者竹中憲一推測,是由于1928年末張學良“東北易幟”,排日運動高漲,神話教育在政治上失去“效力”。與其對中國學生進行神話教育,不如增加現代史部分,令其理解當前殖民地政策的“正當性”更重要。(2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215頁。
二、九一八事變前滿鐵附屬地公學堂的歷史教科書
滿鐵針對東北地區中國人設立的初等教育機構最初亦稱“公學堂”,1931年4月改稱“公學校”,但兩者在性質、內容上并無太大差別。(21)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368頁。相較于“關東州”,滿鐵附屬地被中國人的居住區包圍,“猶如大海中的小舟”,是“庭石般的存在”,(2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3頁。很容易受中國政局變動的影響,成為排日運動的對象,“不只是日本人,也針對上日本人學校的中國學生”。(2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172頁。因此,滿鐵當局以“日中親善、共存共榮”為號召,“日人教師多為留學中國者,中國人教師也不特別培訓,多采用他們中的讀書人”。(24)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24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1920年代之后排日運動高漲,1923年奉天教育界又針對滿鐵附屬地展開了教育權收回運動,故可以1923年為限,將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所用歷史教科書的情況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一)1923年前滿鐵附屬地公學堂的歷史教科書
蓋平公學堂是滿鐵在東北地區建立的第一所中國人學校,早在1909年成立。在僅以“通知”形式發布的《蓋平公學堂規則》中,歷史課程被列為教學科目,不過未標明講授課時。(25)満鉄地方部學務課編:『満鉄教育沿革史』、大連:南満洲鉄道株式會社、1937年、第1564頁。1914年3月公布《附屬地公學堂規則》,自高等科開始,歷史、地理每周共講授三課時,采用商務印書館的《共和國教科書 新歷史》與中華書局的《中華高等小學歷史教科書》,由中國教員以中國語講授。(2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209頁。1917年,滿鐵在教育研究所內設立教科書編輯部,負責滿鐵管轄范圍內日、中各學校教科書的編纂,(27)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562頁。面向中國兒童的公學堂盡量“選擇采用文部省臺灣總督府及上海等編纂的教科書、參考書”。(28)広島高等師範學校編:『大陸修學旅行記』、1915年、第162頁。當時經民國教育部審核采用的教科書主要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出版,教育研究所教科書編輯部刪除其中的三民主義及排日記事,經關東廳長官核定后方準發行。
1920年關東廳設立教科書編纂委員會,負責“關東州”教科書的編輯,“狹小的地域內,(‘關東州’、滿鐵)各自編輯教科書,頗費人力、財力,導致難以提供價廉質優的教科書,兒童轉校時也多有不便”。(29)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562頁。鑒于此,關東廳、滿鐵協議合署辦公,組成兩家合作經營的編輯部,設在南滿洲教育會內,計劃自1922年起,“州內、滿鐵編纂、使用同一教材”。(30)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368頁。然而,這一設想在日益高漲的排日運動形勢下未能實現,一直到1932年偽滿政權建立前,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未能如“關東州”一樣講授“日本歷史的大要”,日本史僅作為世界史的一部分來講授。
既然與“關東州”使用同一教材的計劃難以實現,滿鐵當局便盡可能減少講授中國歷史的時間,1923年4月滿鐵公布《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公學堂規則》,歷史、地理作為高等科社會科目,每周由三課時縮減至兩課時,課程為“中國及世界歷史的大要”“中國及世界地理的大要”,(31)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378頁。采用中華書局的《新式歷史教科書》與商務印書館的《新法歷史教科書》。(32)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209頁。由于滿鐵附屬地公學堂使用民國教科書,日本學者竹中憲一據此認為,“九一八事變前,滿鐵附屬地內針對中國人的初等歷史教育與中國其他地方無太大差異”,(3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172頁。但這僅就教科書而言,由于滿鐵轄內的公學堂堂長皆為日人,同時在補充教材的選擇,以及教學實踐中也大有可操作的余地,因而針對中國兒童的殖民化教育仍在日益深化。比如,蓋平公學堂在開校典禮上便讓學生唱日本國歌“君之代”,以至于村民懷疑學校建立是為了培養日本士兵。(34)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379、380頁。
日本的殖民化教育令東北教育界產生亡國滅種的憂思,時任奉天教育廳廳長的謝蔭昌深懷警惕:“今南滿鐵道橫貫我之中心,其所設附屬公學,以日本語言文字編寫歷史、地理教我兒童。年號則用日本的‘大正’,唱歌行禮則三呼天皇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之聲徹于霄漢,我之昆季謂他人之父兄為父兄者,有不為之痛心疾首者乎!”于是,謝蔭昌呼吁“奉省教育上應著手從事者,即收回南滿鐵道用地國民教育權是也”。(35)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沈陽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沈陽文史資料》第9輯,1985年,第39頁。他就此問題數次向代省長王永江提議,并派省視學會同教育會調查日本各學校的情況,通過報刊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主張在滿鐵附屬地內開設中國人自辦的學校。
(二)1923年后滿鐵附屬地公學堂的歷史教科書
1924年,奉天教育廳倡議收回教育權,抵制日本同化式教育的文化侵略,奉天當局向日本總領事提出要求,“希望日本方面明年度起停止招募公學堂學生”,(36)中國社科院上海歷史研究所籌備委員會、復旦大學歷史研究所編:《大事史料長編草稿·一九二四年五月》,1961年,第49頁。遭到關東廳及滿鐵拒絕;1925年6月上海五卅慘案;1927年5月田中內閣第一次出兵山東;1928年5月為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田中內閣第二次出兵山東,制造了濟南慘案。一系列的事件致使東北各地學生排日運動高漲,1927年9月,熊岳城、公主嶺農業學校、營口、遼陽商業學校等,或相繼廢校,或著手改革,于是滿鐵內部出現了放棄對中國人實施教育的“悲觀論調”。(37)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854頁。為了避免激化中國人排日的民族意識,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于1923、1925年編纂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卷二(稿本)、卷一不僅未能在滿鐵附屬地施用,反而不得已在既有民國教科書刪改版中加入孫文、青天白日旗等內容。(38)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856頁。即便如此,南滿洲教育會仍于1929年出版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有高嚴氏輯錄的《滿洲歷史教授資料》,作為“滿洲初、中等學校以及一般諸學校講授東洋歷史的參考書”,(39)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143頁。該書目次為:古代的滿蒙、渤海、遼、金、元、明與清初、近代滿蒙。觀其目次可知,在九一八事變前,盡管滿鐵附屬地公學堂表面上采用的是中華民國歷史教科書的刪改版,但在具體講授中已在灌輸“滿蒙獨立于中國”的殖民意圖。
1928年末東北局勢更為緊張,張學良宣布“易幟”,東北四省降下北洋政府時代的五色旗,改懸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凡學校或聚集場所,必張貼孫中山先生的肖像與遺囑”。(4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5頁。自1929年初,東北政務委員會制訂新規,“寒假后東省各級學校開學均須施行黨化教育,改用黨化教科書籍”,(41)《核閱黨化教科書》,《盛京時報》1929年1月27日,第5版。自小學開始設“黨義”科目。在三民主義的宗旨下,“教育者逐漸從日本留學生轉向歐美留學生,一切的學制由日本改為美國制”,(4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5頁。“排外教科書也傳播至東北四省,(滿鐵)周圍的中國側學校一律使用”。(43)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854頁。
根據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1929年9月發行的《中國排日教材集》,國民政府治下教科書中的排日內容比比皆是,力圖喚醒國人的民族意識。如《新中華歷史課本》高級用第四冊第十七課稱“日本民族本是好侵略的民族”,又譴責日本兩次出兵山東,是“國民的奇恥大辱,不能一刻忘記”。(4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6頁。《新時代高級小學 歷史教科書》第二冊講甲午戰爭,與“關東州”使用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中的敘述截然相反,指責日本“首先吞并琉球,不理中國的抗爭”,硬稱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屢次煽動內亂”。(4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65頁。正式教科書之外,另有宣傳抗日的各種國恥教材、唱歌集,《國恥讀本》第二冊《黃大》一文將中國喻為懦弱無能的村民黃大,日本是侵吞黃大房產的奸詐租客,《小學黨化教育唱歌集》中有《五七國恥紀念歌》:“高麗國、琉球島與臺灣,地不小,可憐都被他并吞了……又提出滅國條,無公理蔑人道……最傷心四年五七噩耗,為奴為仆眼前到,這國恥何時消。”(4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8頁。在悲壯的抗日情緒中,日本的形象不再是“中日親善”的主導者、東亞和平的維護者,而是曾向中國朝貢,屢蒙中國文化恩惠,經近代維新洗禮,不知反哺卻落井下石、同根相煎的暴發戶。排日教科書的對象是十歲左右的少年,聯想到十年后彼等將成為激烈的反日派,滿鐵當局“寒心不堪”。
鋪天蓋地的抗日宣傳、激蕩的民族情緒,未使日本蓄謀已久的“滿蒙政策”卻步。東亞經濟調查局一面為日本的侵略行徑辯解,一面警告主張“認同關稅自主,放棄沿岸、內河的航行權,則日中親善可實現”的某些“考慮輕率”的日本人,如果按照排日教材所言,滿足現代及今后的中國人,意味著補償鴉片戰爭后中國的一切損失,“關東州”的返還自不必說,甚至必須放棄朝鮮、琉球,歸還臺灣,“若失去上述地方,日本只有滅亡一途”。(47)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8巻、第94頁。
面對措手不及的新形勢,滿鐵召開中國文教科書調查選擇會,摸索相應對策,最初的權宜之計是修改、復刻舊版教科書。1930年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發行《新學制 歷史教科書》,便是先取得商務印書館的許可,將商務《新學制 歷史教科書》中的五色旗以及北京、遼陽等地名進行修改。同時,不但在“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內,不準中國施行任何教育,即便中國境內學校之鄰近兩地者,亦常被日警干涉校內行政:1929年春日警屢次前往遼寧省海城南臺小學,禁授三民主義;1930年5月,日警禁止鐵嶺小學懸掛國恥地圖及三民主義圖解;1930年秋,日警干涉吉林省長春小學校懸掛三民主義大綱。(48)吳瀚濤:《東北與日本之法的關系》,北平:東北問題研究會,1932年,第68—69頁。
三、九一八事變后的新版《歷史教科書》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軍撤出關外,翌年3月日本扶植溥儀成立偽滿洲國。形勢巨變,南滿洲教育會教科書編輯部遂于1932年4月發行《歷史教科書》上、下冊,上冊為“滿洲史”,下冊分為東洋史、西洋史兩編,中國、朝鮮、日本皆列入東洋史范疇。新發行的《歷史教科書》適用于“關東州”內外,(49)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138頁。南滿洲教育會當初謀劃在“(關東)州內、滿鐵編纂、使用同一教材”的愿望最終得以實現。不止如此,因偽滿政權建立倉促,直到1935末,“國定”小學教科書才由偽“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編纂告竣,在此之前,南滿洲教育會編纂的《歷史教科書》作為“審定教科書”暫時使用,以清除“東北易幟”后中華民國三民主義、排日教科書的影響。
新版《歷史教科書》上、下冊與以往滿鐵附屬地公學堂使用的民國教科書修改版截然不同,凸顯“滿洲”主體性的意圖也比“關東州”的《公學堂歷史教科書》更加昭然若揭。上冊直接設置為“滿洲史”,不再講授中國通史,而從上古滿洲族“肅慎”講起,課目依次為:肅慎、萬里長城、漢人的移居南滿、挹婁和夫余、高句麗的興亡、渤海的建國、遼的興起、金的統一、蒙古的勃興、蒙古的盛世、元的盛衰、清的創業、清的黃金時代、清的滿蒙政策、俄國南下政策和清國“滿洲”實邊策、“日清戰爭”和俄國的經略“滿洲”、日俄戰爭與“滿洲”、清的滅亡和革命的爭亂、最近的“滿洲”。如此的敘述脈絡下,似乎東三省與東蒙地區自古以來上演的只是女真、契丹、蒙古族的政權更迭,漢人被描述為無足輕重的外來角色,“因著(漢)武帝的東征,漢人就逐漸地移居于南滿,開墾耕地”,(50)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76頁。“清朝雖然限制漢人入滿洲境,可是他們仍然注目到柳條邊墻及萬里長城外,繼續著向滿洲廣野移住,更有漢人想不到的福音,是清朝為遏止俄國的南下,才有獎勵漢人移居滿洲的一件事”。(51)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0頁。傳統中國通史的敘事方式,中原、東南地區是中心,東北是邊疆,日本殖民意圖下的“滿洲史”則恰好相反,“滿洲”是具有獨立國家主體性的核心,長城以南的漢人成了外來的“他者”。正如《中國排日教材集》增訂本《打倒日本》的監修者保保隆矣所言:“將滿洲原為東夷北狄這一歷史事實巧為理論化,是教科書編輯上的重要技巧。”(52)保保隆矣:「満洲の教育」、第49頁。
新版《歷史教科書》上冊夸許清朝開國的事跡與極盛時代的文功武略,以提升偽滿洲國的存在感,稱清太宗改國號為清,“是要使人心振刷一新,并表示綜合滿、漢、蒙各民族,創成大帝國的大雄圖”,將金國改稱“滿洲”,“這是滿洲二字最初出現于東洋史上的”。歷史上“滿洲”與日本有“兩情相悅”的往來,當下的日本被鼓吹成勇于革新、值得信賴的盟國與救世主,“清國當著北受俄,南受英法兩國壓迫的時候,日本從久行鎖國的夢中驚醒,成了明治維新。明治大帝之治世時,國運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頗為昭著,又是世界人人驚嘆的時代”。(53)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2頁。日俄戰爭被宣揚為“滿洲”的“乾坤再造”,日本“為保持極東的和平,和自衛上著想”,更為“清國的領土保全,韓國的自由獨立,以及東亞的和平”,“不得已,才布告宣戰”。由于日本的“這一次大犧牲”,“清國才免去瓜分的大禍,且能使輕視有色人種的歐美人等,從良心上反省,并促進亞細亞民族的奮起,實在都是依賴日本勝俄的成績”。(54)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3—94頁。至于妄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教科書辯稱“歐戰后日本把青島還附民國,以表示沒有領土上的野心”,完全抹去要求中國四十八小時內答復時的蠻橫,而條約中妄圖分割滿蒙的侵略行徑,也被日方粉飾為善意之舉,“在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地,因為有鐵道的便利,經濟和文化都能發展得很快,將來或能建設理想生活的區域”。(55)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6頁。
不止如此,由于“東北易幟”打亂了日本謀取東北的計劃,中國形式上得到統一,修建“滿蒙新五路”、臨江設領事館、課稅等“滿蒙懸案”成為日方唯恐避之不及的“國際問題”,“滿洲史”遂對張學良父子極力貶低。“皇姑屯事件”乃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策劃,教科書卻描述成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結果,“蔣、馮、閻三派就組織國民革命軍,協力壓迫他,他不得已,才向奉天退歸,途中被炸彈擊斃”。(56)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6頁。張學良愛國抗日的民族壯舉,被污化為“忘敵事仇……不知持盈保泰,但極力擴張軍備,儲蓄私財,充實自己的勢力”,“忘卻和睦鄰邦的大義,遂蹂躪日本在滿洲的各種權利,并迫害鮮農”。(57)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7頁。九一八事變是在關東軍的授意下,滿鐵“守備隊”力圖打破“現狀”的自導自演,卻栽贓嫁禍成東北軍炸壞南滿鐵路線、擊射巡察路線的日本兵而引起的不幸大沖突,日軍將東北軍從“滿洲”驅逐,“滿洲”人民才得以從虐政中被救得更生。緊接著1932年春,“完全脫離國民政府和舊軍閥等關系”,“尊重民意,努力治安,使三千萬民眾享最大幸福的新國家”的“滿洲國”便粉墨登場。(58)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97頁。
包藏禍心的“滿洲史”既然將“滿洲”從中國分離,于是在《歷史教科書》下冊中,中國史便被劃入與西洋史對等的東洋史大范疇,與朝鮮史、日本史并列。在“最近世的東洋”兩節課中,日本儼然以“共圖東洋的和平”的盟主自居,日俄戰爭后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令之飄飄然自畫自贊,“從此以后,日本占有亞細亞大陸中的堅固地步,東洋諸國,仰望日本作指導者”。(59)竹中憲一編:『「満州」植民地中國人用教科書集成』第5巻、第117頁。
結 語
通過梳理“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公學堂歷史教科書的變遷,可知日本對東北兒童的歷史教育與其近代以來侵略滿蒙的長期國策相一致。首先根據“關東州”、滿鐵附屬地的不同形勢,設置兩套平行的教育體系,“關東州”幾乎不受中國動蕩局勢及學潮的影響,即便講授以“皇國史觀”為核心的日本史,也較少遭受反對。滿鐵附屬地公學堂則處于可進退伸縮的前沿,歷史教科書根據各方勢力的消長適時做出改動。其次,在公學堂歷史教科書不斷調整的脈絡下,日本試圖將“滿洲”從中國分離的主調始終未變,從開始的小心翼翼,到九一八事變后的明目張膽。從日俄戰爭結束到偽滿洲國建立的近三十年間,日本在東北地區苦心經營以扶植“親日派”,進而攫取土地、資源等巨大利益。1914年成立的四平街公學校,首批畢業生大都任職于滿鐵控制下的四洮、洮昂鐵道,(60)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385頁。另據統計,1932年后在偽滿洲國政府任職的原留日學生中,原籍為東北地區者占總數的90%,擔任偽滿洲國政府大臣的大多數是“關東州”或奉天出身,(61)劉振生:《近代東北人留學日本史》,第110頁。他們多出生于19世紀90年代末或20世紀初,其童年正與日本開始在東北攫取教育權、實施同化政策的時期相重合。1920年代,中國人排日情緒高漲,一些日本人開始對在東北的殖民教育感到躊躇,1928年安藤基平在《滿洲公論》上回應這一消極態度:“日本人開口即言為中國人教育投入了巨資,然與日本在滿洲獲得的利益相比,不值一提。”(62)島田道彌:『満洲教育史』、第850—851頁。可以說,安藤氏口無遮攔的自白無疑是日本意圖吞并東北、欲“滅其國先滅其史”的最好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