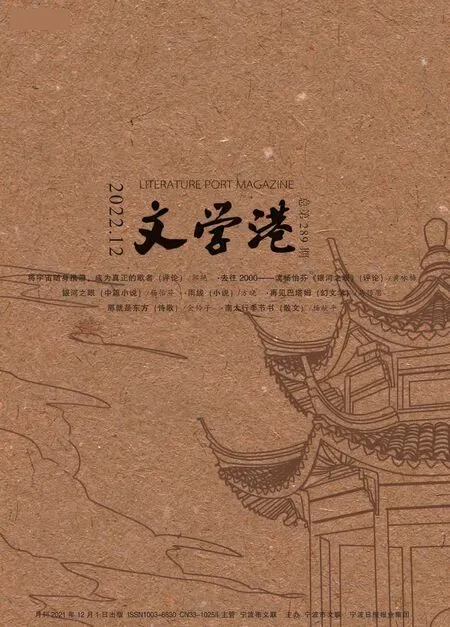將宇宙隨身攜帶,成為真正的歌者
□郭 艷
楊怡芬以《披肩》出場,帶著特有的敘述腔調,耐心又體貼地呈現了屬于當下生活的現代性經驗。她的敘事細膩、溫婉中帶著深入骨髓的柔韌秉性,尋常家事中透露出復雜的人生況味,草蛇灰線的情節中凸顯命運的復雜和人性的真實。海島農家父輩們在隱忍的堅韌中守護著屬于下一代的未來,子輩們則在被拋入的時代情境中長成了應該有的樣子。作者以工筆加寫意的方式塑造了小說主人公小葵,小葵是那個時代海島農家女孩的特例,她走出海島,進入城市,且實現了鄉土社會價值倫理和現代教育雙向的心智成長。小葵成為一個真正能夠回望和凝眸海島鄉土的現代主體。
海島農家折射時代變遷:這個文本以少女視角講述海島農家日常,呈現了改革開放初期海島農事變化和少年男女成長圖景。小說呈現出城鄉之間的身份差異,海島務農和吃上“國家糧”——這一矛盾是文本內在強勁的敘事動力。城鄉之間的差別是通過海島上一家人日常細節表現出來的:島嶼的水泥地上鋪著新曬的稻子,稻谷熱烘烘的香味中,透露出水泥地的特殊性;雙搶的日子過去了,一家三口剛剛松了口氣,卻要接待兒子從城里帶來的朋友,廁所和廚房的打掃是重點,暗示城鄉衛生標準的差異;那個時代標志城鄉差異的各種物質標識,比如華僑劵、糧票、布票、彩色照相機,乃至電視上城里女孩子的吃相、步態和說話;各種時代性色彩很鮮明的詞語:國家正式工、戶口、公社、鄉政府……一切都在悄悄變化著。在作者守望的敘述中,海島農家夏天一日三餐的瑣屑日常呈現在讀者面前。阿爹和阿姆對兒子工作切實的擔憂和謀劃,阿爹對女兒小葵未來默默的期許,小葵一家人面對生活的種種擔憂和憧憬,哥哥年少的懵懂、貪玩與懈怠,少年男女之間新鮮而盲目的相互吸引等。這些人物和場景是那個時代海島農家普遍的生活真實,文本在對整體性鄉土經驗進行描寫的同時,灌注了自身對故鄉深切而真摯的情感,以島嶼歲月的流變來折射特定時代人情風俗倫理的變遷。
成長的自重與時代少女形象建構:這個文本重點寫時代嬗變中主人公小葵的內在成長。小葵懂得農家生活的艱辛,體恤父母的不易,同時又勇敢地追求屬于自己的未來。相對于更加叛逆和自我的青年人來說,小葵是自重的,她和男孩一起外出是需要阿姆答應后才出門的;她見生客時還是脫下簇新的套裝,換成穿了三年的粉色銅盆領短袖襯衫;她少女懷春,憧憬美好愛情,卻能在田間地頭遙望海那邊的風景,在心旌搖曳的時候,把持住少女的那份矜持。小葵是善解人意的,比如她會想到田雷的悲傷比自己大,他高考落榜,而她只是心愛的小牛被賣了,她會在日常勞作的付出中體恤父母的不易,原諒哥哥有些自私的行為。小葵更有著自己的反思:冷眼看著哥哥討好同事的低眉順眼,想到人會幫自己瞧不起的人么?正式工有那么重要?哥哥已經開始為他的城市生活付費了等。她覺得阿姆夠苦的了——對于命運給的每一天,她都努力承受。這會是自己的將來嗎?小葵會在農村少女可能的限度內,做最好的自己,成了少數通過讀書改變自己命運的農村女孩。她對感情心懷期許的同時又心存芥蒂,直到明白自己也曾經被鄭重對待過,才最終釋懷。小葵擁有了自己選擇的愛情和婚姻,也在偷偷消費百元一瓶化妝水的過程中,日漸融入現代生活的俗世煙火,成為一個堅定而真實的現代個體。
守望的現實與飛揚的心智:文本中阿爹是一個極具社會文化景深的父親形象。他是個海島農民卻經常做出不像農民做的事情。比如阿爹在島上素來有“怪”的名聲,他總會拿著爺爺從海外寄來的錢,做一些不實用的事情。比如買書,給小葵買時尚的衣服,拿著錢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阿爹拿著華僑券,買了水泥,鋪成了自家院子里的水泥地。水泥地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無論從質感上還是形態上都標志著對現代生活和現代文明的向往。小說中城里青年工人對小葵家水泥地、錄音機和鄧麗君磁帶發出驚嘆,也對水泥地的平整光滑贊嘆不已。在父親跳出農家小島的視域里,小葵看到了別的女孩子看不到的很多風景和事物,也擁有了不一樣的看世界的視角。書籍成為她的理想國、避難所,也成為她心智成長的最豐厚資源庫。電視機里的城市生活,為城市生活準備的裙子,三年艱苦的高中學習……在守望現實的成長時光中,這些東西使得她免于流俗和懈怠,從海島農家的日常中生長出屬于鄉土更屬于現代的情思和心智,成為她自己那個時代最美好的少女形象之一。
總而言之, 《銀河之眼》以少女成長視角講述歲月流變,在看似窄小的題材中容納時代整體性經驗表達。在緩緩移動的特寫鏡頭中,解讀著關于當代生活細小符碼的象征性內涵,在漢語白話文塑造的文本時空中,上世紀80年代的精神情感和倫理風俗氣息充溢而靈動。小說在守望的回溯中抵達中國式溫柔敦厚的審美韻致。小說最后提到了“天眼”,天眼之下,盡管世間眾生萬物不過如白駒過隙之后的滄海桑田,然而人之所以為人,畢竟是在螺螄殼中做道場,一沙一世界中悟現實。銀河之眼既成為知識上的星群,又成為血脈情感記憶中的天眼。由此,躺在現實里的個體才可能以更加澄明的方式向未來敞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