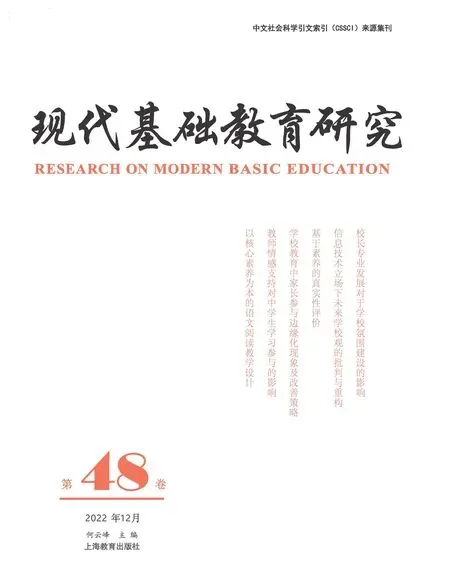教研方式變革對教師專業發展狀態影響的敘事探究
鄭蕊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提高教師專業發展水平對提升教學質量具有顯著意義,而基于對課堂教學思考與探究的教師教研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重要方式之一。①叢立新:《教研制度要有自己的堅持和自信》,《人民教育》2019年第21期,第18-20頁。中國基礎教育教研體系中,主要的教研方式有教師個體鉆研、同儕交流與互助、教研員指導、教師集體備課、大中小學合作開展的“聽評課”活動等。在本研究中,教研方式主要是指教師圍繞課堂教學質量提升與改進而進行的思考與探究活動,依據參與教研活動主體的不同,可以分為個人鉆研、教研員指導和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三種方式。基于此,本研究以某位教師為對象,對他在不同教研方式影響下的專業發展狀態開展敘事探究,并借助活動理論(Activity Theory)進一步解釋和回答問題:教師在不同教研方式的影響下為何呈現不同的專業發展狀態?
一、理論基礎及其適切性分析
本研究以活動理論及與之相關的四級矛盾思想為理論基礎。該理論最初是由維果茨基(Vygotsky,L)提出,后經列昂節夫(Leont’ev,A.N)和恩格斯托姆(Engestr?m,Y)等人的繼承與發展成為重要的理論學派。作為第一代活動理論的創始人,維果茨基將人的心理機能分為低級和高級,后者的發展需要借助一定的中介。②張大均,李曉輝,龔玲:《關于心理素質及其形成機制的理論思考(一)——基于文化歷史活動理論的探討》,《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71-76頁,第174頁。因此,在第一代活動理論搭建的三角模型中,有主體、客體和中介三個要素。此后,列昂節夫具體闡述了共同體內因勞動分工的出現而導致行動與活動的分離,繼而在維果茨基三角模型基礎上又引入了規則、共同體和勞動分工三大要素,并將分析單位由個體活動系統拓展為集體活動系統,此為第二代活動理論。第三代活動理論由恩格斯托姆提出,他強調將活動系統視為基本分析單位,尤其關注活動系統的社會性①Engestr?m Y.,“Expansive Learning at Work:Toward an Activity Theoretical Reconcept-ualization”,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Vol.14,no.1(January 2001),pp.133-156.,認為不同活動系統之間唯有交互協商與合作,才能更好地應對困難與挑戰。②Engestr?m Y.,Learning by Expanding:An Activity-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Research,Helsinki:Orienta-Konsulti,1978,p.78.第三代活動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第三代活動理論模型
本質上來說,個體鉆研、教研員指導以及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都是以具體的活動形式進行。個體鉆研涉及單一主體,能夠對應第一代活動理論。教研員指導和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因涉及兩個以上主體的參與,而形成一個包含多主體的活動系統。因此,后兩種教研方式對應第三代活動理論。第三代活動理論認為,矛盾是促進活動系統變革與發展的重要驅動力,恩格斯托姆將“矛盾”分為四個層級:一級矛盾是指活動系統中每一個要素自身存在的張力;二級矛盾是指活動系統內部不同要素之間的張力;三級矛盾指涉不同客體之間的矛盾,即既有活動系統之客體與更為先進的活動系統之客體之間的矛盾;四級矛盾則是指向當前活動系統與其周邊鄰近活動系統之間的矛盾。可以看出,一、二級矛盾均發生于活動系統內部要素層面,或是存在于某一要素內部,或是存在于不同要素之間。借助活動理論的不同模型和四級矛盾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窺探出不同教研方式導致教師不同專業發展狀態的原因。
二、研究設計
1.研究對象
辛老師自2001年師范專業學校畢業后,一直在小學擔任英語教師,并于2012年9月入職深圳市光明區美音學校③該校于2020年3月正式升級為一所九年一貫制學校,研究者早在2019年就開始在該校進行階段性扎根研究,由于調研時間跨越2020年3月這一重要節點,因此,在本研究中是以“學校”對該校進行命名。(化名)。該校在2014年7月參與由華東師范大學葉瀾教授領銜并主持的“新基礎教育”學校變革研究項目,該項目重視通過變革學校教研方式以推動學校整個教師隊伍的專業發展。辛老師提及其專業穩步發展是從2015年9月開始,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說明教研方式變革會對教師專業發展產生積極影響。根據辛老師的描述,可以將其職業生涯劃分為三大階段:專業停滯不前階段(2001—2010年),專業點狀發展階段(2011—2014年),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階段(2015年至今)。④辛老師雖然是于2012年9月入職美音學校,但其在講述自己專業發展時,是將2015年作為重要的時間節點來凸顯的。因此,本研究是直接選擇從2015年為第三階段的起始時間,這并不意味著從2012年到2015年間是辛老師的職業空檔期。筆者認為,專業發展的三個階段與三種教研方式的影響有關,因此,以其為研究對象開展教研方式變革對教師專業發展狀態的影響研究。
2.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敘事探究為研究方法。敘事探究是“對經驗的經驗研究”①Xu S,Connelly F.M.,“Narrative Inquiry for School-Based Research”,Narrative Inquiry,Vol.20,no.2(January 2010),pp.349-370.,關注經驗的時間性、社會性和地域空間性,因而有助于呈現辛老師專業發展過程的完整性與動態性。訪談和參與式觀察是本研究資料的主要收集方法。研究者對辛老師進行了3次正式訪談和5次非正式訪談。每次訪談時長40—90分鐘不等,所有訪談錄音均被轉錄為文本。對教學及相關活動進行觀察并撰寫田野筆記,包括日常課堂教學3次,英語學科組開展的“新基礎教育”研究線上“節點研討課”活動(辛老師作為評課者)3次,線下“節點研討課”前、中、后課堂教學及相關研討活動(辛老師作為授課者)1次。此外,辛老師的個人反思、研究日志及其公開發表的期刊論文亦被收集,多樣化研究資料之間可以互證。
3.資料分析
本研究借助巴羅內(Barone)的敘事建構(Narrative Construction)思想分析研究資料。敘事建構主張研究者為“故事”設定時間、人物、地點等多個“邊界”,將發生在“邊界”中的故事片段組織成完整故事,最后經由研究者理解和闡釋,再以“敘事”的方式呈現研究結果。②Barone T.,“A Return to The Gold Standard?Questioning the Future of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s Educational Research”,Qualitative Inquiry,Vol.13,no.4(May 2007),pp.454-470.在具體資料分析中,借助克蘭迪寧(Clandinin)和康納利(Connelly)三維敘事探究空間的分析結構,對資料進行編碼(見表1)并呈現編碼示例(見表2)。在三維敘事探究空間中,“完整的故事”會按照時間、個人與社會和地點三大維度被重組起來。③Clanninin D.J.,Connelly F.M.,Narrative Inquiry: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2004,pp.21-32.

表1 三維敘事探究空間分析結構

表2 編碼示例

(續表)
三、敘事建構
1.專業停滯不前階段
辛老師自2001年7月從師范專科學校畢業后的前十年,先后在一所公辦學校和一所民辦貴族學校工作,直到2010年7月。辛老師在訪談中不止一次提及從2001年畢業到2010年這十年間,其專業發展未有顯著提升,甚至以“停滯不前”“倒退”這類詞來描述這一時期的專業發展狀態。原因在于缺乏專家型教師的指導,辛老師在專業發展上只能依靠個體鉆研,無法觸及現象背后的本質。
2.專業點狀發展階段
2010年7月,辛老師從民辦貴族學校離職后,又進入一所公辦學校工作了兩年。但在回顧這段經歷的時候,辛老師提到,他入職的第一個學期每一次英語學科科組會上,他都只是一個默不作聲的旁聽者。究其原因,辛老師認為自己對教學知之甚少,因而在科組會上什么都不敢說。這種“什么都不敢說”的狀態持續了將近半年。辛老師指出,上“研討課”及課后區教研員的指導是結束專業發展停滯不前狀態的重要原因。然而,這一階段的專業發展卻是零散的。因為教研員雖然實踐經驗豐富,但是理論儲備不足,無法給予系統且全面的指導。
3.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階段
從時間上來看,辛老師雖然早于2012年9月就入職了美音學校,但他認為自己的專業發展卻是從2015年9月才開始的,這與該校在2014年7月正式加入“新基礎教育”學校變革研究有關。從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辛老師一直在學習“新基礎教育”研究相關理念。在此之后,辛老師上了數次“新基礎教育”研究倡導的“節點研討課”。
辛老師提及的“節點研討課”活動是一種以“節點研討課”為紐帶,將集體備課、教研組研討等多種教研活動有機聯系起來的教研方式(見圖2),磨課與教師個體反思也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次“節點研討課”之后,英語學科指導專家、區教研員以及學科骨干教師等主體都會分析課堂教學設計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繼而提出可能的改進意見。在參與“節點研討課”活動5年有余后,辛老師已然得到系統的專業發展,并且能夠較好地將理論與實踐融通起來。由于“節點研討課”關注參與主體的多樣性與異質性,同時強調學科指導專家引領和指導教師通過理論結合實踐去關照和改進課堂教學,因而也被稱之為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這也是促使辛老師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

圖2 “新基礎教育”研究“節點研討課”的實際組織和開展
四、理論闡釋
從辛老師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個人鉆研、教研員指導和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三種教研方式與三大專業發展階段分別對應。三種教研方式為何導致三種不同的專業發展狀態呢?可以借鑒活動理論來審視和闡釋這一問題。
1.個人鉆研造成教師專業發展停滯不前
個人鉆研注重學習者個人對學習過程中獲得的經驗進行積極反思與總結,其背后的學習理論假設是體驗學習理論。杜威作為體驗學習研究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曾指出,“從教育上來說,就是要使學校中知識的獲得與在共同生活的環境中所進行的種種活動或作業聯系起來”①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王承緒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1頁。,“做中學”有助于學習者的整體發展,包括身體和心智兩個方面的發展。②單中惠:《杜威教育學說的永恒價值——紀念〈民主主義與教育〉出版一百周年》,《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16-21頁。基于對杜威等人相關思想的借鑒,大衛·庫伯(Kolb)建構了體驗學習理論模型,包括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概括和行動應用四個適應性學習階段。③D·A·庫伯:《體驗學習:讓體驗成為學習和發展的源泉》,王燦明,朱永平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117頁。庫伯認為,個體經驗以及個體對經驗的反思對促進學習者的學習具有重要意義與價值。④Kolb D A,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4.誠然,學習者個體在學習過程中經由鉆研獲得的經驗及反思對其成長與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意義,但如果過分強調個人學習而忽視學習的社會性,則無助于個體的長遠發展。⑤Miettinen R,“About the Legacy of Experiential Learning”,Lifelong Learning in Europe,Vol.3,no.3(1993),pp.165-171.維果茨基認為,人的高級心理機能發展需要借助語言、習俗、經驗等心理工具為中介,個體可以通過內化心理工具實現對心理機能質的改造,但個體需要在與更有經驗的同伴之相互交流中才能逐漸習得這些心理工具。⑥潘慶玉:《新維果茨基學派主導活動理論述評》,《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第133-141頁。
第一代活動理論模型中包含主體、客體和工具(中介)三個要素,所表達的內涵是:外部刺激使得主體尋找既有中介與刺激之間的聯系,并基于兩者之間的融合開展進一步的行動。⑦李陽杰:《文化—歷史活動理論視角下的小學師徒教師互動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年,第53頁。將以上闡述與辛老師的成長故事聯系起來,則可理解為:辛老師想要在專業方面獲得成長,開始尋找能夠促進其專業發展的關鍵要素,他發現若想獲得專業發展,他需要得到有經驗的教師的指導。其實,教師指導本身不是中介,指導者的教學理念、經驗、技巧等才是中介。也就是說,在第一代活動理論模型的透視下,在辛老師此階段專業發展過程中,主體(辛老師)、客體(專業發展)和中介(資深教師的教學理念、經驗、技巧等)都存在,卻沒有促成辛老師的專業發展,其原因正是在于缺乏有經驗的教師的指導,以致他人的經驗未能轉化為辛老師真實的專業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彰顯出社會交往對學習的重要影響,同時也暴露第一代活動理論解釋力不足的問題。
2.教研員指導導致教師專業點狀發展
辛老師所提及的“研討課”活動是由區教研員參與的集體教研。有研究者指出:“教研員在被賦予的課程自主空間里承擔更多的專業指導的責任。”⑧沈偉,孫天慈:《中國教研員研究的歷史脈絡與多重視角》,《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1年第5期,第116-129頁。因此,教研員角色的恰當發揮會對教師專業發展等方面具有促進意義。教研員的工作對象是教師,雖然其“工作涉及理論與實踐、教育行政管理與專業服務、教育理想與教育現實等矛盾關系,但教學研究能力是其核心能力。教研員通過研究教學以及教育中的其他要素,最終目的是引領教師的專業發展”。⑨康曉偉:《論教研員作為教師教育者》,《教育科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92-96頁。這就是說,雖然教研員是從一線教師中選拔出來的,但教研員的工作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工作重心更多偏向于教學研究,而且教研員有較強的教學能力與豐富的教學經驗,可以給予教師教學上的指導。
當教研員作為指導者參與辛老師教學的時候,一個新的活動系統由此形成(見圖3)。其中,主體是辛老師和教研員,客體是促進辛老師專業發展,工具是語言、思維、教學經驗、教學方案設計、板書等。參與活動的共同體成員除了辛老師和教研員以外,還有同一學科組內的其他教師。活動分工為辛老師上課,教研員及其他教師一起聽評課。

圖3 以辛老師為主體的集體活動系統
區教研員的介入使其與辛老師之間生成了一個新的充滿張力的話語空間,由此形成教研員和辛老師共同參與的新的活動系統。雙方可以在此空間中就教學中的問題進行對話與交流。在此過程中,教研員基于自身過往教學經驗對辛老師教學予以指導,就其中有待改進的地方給予意見或建議。
教研員大多是從中小學學科教師中選拔而來,在研究、指導、管理和服務中,能夠較好地實現其指導職能,并通過多種形式進行教學指導,但也可能因為存在缺乏系統的培訓、學習,自身的理論基礎薄弱等不足,繼而導致一些教研員的指導內容偏向技能化和經驗化。①沈偉,汪明帥:《何以為師?教研員的素質狀況與提升途徑》,《中國電化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2-109頁。換句話說,教研員在指導課堂教學改進過程中,所使用的工具多為教學經驗或技巧,相對來說缺乏教育教學理論層面的指導工具。而這就意味著,當針對辛老師想得到“教研員理論結合實踐地指導其專業發展”這一活動客體來說,教研員缺乏促成這一客體實現的理論工具。在活動理論的四級矛盾思想中,所彰顯的恰恰就是二級矛盾,也即工具與客體這對矛盾之上,這可以從辛老師提到的“教研員大多都是從一線老師中走出來的……就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和“不能結合理論指導實踐”看出。具言之,教研員對辛老師的指導所借助的工具更多是其過往的經驗。當教研員缺乏足夠的教育理論,則雙方可能無法進行更深入的、理論結合實踐的探討與交流,最終導致辛老師只是獲得了教研員的教學經驗與技巧。
3.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促進教師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
作為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的“新基礎教育”研究倡導的“節點研討課”活動,將集體備課、教研組研討等多種教研活動有機連接。執教教師的教學及其個人反思雖然未在圖3中呈現,但卻也是重要構成。接下來,將抽取田野筆記片段,來具體分析此種教研方式何以有效地促進了辛老師理論與實踐的綜合融通發展。
辛老師系2020年11月9日英語學科組“節點研討課”的執教老師。在此之前,辛老師與其所在備課組其他教師進行了集體備課,生成了一個初始的教學設計方案。備課過程中教師的一些話引起了筆者的關注,如提醒辛老師要注意:將問題下放給學生以促進他們的思考;教材中有兩段內在結構基本一致的文本,可以用第一段文本來帶著學生歸納維度,第二段文本就讓學生自己去歸納維度,然后基于歸納出來的維度將文本復述出來,等等。據此,辛老師又結合本班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以及個人教學風格,形成了一份更為具體的教學設計方案。而后辛老師進行了第一次試教,學科組內教師參與了聽課,并在課后與辛老師共同開展了研討活動。一位聽課教師指出教學中有很多學生不怎么開口表達,原因在于學生還沒有討論完,就進入了回答問題環節,于是建議給學生更多的討論時間。事實上,如上集體備課中其他教師的“提醒”背后所隱含的是“新基礎教育”研究的“重心下移”“教結構、用結構”的思想,而課后研討活動中教師的“建議”背后蘊含的是“生生互動”思想。
而在“節點研討課”后,辛老師與大學研究人員、區教研員、校長和教學主任以及校、內外同學科骨干教師等數十人,開展了歷時兩個多小時的研討活動。①為了與備課組和教研組對應,在此將參與“節點研討課”合作教研的人員劃歸為“跨域組”。在此過程中,絕大多數點評主體在分析辛老師課堂教學中的問題以及給出可能的改進意見時,同樣也都是在引用“新基礎教育”研究相關教學理論中的概念,如“重心下移”“資源回收”“教結構、用結構”等。總之,以上能夠在極大程度上反映出辛老師及其所在教研組其他教師已然具備了一定的設計、分析、改進課堂教學的意識與能力了。
基于辛老師所繪制的“節點研討課”與集體備課和教研組研討三者之間的關系圖(見圖2)以及田野筆記的描寫可以發現,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的完整展開過程包括:時間序列上的備課組集體備課、教研組的“聽評課”活動以及跨域組的“節點研討課”研討活動,并由此形成了三大活動系統,如圖4所示。
事實上,“節點研討課”這一活動系統中還蘊含著另一個由大學研究員(教育理論者)、辛老師(教育實踐者)和區教研員(教學指導者)為代表的三大活動系統,在此不做贅述。
在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方式中,參與聽評課的人員在研討過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既有經驗,也有理論;而從活動系統的分工內容和實施狀況來看,參與人員也是理論與實踐并行,對辛老師的課堂教學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給出可能的改進意見。辛老師正是在這樣的研討過程中不斷被打磨,才逐漸獲得了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辛老師為何能夠在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方式的影響下,獲得理論與實踐的協同發展。綜上所述,是由于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注重以不同活動系統之間的聯動與跨界來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五、結論與反思
借助活動理論為視角發現,個人鉆研這種教研方式由于忽視學習的社會性特征而導致他人優秀教育教學理念、經驗等無法在交流中更好地被吸收和內化,因而會造成教師專業發展停滯不前;教研員指導又因指導者缺乏理論層面指導工具而無法以理論結合實踐的方式對課堂教學進行指導,因而造成教師只是點狀地獲得教研員教學經驗、技能等;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因注重持續性的多活動系統間的聯動和跨界研討(教育理論界與教育實踐界合作研討)來對課堂教學進行指導與改進,并注重在指導過程中不斷引領和引導教師自覺以理論關照和完善實踐,因而能夠促進教師理論與實踐的協同發展。
本研究也引發研究者對上述三種教研方式的反思:首先,就個人鉆研來說,主體反思往往與之相伴,而反思在所有學習活動中都不可或缺。因此,個人鉆研雖然未能很好地促進辛老師的專業發展,但不能因此否認它在教師專業發展中的重要價值。其次,教研員指導是教育實踐中最常被用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方式之一,由于教研員大多是從一線教師中走出來的,他們更加清楚一線教師課堂教學中可能面臨的問題或困惑,因而能夠給予更具針對性的指導,但也需要看到,教研員因相對缺乏系統教育理論,有時候并不能促進教師系統、全面的發展。最后,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有助于促進教師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但其成效也極有可能會因教師習慣性的工作思維而削弱。
研究表明,一線教師往往更關注“怎么做”,而不是追問“為什么這么做”,長此以往,異質共同體合作教研帶來的理論與實踐綜合融通的積極影響在教師個體身上很有可能會漸趨減少。總之,每一種教研方式都各有優缺點,應當努力推動各種教研方式之間發生聯動效應,使它們在優勢互補中形成合力以更好地為教師專業發展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