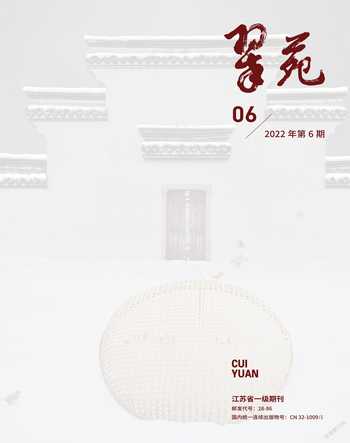最后的水手
一
凡是和大斌打過交道的人,都會對他的豪爽和義氣印象深刻。大斌一張標準的國字臉,額頭袒平,兩耳高闊,口鼻眼分布規(guī)整,輪廓清晰。他的身高從初中就固定了,中等身材,腰背挺直。他在人群中,不突兀不張揚,而自信的態(tài)度給人以信賴。超過三十歲,這幾年他的發(fā)量在減少,留著蓬松的發(fā)型。
千禧之年的北方,8月一個暑氣盛大的日子,我們成為光榮的中學生。中學近觀水庫、遠眺青山,位于一條省道的北側。烈日炎炎。校園里,梧桐樹碩大的葉子茂盛無邊,遮不住少年們的興奮、激動和緊張。葉子與葉子之間,彌漫著綠色的氣息。
我們躲在樹下乘涼。老譚走過來,把教室的鑰匙交給大斌,把宿舍的鑰匙交給我,就這樣,把那個班交給了我倆。
三年里,大斌當班長,我做團支書。合作中,我們形成的默契,就像風吹草木在山谷里引出回響,這種默契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漫漫人生路,進入初中,只能算作一次演習。今后的人生,我們將完成更多、更驚險的跳躍。
年少求學,讀書的意義所在,正是讀書本身。
那時我們精力充沛,泉水從山間汩汩而出,源源不竭。熄燈以后,寒冬雪月,冷風侵肌透骨,我們掇條馬扎坐在雪地里,借著路燈的微光看書。此事在學校里傳為美談,大家都知道了四班的學生學習之刻苦。對知識的那種強烈渴望,在今后的歲月里不復出現(xiàn)。那是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激情。
人與人情感的加深,一定是共同經歷過難忘的事件。支撐事件的情節(jié),作為雙方共同的記憶點,成為日后心照不宣的觸發(fā)機制。
北方鄉(xiāng)村學校,基礎設施落后,學校沒有專門的保衛(wèi),傳達室只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大爺,作為一種象征存在。據(jù)說一女生起夜,看見窗臺上趴著一個腦袋,頭發(fā)像鞋刷的毛一樣短。那女生摸了摸自己的長發(fā),忽然反應過來。女生凄厲的驚叫,甚至傳到了幾百米外校長的家中。
女生宿舍偷窺事件鬧得人心惶惶。學校召開緊急會議,聲言一定要抓住偷窺者。此后,各班派出學生輪流巡夜,每個月會輪到一次,就像月盈月虧,潮漲潮落,朔望輪轉,非常準時。
我、大斌、啟東、彥偉四人一組守前半夜,另一組守后半夜。學生們睡下后,月明星稀的夜晚,暑氣燠熱的夜晚,以及其他一些躁動的夜晚,我們扛著滑溜溜的橡木棍子,仿佛揣著繡春刀,在校園里巡邏。我們是暗夜的守護者。
走著走著,夜色被踏得越來越深,像是從深潭中打撈出來的水草,帶著濕漉漉的暗澤。微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在夜里幻化為巨大的聲響。偷窺者很有可能藏在暗的后面,一切細微的聲音都變得夸張而龐大。
在尋找偷窺者的夜巡中,我們建立起信任,可以把安全放心地交付于對方的信任。
冬天,保衛(wèi)處生有炭火爐子,我拿火棍撥弄紅通通的炭塊,消解夜晚的寒寂。更深露重,我們圍坐在火爐旁,用不銹鋼快餐杯煮面條,只加一點鹽,沒有其他配料。而后熱氣彌漫,蒸騰裊裊。
魯迅先生在《社戲》里說:“一直到現(xiàn)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二十年后,我們一致認為:再沒吃到過那夜那么好吃的面條了。
一個夜晚,我和大斌站在滿天的星光下,晚風輕輕地吹拂著我們長滿青春痘的臉頰。月光灑落人間,廣袤而博大,我們向月亮致以問候,月亮也向我們致以微笑。月色如水如絲如滑,我忽然覺得夜色像是剛出浴的美人,冰涼中透著深深的神秘氣息,遠處黑魆魆的連綿的丘陵,像是女性凹凸的曲線。我的心臟忍不住悸動了一下,就像猛踩剎車,后備廂里的物件由于慣性發(fā)出了沉悶的聲響。
那夜過后,我知道了什么叫作自我的覺醒。那夜大斌有沒有覺醒,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在那夜或前或后不長的時間里,也是覺醒了的。
在覺醒的一些年后,我才觸摸到覺醒的肉身。那也是在一個夜晚。我和她坐在小河旁,身后垂下萬條柳絲,月亮識趣地躲到柳樹后面,夏天的蟲鳴一波一波貼著水面飄過來。那晚在月亮的見證下,我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我聽到了兩顆心合奏演出的二重唱。看著河面上月亮的倒影,我覺得那晚的月色特別的美。
小學五年級,有一次做廣播體操,大斌的手指碰到了一個女孩的手指。他說唯一的那次接觸:“像有一股電流順著指尖傳遍全身。”從他的講述中,我能察覺到他對那個女孩有過朦朧的情愫。他是一個標準意義上的好學生,三年里,他只與我談過這一次關于異性的話題。
進入初三,中考是繞不過去的大河。累了的時候,同學們以唱歌的方式放松和打氣。啟東的左臉上有一塊硬幣大的胎記,他握著歌詞,站在教室里唱《水手》的時候,那塊胎記起起伏伏,一會緊縮起來,一會氤氳開去。那種起落的狀態(tài),像極了躁動的青春。
那時候,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大海上最勇敢的水手,縱然風大雨大,依然可以破浪前行。只要再努力一些,就可以把船頭駛進可眺望的未來。那未來,虛空而縹緲,美麗而迷人。
初中畢業(yè)后的幾年,我們回過兩次學校,后來隨著外出求學、生活變故和聚散離合,中學漸漸地偏安于記憶深處了。每次乘車從校外匆匆而過,雖是短暫一瞥,仍能看到學校數(shù)年間的變化。一年又一年,新的學生進來,老的學生離開,學校就這樣在迎來送往中,佇立于時間的風霜雨雪里。她像一個守在故鄉(xiāng)的母親,默默地等著遠方的兒女回家。
二
縣城有四所高中,大斌去了四中,我到了二中。高中幾年,聚少離多。一次會考,我們被分到同一所學校。中午一起吃飯,17歲的他已經表現(xiàn)出超越年齡段的成熟,倒茶布菜,妥帖周全。
我喜歡過一個女孩多年,大斌對我說:“等你不再喜歡她的時候,你就長大了。”那時我覺得他的話簡直不可思議,我喜歡了她那么久,怎么會有一天就不喜歡她了呢,我相信我會一直喜歡她到永遠。
后來的事情印證了大斌的預言。他總能看到事情未來的樣子,而我只能不斷地返回過去。他在思想和行為上的成熟,有如神跡。
一封2004年大斌寫給我的信,記錄下一個十幾歲少年思考。他在信中寫道:
“整個社會大環(huán)境總是好的,新漸生起的一些不良習氣卻弄得我很混亂,有些疲憊,有時發(fā)覺理想已被淡漠,自私、自負占主角了,心里也很氣憤,常常責備自己,太不爭氣了,忘不了曾經豪言,只是心里有些茫茫然,太可怕了,或許也太現(xiàn)實了。”
以成人視角去反察少年的想法,可能會覺得有些不自量力甚至矯揉。可是啊可是,那是17歲才有的真實心態(tài),那份赤子之心難能可貴。我們都有過那樣一段理想主義的時期,那時我們以為自己法力無邊,可以匡扶社會、改變世界。后來,再長大一些,我們發(fā)現(xiàn)并不能改變世界,甚至連堅守初心都非常困難。
只是,我們要承認那顆赤子之心的可貴,如若人人堅守年輕時的理想,那些關于真誠、善良和美好的圖景,就像七彩的陽光照進房間。
我和大斌的大學時光,在煙臺那座海濱城市度過。在學校附近尋一家小飯館,一盤辣炒蛤,一盤土豆絲,幾瓶啤酒,就那么喝著聊著。對一些話題的思考,他常常可以另辟蹊徑。比如關于懷舊,大斌說,小時候,吃到一包泡面,讀到一本新書,感覺都是幸福的。我們之所以懷舊,不是因為過去豐富,而是因為今天我們所能得到的太多,并且容易。當獲得滿足變得輕易,那滿足也來得沒那么充分。
種一棵樹什么時間最合適?當然是十年前。十年前種下一棵樹,現(xiàn)已經亭亭如蓋矣。如果十年前沒有那樣的先知先見,還有一個時間,就是現(xiàn)在。因為離過去和未來最近的,只有現(xiàn)在,我們無法抵御時間的流逝,但可以在時間的兩岸種下草木,總有一天會繁花夾道。
如今看來,那樣的交流不過是心接青冥,縱以清談,兩個書生扮演起指點江山的角色。在那座城市,我們仍是十幾萬大學生中微不足道的存在。我們都在積蓄力量,等待一場涅槃,破繭而出。
畢業(yè)后,大斌去了淄博,換了三份工作。初出茅廬,這是試探的代價。他就職的一家管材公司位于郊外,靠近廣闊的山林地帶,卡車將產品運往全國各地。有一次,大斌押車去山西,來到曾經“農業(yè)學大寨”的晉中大寨村,撫今追昔,那個烈烈揚揚的年代不過才過去了幾十年。他在大寨村給我打電話,我站在煙臺清泉寨的陽臺上,望著海面上澎湃的夜色,與他聊了很久。
更多的時候,大斌會到院子周邊走走,他看著太陽從朝陽變成了夕陽,看著天空從藍色慢慢變成了紫葡萄色。他從諾基亞手機上獲取外部資訊,小小的屏幕成為他與外界聯(lián)絡的隧道。隧道的外面,是一個高速運轉的世界。
日子就這么一天一天過去,一日三餐,日落而息。沒有朋友,沒有娛樂,他仿佛蟄伏在地下的蟬的幼蟲,等待著一朝破土,羽化飛升。他還記得《逍遙游》中“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的句子。他在聚糧,準備一場遠行。
王小波在《黃金時代》中寫道:“那一天我二十一歲,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來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變成像挨了錘的牛一樣。”
還好,24歲的大斌,沒有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他也沒有被劁掉。他還有熱情,他想去看看隧道另一頭的世界。
三
寫下“北京紫竹院”這五個字,像是寫下了一種豪邁。正如李敖的《北京法華寺》,這類城市加具體地點的命名,充滿了空間上的縱深和歷史上的延展,讀起來有一種豪情萬丈的感覺。雖然,紫竹院只是一個鬧市中的公園。
2012年,除夕的鞭炮余響猶在,大斌乘上了北漂的列車。他在北京西五環(huán)的城中村,租了一間小小的房子。房間位于一棟二層建筑的上層,鐵質樓梯置于樓房外側,上下樓時發(fā)出當當?shù)牟忍ぢ暋N堇镏挥幸蛔酪灰我淮惨灰录芏选O掠甑臅r候,雨點敲擊屋頂?shù)穆曇繇樦鴫p傳到他的耳朵里,晴天的時候,沙塵會鉆過小小的氣窗飄到屋子里。北漂的艱辛與苦澀,在這間屋子里一覽無余。
他在一家職業(yè)培訓機構工作,據(jù)說他們的客戶都是小有所成的經理級人物。大斌與同事拿著幾千塊的工資,培訓那些收入遠遠高于他們的人,現(xiàn)代文明下的一些工作,充滿了荒誕。公司位于紫竹院公園南側,午飯后,大斌喜歡到公園走一走,那個公園接納了一個北漂者的孤獨。
兩個月后,我到北京參加研究生復試。四月的一個中午,我們約在公園附近的一家小店碰面,吃的是河間驢肉火燒,喝的是驢雜湯。飯后,他第一次帶我走進了紫竹院。春日的紫竹院,竹葉蕭蕭,幽篁深深,碧水悠悠。京城的大爺大媽們在賣力地踢毽子,抖空竹,拉二胡,唱京劇。一群掛著單反的學生,在老師的指點下,對著盛開的桃花調整著焦距,記錄下一幅幅虛虛實實的春景。游人們買了鳥食,灑向空中,鴿子撲棱著翅膀準確地銜住食物,像是受過特殊的訓練。情侶們手牽著手,頭貼著頭,竊竊私語走在竹林的幽影里,把春天釀造成一個幸福而甜蜜的季節(jié)。
而公園的外面,是一座奔跑的城市,車流穿梭,樓宇林立。這樣的公園,在城市地圖上會以綠色的模塊標注。走進這片綠色,不管是居民還是游人,都能在這里獲得想要的輕松與舒適。
我向大斌感慨,在北京這樣喧鬧的大都市,能有這么一個公園,真是難得啊。大斌告訴我,每個工作日的中午,他都會繞著公園走一圈,漫步之間,仿如能走掉一身的勞累與煩心。就像史鐵生形容他的地壇那樣:“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這樣一個寧靜的去處,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紫竹院公園,成為大斌北漂生活的見證。
很多年里,我們總能相聚在一起,這不是一個人追隨另一個人的腳步,而是兩個人在選擇和性格上的契合。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我在他的小屋里擠了半個月。床上只鋪了一張木板和一張薄薄的褥子,兩個人躺在一張床上,翻翻身子,床板會發(fā)出咯吱咯吱的聲響。我對大斌說,隔壁不會以為咱倆在干什么吧。
北京城還是冷冷地關上了城門,我最終也沒有到北京讀書,我從慢慢閉合的城門縫里,看到了一個步履踉蹌的孩子,一個孜孜苦學的少年,一個帶著苦笑淚花的青年。后來大斌推薦我讀野夫的《鄉(xiāng)關何處》,看到作者“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聲,仿佛沉積了一個世紀的淚水陡然奔瀉”時,我的淚水也忍不住流了下來。
那一年,大斌的母親身體有恙,這讓他不得不審視“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他是一個孝子,他不想留下不能盡孝的遺憾。京城米貴,居之不易。在北京,他只是一片蒲公英,就那么飄著游著,他不是一棵樹,他的根扎不下來。他說他的根在故鄉(xiāng),在山東。他總是要回去的。既然要回去,那就早些回去吧。一年后,大斌回到濟南,此后一直在銀行業(yè)深耕,結婚生子。
他也迷惘也自問,難道人生就這樣度過嗎?人生終究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大斌說,結婚之前,他關心社會、大眾與自我。有了孩子以后,他的心態(tài)變了,他的根牢牢地扎入了大地。經營好家庭、婆媳間和睦、孩子茁壯成長,他熱愛這些現(xiàn)世的幸福。那些宏圖大志和偉大構想,不是消失了,而是被藏起來,被貯藏在一間特別的屋子里。“我把自己經營好了,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四
2019年大年初一,我和大斌回了一趟中學。年關當下,校門大開,我們徑直駛了進去。原來正對門口的花壇已不見蹤跡,一條大道直通底部的院墻。過去我們挑燈夜讀的老教學樓也消失了,那座樓曾是鎮(zhèn)上唯一的三層樓房。90時代,有的孩子為了看樓,從遠處騎幾個小時的自行車前來觀瞻。這在今天簡直不可思議。
我們沿著塑膠跑道走著,冬日和煦的陽光灑滿操場,一群青年在綠茵上踢球,汗水淋漓,陽光落在他們的球衫上,汗珠里映照著初春的校舍。他們帶著青春的氣息奔跑著,就像多年前的我們。
無須太久,我們便走完了一圈,記憶中的學校縮小了,就像一只漏了氣的氣球。從13歲到16歲,這個學校就是我們的整個世界。我們蟄伏在此,覺得它是無比的廣闊與曲折。我們在樓道里嬉鬧,在雪地里奔跑,提著長棍順著圍墻夜巡,學校里有那么多的房間,房間里有那么多的桌椅,甚至連每一棵樹和每一朵花都充滿神秘。如今回來,學校怎么會變得那么小了呢,難道是我們的腳步太快了嗎?
14歲這年,大斌在課堂上向全班提出了一個問題。大斌左手托著筆記本,右手拿著筆,帶著少年的老成問道:十年后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這其實是一道簡單的職業(yè)規(guī)劃題,這題目若是放在大學時期,一點都不足為奇,但那時我們剛剛邁入青春期的大門。大家感到新奇而激動,回答得積極而熱烈,大斌也認真地做了記錄。大斌說他想成為一名戰(zhàn)略指揮家,我說我想成為一名作家。
在大斌提出那個問題后的十年,我成了一名記者,他成了一名銀行職員。同窗之中,有的讀研深造,有的進入體制,有的身陷囹圄。而大部分人,成為所謂的“打工人”,在這個遽然變化的社會中,匯入了人潮人海。
做了兩年記者后,我去上海讀研。“到北京,上大學”的理想終究沒有實現(xiàn)。就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2018年我到北京出差,住處位于展覽館路,離紫竹院公園只有兩站。也是一個中午,不同的是,這次是一個秋日,我又走進了紫竹院。
故地重游,我和紫竹院已經是老朋友了。我拍照片發(fā)給大斌。他說,沒變,還是過去的樣子。在一棵巨大的欒樹下面,一對中年男女悠然舞蹈,步伐輕盈,他們踩在金黃的落葉上,像踩在秋天的色彩和韻律上。
時間這艘大船,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前挺進。曾經在京城里清談闊論的我們,此刻被山水和云霧阻隔。借著理想的余暉,在黃昏面對著大江大河之時,我還能看到在紫竹院漫步的那對青年。大斌說,有那么一個地方,就像有那么一個人,可以讓我們常常想起,可以讓我們在聽到簌簌竹聲時,想起年輕時的日子,這足矣是一件美妙的事了。“那個公園里住著我們的青春。”
從過去到未來,大斌永遠是一個符合中國式理想的人物,一個嚴以律己的君子。他待人真誠、周到、熨帖,彬彬有禮,他堅守著一些牢固的規(guī)則和道德律。他曾經豪情滿懷,走向遠方。當返回生長他的土地,他的身上依然有閃閃發(fā)光的東西。他是我身邊最后的水手。
作者簡介:
朱未,本名朱軍,文藝學碩士、江蘇省作協(xié)會員,作品見于《散文選刊》《揚子江詩刊》《詩歌月刊》《青春》《文學報》《文藝報》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