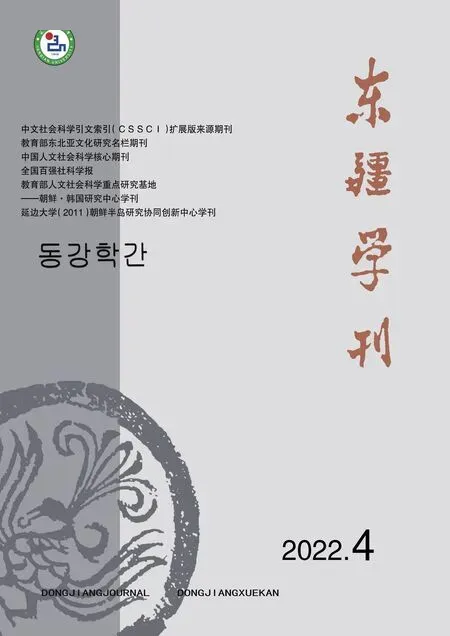“湖蘇芝”對朝鮮王朝詩風轉變的關鍵作用辨析
王琳,嚴明
明清時期,華夏詩壇經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唐宋詩之爭”①有關明清時期中國詩壇上發生的“唐宋詩之爭”的論述請參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王英志《清代唐宋詩之爭流變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而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詩壇上也遭遇了一次唐宋詩風的轉變。16世紀朝鮮朝詩壇以學蘇軾和黃庭堅為代表的宋詩風占據絕對優勢,后逐漸轉變為唐詩風。[1](232)這個轉變并非一蹴而就,成宗時(1469—1495年在位)出現轉變苗頭,宣祖時(1567—1608年在位),以“三唐詩人”的出現為標志,古代朝鮮朝詩壇完成了詩風轉換。此后呈現出“詩人極眾,詩話亦盛,其作詩風尚則自宋易唐,自蘇還杜”[2](12)的特征。
在這場詩風轉換的過程中,“湖蘇芝”三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湖蘇芝”指的是湖陰鄭士龍(1491—1570),蘇齋盧守慎(1515—1590)和芝川黃廷彧(1532—1607)。目前中韓學界對“湖蘇芝”三人的詩作定性尚有不同看法。1994年李鐘默發表博士論文《海東江西詩派研究》(首爾大學),將鄭士龍、盧守慎、黃廷彧三人歸入“海東江西詩派”,認為三人宗尚宋詩。2015年,李鐘默在《湖蘇芝律詩的文藝美》一文中進一步指出:三人“在以精巧的‘宋風’作為共同點的同時又在個性上有些許不同”。[3](102)中國學者也接受了這個觀點,如馬金科在論述“海東江西詩派”時,提及鄭士龍、盧守慎、黃廷彧三人的漢詩創作。[4](168-170)但另一方面,也有韓國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如在閔丙秀《韓國漢詩史》一書中將“湖蘇芝”列入穆陵盛世時期,認為他們是“館閣的大手筆”,但并不認為他們歸屬于“海東江西詩派”。[5](266-271)2013年曹喜昌發表論文《湖蘇芝詩文學的研究——以唐詩風為中心》認為,“湖蘇芝”三人推動了唐詩風的發展。[6](125-167)因此,厘清三人的詩作淵源及詩學宗尚,對于把握朝鮮朝時期唐宋詩風的轉變意義重大。三人中以盧守慎對當時詩風轉變的作用最大,因此本文以分析盧守慎漢詩為切入點,進而討論三人在唐宋詩風轉變中的重要作用,并探究其原因。
一、盧守慎的典型學杜
盧守慎(1515—1590),字寡悔,號蘇齋、伊齋、暗室、茹峰老人,謚號為文懿,后改為文簡,其一生歷經中宗、仁宗、明宗及宣祖四朝。因“乙巳士禍”之故,1547年(明宗二年)盧守慎遭遇流放,先后流放至順天、珍島、槐山,共計22年,在珍島度過了人生艱難的19年。宣祖繼位后,盧守慎重返仕途,曾先后擔任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最后官至領議政。《宣祖實錄》云:“還朝七年,寵遇特異,擢置相位。”[7](宣祖二十三年四月一日條)其漢詩主要載于《蘇齋先生文集》,該文集共十卷,卷一至卷六為詩,共有漢詩約1501首。從詩體分類看,五律占比最多(758首),其次為七律(267首)和七絕(263首)。從創作時間看,流放時期最為高產,22年間共創作了1023首漢詩。①數據源自??? 〔曹喜昌〕:《蘇齋盧守慎的詩文學》,誠信女子大學校博士論文,2010年。如申欽所言:“其在海島所作詩多警絕,膾炙人口。”[8](1391)
在朝鮮朝詩壇上,盧守慎是一位典型學杜的詩人。權應仁評曰“蘇齋相國之詩,專學老杜,純正老雅”[9](550),許筠以為“盧蘇齋得杜法”[10](1486)。盧守慎的學杜功夫,主要表現在化用杜詩詩句、五律規模杜詩、詩風追求杜詩等三個方面。
盧守慎對杜詩稔熟于胸,詩作中常自覺化用杜詩句式。如《芝峰類說》云:
盧蘇齋因送客醉后作一詩未成,有蟬為驟雨所驅墜于席前,公即續之曰:秋風乍起燕如客,晚雨暴過蟬若狂。似有神助。杜詩云“秋燕已如客”,乃用此也。[11](1287)
秋風句出自《送盧子平埈赴東萊》,原詩為:
古敦同姓今何薄,人旺分宗我獨涼。
舊友若干常抱介,新恩千里更情傷。
秋風乍起燕如客,晩雨暴過蟬若狂。
南翁七十又二歲,生別死別俱茫茫。[12](197)
其中“秋風乍起燕如客,晩雨暴過蟬若狂”句,化自杜詩《立秋后題》“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玄蟬無停號”即盧守慎筆下的“蟬若狂”,許筠《國朝詩刪》評為“換杜之胎”。[13](521)從“南翁七十又二歲”,可知此詩作于盧守慎晚年,用“秋風”渲染凄清環境,再以孤燕喻自身,以狂蟬喻政敵。
盧守慎于五律用力最深,他曾對學生康復誠(1550—1634)說:“我與湖陰詩名相埒,世不能辨其優劣,余之長律不及湖陰,湖陰短律不及于余,各有長處。”[14](1430)后世朝鮮詩人多贊同此說法。金萬重《西浦漫筆》云:“蘇齋自謂七律不如湖陰,而五律勝之,此言甚公。”[15](2251)許筠亦言:“盧蘇齋、黃芝川,近代大家,俱工近體。盧之五律,黃之七,俱千年以來絕調。”[16](1494)南龍翼《箕雅》一書選盧守慎詩34首,其中五律17首,占比最高。可見盧氏五律最佳,實為詩壇公論。盧守慎擅長五律,源于其對杜詩五律的模仿最下功夫,梁慶遇《霽湖詩話》評曰:
盧蘇齋五言律酷類杜法,一字一語皆從杜出,其“詩書禮學未,四十九年非”之句世皆傳誦,實出于老杜《詠月詩》“羈棲愁里見,二十四回明”,可謂工于依樣矣。[17](1430)
許筠在《國朝詩刪》中評“詩書禮學未,三十九年非”為“奇對”。[13](413)此對句出自盧守慎《別白文二生(八月)》詩,白指白光勛(1537—1582)、文指文益世(生平不詳)。原詩曰:
莽蕩乾坤阻,蕭條性命微。
詩書禮學未,三十九年非。
露菊憑烏幾,秋蟲掩竹扉。
此時文白至,三宿乃言歸。[18](152)
杜詩中“羈”對“棲”,“二”對“十”,而盧詩中“詩”對“書”,“三”對“十”,仿效杜詩對仗而“工于依樣”。方回分析杜甫《杜位宅守歲》詩中“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聯云:“以‘四十’自對‘飛騰’字,謂‘四’與‘十’對,‘飛’與‘騰’對,詩家通例也。唐子西詩‘四十緒成素,清明綠勝紅’祖此。”[19](571)可見盧守慎學杜,除了化用杜詩句式典故,對杜詩中的對仗也有專門借鑒。此外,這首詩頷聯,梁慶遇《霽湖詩話》記為“四十九年非”,而《蘇齋集》中記為“三十九年非”。到底是三十九還是四十九?筆者以為應為后者。因為盧守慎詩集按時間順序分卷,《別白文二生(八月)》載于《蘇齋先生文集》卷四,同卷中有《聞河西亡》《哭河西》等詩。盧守慎《年譜》云:“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在島。二月,哭金河西,有悼亡律。又有哭河西二十韻。”[12](294)據此可知《別白文二生(八月)》作于三十九年庚申。詩中所言“三十九年”,當指嘉靖三十九年(1560),而非三十九歲。時年盧守慎四十五歲,古人記歲虛長一歲,故《年譜》曰四十六歲。產生這樣的誤解,可能與當時大量次韻李白《潯陽紫極宮感秋》的風氣相關,“四十九年非”句成為模寫唐詩的一種符號。[20](245)
對杜詩的細致揣摩,使盧守慎形成與杜詩相似的詩風特征。南龍翼《壺谷詩話》給當時許多知名漢詩人二字評語,比如評盧守慎為“淵宏”。[21](2199)金錫胄則評盧氏為“懸崖峭壁,老木蒼滕”。[22](2915)金昌協《農巖雜識》中的論述最為一語中的:
盧蘇齋詩,在宣廟初,最為杰然。其沉郁老健,莽宕悲壯,深得老杜格力,后來學杜者莫能及。蓋其功力深至,得于憂患者為多。余謂此老十九年在海中,只做得《夙興夜寐箴》解,而亦未甚受用。后日出來,氣節太半消沮。獨學得杜詩,如此好耳。[23](2844)
在金昌協看來,盧守慎“深得老杜格力”,不僅是宣祖初年最優秀的漢詩人,也是朝鮮王朝時代學杜最成功的詩人,而這份功力來自其被長期流放偏僻海島的人生經歷。比如盧氏《十六夜,感嘆成詩(乙丑八月)》詩云:
八月潮聲大,三更桂影疏。
驚棲無定魍,失木有奔鼯。
萬事秋風落,孤懷白發疏。
瞻望匪行役,生死在須臾。[12](162)
這首詩作于乙丑八月(1565),時年盧守慎51歲,是其流放珍島的第19年。“八月潮聲大,三更桂影疏”渲染出了本詩寫作的時空背景,“大”既點出了聲音之響,也說明了浪潮之高。“三更”明示夜已深,“疏”呈現出桂影斑駁之狀,與“大”字形成對比,故而《國朝詩刪》評此句:“磊落軒騰”。“失木有奔鼯”化用杜甫“寒日經檐短,窮猿失木悲”(《寄杜位》),點出了盧氏受人迫害,驚魂甫定、流離失所的人生慘境,被許筠評為“壯浪語”。“萬事秋風落,孤懷白發疏”透露出落寞傷感的情懷,秋風掃落葉已是凄涼之態,又逢“孤懷”與“白發”,更顯加倍慘戚,被許筠評為:“蕭瑟語”。許筠又評其“瞻望匪行役,生死在須臾”為“慘然”。[13](413)盧守慎這首詩還引起朝鮮朝詩壇的關注和討論,《東詩叢話》云:“盧蘇齋詩句可壓當時諸輩,以其雄壯近古也。如《八月十六夜》……海翁常言:此可見蘇翁雄處。第四不欲讓老杜一步,而但‘魍’字離‘魎’字做不得。”[24](9364)海翁即尹善道(1587—1671),他認為這首詩充分體現了盧氏的雄壯詩風,“失木有奔鼯”雖化用杜甫詩句,但可與杜詩爭奇。美中不足的是,“驚棲無定魍”只用了“魍”字,而未用“魎”字,但這恰恰顯示出盧守慎用字較為追求出新。
以上三點體現了盧守慎詩作與杜詩的密切淵源。需要指出的是,盧守慎并不只是推崇杜甫,他也十分欣賞王、孟的詩風。其詩作還呈現出清新淡遠的風格,如《送李欽哉》頸聯云:“寒雨孤蓬卷,芳尊兩眼明”[12](195),許筠評曰“降格為王孟,亦自明概”[13](419)。
二、鄭士龍、黃廷彧的由宋轉唐宗尚
鄭士龍(1491—1570),字云卿,號湖陰,東萊人,著有《湖陰雜稿》。1509年(中宗四年)文科狀元及第,1514年(中宗九年)賜假讀書,1554年(明宗九年)典文衡,同年因泄露科舉試題而遭罷官,后復職,官至判中樞。1534年(中宗二十九年)、1544年(中宗三十九年)兩次作為冬至使出使明朝。其人性格暴虐,《宣祖實錄》載:“自少酷慕豪富,營產致饒,侈美自奉,不恤人言”,但文采出眾,后世皆重其文采,《宣祖實錄》云:“丑名亦為所掩云”。[25](宣祖三年四月一日條)
與盧守慎有所不同,鄭士龍最擅長的詩體為七律。當時文人傳言“申企翁眾體皆具,而湖陰獨善七律”,就此鄭士龍回應曰:“渠之眾體安敢當吾一律乎?”①《韓國詩話全編校注》(第2冊,1486頁)及《韓國文集叢刊》(第74冊,326頁)皆作“渠之”。筆者以為,“渠之”當為“漢之”之誤。原因有二:一、根據上下文,“渠之”指的是“申企翁”,即申光漢(1484—1555),字漢之,號企齋。字、號中皆未有“渠之”。二、金安國和申企齋之間有唱和之作,金安國詩題為《題僧浻峻長老詩軸,次申漢之韻》(第20冊,106頁),詩曰:“轟飲東臺記昔年,臺前仍系下江船。春光欲老花猶在,天氣全晴月正圓。一紀往來頻換主,千篇吟詠似欽禪。溪橋又發無端笑,怕落塵中上畫傳。”申光漢詩為《用靈運詩軸韻,書俊上人軸》:“家住江南已六年,偶隨秋水放江船。重尋甓寺橋憐舊,一揖山僧性覺圓。宦味紅塵曾染指,儒林白首欲逃禪。題詩只記登臨日,不用人間萬口傳。”(第22冊,398頁)根據兩詩內容及韻腳,得知金安國詩題中的“申漢之”當為“申光漢”無疑。申企齋即申光漢(1484—1555),字漢之。據此可知,鄭士龍自以其七律為傲。關于鄭士龍的詩學宗尚,李睟光曾云:“鄭湖陰為詩主蘇、黃,晩年甚悔之,每讀樊川、義山”[11](1345),可知其初學蘇軾和黃庭堅,后轉為學習杜牧、李商隱。
鄭士龍初期詩作可以《荒山戰場(即我太祖捷倭之地)》為代表,詩云:
昔年窮寇此殲亡,鏖戰神鋒繞紫芒。
漢幟豎痕留石縫,斑衣漬血染霞光。
商聲帶殺林巒肅,鬼燐憑陰堞壘荒。
東土免魚由禹力,小臣摹日敢揄揚。[26](13)
荒山位于全羅道南原市,此詩詠荒山大捷。荒山大捷指李成桂、李之蘭于1380年在荒山擊退元朝阿其拔都軍隊侵犯。為了紀念此役,宣祖在南原建立“荒山大捷碑”。此詩中使用“漬血”“鬼燐”“殺”“陰”等字眼,奇崛鮮明。明人吳明濟批評此詩:“爾才屠龍,乃反屠狗,惜哉。”許筠則指出此詩不受好評的原因是“蓋以不學唐也”。[16](1487)
鄭士龍晚年詩風可以《紀懷》詩為例,詩曰:
四落階蓂魄又盈,悄無車馬閉柴荊。
詩書舊業拋難起,場圃新功策未成。
雨氣壓霞山忽暝,川華受月夜猶明。
思量不復勞心事,身世端宜付釣耕。[26](176)
李達年輕時曾向鄭士龍學習杜詩,詢問鄭士龍平生最得意的詩句,鄭士龍答曰:“雨氣壓霞山忽暝,川華受月夜猶明”為其平生得意句,事見許筠《惺叟詩話》。從“商聲帶殺林巒肅,鬼燐憑陰堞壘荒”至“雨氣壓霞山忽暝,川華受月夜猶明”,頗能見出鄭士龍早年和晚年詩風的不同。洪萬宗《小華詩評》引蘇世讓(1486—1562)評語云:“鄭湖陰士龍,奇古峭拔,一洗萎累之氣,可與唐之長吉、義山并較才”[27](2333),認為鄭士龍與李賀、李商隱才力不相上下。也就是說,鄭士龍晚年詩體現出了晚唐詩的特征。可見,鄭士龍詩作取徑由宋入唐,先主蘇黃詩,后轉學晚唐。
黃廷彧(1532—1607),字景文,號芝川,謚號文貞,長水人,有《芝川集》四卷,附錄(上下卷)。1558年(明宗十三年)登第,1584年以宗系辯誣使②宗系辨誣:明《皇明祖訓》和《大明會典》中將朝鮮朝太祖李成桂之父誤記為高麗權臣李仁任,朝鮮朝就此事多次向明朝遣使辨誣,歷經中宗、仁宗、明宗和宣祖四朝,直至1589年尹根壽等人帶回修正后的《大明會典》,辨誣才結束。的身份出使明朝,次年因功受封光國功臣、長溪府院君。在“壬辰倭亂”中,黃廷彧被日軍加藤清正脅迫,給宣祖寫勸降書,此事成為其政治生涯的污點,“壬辰倭亂”結束后受到執政東人的攻擊,流放吉州。后因宣祖特命,結束流放,準許其回歸鄉里,但直至去世也未能重返朝廷,享壽七十六。
黃廷彧自幼學習杜詩,其曾祖父“手抄杜詩五七言律若干首口授”。[28](479)其好友尹根壽認為他“詩規老杜,卓然自樹,力振弱調,雅健為主。”[29](296)可見,他以杜詩為源頭,經過磨煉,形成剛健凌厲的詩風,別具一家,與當時詩壇卑弱詩風相抗衡。如《海》詩云:
目力東收碧海來,茫茫溟渤在亭臺。
二儀高下輪輿轉,太極鴻蒙汞鼎開。
貝闕珠宮生睇眄,馮夷河伯送風雷。
時危兵甲猶如許,誰挽滄波洗得回。[28](442)
詩中使用與宇宙、天宮、自然相關的詞語,如“太極”“珠宮”“風雷”等,形成一種壯大開闊的氣象,襯托出海的雄偉。許筠評首頷頸聯分別是“突兀”“昌大得襯”“古今有得么”[13](534),著眼點都在矯健宏大的風格上。其中“貝闕珠宮生睇眄”化用黃庭堅“貝闕珠宮開水府”(《宮亭湖》),“時危兵甲猶如許”化用杜甫“時危兵甲黃塵里”(《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許筠又評其“自作一家,非杜非黃”[13](534),就是說通過向杜甫和黃庭堅學習,黃廷彧詩作形成了獨具一格的面貌。
黃廷彧擅長的詩體亦為七律。《箕雅》收黃廷彧七絕一首,七律十五首,從數量上可以看出選編者南龍翼對其七律成就的認可。[28](614)《送沈公直忠謙赴春川》七律詩云:
清平山色表關中,下有昭陽江漢通。
馳出東門一匹馬,泝洄春水半帆風。
送人作郡鬼爭笑,問舍求田囊久空。
為語當時勾漏令,衰顏須借點砂紅。[28](438)
此詩頗受許筠贊賞,他評頸聯曰:“湖、蘇無此奇”[13](533),指出這句詩表現出了與鄭士龍、盧守慎截然不同的詩歌風格。在“湖蘇芝”三人中,許筠最欣賞黃廷彧,曾云:“其矜持勁悍,森邃泬寥,是千年以來絕響……而出入乎盧、鄭之間,殆同其派而尤杰然者。”[30](181)許筠是古代朝鮮的著名詩論家,其論詩“以唐詩性情本質作為詩歌批評的標準,崇尚唐詩,輕視宋詩”[31](36),從許筠的贊賞中也可見出黃廷彧詩作與唐詩風的密切關聯。
綜上所述,“湖蘇芝”三人漢詩創作上的共同點是皆由宋入唐,或學習晚唐詩人,或奉杜甫為圭臬。在漢詩體裁上,盧守慎擅長五律,鄭士龍、黃廷彧擅長七律。三人不同的人生經歷、氣質秉性又造就了三人不同的詩風。金昌協曾評論三人的詩風曰:“世稱湖蘇芝,然三家詩實不同。湖陰組織鍛練,頗似西昆,而風格不如蘇;芝川矯健奇崛,出自黃陳,而宏放不及蘇。蘇齋其最優乎?”[23](2844)金昌協以為鄭士龍漢詩與西昆體頗為相似,黃廷彧漢詩矯健奇崛,但二人皆不如盧守慎。金昌協認為黃廷彧的漢詩出自黃、陳,溯其根源,實源于杜詩。在宋詩風彌漫的朝鮮朝初期詩壇,“湖蘇芝”三人的詩學主張對當時詩風的走向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具體論述如下。
三、“湖蘇芝”對朝鮮朝詩壇詩風轉變的影響
對于朝鮮朝建國以來的詩風走向,李睟光(1563—1628)曾云:“我東詩人,多尚蘇黃,二百年間,皆襲一套。”[11](1051)許筠(1569—1618)也曾說過:“二百年來俊民出,燦如象緯羅天闕。中間縱許湖蘇芝,毋奈劌刃遭磨缺。”[30](143)李睟光和許筠為同時代詩人,他們所言的二百年間,是指從高麗朝末期直至“三唐詩人”出現之前的這一時段。這一時段主要受宋詩風的影響,到了末期學宋弊端愈發明顯。在“三唐詩人”出現之前,朝鮮朝詩壇上與宋詩弊端相抗衡的就是“湖蘇芝”三人。許筠《惺叟詩話》云:“我朝詩至宣廟朝大備,盧蘇齋得杜法,而黃芝川代興。崔、白法唐而李益之闡其流。”[16](1486)可見,盧、黃二人將學習對象轉向杜詩,三唐詩人在此基礎上又繼續推動了學唐一派的發展。如果說“三唐詩人”的出現,代表著朝鮮王朝詩壇完成了由宋轉唐的詩風改變,那么“湖蘇芝”三人的作用,就是在這之前最早推動了朝鮮朝詩壇由宋轉唐詩學風尚的轉向。
“湖蘇芝”三人為何能夠推動詩風走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三人都身居館閣要職,有較大的詩壇影響力;二是三人幾乎都與“三唐詩人”有交往,或作為“三唐詩人”的老師,或與他們保持長期聯系。尤其是盧守慎,對白光勛有知遇之恩,與崔慶昌的交往一直持續到晚年。對“三唐詩人”的詩學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湖蘇芝”又稱“館閣三杰”,因三人都曾擔任文衡一職。文衡是古代朝鮮朝館閣機構的最高代表。當時的館閣機構主要指弘文館和藝文館,兩館都設有大提學一職,文衡是大提學的簡稱。文衡對文壇發展有重要意義,朝鮮朝趙復陽(1609—1671)曾云:“竊惟國朝以來,最重文衡之任。哲匠宗師,遞相傳授。詞垣故實,可以歷數。以臣耳目所及睹記者言之。中興以后,迭主齊盟,皆是文章老手世所稱大家數者。風流文采,炳烺前后。”[32](170)此外,擔任文衡一職的必是德高望重之人,“文衡之任,非徒取其才藝,必位望德行俱優者能稱其任。”[33](成宗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條)擔任館閣機構要職,有一定的行政影響力,同時品德高尚、詩藝精湛,這是三人能夠推動當時詩壇發展、詩風轉變的重要前提。
鄭士龍明宗九年(1554)擔任文衡,盧守慎宣祖五年(1572)擔任文衡,黃廷彧宣祖二十四年(1591)擔任文衡。[34](63—92)黃廷彧擔任文衡,主要是因為盧守慎的推薦。許筠載:“先王又喜黃芝川文,而蘇齋相極力推轂之,遂自提學進兼大提學。”[30](344)可見,盧守慎因激賞黃廷彧而推薦其擔任文衡一職。盧守慎詩學老杜,而其推薦同樣學習接受杜詩的黃廷彧接任文衡,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當時學杜詩風的延續。
“湖蘇芝”三人與“三唐詩人”交往密切。李達年輕時曾向鄭士龍學習杜詩,許筠《惺叟詩話》云:“李益之少時學杜詩于湖陰。”[16](1487)“湖蘇芝”三人中以盧守慎對“三唐詩人”的影響最大。與盧守慎交往最早的當屬白光勛。白光勛22歲時,曾去珍島拜訪盧守慎,并結下深厚師友情意。白光勛《年譜》云:“戊午,公二十二歲……時盧蘇齋謫居珍島,公又往學焉。蘇齋贈公詩云:‘神交久名聞,義合可年忘’,又云:‘吾衰不足畏,子邁莫須遲’。兩詩皆在蘇齋集中。”[35](159)“神交久名聞,義合可年忘”出自《白生光勛至,夜飲,十月》,“吾衰不足畏,子邁莫須遲”出自《來日將別白生,生請一語,乃醉書與之》。二詩載于《蘇齋集》卷四,同卷中亦有《哭權直學(五月)》。權容,字公擇,號奇齋,生于1515年,卒于1558年,可知二詩作于盧守慎四十四歲時。從“神交久名聞,義合可年忘”之句,見出二人在精神氣質上十分契合。“吾衰不足畏,子邁莫須遲”則透露出一位老者對后生殷切的期盼與鼓勵。盧守慎重入仕途后大力舉薦白光勛,白光勛因而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成為制述官。白光勛《墓志銘》載:“蘇齋膺命館伴,請于朝,以公為白衣制述官。”[35](160)制述官的職責之一就是與中國使臣相互唱和,“凡制述官必和進《皇華集》,例也”[36](135),所以一般選用詩才出眾的人擔任。由此可見,盧守慎對白光勛漢詩才能的欣賞。
盧守慎流放珍島時,崔慶昌也曾前去探訪。盧氏詩集中現存兩首與之相關的詩。一首題為《登道岬寺,次韻子靜。十一日晴,與子靜上是寺,寺甚輪奐,靜邀崔慶昌來,飲其酒,同宿》,詩云:
三生未了是前因,不爾能逢萬死濱。
只愧十年閑過卻,更教人誚弄精神。[12](142)
另一首題為《崔正字慶昌攜酒相看(時患痁戒酒)》:
瘧癘三秋忍,風塵一月開。
賢人酒冷冽,正字意胚胎。
破戒緣生興,忘言為死灰。
摧頹老癡漢,非子復誰哀。[12](144)
從“同宿”“忘言”等字眼可見二人相聊甚歡。崔慶昌對盧守慎點化地名之巧妙非常嘆服,前引《鶴山樵談》崔氏贊賞“路盡平丘驛,江深判事亭”之句便是一例。
盧守慎與李達曾在神勒寺有過短暫交往。盧守慎詩題為《神勒寺覺長老軸中次韻》,詩云:
神勒前朝寺,高僧普濟居。
煙云暮帆落,水月夜窗虛。
名利身猶縛,山林跡若疏。
孤懷感泡沫,萬事付澆書。[12](176)
李達詩為《次盧相國韻,題甓寺僧軸》,詩云:
客路隨山轉,僧房枕水居。
村煙團野直,江沫汰沙虛。
接物心肝在,流年鬢發疏。
驪江連漢水,雙鯉可轉書。[37](10)
神勒寺現位于韓國京畿道驪州市,相傳為新羅真平王時期元曉大師所建。該寺內有一座用磚頭砌成的殿塔,故而又名甓寺、驪州壁寺。從李達詩題“盧相國”三字可知,李達與盧守慎相遇應是盧守慎晚年時。此外,盧守慎還有一首贈李達的詩,題為《興原舟中,贈李達》,詩云:
遠岫轉佳氣,長灣收日華。
親朋眼中一,芳草席邊多。
文會詩無敵,清談酒不賒。
如何憂患仕,終日在風波。[12](200)
“文會詩無敵”贊美李達才思敏捷,“清談酒不賒”稱譽李達風流氣度。李達出身低微,仕途坎坷,一生幾乎在流浪中度過。而此時盧守慎一心歸隱,數次請辭,都被宣祖拒絕,因此末句“如何憂患仕,終日在風波”既可以看成是對李達的寬慰,也可釋為盧氏無奈的自白。
四、結論
16世紀朝鮮朝詩壇風氣由宗宋轉為宗唐,其中一個重要表現是學習對象的遷移:由宋蘇軾、黃庭堅轉為唐代詩人,尤其是轉向了對杜甫的學習。宋代詩人主要學習杜詩中奇絕拗健的風格、以文為詩的手段等,由此形成了宋詩風貌。而朝鮮朝詩壇風氣變化的路徑與之相反,他們從清除宋詩派末流的弊端出發,向上溯源至杜甫,由此開啟了全面學唐的局面。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館閣大臣“湖蘇芝”的作用極為重要。三人都表現出了崇唐的詩作傾向,不過又有所區別。湖陰鄭士龍年輕時學蘇黃,晚年轉向學晚唐,蘇齋盧守慎與芝川黃廷彧的漢詩都源出杜甫。盧守慎對杜詩的模學推崇最為徹底,他是古代朝鮮詩壇上大力模仿杜甫的詩人,后世鮮有人能超越。三人生活于詩壇風氣轉變的歷史關頭,他們的漢詩既帶有宋詩風的因素,又表現出自覺向唐詩風過渡的傾向,情況較為復雜。也正因如此,后來詩壇學界對他們的評價才會出現不同的聲音。
綜上所論,在朝鮮朝詩壇唐宋詩風轉換的過程中,“湖蘇芝”三人最早推動詩風由宋轉唐的走向。究其原因,首先是三人身居高位,漢詩造詣較高,這是三人能夠推動當時詩壇風尚轉向的重要前提。其次,三人通過師生交游關系,直接影響了“三唐詩人”的詩學宗尚形成。三人中以盧守慎與“三唐詩人”的交往最深厚,尤其是盧守慎與白光勛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因此盧守慎當之無愧地成為“湖蘇芝”中的代表性詩家。
值得注意的是,三人學唐是在明七子復古思潮傳入之前①“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朝鮮朝文人在中朝外交使節交流的過程中認識到李攀龍、王世貞在中國文壇的聲名及其復古文學思想”,明七子的復古思潮最早于16世紀末傳入朝鮮,首倡者為尹根壽。具體論述參見韓東:《李攀龍、王世貞復古文風在朝鮮朝文壇的傳播與影響》,《東疆學刊》,2021年第4期。。可見朝鮮王朝詩壇風尚的由宋入唐,絕不僅僅是受到外部原因的影響刺激,而是因其內部已產生這一轉變的萌芽,故而當明七子詩論傳入時便能被迅速接受。朝鮮朝詩壇崇尚唐詩浪潮的演變與發展途徑和趨勢,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這對于探索和界定古代朝鮮漢詩整體演變脈絡的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