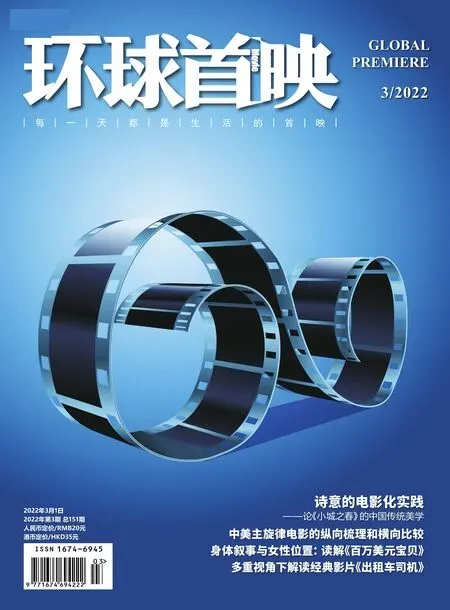拉康視域下巖井俊二電影中的成長敘事
佟安琪 中國傳媒大學
20世紀90年代,在日本國內對電影產業的政策鼓勵的推動下,從70年代進入“夕陽”時期的日本電影復蘇,“新電影”運動的序幕被拉開,出現了一批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新銳導演,巖井俊二因其獨特的青春映像風格在“新電影”導演中獨樹一幟[1]。1995年,巖井俊二電影處女作《情書》上映,因此他獲得第8屆日刊體育電影大賞新人獎、第20屆報知電影賞導演獎、第21屆大阪電影節導演獎三項大獎。此后的時間里,他接連創作了電影《夢旅人》(1996)、《燕尾蝶》(1996)、《四月物語》(1998)、《關于莉莉周的一切》(2001)、《花與愛麗絲》(2004)等青春題材影片。在這些影片中,巖井俊二展現了他對于青春強大的感知能力,因此,其也被稱之為日本青春片的代言人,巖井俊二擅長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他記憶里的少男少女,青春這個母題在其電影創作過程中不斷形成。青春,既是唯美的也是殘酷的,這種矛盾體現在導演的個人創作的方方面面。巖井俊二筆下所描繪的青春也恰好體現了日本電影這種矛盾的美學特質,他不會只描述青春的燦爛美好,同樣也執著于去探尋少男少女們成長中的那些迷茫疼痛、掙扎與無奈。他所創作的青春,更加的開放、多角度,在冷峻的殘酷和心碎的溫柔中反復展演。在這樣一番圖景中生存的主人公經歷著成長帶來的陣痛與轉變,不斷的完成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如果用拉康的鏡像理論審視其電影中的成長敘事,成長的殘酷體現得淋漓盡致。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開啟了精神分析電影符號學,其著名的鏡像理論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基礎上重新詮釋了主體的本質。弗洛伊德看來,自我的形成是從俄狄浦斯階段開始,但拉康認為,俄狄浦斯情節是主體形成過程中需要克服的第二異化階段,這之前的第一次異化是鏡像階段的鏡像認同[2]。在拉康的鏡像理論中,6~8個月嬰兒這一主體不斷地通過鏡子中自身形象,來逐步獲得自己身份的同一性。這一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是通過與他人一起看到和確認自己;第二是在他人的現實中將自己區分出來;第三是形成自己基本人格的同一性[3]。可以說拉康的鏡像階段是主體形成的過程,也是成長的開始。
一、認同受挫:無望的尋找自我
(一)難辨“自我”與“他者”致使認同受挫
影片《夢旅人》是以可可、卷毛、小悟三個精神病人為主角,展現了他們在精神病院的生活,以及在外面尋找世界末日的旅行的圖景。可可因為奇怪的舉止、掐死自己的孿生妹妹的罪行被父母送進了精神病院,她一直堅信自己的死亡才代表著世界末日的到來,在她結識了病友卷毛和小悟并與之成為朋友后,三人便一同踏上了醫院的圍墻,去追尋世界末日的到來。一路上,他們經歷了許許多多的人和事。中途,小悟走失落隊,從高高的圍墻摔落,弄得滿身的鮮血,從此再也沒有醒過來。緊接著的一場暴雨,孤獨的卷毛向可可訴說著自己內心的痛苦和恐懼,互相取暖的兩人相擁并熱吻在一起。影片的最后,當兩人來到了燈塔上,可可為了使卷毛的靈魂得到解脫,搶過卷毛原本射向太陽的槍,開槍選擇了自殺。在這個充滿著奇幻和尋找的故事中,我們可以在可可的身上清楚地看到認同受挫的迷茫。
鏡像階段的開始,嬰兒自身并不具有完備的感知與自主行動能力,鏡中的形象對于她來說是突然收獲的整體的形象,因此導致無法辨識自己的迷茫。這是嬰兒最初的,能夠擁有自我意識的階段,之后她將要去學習如何在鏡中分辨出自己的形象,也就是通過“他者”辨認出“自我”,來完成關于自我的完整的統一的身份認同。所以由此可見,分辨出“他者”與“自我”是在確認自我過程中尤為重要的一步。
巖井俊二將《夢旅人》中自己的主角設置為精神病患者,致使角色本身就帶有了認同受挫的特征。以鏡像理論看影片中的人物可可,在她的想象中,父母是造物主,世界隨她的出生而誕生,在她眼中,她就是世界的主宰,一切都是因她而存在,也就是她即世界,世界或稱作“他者”,在她的眼中,這本應是“他者”的“世界”已與她的“自我”混為一體。這樣看來,可可無疑是仍活在拉康的想象域中的嬰兒,她的世界也如嬰兒一般,是破碎的,尚未形成“物”與“我”分離的意識,分不清“自我”與“他者”。由此可以窺見其無法辨識自我的“認同受挫”的特征。巖井俊二的電影是關于成長的,在《夢旅人》中,出現“認同受挫”的主角的成長,是迷茫而又無望的。
(二)認同受挫引向無望的自我追尋
正因為她無法分辨出“自我”與“他者”,為了證明自己和孿生妹妹誰是冒牌貨而打賭,因此掐死了自己的孿生妹妹,導致她被她視為造物主的父母“拋棄”,滿臉堆笑著哄騙可可進了精神病院。對于個體來說,自我認同的過程與成長息息相關。早早被關入精神病院的可可雖然是行為奇特且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分辨障礙,但其依舊是獨特的,她有著強烈的尋找自我的意識,自進精神病院起就要與他人不同,她要穿著黑羽毛的衣服與一片慘白的精神病院形成區別,她帶領卷毛和小悟踏上了邁出精神病院的第一步。
但她這種對于自我的追尋是無望的,她無法分辨“自我”與“他者”也就無法形成一種“主體”觀念。“主體”是與“自我”“他人”共同構成鏡像階段的三分結構之一,它不等同于“自我”,僅僅是“自我”建構過程中的產物[4]。從可可無法區分他人這方面看,她是無視客體,以自我為中心的,但可可不曾擁有這一“自我”建構的階段,毫無“他者”觀念,也就談不上進入認同階段,由此發生了認同受挫,意味著人生中重要的“一次同化”,也是第一次異化的失敗,引向無果的自我追尋。在影片的結尾,可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為卷毛展現世界末日的模樣,這一凄美的場面在視覺上展現了殘酷美,同時也完成了自我尋找無望后迎來毀滅得更為徹底的青春成長殘酷敘事。
二、自戀式侵凌:保護誤認的自我
(一)自戀認同
電影《關于莉莉周的一切》同樣是巖井俊二電影中殘酷青春物語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故事講述了蓮見雄一與同班的星野修介,兩人是要好的朋友。在暑假里,他們一同去沖繩參加社團活動,讓人沒想到的是,旅行過后星野脾氣的變化,粗暴且孤僻,升上中二的時候,星野甚至開始欺負蓮見,隨之而來的是蓮見性格漸漸變的孤僻自卑,他只能在喜歡的歌手“莉莉周”的歌聲里尋求安慰。而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其中所暗藏的原因正在于主角星野在他的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一次次欺凌,最后在多次無法獲救的情況下,星野意識到自己溫柔善良無法得到回報,于是丟棄掉了原來的軟弱的自己,轉而變成欺凌人,這便是一次自我認同的失落。
在鏡像第三階段中,嬰兒將自我與他人分離開后,瘋狂迷戀上自己的鏡像,產生了自戀認同。拉康式的自戀是對自我完美鏡像的迷戀。升入高中后星野雖然性情大變,但一直沒變的是對歌星莉莉周的迷戀。莉莉周之于星野,正是理想的“以太”一般的存在,純潔美好。戴錦華老師總結道:“忘我的他戀,同時也是強烈的自戀。”[4]星野滿懷欣喜,將自己所有對于美好的向往映照在莉莉周這一“他者”的幻想上。在鏡像階段中,自我的形成與他人的形象密切相關,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來自于對于他人的誤認。星野將自己理想中的完美自我投射到莉莉周的身上,是一種誤認,對莉莉周的愛正是對完美理想自我的一種自戀。當這種誤認他者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形象產生沖突時,這種自戀會引發主體對于現實對象的否認與侵凌。
(二)欺凌是保護誤認自我的一種形式
《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一片中充斥著青春里種種欺凌行為,主角星野從優等生變作霸凌的主使者的過程,體現了一種自戀式的侵凌。拉康在其博士論文《論妄想型精神癥與人格的關系》中重點分析了女患者“埃梅”這一病例,埃梅因妄想而持刀傷害了著名演員蓋特,埃梅的妄想對象都是她理想中的但其本人無法成為的存在,她的傷害行為從一定程度上是由自戀引發的自我懲罰,妄想理想形象是迫害者,故對其攻擊以達到保護理想的目的。星野暗戀的初中同桌久野,是星野喜歡莉莉周的原因之一,在星野眼中可以說久野成了莉莉周之影,是“以太”的代表,乖學生時期的星野被人百般欺凌時,久野其實也是將自己置身事外的視而不見的同學們之一。所以在星野開始作為霸凌者向過往復仇時,象征純潔與美好的久野亦被當作迫害者,星野對久野的傷害,也體現他的自我懲罰,來保持理想中最純潔的“以太”的存在,以保護理想中的自我。
《關于莉莉周的一切》中充斥的欺凌場景從視聽上足以展現成長中的殘酷,但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上來看,拉康將嬰兒自戀認同時的鏡像合一稱為“一次同化”,這同時也是第一次自我異化,嬰兒所認同的鏡像并不是他自身,而是影像,二者是對立分離的。所以對于星野來說,他理想中的自我只是虛幻的存在,這一點使得星野的成長更令人唏噓。
三、凝視印證匱乏:發現真實自我
(一)“凝視”得到的真相
影片《情書》講述了因為一封記錯地址的信牽扯出來女藤井樹(下稱“女樹”)、男藤井樹(下稱“男樹”)以及遠藤博子之間的愛情往事。男樹因為一直埋藏在心中多年的年少暗戀與遠藤博子相戀,深愛著男樹并無法走出男樹逝世陰影的博子在忌日寄出了一封代表思念的信件,沒想到卻收到了回復,博子最終得知自己多年來的愛戀對象男樹和自己相愛的原因竟是因為與自己長相酷似和男樹擁有同樣姓名的女樹。不管是相似的容顏還是名字,該片充分體現了鏡像之戀,雖是清純愛情的書寫,但其中未能如愿的兩段愛戀仍體現了成長之殘酷。
拉康在論述鏡像階段時引申出“凝視”的概念,這里的“凝視”帶有自身欲望的投射,在鏡像階段中的自我認同無法離開對于“他者”的帶有欲望的“凝視”。以影片《情書》女主角女藤井樹為“凝視”主體可以窺見在鏡像階段中發現自我的成長。
《情書》中女樹與博子互為鏡像,隨著故事的展開與推進,擁有著與博子同樣容貌,又擁有與男樹同樣的名字的女樹逐漸發現自己的愛情真相。起初,她長期處于一種對一切視而不見的狀態,面對自己日漸加重的病情卻抵觸就醫,在街道上與博子擦肩而過而不自知,對年少時的暗戀更是無所察覺。但后來,通過與博子不斷的書信往來過程中,她打開了自己封閉起來的帶有創傷的年少記憶,那里有病逝的父親還有暗戀她的少年男樹。最終的她迎來了可以稱得上是“圓滿”的結局。在影片的結尾,她收到了博子歸還的所有信件,她又看到了學妹送來的男樹在借書卡背面畫她的小像。一來一往的信件勾起的回憶,加之最后借書卡的點明,女樹終于在“凝視”中明確了男樹在少年時代曾深深暗戀她的愛情真相。
(二)“匱乏”背后的錯失
叔本華曾指出欲望就是匱乏,“凝視”本身投射了欲望,而欲望的存在證實著在認同過程中的“匱乏”,是難以滿足的欲望促使我們去追求永遠失去的“匱乏”。這份匱乏于女樹身上體現在年少歲月的流逝,愛人亦不在人間。自女樹收到博子的信開始追憶往昔時,起初是迫于博子的問詢,之后女樹也沉浸在追憶過去的過程當中,在這個“凝視”過程中,她慢慢發現了愛情真相,她的“凝視”帶有好奇,也表現著欲望,也正是因為“凝視”印證了女樹過去視而不見的“匱乏”,使得女樹發現了自己真實的曾愛過,也被愛過的自我。這種成長看起來是圓滿的,但又透露出殘酷的真相,當女樹終于發現男樹在少年時代就現端倪的愛時,男樹已離開人世,那段純美的愛情永遠封存在過去,于她而言顯得遙不可及,可以說,就像“凝視”的對象是永遠得不到的“匱乏”一樣,這無疑也印證了巖井俊二成長敘事中的殘酷,即使是用干凈純美的愛情故事包裹著,內里還是一個主角與真愛錯失的故事。
四、結語
鏡像認同帶有主體建構過程中理想化的成分,當主體發現之前的認同是一種誤認后,會導致這一建構的破滅,由此認同和破滅不斷重復,人便在殘酷不斷的挫折中成長不止,可以說拉康的鏡像階段是關于人是如何構建自我的過程,這個過程帶有悲劇色彩,正如成長的痛苦一般,而巖井俊二在創作中著力書寫著青春成長的殘酷,用鏡像階段對照巖井俊二電影中的人物,就像可可、星野、女樹,他們受困于“自我”與“他人”的迷霧中,在挫折中尋找自我,在誤認中保護自我,在凝視中發現自我,這些都是青春的真實寫照,是每個人內心深處的迷茫,巖井俊二的成長結局是殘酷的,但又給人以破繭成蝶的希望,這大概就是巖井俊二的青春題材電影獨特的迷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