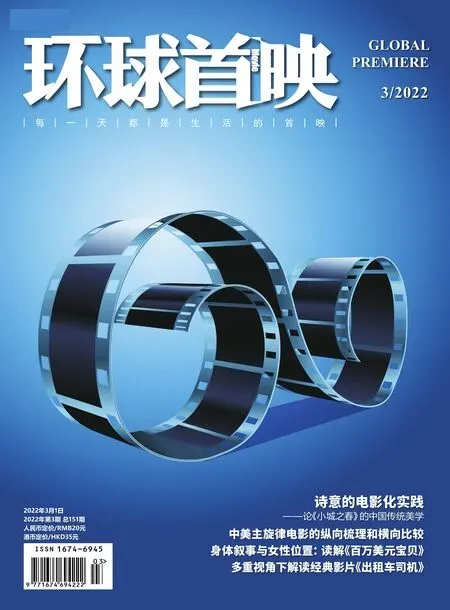詩意的電影化實踐
——論《小城之春》的中國傳統美學
2023-01-05 09:29:42王玥萌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
環球首映
2022年3期
王玥萌 江蘇師范大學科文學院
創作于1948年的《小城之春》是中國著名導演費穆所執導的最后一部長故事片,也被看作是中國詩化電影的高峰,影片拍攝時間距今已有70多年,這部散發著文人氣質的沉靜憂郁電影在當時并沒有引起巨大轟動,甚至受到業界的批評和質疑。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與歷史的沉淀,我們越發能夠感受到這部具有中國傳統美學風格的實踐電影作品所蘊含的豐厚詩意特色。
一、內斂的人文情感
電影是一種綜合時空藝術、節奏藝術和造型藝術元素的第七藝術形式,其中文學與電影的關系最緊密,而詩歌是歷史最為悠久的一種文學體裁,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理論,到早期法國先鋒派及法國詩意現實主義的發展,無不體現出藝術家將富有動感的影像與浪漫的文學相結合,創作出一副悠揚詩意的電影畫卷。而中國詩歌自身就具有一種含蓄美,再加之“賦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都呈現出與西方電影有所不同的情景交融的美學特色,不斷出現的城墻場景,極具南方特點的老宅子以及周玉紋的獨白或是與章志忱之間含蓄的對話方式等,都體現著中國傳統美學的詩意特征。筆者將從影片的人文情愫、鏡頭語言、敘事手法這三個方面,來分析影片在中國傳統美學上的藝術表現及其美學價值。
電影的開端,是女主角玉紋買完菜走在城墻上的鏡頭,戰爭使他們一家瀕于頹敗,整日也是了無生機的樣態,每天在妹妹戴秀的房間里獨自繡花和嘆息,誰曾想這一切平靜的日子會被章志忱的到來而打破。……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杭州(2023年3期)2023-04-03 07:22:36
美食(2022年2期)2022-04-19 12:56:08
綠色中國(2019年18期)2020-01-04 01:57:12
文苑(2019年22期)2019-12-07 05:29:06
現代裝飾(2019年7期)2019-07-25 07:42:08
福建開放大學學報(2019年2期)2019-07-10 00:50:18
流行色(2018年5期)2018-08-27 01:01:42
藝術啟蒙(2018年7期)2018-08-23 09:14:14
Coco薇(2017年8期)2017-08-03 02:01:37
Coco薇(2015年5期)2016-03-29 23:1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