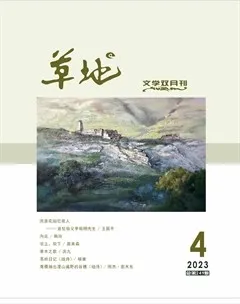民族花燦憶故人
一
去歲春早,乍暖還寒。
三月的某日,收到吾兄李銑代父李紹明先生轉(zhuǎn)贈的圖書《變革社會中的人生與學術(shù)》,一冊厚達300頁的書濃縮了乃父跌宕曲折的一生,留下了費孝通、馬長壽、馮漢驥、李安宅、吳澤霖、林耀華、宋蜀華等一個群體厚重無言的剪影。
李銑兄在扉頁題字云:“亦先生亦伯父”。
彼時,春風依然料峭,但心中卻有暖意升起。誠如斯言,李紹明先生于我,既是關愛之師長,亦是慈祥之伯父。
撫書追昔,墨香撲鼻,偶爾從柔軟的時光里抬起頭,驀然驚覺:秋去春來,伯父李紹明先生竟已離去十年。
二
十二年,蒼山的云聚了又散。
十二年,邛海的月圓了又缺。
十二年,格桑的花開了又落。
十二年,蘿卜的寨毀了又建。
十二年,我們在時光里沉睡,又從思念中醒來。
三
我第一次見到伯父,是在2005年7月11日。
當時,我參與策劃的“大禹文化與江源文明學術(shù)研討會”在都江堰市二王廟賓館舉行,在與會名單中我見到了素所敬仰的著名學者李紹明的名字,內(nèi)心的喜悅無法描述。因為早在很多年前,我就已讀過他的重要著述《羌族史》,由此開始對羌族文化有了初始認知。而他的兒子李銑,則是我多年前就已因詩相交的兄長,因了這一層關系,我對伯父便更有了一份親近之心。
見到伯父時,一點也沒有尋常意義上的意外驚喜,我就像一個內(nèi)向的晚輩見到了自己尊敬的師長,稍顯拘謹。而伯父卻沒有一點大學者的架子,他一手瀟灑地搖著折扇,一手挽著脫下的外套,談吐之間,風度翩翩,完全是我想象與期待中的大家風范:溫良儒雅、平易近人……后來,當我與他談起李銑時,伯父毫不遲疑地說:“那你肯定認得到廖永德!那是個熱心人啊……”
多少年過去了,當日的情形宛在眼前。
艷陽之下,樹影婆娑,我陪伯父伯母緩步向房間走去,院里潔白的梔子花開得正繁,清香不時襲來,濃郁了那個夏天。
四
以至于我后來在讀到李銑兄的詩歌《梔子花》中的那句“依然盛開在往昔的風中”時,總有一種時光倒流、似曾相識的感覺,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個下午和穿行在梔子花香中的我們。
疏忽之間,多么像一幅寫意的油畫,在歲月里慢慢凝固。
五
我時常在想,假如許我以更多時光,我多么愿意陪伯父跋涉在祖國的山水之間,在他的身邊默默地做一個助手、一個學生甚至一個書童,為他煮茶、擔酒、掌燈、抄書……
但是沒有假如,所以我只能在往事里遙想伯父的身影。
六
伯父祖籍系原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今重慶市),李家在秀山本是望族,到了伯父父親李亨這一代開始破落。李亨上過私塾,二十歲不到就到酉陽邊做雜事邊旁聽講學,后結(jié)識名人吳嘉謨并隨吳到成都做事。吳后任關外學務局總辦,李亨亦隨之出關,1907年,創(chuàng)辦了涉藏地區(qū)第一所官辦學校——巴塘小學。后來,李亨四處辦學,并曾得到清廷嘉獎,提拔為縣丞。清末,同盟會進入巴塘,李亨參加了同盟會,成為涉藏地區(qū)早期會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吳嘉謨離開關外學務局回康定,眾人便推舉李亨代理總辦。隨后不久,蜀軍政府委任李亨為昌都府知事,結(jié)果因為當?shù)貞?zhàn)事而未能到任。返回成都后開過錢莊、煤礦,經(jīng)營過百貨,搞過交通運輸。1927年,四川進入劉文輝時代,劉派李亨擔任漢源縣縣長,李亨在當?shù)貫槊褡隽撕芏鄬嵤潞檬拢鉀Q了很多民族問題糾紛,被譽為“草鞋”縣長。
1933年12月23日,伯父生于成都,1950入華西大學社會學系學習。他是教會大學的最后一批學生,也是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批學者;他專攻民族學,也受過歷史學的訓練;他受西方理念影響,也有中國傳統(tǒng)道德觀念的熏染;他既是田野工作的踐行者,又參與推動了諸多學術(shù)機構(gòu)的創(chuàng)立并擔任過領導者。他曾做過費孝通、馬長壽等民族學大師的助手,親身經(jīng)歷了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學科歷史上的諸多重大事件,他先后參與少數(shù)民族大調(diào)查。他著述宏富,在學術(shù)界享有巨大聲譽和廣泛影響,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點對藏族社會進行研究,并提出康區(qū)的特殊性以及“穩(wěn)藏必先安康”的重新認識,受到中央主要領導的肯定;生前曾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民族學科規(guī)劃組成員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委、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西南民族學學會會長、四川省人大常委、四川省社科聯(lián)副主席、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長、享受國家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伯父是一位道德文章堪稱楷模、學術(shù)聲望名播天下的大學者,他的一生幾乎是那一輩中國學人的縮影。他尊重長輩,關愛同仁,提攜后學,其治學成就和師表風范,足以成為我之楷模。
七
多少年過去了,羌族高山上的羊角花沒有忘記。
1951年夏天,黑虎鄉(xiāng)的青草才剛剛拔節(jié),伯父就隨著老師玉文華先生開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少數(shù)民族調(diào)查。
伯父一行八人,背著口糧和鋪蓋,從成都出發(fā),向羌族聚居區(qū)而去。經(jīng)過灌縣(今都江堰)時,他們買了豆豉、豆瓣、豬油,用一口大鍋把它們混在一起炒好,帶著在路上當菜吃。當時伯父只有17歲,沿途也沒有公路,他們沿著岷江河谷遺留的松茂古道,時而翻越高山,時而穿過峽谷,艱難前行,用了7天時間抵達茂縣,又走了5天,來到赤不蘇區(qū)。
隨后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一行四人挨家挨戶地調(diào)查羌族政治、經(jīng)濟、生產(chǎn)、人口、文化、婚姻、家庭狀況等相關情況。不久又協(xié)助地方工作組,推動建立新的基層政權(quán)。
據(jù)伯父回憶,調(diào)查工作非常危險,有一次過一條河,同行的背夫一腳沒有踩穩(wěn),米就掉下去了,背夫下去撿米,結(jié)果米沒有撿回來,人卻被沖走了。背夫被沖走了,大家心驚膽戰(zhàn),但自己還得過河。最后不得已,決定女同學走上游,男同學走下游,一旦女同學發(fā)生意外,方便救援。結(jié)果女生張亞慶一不小心跌入水中,幸得搶救及時,才撿回一條性命。
鄉(xiāng)政府成立時要選舉領導,投票效仿解放區(qū)的做法,被選舉的人坐著,每個人背后放一個碗,選舉者想選誰就在誰背后的碗里投一個豆子,這個鄉(xiāng)政府就稱為“豆選鄉(xiāng)”。
后來,伯父又多次前往羌族聚居區(qū)調(diào)研考察,1985年,他和冉光榮、周錫銀合著的《羌族史》正式出版,為羌學研究奠定堅實基礎,成為羌族研究領域極其重要的學術(shù)著作。
八
多少年過去了,大小涼山上的索瑪花沒有忘記。
1952年,伯父隨川南民族訪問團一行前往小涼山、峨邊地區(qū),進行社會調(diào)查。當時國民黨特務控制了峨邊縣的西河地區(qū),伯父們不僅要做民族調(diào)查,同時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在特務、土匪的密切關注下,積極勸說和爭取彝族上層人士,靠攏政府,一個多月的調(diào)查,讓他對彝族有了嶄新的認識。
據(jù)伯父講,當時彝族地區(qū)盛行買賣奴隸,一個黑彝奴隸主居然看上了訪問團的兩位女團員,想用錢來買她們。伯父當時就開玩笑問:“怎么個買法”,黑彝奴隸主給出的價格是胖點的女團員50兩銀子,瘦點的女團員40兩銀子。
1956年至196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組織有計劃對全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狀況進行科學調(diào)查。此活動由毛澤東倡議、彭真負責。調(diào)查工作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持,成立了由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主任劉格平、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劉春和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費孝通組成的調(diào)查領導小組。在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上,編寫出少數(shù)民族的《簡史》,為我國少數(shù)民族名稱確認和民族劃分提供了科學依據(jù)。
伯父認為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學術(shù)實踐活動,萬萬不能錯過,于是他通過多種渠道爭取到了名額。1956年10月1日,伯父隨四川民族社會調(diào)查組前往涼山,參加了布拖縣則諾鄉(xiāng)(黑彝統(tǒng)治腹心區(qū))、雷波縣馬頸子鄉(xiāng)(黑彝邊緣區(qū))、雷波縣土壩鄉(xiāng)(獨立白彝地區(qū))、甘洛玉田鄉(xiāng)(土司統(tǒng)治區(qū))。伯父和同事們一起,白天走家串戶做調(diào)查,晚上還必須將調(diào)查資料趕緊整理出來,調(diào)查時間長達一年多。
第一階段調(diào)查結(jié)束后,涼山發(fā)生了武裝叛亂,調(diào)查組再次開赴涼山調(diào)查。為了保證調(diào)查人員安全,伯父等接受了軍事訓練,人人配槍出門調(diào)查。當時,為了解決民主改革中的叛亂平息問題,專門成立了中央慰問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民委主任王維舟任團長,四川調(diào)查組夏康農(nóng)任副團長,夏先生讓伯父做他的秘書,從調(diào)查組借調(diào)到慰問團工作。
伯父回憶,1956年底的一天,他帶上一個武警,去布拖鄉(xiāng)下了解一個奴隸主的情況,本來是準備當天返回城里的,后來因事耽擱,當天沒有回城。后來才知道,當天叛亂分子就埋伏在他們回去必經(jīng)的一個山埡口,等著收拾他們。要是當天趕著回去的話,可能已經(jīng)沒命了,想起都后怕。
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調(diào)查工作依然堅持開展,伯父憶及此事時說:“本來涼山奴隸制度解剖一兩只麻雀就可以了,但我們解剖了十幾個麻雀,前前后后那么長時間,花了那么大力量,就是為了要最終確定涼山的社會性質(zhì)。”
最終,依據(jù)涼山彝族的等級關系、階級關系、土地制度和剝削方式證明當時的涼山就是奴隸制社會。1982年,由伯父擔任總篆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介紹涼山彝族社會的著作,該書對涼山彝族奴隸社會的生產(chǎn)力、生產(chǎn)關系和上層建筑等各個方面作了介紹和分析,同時還對彝族的來源和它經(jīng)歷的原始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該書被學界譽為“科學大廈的奠基石”。
九
多少年過去了,阿壩高原的格桑花沒有忘記。
新中國成立之初,阿壩州民族教育非常落后,僅有一個民族干部訓練班。1954年,伯父從西南民族學院畢業(yè),受命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阿壩,創(chuàng)辦阿壩州民族干部學校。
學校原在茂縣,后遷薛城,最后遷到刷經(jīng)寺,伯父去后,負責學校的教育科工作,同時教授《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學校創(chuàng)辦之初,從各個地方招收學員,學制一年,學校定位是為新生的阿壩州培養(yǎng)區(qū)、鄉(xiāng)一級民族工作干部。
在阿壩工作期間,雖然曾被錯誤地列為肅反對象,但是伯父依然對那一段時光充滿感情。他曾講到當時的學員主要是藏、羌兩族,也有少量回族和漢族,人數(shù)達二百多人。學校雖然搬遷多次,但是當時的教學環(huán)境始終沒有得到改善,極其簡陋。當時薛城旁邊有個川主廟,大殿可以容納幾百人,學校就將大殿改做禮堂,二百多學員在那里一起上大課。
因為學員來自不同民族,很多學員不懂漢語,上課必須要三個翻譯,一個嘉絨藏語翻譯,一個安多藏語翻譯,一個黑水話(羌語北部方言)翻譯。因此當時一個課時雖然有一個小時,實際上只能講半個小時,因為翻譯就要占用一半時間。一般是伯父先用漢語講課,會羌語南部方言的學員懂漢語就不用翻譯了,其余三組學員各圍成一個圈,中間坐一個翻譯,伯父講完之后,聽懂了的人就在旁邊等著,教室里啊嗡嗡嗡的聲音四起,等其他三組翻譯完之后,才能繼續(xù)講課。
教學之余,伯父依然沒有放棄在學校附近做民族調(diào)查,遠到蒲溪溝、雜谷腦,近到大岐山、小岐山、九子屯,許多山寨都留下了伯父騎著自行車或步行的身影。
學校創(chuàng)辦后,培養(yǎng)了大批民族工作干部,他們就像撒在阿壩州的一粒粒革命的種子,他們把知識帶進了當時還顯落后的山區(qū),為阿壩的建設與發(fā)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伯父還與許多學員成了好朋友,幾十年來,保持著深厚的友誼。
十
伯父不僅重視社會實踐與民族調(diào)查,同時也始終關注和積極推動民族學/人類學的學科建設。即使在文革中,他也利用五七干校設在民族雜居區(qū)的條件,在節(jié)假日進行調(diào)查訪問。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恢復,他回到自己熱愛的研究領域,全面整理過去的成果,進行理論升華。
1980年,中國民族學學會的前身中國民族研究會成立,伯父先任理事,后任幾屆副會長,期間,恪盡職守,兢兢業(yè)業(yè),積極支持時任會長秋浦和宋蜀華先生的工作。同年,伯父在四川大學,將中斷了很多年的民族學撿了起來,重新開課,后來童恩正、程賢敏又先后開講文化人類學。為了建立民族學學科,伯父將講稿作了理論提升,撰成《民族學》一書,中南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廣西民族學院等多所大學將其作為本科教材,在民族學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
為了推動西南地區(qū)的民族學科建設,伯父從1978年就開始思考怎樣整合與優(yōu)化西南民族學研究資源,推動西南地區(qū)民族學發(fā)展。1980年,伯父聯(lián)絡了云南的何耀華、貴州的余宏模等人,成立了籌備組。1981年,在伯父等人的奔走下,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正式成立,伯父作為秘書長,殫精竭慮、不遺余力地推動學會工作。學會成立迄今已有37年,舉辦過20余次高規(guī)格、大規(guī)模的學術(shù)會議,出版《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集刊》多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伯父與何耀華、童恩正主持了“六江流域”民族綜合考察,隨后,伯父等又致力于“藏彝走廊”民族綜合研究,得到了費孝通先生的大力支持。同時,伯父還主持了酉水流域土家族調(diào)查、西南絲綢之路調(diào)查、金沙江流域考古文化調(diào)查等、“康巴學”研究,均在學術(shù)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5·12”汶川大地震后,伯父又致力于羌族文化搶救與保護,即使在病床上,伯父也念念不忘那個云朵上的民族。
十一
伯父認為,自己此生最大的幸運,就是在每個時期,都接觸了當時非常優(yōu)秀的民族學家、人類學家,他們對伯父的成長至關重要。伯父在讀書的時候,受教于蔣旨昂、羅榮宗、馮漢驥、玉文華、陳宗祥、蒙文通、徐中舒,這一批先生都給伯父留下了深刻印象,讓伯父受到了最好的教育。
后來在調(diào)查實踐中,另一批老師對伯父幫助很大。比如費孝通先生,這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逃不過去的大山,伯父曾經(jīng)做過他的學術(shù)秘書。費先生對伯父主持的六江流域考察寄予厚望,并提出了許多建議,費先生當時有個觀點,他認為民族學研究要重視民族之間的融合、交流與溝通,這為先生后來的倡議藏彝文化走廊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基礎。
1959年,云南晉寧石寨山出土了一批文物,云南考古界認為這是彝族文物,但沒有達成共識,所以調(diào)查組就請著名考古學家、四川省博物館館長馮漢驥先生去考察,伯父被組織安排做馮先生的學術(shù)助手。再后來,民族學大家馬長壽先生去云南調(diào)查組工作,組織安排伯父又做他的學術(shù)助手,陪同馬先生下鄉(xiāng)考察,同時負責收集彝族古代資料,為馬先生整理訪談材料。李先生回憶,雖然工作辛苦,但是受益良多。后來伯父還為馬先生整理出版了《彝族古代史》《涼山羅彝考察報告》和《涼山美姑九口鄉(xiāng)彝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報告》。
伯父還講過一件事。1956年時,中央民大歷史系教授林耀華將招收副博士生,伯父知道后,寫信給林先生,希望能報考他的研究生。林先生給他回信,說自己將參加社會歷史調(diào)查組,沒有時間帶研究生,同時希望伯父也去調(diào)查組,并說:“以后你要做得好的話,你不是來讀我的研究生的問題,而是以后你可以教研究生的問題。”每每回憶起師生之間的情誼,伯父總是感慨,這一生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師。
老師們的學術(shù)風范和道德文章成為伯父一生的追求。
正如今天的我,追慕伯父的遺風。
十二
遺憾的是,我與伯父相識恨晚,加之生性懶散,雖然相見不少,卻沒有珍惜向伯父學習與請教的機會,虛度了很多光陰,但是伯父對我的鼓勵和扶持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2008年4月8日,都江堰市舉行我的新書《都江堰——兩個世紀的影像記錄》作品研討會,邀請的嘉賓名單中,當然有伯父。我向伯父送請柬時,他抱歉地說:“小王,書看了,非常好,現(xiàn)在沒有幾個人愿意做這個事了。真的很遺憾啊,我要去參加湖北的一個學術(shù)會議,來不了啰。”伯父又說:“我這里有一批靈巖山的老照片,是加拿大人在1940年代拍攝的,很珍貴,我資料太多,找到后交給你。”
告別時,我很失落,伯母悄悄跟我說,伯父為了參加我的作品研討會,專門向?qū)W術(shù)會議主辦方請了半天假,但是因為時間緊迫改簽不了機票,不然定會參加我的研討會。伯母的一席話,讓我心中的失落一掃而空,滿滿的都是感激之情。
也是在當年,因為我擬申報成都市有突出貢獻專家,需要請四位專家推薦,我立即想到了伯父、譚繼和先生、張新泉先生和意西澤仁先生。我與伯父電話說明了此事,伯父欣然答應。4月25日晚,我匆匆趕到伯父位于民研所的家中,他則已等候多時,并已提前寫好了草稿。伯父說:“時間過得好快啊!十多年前,我還給譚繼和先生寫過推薦意見,沒想到,轉(zhuǎn)眼之間,就已輪到你們這一批年輕人了。”
隨后伯父在推薦表格上認真地寫下了推薦意見:“王國平業(yè)績突出,思想敏銳,長期從事地方歷史文化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成績顯著,成果豐富,是難得的青年學者型作家人才。”
鼓勵與褒獎之意,溢于筆墨之間。
臨走時,伯父送我到門口,拉著我的手說:“小王,好好干,我們的事業(yè)需要你這樣認真好學的年輕人。”昏黃的路燈下,春風透著涼意,吹亂了伯父額前花白的頭發(fā),但他鏡片后的眼神里卻滿含著希冀與期待。
我心激動,緊緊握住他手,鞠躬,說了聲“謝謝!”
十三
2009年5月,我與殷波合著的《現(xiàn)在的我們——“5·12”都江堰大地震幸存者口述》出版,我以為這是一本接近地震原貌、很有意思的書,非常想送一本給伯父,請他批評。
然而,我連續(xù)三天撥打伯父的電話,都沒有人接聽。最后,我實在放心不下,就給李銑兄去了電話。聽筒對方的李銑兄聲音憔悴而傷感,他說:“父親住在三醫(yī)院,這次病情很嚴重!”
我難以相信,因為半年前見到伯父時,他還精神抖擻。我匆匆趕到醫(yī)院。躺在病床上的伯父神形憔悴,不過精神不錯,談興很濃。聽說我出了一本口述史,伯父異常興奮,蠟黃的臉上泛著喜悅的光澤,他說現(xiàn)在看書不便,想聽我講講。于是我強打起笑臉,與伯父談起了我們采訪的幸存者在“5·12”大地震中驚心動魄的逃生經(jīng)歷。特別是講到地震前一秒,一位練氣功的老太太正懷抱太極,往外一推,墻就倒了,老太太以為自己練功幾十年,終于圓滿了,于是欣喜地大叫一聲“兒子,大功告成!”時,伯父哈哈大笑,說:“你們這個口述史做得好,地震中的每一個人就是一個災難樣本,它具有多重價值!我要建議羌族地區(qū)也要做一部口述史,對很多歷史文化進行搶救式保存。”臨走時,我本不想留下帶來的圖書,伯父卻說:“放在這兒,我慢慢看。”
十四
然而,我依然低估了伯父的病情。
當李銑兄告訴我伯父已是肝癌晚期時,我一下子懵了。
我記起了馮廣宏先生曾經(jīng)給我講過的一件事。多年前,伯父曾受邀去韓國講學,臨走時,韓國總統(tǒng)問他有什么愿望,伯父說:“我想見見你們國家的薩滿。”薩滿是對北亞薩滿教中高級神職人員的尊稱,當時韓國總統(tǒng)聘請有不少薩滿,于是便安排了編號為4的薩滿與伯父見面,但是見面時有一個要求,薩滿只會談兩個問題,伯父只能問一個問題。薩滿說的兩件事是:一、伯父的學問來自母親的教育;二、伯母此時正在生病,伯父回國后,自然會好,此事后來應驗。伯父問了一個問題:自己能活多少歲?薩滿告訴伯父,以伯父的身體狀態(tài),應該可以活到80歲。
而伯父,辭世那一年才剛剛76歲啊。
對一個學者來說,正是他的白銀時代。
十五
伯父去世后,我讀到了上百份唁電、悼詞和紀念文章,作者既有中央、省、市各級領導,又有民族地區(qū)的兄弟姐妹,更有廣大學界的學術(shù)同仁,文字里既有對他道德文章的尊崇,也有對他學術(shù)成就的敬仰,更有對他人格魅力的欽羨。
從那些溫暖的文字里,我又再次認識了伯父。
十六
伯父的足跡曾踏遍西南少數(shù)民族聚居區(qū)的山山水水,山水間,每個民族都是祖國大花園中的一朵燦爛之花。
而沿途的每一朵花開,都是一次深情的憶念。
岷山蒼蒼,蜀水泱泱,伯父之風,山高水長。
本欄目責任編校:周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