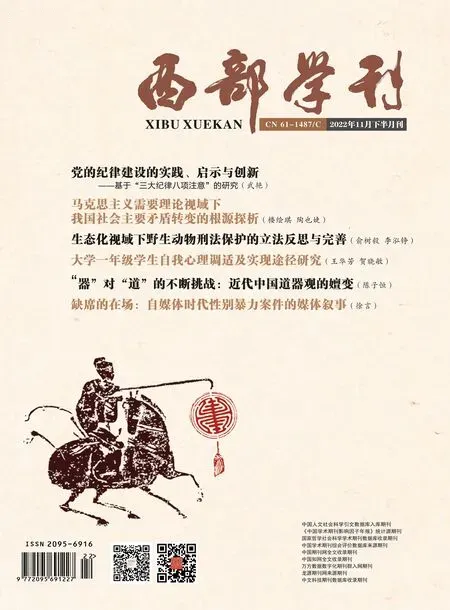“器”對(duì)“道”的不斷挑戰(zhàn):近代中國(guó)道器觀的嬗變
陳子恒
隨著西方事物在近代大規(guī)模傳入中國(guó),時(shí)人對(duì)西方事物的認(rèn)知以及是否學(xué)習(xí)西方、如何學(xué)習(xí)西方提出了多種多樣的觀點(diǎn)并展開了激烈的探討,不但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對(duì)社會(huì)思潮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更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寶貴的學(xué)術(shù)思想史財(cái)富。其中有一定價(jià)值但較少有人展開系統(tǒng)研究的一個(gè)重要問題,是近代中國(guó)道器觀的發(fā)展嬗變,筆者嘗試初步探討。
一、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中的“道器之辨”
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1]提出“道器之辨”后,“道”與“器”這一對(duì)概念就相伴而行。“道器之辨”成為中國(guó)哲學(xué)發(fā)展史上一個(gè)重要問題,由此展開的討論不計(jì)其數(shù)。筆者僅從宏觀層面對(duì)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發(fā)展史中的“道器之辨”之演變做一簡(jiǎn)要梳理。
孔穎達(dá)在《周易正義》中提出了“道先器后”說,而“忽然而生”之說難以有力保證和維護(hù)儒家倫理和道德規(guī)范[2]。這樣的道器觀無論在學(xué)理基礎(chǔ)上還是現(xiàn)實(shí)作用上均有難以彌補(bǔ)的缺陷,因此其活力亦非常有限。
及至宋明,朱熹兼取張載的氣本原論和二程的理本論,形成了理本體論哲學(xué)范式,將描述“道器”關(guān)系的形上形下之分用于區(qū)分“理氣”,道器關(guān)系不再是時(shí)間生成上的先后關(guān)系,而是體用關(guān)系,即“道體器用”說。之后,理學(xué)愈加存理遺人,而心學(xué)及至陽明后學(xué)也逐漸淪為空談心性[2]。
適逢明清巨變,知識(shí)分子反思宋明理學(xué)之弊,王夫之進(jìn)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提出了卓越的創(chuàng)建。他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強(qiáng)調(diào)“器”的優(yōu)先性,有器方顯形上之道。“治器”、踐行、事為都是人的動(dòng)態(tài)歷史過程,故而“道”也處于動(dòng)態(tài)變化中,隨著人類活動(dòng)的發(fā)展“因時(shí)而萬殊”,“漢、唐無今日之道,則今日無他年之道者多矣。”[3]王夫之的道器觀開啟的是一個(gè)開放、求新、尚變的價(jià)值取向。他對(duì)道器的區(qū)分,不是時(shí)間上、空間上和邏輯上的區(qū)分,而是從人的生存和踐行活動(dòng)出發(fā)給予的命名區(qū)分。“器”在生存論范式下其真實(shí)性得到肯定,并取得優(yōu)先的地位,而“道”則在人的“治器”實(shí)踐活動(dòng)中顯現(xiàn),并隨著這一活動(dòng)過程而趨時(shí)更新,故王夫之的道器觀可概括為“治器顯道”說[2]。可見“器”的地位在王夫之這里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
船山①之后,對(duì)“道器之辨”的諸多闡發(f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章學(xué)誠的“道器合一”說。章學(xué)誠在還原六經(jīng)②原貌的同時(shí),形成了“道器合一”的觀點(diǎn),并與“六經(jīng)皆史”聯(lián)系起來。六經(jīng)是載道之書,先王之道借由六經(jīng)所載典章事跡而使人知,六經(jīng)是載道之器[4]。“道”在不斷地變化,不同的時(shí)代,“道”的含義也不同,所以需要后世隨時(shí)撰述以彰顯道的不同樣貌。“道器合一”是“六經(jīng)皆史”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厘清道器關(guān)系為“六經(jīng)皆史”說提供了有力論據(jù)支撐。其說之影響不僅在于治史,更在學(xué)術(shù)思想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經(jīng)過以上的簡(jiǎn)單梳理,可以看到“道器之辨”大致上經(jīng)歷了一個(gè)由虛入實(shí)的過程:孔穎達(dá)“無形生有形”之說將道器關(guān)系引入虛幻,讓人難以捉摸;朱熹以“理”與“物”論“道”與“器”,將“道器之辨”由虛幻引入抽象,視“道”為“體”,“器”為“用”,更重“理”即“道”;王夫之則更重視人在生存與踐行活動(dòng)中與“器”的種種關(guān)系,強(qiáng)調(diào)“器”的優(yōu)先性即強(qiáng)調(diào)人“治器”之實(shí)踐活動(dòng)的重要性,“治器”方能“顯道”;章學(xué)誠在“六經(jīng)皆史”說中強(qiáng)調(diào)“道器合一”,治學(xué)的目的是明道,但治學(xué)本身及其對(duì)象都是“器”,道器不能分離。由此可見,“器”之地位愈加得到肯定與重視。但必須指出,這樣的道器觀是在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自身相對(duì)獨(dú)立情況下的發(fā)展脈絡(luò),與之后在西方大規(guī)模的沖擊和影響下的近代道器觀不可簡(jiǎn)單直接并而觀之。
對(duì)晚清道器觀影響最大的是朱熹和王夫之(章學(xué)誠或可歸入其中)的兩種觀點(diǎn)。前者被視為儒家正統(tǒng),多作為較保守方的思想武器;后者多作為提倡改良、變通方的思想資源。不少涉及晚清道器觀的論文,僅提及“道本器末”論的巨大影響,而忽視“治器顯道”說和“道器合一”說的影響。雖然它們影響有大小之別,前者長(zhǎng)時(shí)間被視為“正統(tǒng)”,但若僅強(qiáng)調(diào)前者且忽略后者,難免有失全面。
二、晚清道器觀的多元發(fā)展與復(fù)雜面向
西方的沖擊和影響為晚清的道器觀打下了最為標(biāo)志鮮明的時(shí)代烙印,因此晚清道器觀與此前最大的不同也是其自身最顯著的特點(diǎn)為,除了相同的將“道器”與“體用”“本末”等放在一起討論外,還加入了“華夷”“中西”與之緊密相連,“道器”幾乎是與“中西”綁定出現(xiàn),被一并論及的;提及的這幾組成對(duì)的概念也往往一并出現(xiàn)。但當(dāng)時(shí)論者對(duì)這些概念似乎并未有意加以區(qū)分,常常一并混用;且不同論者對(duì)這些概念的界定和使用也因不同語境而異。因此,筆者也難以直接抽象地將它們區(qū)分開來,只能具體語境具體分析。
若談到“西器”,魏源無疑是必須提及的開山鼻祖般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句“師夷長(zhǎng)技以制夷”可謂是開倡導(dǎo)學(xué)習(xí)西方技術(shù)之先河,對(duì)后世有著極為深遠(yuǎn)的影響。但可以看到,魏源論述的重點(diǎn)在西方先進(jìn)的技術(shù)即“西器”,而較少論及與“器”相對(duì)應(yīng)的“道”,因而也較難由此論及道器觀。
魏源是走在時(shí)代前列的先驅(qū),也是少數(shù)人。在面對(duì)西方?jīng)_擊之時(shí),或受傳統(tǒng)華夷之辨③觀念的影響或出于對(duì)侵略者的憎惡,不少人對(duì)西方及其事物持拒絕、排斥甚至仇視之態(tài)度。比如,一些保守的地方精英排斥外來事物。豫師,一位在清同光年間出任西北都護(hù)的學(xué)者,醉心于宋儒之學(xué),并公開表示自己“生平最惡洋字”,家中無一物來自泰西④。與他同時(shí)代的劉恩溥,是一位在19世紀(jì)末頗為活躍的官員,同樣“痛惡洋字”。不過,他家中有一個(gè)帽架是由歐洲進(jìn)口的馬口鐵所制。由此可見,歐風(fēng)美雨的浸染是無孔不入的,哪怕是最保守的士大夫的深宅內(nèi)院也無法幸免[5]。由此看到,縱使主觀意愿上排斥抵制外來事物,但客觀上西器無處不入;可以說,隨著歐風(fēng)美雨的日趨深入浸染,很難有人能夠絕對(duì)置身西器之外。于是,關(guān)于“中西”與“道器”的種種討論日益盛行開來。
同治五、六年間(1866—1867年)的天文算學(xué)館之爭(zhēng)可謂是反映當(dāng)時(shí)道器之爭(zhēng)的一個(gè)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朝廷同意總理衙門的奏議,在同文館設(shè)立天文算學(xué)館,令科甲正途學(xué)習(xí)西方天文算學(xué),卻遭許多士人反對(duì)。隨之而來的爭(zhēng)論所關(guān)涉的觀念沖突,除了是否應(yīng)“以夷為師”的中西沖突之外,更重要的其實(shí)是士人是否應(yīng)學(xué)習(xí)器物制造的道器沖突。原本是儒家六藝之一的算學(xué)之所以會(huì)淪為“機(jī)數(shù)”⑤而遭抵制,也與這種中西、道器沖突密切相關(guān)。既要維持道高于器的理念,又要讓士人學(xué)習(xí)西方所長(zhǎng)的器物,這是爭(zhēng)論雙方都非常關(guān)注卻又無法調(diào)和的問題。綜觀此次天文算學(xué)館之爭(zhēng),道高于器的傳統(tǒng)理念是讓士人學(xué)習(xí)“西器”的觀念障礙。這一觀念既不能被顛覆,也無法被繞過,使得這次天文算學(xué)館之設(shè),最終演成紛紛爭(zhēng)論。西方到來使中國(guó)人感受到了“器”的威力,“器”之于“道”,一如“西”之于“中”,原本皆處于次要地位。而隨著中國(guó)的數(shù)次失敗,“西”與“器”的地位逐漸相互增強(qiáng)。朝廷為了應(yīng)對(duì)西方而提倡“西器”,而士人又將“西器”視為末藝,這種錯(cuò)位充分體現(xiàn)了近代西方?jīng)_擊中國(guó)所產(chǎn)生的復(fù)雜性[6]。此后,“器”對(duì)“道”的沖擊與挑戰(zhàn)亦日益猛烈。
通過此案例,或可看出當(dāng)時(shí)“洋務(wù)派”與“保守派”在道器之爭(zhēng)上的大致樣貌。若要給19世紀(jì)末的道器觀一個(gè)整體性的概括,筆者想用“中道西器”“中體西用”以及“道高于器”或大概不錯(cuò)。但整體并非全部,有主流也并不代表千篇一律,這其中的不同音,或許更加值得被關(guān)注。
首先是郭嵩燾。分析他的道器觀,要注意他中西相通的理念和中西在“道”上對(duì)抗之焦慮,與當(dāng)時(shí)中西相別之觀點(diǎn)互動(dòng)又競(jìng)爭(zhēng)[7]。他繼承古代儒家“道”的概念,以此作為其文化思想的理論基礎(chǔ);繼承發(fā)揮王夫之的“道器論”,將之作為中西方文化觀的理論指導(dǎo)。在肯定西方國(guó)家有“器”的認(rèn)識(shí)基礎(chǔ)上,指出西方“道器”兼?zhèn)洌瑥亩鼊儆谕瑫r(shí)代人視西方“有器而無道”的觀點(diǎn),并進(jìn)一步否定了傳統(tǒng)的道器一元論,提出道器多元論[8]。
另一位值得關(guān)注的重要人物是康有為。他在《物質(zhì)救國(guó)論》中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的重要性,認(rèn)為救國(guó)需要強(qiáng)大的物質(zhì)基礎(chǔ),包括工商經(jīng)濟(j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軍備國(guó)防。要學(xué)習(xí)西方的物質(zhì)文明,但并未否定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僅靠“物質(zhì)”當(dāng)然不能救中國(guó),但“物質(zhì)”是立國(guó)的前提和基礎(chǔ),自由、民主、道德、精神統(tǒng)統(tǒng)離不開“物質(zhì)”[9]。康有為有心要將對(duì)西方的學(xué)習(xí)由“精神”重新拉回“物質(zhì)”的層面。然而康有為此說提出后并不為時(shí)人乃至不少后人所認(rèn)同,尤其是受到梁?jiǎn)⒊摹袄溆觥保灾劣凇段镔|(zhì)救國(guó)論》一書的出版也一延再延。康有為的“物質(zhì)救國(guó)論”或許與當(dāng)時(shí)的主流有些格格不入,但其自身獨(dú)特的價(jià)值,也是我們觀察晚清道器觀發(fā)展嬗變的一個(gè)重要思想資源。
綜上,晚清道器觀所關(guān)注的道器關(guān)系的核心問題其實(shí)是如何對(duì)待西方事物以及如何學(xué)習(xí)西方,因而前文所提及的好幾組成對(duì)的概念往往一并出現(xiàn)。呈現(xiàn)多元發(fā)展的情形,并有著諸多復(fù)雜的面向,并不能以“道本器末”或是“中道西器”“中體西用”一言蔽之。晚清的“道器之辨”或許是中國(guó)歷史上在較短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討論最為激烈的,不僅是不同派別之間,同一派別的不同人之間的觀點(diǎn)都會(huì)有所不同;留下的豐碩而寶貴的思想財(cái)富,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關(guān)注、發(fā)掘和深耕。
三、民國(guó)時(shí)期趨于統(tǒng)一的道器觀
及至民國(guó),隨著民主共和政體的建立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逐步開展,此前關(guān)于如何學(xué)習(xí)西方的一系列討論正逐一成為現(xiàn)實(shí)。有識(shí)之士將主要目標(biāo)放在如何建立一個(gè)更好的民主國(guó)家上來,而對(duì)“道器之辨”的關(guān)注和討論則日趨減少。
因?yàn)椤捌鳌彼傅目纱笾吕斫鉃?西方的)器物和技術(shù),已經(jīng)在中國(guó)大地上遍布開來。相比于上文所舉出的此前劉恩溥的例子,這時(shí)西方器物和技術(shù)早已更深更廣地融入了時(shí)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們已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當(dāng)中無法避開甚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對(duì)于這些司空見慣的東西,人們會(huì)漸漸認(rèn)為它們的存在不言自明甚至是理所應(yīng)當(dāng),并不會(huì)過多產(chǎn)生懷疑、思考和討論。雖然抵制洋貨的運(yùn)動(dòng)時(shí)有發(fā)生,但人們所抵制的并非器物本身及其科學(xué)技術(shù),而是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和民族主義內(nèi)涵。
此時(shí)“道”所包涵的內(nèi)容,可以大致理解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這時(shí)它們已經(jīng)逐步在中國(guó)實(shí)現(xiàn)和推廣開來。此時(shí)道器之間似乎并沒有什么沖突和矛盾,它們確實(shí)處在不同層面,或許在時(shí)人觀念中也會(huì)有高低之分,但這些并不是主要的關(guān)注點(diǎn)。人們更關(guān)注的問題是,如何改進(jìn)并推廣它們,如何更好地讓它們共同服務(wù)于中國(guó)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道路。
這一時(shí)期最具代表性和總結(jié)性的是梁?jiǎn)⒊?922年《五十年中國(guó)進(jìn)化概論》中提出的一段著名論述。其將五十年中國(guó)思想的進(jìn)步描述為線性進(jìn)化的三期,從一開始在“器物上感覺不足”,到甲午以后“制度上感覺不足”,再到“最近兩三年間”的“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10]。這是一種帶有濃重“進(jìn)化”意味且明顯受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影響的論述。該說于近代中國(guó)人對(duì)西方態(tài)度演變的描繪,不乏精到之處,然值得討論之處亦有許多,已有不少研究對(duì)此有過精彩的探討,便不再展開了。筆者想要探討的是,這樣的論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怎樣的道器觀?
仔細(xì)分析梁?jiǎn)⒊倪@一論述,可知三階段的“不足”與進(jìn)步均參照西方,此敘事脈絡(luò)暗設(shè)著“趨西”具有天然的優(yōu)越性,還預(yù)設(shè)著文化比制度比器物更接近西方文明某種實(shí)在的“本質(zhì)”,如此認(rèn)知邏輯也蘊(yùn)含著中國(guó)人自己的認(rèn)知傾向。盡管身處變局的近代國(guó)人眼光日漸趨西,道高于器的思路卻相對(duì)穩(wěn)定,人們相信文化的面相要比制度、器物更能界定一個(gè)文明的核心內(nèi)涵,和依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的“道高于器”的觀念有著相關(guān)聯(lián)的邏輯。以較長(zhǎng)時(shí)段觀之,中國(guó)人原本視“道”高于“器”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并沒有被顛覆[7]。但同樣要看到,這樣的論說至少肯定了器物的重要地位,梁?jiǎn)⒊膊⑽摧p視器物,相反,他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同樣關(guān)注并重視著物質(zhì)文明的發(fā)展。
可以說,梁?jiǎn)⒊@樣的認(rèn)識(shí)很具有代表性和總結(jié)性。之后人們直接關(guān)于道器關(guān)系的討論并不多見。雖然自20世紀(jì)初開始,中國(guó)大地上陸續(xù)涌現(xiàn)出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彼此之間也多有爭(zhēng)鳴,但他們的爭(zhēng)論大多集中于“道”之上,即不同“道”之間的爭(zhēng)論,而較少提及“器”以及道器關(guān)系。且這些為數(shù)不多的討論絕大多數(shù)都是從學(xué)術(shù)史、哲學(xué)史的角度對(duì)前代特別是古代的“道器之辨”進(jìn)行探討和研究的學(xué)術(shù)性文章。例如,在《東方雜志》上先后刊登過的繆天綬《宋學(xué)重要的問題及其線索》[11](1927年)、郭紹虞《文學(xué)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12](1928年)、何炳松《程朱辨異(一)》[13](1930年),其他有紀(jì)玄冰《“依照說”與“道器論”》[14](1943年)、羅香林《道器雙溶,理行并入:文理學(xué)報(bào)發(fā)刊詞》[15](1946年)、韓少蘇《道與器》[16](1946年)等。它們大都是從哲學(xué)出發(fā)探討抽象意義上的道與器,和“中西”已無太大聯(lián)系,反映出的道器觀也基本不離由器至道是逐漸深入的發(fā)展過程或是道高于器這樣的觀念,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對(duì)梁?jiǎn)⒊叭A段說”的繼承與再發(fā)展。
綜上所述,民國(guó)時(shí)期的“道器之辨”已日趨平息,民國(guó)時(shí)期的道器觀到梁?jiǎn)⒊岢觥叭A段說”已基本趨于統(tǒng)一,其后關(guān)于道器關(guān)系的論說也基本不離梁說的思路框架。如此看來,民國(guó)時(shí)期的道器觀似有些乏善可陳,這不免讓人生疑,在那樣一個(gè)風(fēng)起云涌的時(shí)代,各種思想的碰撞不應(yīng)該十分激烈嗎?筆者認(rèn)為,民國(guó)時(shí)期的道器觀或許已漸漸演化成為另一種表現(xiàn)形式即科學(xué)主義。由此提出兩個(gè)問題:第一,道器觀與科學(xué)主義有著怎樣的相互聯(lián)系?第二,隨著科學(xué)主義的盛行,人們視科學(xué)及其器物為時(shí)髦,紛紛追捧,此時(shí)的道器觀又發(fā)生著怎樣的轉(zhuǎn)向?期待之后的研究能對(duì)此進(jìn)行解答。
結(jié)語
通過梳理中國(guó)古代哲學(xué)當(dāng)中的“道器之辨”,可以得出兩派最具代表性的觀點(diǎn),即朱熹的“道體器用”說或“道本器末”說,以及王夫之、章學(xué)誠的“治器顯道”說或“道器合一”說,二者共同成為晚清道器觀的重要思想來源。“道本器末”或在一定時(shí)期內(nèi)占據(jù)主流,但絕非傳統(tǒng)道器觀的全部,我們需予以重視。
對(duì)中國(guó)古代傳統(tǒng)道器觀具有一定繼承性的晚清道器觀,面臨的大變局卻是前所未有的,其關(guān)注的道器關(guān)系的核心問題成為了如何對(duì)待西方事物以及學(xué)習(xí)西方,因而“道器”幾乎是與“中西”綁定出現(xiàn)被一并論及的,“華夷”“中西”與“道器”“體用”“本末”這幾組成對(duì)的概念往往一并出現(xiàn)。總體而言呈現(xiàn)多元發(fā)展的情形,并有著諸多復(fù)雜的面向,并不能以“道本器末”或是“中道西器”“中體西用”一言蔽之。與當(dāng)時(shí)思潮主流存在著不同的兩種觀點(diǎn)——郭嵩燾的“道器多元論”和康有為的“物質(zhì)救國(guó)論”,各有其價(jià)值,值得我們更多予以關(guān)注。
由于晚清道器觀所關(guān)注的核心問題“道”的逐一實(shí)現(xiàn),民國(guó)時(shí)期的“道器之辨”已日趨平息,道器觀到梁?jiǎn)⒊岢觥捌魑铩贫取幕比A段說已基本趨于統(tǒng)一,其后關(guān)于道器關(guān)系的論說也基本不離梁說的思路框架。這時(shí)的道器觀又與之后的科學(xué)主義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其相互關(guān)系還需要進(jìn)一步發(fā)掘探索。
綜觀明清至近代,雖然主流觀念中視“道”高于“器”的認(rèn)知結(jié)構(gòu)并沒有被顛覆,但“器”對(duì)“道”也確實(shí)發(fā)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戰(zhàn),“器”之地位同樣得到人們更多的關(guān)注、肯定和重視。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道”“器”各自的內(nèi)涵,還是“道器之辨”、道器關(guān)系或是道器觀,都是隨著時(shí)勢(shì)的發(fā)展變化而不斷嬗變和更新的。道器觀的嬗變,是一個(gè)時(shí)代發(fā)展變化的重要縮影。
注 釋:
①船山:即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其字而農(nóng),號(hào)姜齋,人稱“船山先生”,湖廣衡陽縣(今湖南省衡陽市)人。明末清初思想家,與顧炎武、黃宗羲、唐甄并稱“明末清初四大啟蒙思想家”。
②六經(jīng):指經(jīng)過孔子整理而傳授的六部先秦古籍。這六部經(jīng)典著作的全名依次為《詩經(jīng)》《書經(jīng)》(即《尚書》)《儀禮》《易經(jīng)》(即《周易》)《樂經(jīng)》《春秋》。
③華夷之辨:或稱“夷夏之辨”、“夷夏之防”,用于區(qū)辨華夏與蠻夷。中國(guó)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大致有三個(gè)標(biāo)準(zhǔn):血緣衡量標(biāo)準(zhǔn);地緣衡量標(biāo)準(zhǔn);衣飾、禮儀等文化衡量標(biāo)準(zhǔn)。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
④泰西:舊泛指西方國(guó)家,出自明末·方以智《東西均·所以》。
⑤機(jī)數(shù):漢語詞匯。釋義為謀略;權(quán)術(shù)、權(quán)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