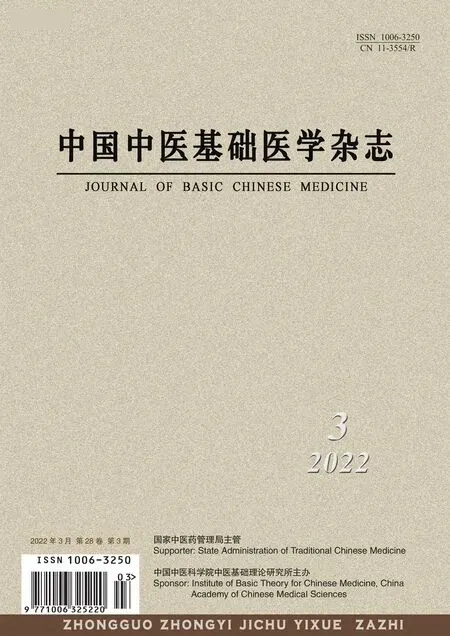敦煌脈書《玄感脈經》研究
劉 冉, 李鐵華
(上海中醫藥大學, 上海 201203)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脈書《玄感脈經》(P.3477)殘卷,是敦煌醫學文獻中的診法類文獻。該殘卷自20世紀30年代由日本學者黑田源次首次自歐洲抄錄見世,后經岡西為人、羅福頤和馬繼興等學者題跋、校錄、整理與研究,形成了一些可資借鑒的有益成果。本文將從“抄錄、題跋與校注”“撰者與撰寫、抄寫年代考證”“文本結構、內容與重要學術問題研究”“文獻、學術與臨床實踐價值揭示”等方面,對《玄感脈經》的既往研究進行簡要評述,并就未來研究進行展望。
1 抄錄、題跋與校注
1.1 早期的錄跋、考證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前,隨著《玄感脈經》文本的發現,相關研究得以開展,但研究內容集中于文本抄錄、題跋和作者考證等方面,主要以黑田源次、岡西為人、羅福頤等為代表。
日本學者黑田源次是較早關注并研究敦煌醫學文獻的學者之一。1931至1934年黑田源次到歐洲考察時,抄錄了不少敦煌和西域醫學文獻,后來匯編為《法國巴黎圖書館藏敦煌石室醫方書類纂稿》,其中即包括《玄感脈經》殘卷。1939年4月,岡西為人編纂出版的《宋以前醫籍考》第二輯中將該殘卷歸入脈經類并作了題錄,簡述了該殘卷的尺寸、形態、紙張和書法特征[1]。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羅福頤在黑田源次類纂稿基礎上,又增入不少國內所藏敦煌西域醫學文獻,并在前人考訂基礎上對相關殘卷進行了考訂補充,最終形成《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匯編》,其中也包括《玄感脈經》殘卷錄文及相關考證[2]。可惜羅福頤原書未出版,目前難以得見,但從馬繼興[3]、王淑民[4]等學者的引述中可知,羅福頤曾對該殘卷的作者等進行過考訂。
1.2 文本校錄和考釋研究的深入
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隨著國內敦煌醫學文獻研究的不斷深入,敦煌醫學文獻的輯佚、校勘和整理工作也逐步展開。作為敦煌醫學文獻中的脈學診法類文獻,《玄感脈經》也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對其文本進行了校錄和考釋,部分學術問題也有相應探討,相關校錄和考釋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收錄在馬繼興、趙健雄、叢春雨、沈澍農等相關著作中。《玄感脈經》的文獻研究在此時期日漸成熟。
1988年,馬繼興和趙健雄分別編撰出版了敦煌古醫籍校注著作《敦煌古醫籍考釋》[3]76-88和《敦煌醫粹-敦煌遺書醫藥文選校釋》[5],兩者都校錄了《玄感脈經》殘卷。馬繼興著作包括提要、原文、校注、按語和備考等內容,趙健雄著作則包括注釋、原文、校勘和按語等內容。馬繼興著作主要依據前后文義和其他敦煌脈學殘卷出校記,趙健雄著作則主要根據前后文義和傳世醫學經典《素問》《靈樞》《難經》《脈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出校記。因當時所據攝影膠片的清晰度有限,兩著在錄文和校注中都有誤認、漏錄、誤補等情況。1994年,叢春雨主編的《敦煌中醫藥全書》[6]也收錄了《玄感脈經》殘卷。叢著在考校體例上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包括述要、原文、厘定、按語、校注等內容。叢春雨基本承襲了馬繼興和趙健雄的校勘成果,對二者部分漏校、訛誤和缺文等作了校正和補錄,并將原文和校補厘定后的錄文共同列出,既保留了卷子文本原貌,也清晰地展示了編撰者的校補成果。1998年馬繼興編撰的《敦煌醫藥文獻輯校》[7]除了將體例變更為題解、原文和校注三部分外,其他則基本與1988年的保持一致。
1.3 對既往校勘研究的補充完善
新世紀以來,隨著研究方法的改進、高清文獻圖片的公布,可利用學術資料增多,陳增岳、袁仁智和潘文、沈澍農等在相關敦煌醫籍校錄論著中又對《玄感脈經》進行了校補和考證。2008年陳增岳編著的《敦煌古醫籍校證》[8]側重語言文字上的整理與解釋,除對《玄感脈經》校錄中的個別地方有所修改外,基本上承繼了前述各著的校釋成果。2015年袁仁智與潘文編著的《敦煌醫藥文獻真跡釋錄》[9]附《玄感脈經》的完整黑白圖版,錄文基本保留了圖版的原貌,但圖版清晰度有限。2017年沈澍農編著的《敦煌吐魯番醫藥文獻新輯校》[10]匯集了前人的校勘成果,首次展示該殘卷的高清彩色圖版,其校錄極大程度地保留了卷子原貌,釋讀更為詳實、準確,是目前《玄感脈經》文獻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1.4 對缺文的校補
另外,原殘卷第4~16行文字殘缺較多,影響前后文意的理解,但在是否校補、如何校補上存在不同意見。馬繼興[3]78-79、叢春雨[6]298-299等依據上下文義及文例,并參照《素問·三部九候論篇》及敦煌出土的其他脈學文獻對之進行了校補。趙健雄則以內容殘缺較多、存疑待考為由未予校補[5]64。陳增岳在原文校錄部分保留了文字殘缺原貌,未對闕文進行補錄,而是以匯校形式展示了前人的校補成果[8]104-105。袁仁智、潘文[9]70-71、沈澍農[10]110-111都采用了分行校補,并用“【】”符號對補錄內容進行標注,但沈著校補內容更為詳細。沈著充分考慮到早期攝影照片與現今高清圖影之間可能存在部分出入,故其校補將兩者一同利用起來,最大程度地保證了校補內容的完整性。
2 撰者與撰寫、抄寫年代的考證
《玄感脈經》未載撰者、撰寫與抄寫年代等信息。羅福頤據《舊唐書·經籍志》所載蘇游撰著的《玄感傳尸方》,推斷認為“玄感”是蘇游的字,并認為蘇游應為《玄感脈經》的作者。此后,馬繼興[3]76-77、王淑民[4]、趙健雄[5]65、蘇彥玲[11]、陳增岳[8]103等在認同羅福頤觀點的同時,又結合相關傳世文獻對蘇游可能的生活時代等做了一些補充考證。如王淑民依據《舊唐書》中的相關記載,推斷認為蘇游為唐或唐以前的醫家。又根據《舊唐書》《新唐書》《宋史》等史書所載蘇游相關著作年代,推斷《玄感脈經》也為唐代寫本。馬繼興則依據原文中未避諱“治”字,進一步推斷其撰寫年代在唐初或以前。
關于該殘卷抄寫年代,學界主要依據殘卷中的避諱字對抄寫的可能年代及上下限問題進行討論。因文中出現三處“旦”字的缺筆避諱,且前后寫法不一,這成為學者們考證《玄感脈經》抄寫年代的重要依據。關于抄寫年代上限學者們的觀點一致,認為不早于唐睿宗李旦執政時期。但對于下限則有分歧,王淑民認為“似在晚唐”[4],馬繼興則推斷在五代時期[3]76-77。其后,趙健雄、蘇彥玲又從相關文字的寫法角度對馬繼興的觀點予以佐證[11]。
3 文本結構、內容與重要學術問題研究
3.1 文本結構與內容
就文本結構來看,雖然該殘卷首全尾殘,前半部分還有部分缺文,但現存文本內容依據其原有標題劃分為三部分的整體結構比較清晰,因此學界對該卷文本結構的認識沒有異議。
就文本內容來看,目前學界關于各部分具體內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兩部分。張紹重、劉暉楨首次對《玄感脈經》的內容結構做了簡要介紹,指出了殘卷內容與《黃帝內經》《脈經》類似,但在字句、次序上有不同[12]。馬繼興[3]76-88、趙健雄[5]64-83、蘇彥玲[11]對第一二兩部分內容進行分類研究,簡要考察了第一二兩部分內容與《平脈略例》等其他敦煌脈學文獻及《素問》《難經》《脈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傳世醫學文獻的相似性。與馬繼興相比,趙健雄除指出殘卷文本內容與傳世文獻相關篇目可互參外,還從文法、語義等方面對兩者的流暢性、合理性、準確性和全面性進行了評析。叢春雨[6]296-312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中醫理論與臨床實際對該殘卷各部分內容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讀,對具體內容的醫學價值進行了多方面分析。
3.2 重要學術問題探討
除上述整體上的探究外,學界還圍繞三部九候、呼吸定息、診脈時間、診脈手法、脈象與形性關系、脈名脈象和精識之主等幾個重要學術問題進行了具體討論。
該殘卷“三部九候”理論引起了學界關注。叢春雨認為,該殘卷所論三部九候是指寸關尺三部,與《素問·三部九候論篇》的“意義”有區別,但并未詳細揭示其不同點[6]297。其他學者雖亦有所論及,但都未對其與《素問》《難經》中相關理論之間的關系做深入討論。
關于該殘卷中的“呼吸定息”研究,趙健雄依據《靈樞》《難經》記載及人之實際呼吸息數對“人一日一夜三千五百息”的論述予以質疑[5]67。田永衍則依據敦煌脈學文獻《平脈略例》對其予以旁校,指出此處有脫文,并結合“天人相應”的思想分析了其與人之實際生理參數存在出入的原因[13]。叢春雨則從醫生診脈基本功的角度對以呼吸定息測脈動的理論予以了肯定[14]。
關于“診脈時間”的研究,馬繼興和趙健雄在原文文意的認識上存在分歧。馬繼興結合《脈經》和敦煌脈學文獻《平脈略例》認為,其分屬2種不同的平旦診脈理論[3]80。趙健雄則從文本本身出發,認為兩者文意重復,后者或為前者的注語[5]68。田永衍則主要結合《平脈略例》《素問》對此進行考證,從本義、平旦診脈與獨取寸口的原因等方面對此予以解讀[13]。
關于“診脈手法”的研究,因對原文斷句的不同,學者們對其認識也存在一定差異。馬繼興認為其為一種診脈方法,即依據指下輕重診斷五臟[3]82。而王淑民[4]則認為其為2種診脈基本手法。趙健雄[5]72與王淑民觀點相同,并比對《難經》《脈經》中所載五臟診法,認為《玄感脈經》論述更為全面。叢春雨在王淑民與趙健雄觀點的基礎上,認為這2種診脈法既是對醫生診脈基本功的強調[14]53,也是對脈象胃、神、根理論的具體應用,可據此判斷疾病邪正盛衰及預后吉兇[14]62、64。田永衍則重點結合《平脈略例》與傳世醫籍對診脈指力輕重與五臟、人體層次對應關系進行考證,指出彼此間的差異,并從文字寫法、抄寫年代、文獻關系等角度指出,《玄感脈經》部分文字存在誤抄可能,還就其臨床意義進行評述[13]。
關于“脈象與形性關系”的研究,叢春雨認為這是對個體差異的重視[14]54,實質是要求醫生診脈知常達變,注重辨證,這正是中醫學的精髓之處[6]303。
關于“脈名脈象”的研究,馬繼興首先將其整理分為23種病脈和6種死脈,并將其與《脈經》《傷寒論》《千金翼方》《察病指南》所載脈象比較異同[3]83-87。趙健雄數目上與馬繼興有出入,整理出24種病脈6種死脈[5]76-82。叢春雨則比對《脈經》《千金翼方》中脈象描述后,推斷其所抄內容或源自《千金翼方》[6]305-312。叢春雨亦就該殘卷所載23種病脈依照脈位、脈至、脈勢、節律、形體進行分類,對其病理和主病予以闡釋,并結合臨床對6種死脈進行解讀,指出其對于預報疾病的危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4]68-83。
“精識之主”也是學者們關注較多的問題。“精識之主”前面有缺文,王淑民首先通過理校和旁校的方法,在其前補足了“頭角者”三字,從而實現了前后文意的貫通[4],其后學者在對此處進行校補時皆與其相同。“頭角者,精識之主”的論斷,王淑民[4]、馬繼興[3]79、叢春雨[6]299皆指出其不見于其他典籍,為《玄感脈經》所首見,學界認為這一論斷的發現意義較為重大。朱定華、王淑民率先對其內涵進行闡釋,指出其為最早的關于頭腦具有精神意識功能的記載,但未能對其進行詳細考證[15]。后王鳳蘭也指出,該論斷是與傳世古醫籍不同的理論[16]。近年來,田永衍在吸收王淑民等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漢唐文獻和佛教思想,對該論斷形成的背景、原因和內涵等做了進一步的考證和分析[17]。
綜觀上述研究,雖然學者們圍繞文本結構、內容、幾個重要學術問題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討,但還有如“形藏、神藏”等內容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與解讀。在研究方法上,學者們多借助傳世醫學文獻進行比較研究,但對同類型、時期相近的敦煌脈學文獻的利用不足。
4 文獻、學術與臨床實踐價值的揭示
自20世紀80年代敦煌醫學文獻研究興起之后,隨著對《玄感脈經》殘卷研究的日漸深入,學界對其學術、文獻及臨床價值也進行了討論,張紹重、劉暉楨率先評價此卷為佚書可珍[12]。就文獻價值看,學者們普遍認為,《玄感脈經》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可以為古醫籍整理提供重要幫助。如王淑民[4]、叢春雨[6]297、王鳳蘭[16]等認為,《玄感脈經》是繼《脈經》之后的一部重要脈書,是未見傳世的古醫籍,是對隋唐前后醫籍的補充。其中不少文字表述與傳世和敦煌出土的其他脈學文獻相同或相似,可以為校勘、輯佚傳世經典文獻提供早期校本。
學界對該殘卷的學術價值也給予了充分肯定。朱定華和王淑民認為,《玄感脈經》保存了唐以前的脈診理論和經驗,為研究唐以前脈診發展史提供了重要文獻資料[15];叢春雨認為,“寸口診脈”理論是對《黃帝內經》《脈經》理論與實踐的豐富和發展[14]55、57,23種病脈的論述是繼《脈經》之后的又一個脈診專論,對發掘脈診理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4]68-81。另外,王淑民[4]、田永衍[13]等對“頭角者,精識之主”這一首見于該殘卷論述的學術價值進行了探討,認為其可以為唐以前醫學思想史研究提供重要幫助。
學界對該殘卷的臨床實踐價值也進行了探討。叢春雨將《玄感脈經》的脈診理論與臨床診斷相結合進行了探討。認為該殘卷的脈診理論具有較強的實用性,對醫家臨證診脈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較好地呈現出脈診的方法和原則。如“呼吸定息”“診脈手法”是對醫生診脈基本功的強調;對診脈手法的要求則是對中醫學脈象“胃、根、神”理論的具體應用,可據此判斷疾病邪正盛衰及預后吉兇;23種病脈及6種死脈則對于預報疾病的危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4]53、62、64、68-83。
5 結語
綜上所述,學界在《玄感脈經》文本的考校、抄寫年代的考證、文本內容的分析、學術價值的揭示等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積極成果,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和啟示。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相關研究還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一些重要問題還不夠全面和深入。如既有研究中對殘卷作者的考證還不夠嚴謹;對《玄感脈經》編撰體例、引書情況和文本特征等還缺乏全面具體的討論;沒有將該殘卷放在隋唐時期脈學演變脈絡中進行全面細致的考察和分析,學術淵源、脈學理論特征研究還未深入。這些問題,都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的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