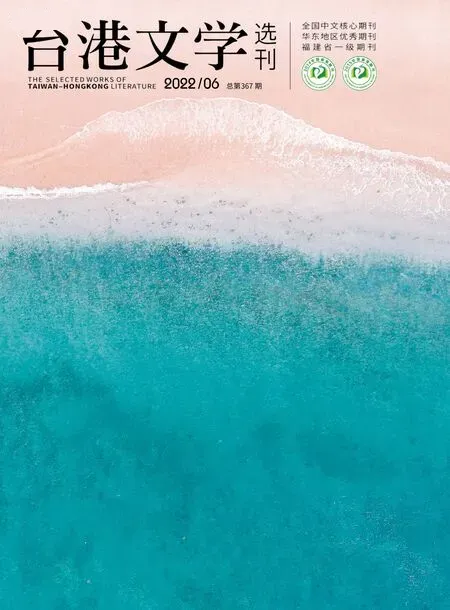看客散盡之后
■ 童元方(中國臺灣)
從前陳先生在的時候,我們整天說個不停。他公認的形象是話少、沉默。我問過他,為什么我不覺得呢?真要說起來,他不遑多讓,何況很多時候,我說話是在答他出的題;誰要那些題又太復雜,答起來沒完。他說:“那是看我跟誰在一起呢!旁人并沒說錯。”現如今可好了,一般是沒人跟我說話,我的雙子個性有時在不知不覺間從鏗鏘走向幽微;在沒有對話的世界,有時自然也從寬廣走向深刻,從星辰大海走向芍藥薔薇。我發現自己會突然想起些詩句,便浸淫其間,又琢磨、又咀嚼的,不論是否脫離了原詩的語境,總會品出些滋味來。千載下,若仍惆悵,已無感傷。
比如陶淵明,我為什么會無端想起《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的幾句詩來: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
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
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
……
這是他歸園田居之后的第四年,家宅忽遭大火,所置草屋八九間,竟無一室幸存,只能暫居門前小船。在這樣窘迫的情況下,既無一瓦遮頭,他亦無怨無悔。倒是身臥小舟,望著將圓的月亮,整個秋夜的天空,一覽無遺的清輝,是否因此而興新生的力量,而得遂其灌園之志?自己人過中年以后,屢遭風雨,才能如宋人一樣,逐漸了解陶淵明的情懷。從文學史發展的觀點看,在前路茫茫之際,或說從“愿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的情境中,無翅可展,無橋可渡,陶潛卻對我們說,其實你還有一個選擇,就是“回頭”。所以他直抒胸臆:田園將蕪胡不歸?然后歸園田,繼而帶出了“歸家”的主題。這是文學史上的驚天一瞬,我每想起都如初讀《歸去來兮》時那樣震動。在讀到“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時,在火災后無家可居的當兒望月,應是另類的驚天一瞬,我心中永遠的大塊文章。有此磅礴而沉穩的底氣,才會有日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渾然天成。
也是在這無聲的世界,最常想起王維,尤其是《輞川集》的五絕來。絕句既斷在未盡之意,五言又相對字少,特別有禪意。好像我隨意想想,就覺得舒服。而且輕省,而且自在;身上連最后一粒紅塵的重量也飄落了。說說《辛夷塢》與《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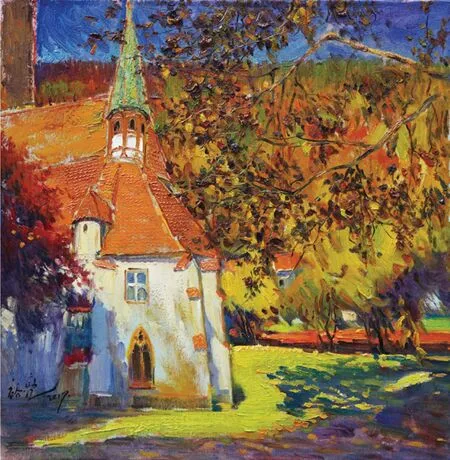
王裕亮 布勞博伊倫小教堂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辛夷塢》
是怎樣的心境會讓詩人留意花開的周期,繼之思及枝頭紅顏自我完成的生命旅程,其實與外界無關,與旁人無關。開滿了,落盡了,無晴亦無雨。理應如此!這樣體會了一“靜”字,一“閑”字。把眼光緩緩收回,從山中澗口的花朵到家中小院的青苔。
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
——《書事》
《書事》是寫眼前實時所見。詩人晨早慵懶而起,步入小院,撲上眼簾的不是花樹,而是雨后冒生的蒼苔;不是靜態的一片綠意,而是洶涌上沖的生命力。我七歲開蒙所學的第一首詩,是白居易的《凌霄花》,第一篇文章則是劉禹錫的《陋室銘》。初讀“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文字在腦海里即刻轉成了圖畫,而且是動態的,苔會上階,草亦入簾;兒童讀著真是太上口,又上心。王維的詩寫得比劉詩早,我卻認識得晚。對照坐看詩人的慵懶之姿,他所凝視的蒼苔綠意,其勢欲飛,實是寓動于靜,悄悄展現了萌發的生機。
在無意間捕捉到人間勝景,即使是小院一角的微小世界,我依然心驚于時光之飛逝于無形,而恐風光之不再!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乃永遠無解的千古一嘆。對于明知將殘的美,只能在日落后強留一會兒。下面這首《花下醉》的后兩句,即是李商隱對絕情時間的回應,不論是說斜陽,還是說花朵。
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
余暉的光彩既盡,一片漆黑中點上紅燭,仔細審視花兒最后的美麗。我在獨處的光陰中,因為安靜而留神流動的“將殘”,也因為詩人這最后的呵護與欣賞而在“殘”中看到生命的完整與圓熟。想到李商隱對花的留戀,最動人的自然是他的《落花》詩了。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我一般不是特別喜歡五言律詩,亦不特別鐘情詠物詩,但對這首詠物的五律卻是情有獨鐘。不談詩人寓意,只說詩人寄情。客散之后,才注意到:啊!滿天翻飛的繽紛的落花!往遠處看,花兒一路飄在院外蜿蜒的小徑上,彎彎曲曲伴送著夕陽的光影。好不容易盼來了春天,如今花容與日色皆殘。只能因不舍而落淚,而延時,但終究是留不住的。
以詩的形式而言,從五絕到七絕,那未斷的欲留的深情在枯荷聽雨的審美上終究于亙古中不朽。
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
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殘荷聽雨聲。
仍在青春洋溢的歲華已因年少喪父而遍歷風雨的李商隱,對剛經失怙之痛的崔氏兄弟說,雖隔天涯,我懂以后人生的孤寂,總惦記著你們,牽掛著你們;枯荷失了顏色,仍可聽雨聲,不是嗎?
《紅樓夢》40回賈母率眾游湖,寶玉說荷葉已破敗,怎么不拔了去?黛玉說李商隱詩自己只喜歡一句,即:留得殘荷聽雨聲。殘荷成了枯荷的變奏,意思卻改了;一語道盡了興衰。
在無人跟我說話的家宅日常,夜色深沉中有時會進入幽獨之境,自會想起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我喜歡,特別覺著寧靜、純粹、恣意、自由。少時喜歡詩的意境,也喜歡其映照出的畫境,而現在,就是詩畫中人。如此,我又在不知不覺間從小院中的一角青苔走向洪荒天地,在幽州臺上應和起陳子昂的歌來:
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我更喜歡了。挾著初唐的氣勢,歸來仍是少年。時間本來只是幻象而已,無所謂過去、現在、未來。如果換成英文,前是未來,后是過去:以唐詩的語境而言,自是相反。所以見不到已成過去的古人,也見不到尚未來到的新人,在高臺之上、時間之流中,與唐人的眼淚不同,必當長嘯慷慨,吐納呼吸,盡情化出滄海一聲笑。
看客散盡之后,回到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選自中國臺灣《文訊》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