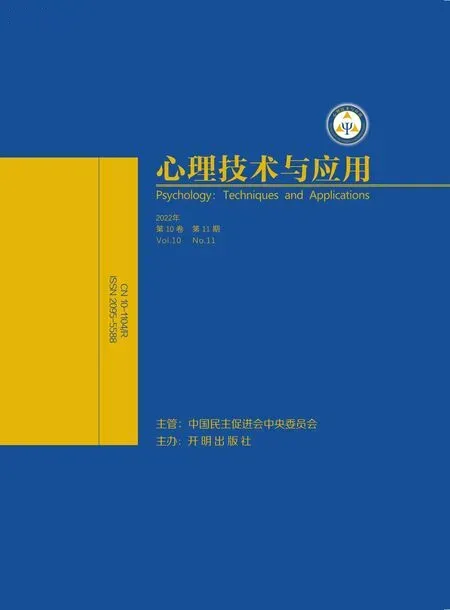中醫藥文化認同影響個體動機性推理
劉 穎 陳麗君 汪新建, 3
(1 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職業教育學院,天津 300222)(2 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福州 350108)(3 南開大學心理學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1 引言
人們經常發現有些人很難被說服,即使面對確定的事實他們也不愿改變與事實相左的想法,依然認為自己是對的而別人是錯的。這一現象其實反映出認知過程中的一種偏見,即“動機性推理”:由于不同個體預有信念不同,受不同動機驅動,在信息提取、分析、處理過程中出現自我服務偏差,導致人們從相同的信息中得到不同推理結論的現象(Epley & Gilovich, 2016; Gilovich & Ross, 2016; Kunda, 1990)。
許多研究已經發現動機性推理會妨礙人們對具體問題的理性分析。例如,人們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會因為招聘啟事中出現對應聘條件模糊不清的表述,而不能結合自身實際狀況進行評估,反而盲目地認為自己格外值得被聘用并獲得高薪資(Kappes et al., 2018);在政治觀點上,很多研究發現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偏好挑選政治信息(劉顏俊, 廖梓豪, 2022),面對有爭論的政治事件時,不同黨派的成員雖然能夠正確地認識積極或者消極事件,但是在討論歸因的時候會產生巨大分歧,雙方都傾向于將積極事件歸因于自己黨派支持的領導者,而將消極事件歸因于敵對陣營的領導者(Bisgaard, 2019; Flynn et al., 2017);在公共議題討論中,如美國的槍支管理問題,雖然人們對槍擊事件有共同的恐懼,但是爭論雙方卻會從不同的角度解讀槍擊事件,以支持或反對槍支管制立法(Pierre, 2019)。
同樣地,動機性推理也會妨礙人們在醫療健康領域的理性分析, 甚至妨礙人們糾正對有關醫療健康的不正確認知。醫療健康領域更加重視人們對復雜問題進行有效推理的能力,包括判斷獲取的信息和提出的主張是否一致, 正確區分真實信息和虛假信息, 以便做出明智的決定(Hamilton et al., 2017; Shah et al., 2017)。人們在尋求或者接收有關健康的信息時,可能會因為感受到威脅而采用動機性推理以進行自我防衛, 從而導致其忽視、回避甚至懷疑對其健康構成威脅的信息(Chasiotis et al., 2021; van’t Riet & Ruiter, 2013),進而妨礙其對醫療健康有關問題做出理性決策。Kunda(1987)發現,在要求研究對象讀了一篇聲稱咖啡因會給女性帶來健康風險的文章后,攝入大量咖啡因的女性比攝入少量咖啡因的女性更不相信這篇文章的信息,而對男性則沒有這樣的影響,盡管他們和女性一樣對咖啡因有先驗認知。van Stekelenburg等人(2020)在糾正關于兒童疫苗接種和食品安全的不正確認知的研究中,通過使用指導語要求實驗參與者從自己觀點的角度出發或者從公正無私的角度出發閱讀不良認知糾正材料,發現在兒童疫苗接種和食品安全兩個主題當中,從自己觀點出發的參與者在接受校正信息的傳播方面比另一組的參與者都要差。
動機性推理對日常生活中個體的態度與行為有普遍的影響,這使我們有必要對影響動機性推理的因素進行分析,從而尋找減少或者抑制動機性推理的途徑。人們一般會認為,個體理性分析的能力和受教育程度有較強的相關。但關于動機性推理的研究發現,科學素養或知識水平并不能夠顯著影響人們的動機性推理,反而可能是科學素養越好、知識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產生動機性推理,在一些問題上產生嚴重的兩極分化(Kahan et al., 2017)。實際上,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文化認同是使人們不自覺地產生動機性推理的原因之一。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或者社會認同的一部分,表現為對共同文化或者祖先的尋根(Hall, 1989)。Kahan等人(2017)就將產生社會爭論的原因歸結于身份認同的需要,認為文化沖突使公眾在理解與科學有關的決策時能力失效,出現動機性推理,避免自己產生有悖于所在群體的觀點,以維護群體身份。關于越南大量使用犀牛角入藥的研究就驗證了這一觀點。研究者發現,即使缺乏科學證據證明犀牛角的藥性和有效性,在越南本土的文化和社會規范影響下,越南消費者仍將其視為靈丹妙藥(Nguyen et al., 2020)。國內一項關于辟謠的研究也發現,辟謠信息有可能會威脅人們的自我身份認同,進而導致人們堅持相信謠言(熊炎, 2021)。
那么,在中國文化背景中,人們是否也會因為文化認同而在中醫醫療有關問題上不自覺地出現動機性推理? 中國傳統醫學與現代醫學之間的爭論已有百余年的歷史(劉理想, 2007; 張效雷, 2007), 公眾至今還是會因為某些刺激線索的出現而討論甚至爭吵,如是否應“廢醫驗藥”,青蒿素的發現究竟是歸功于現代醫學還是中醫等。在中西醫的爭論中,能夠發現存在群體內認同趨同、而群體間觀點極化的現象(刁蓉艷, 楊柳青, 2013; 謝茂松, 2020; 張玲, 張勇, 2019)。中醫藥文化認同是影響中國人中醫醫療健康決策的重要因素,它既是傳統文化熏陶的結果,也是近年來政府相關政策大力支持的結果。國務院2016年印發了《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2016—2030年)》,把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為此,本研究關注患方中醫藥文化認同是否會導致其在中醫醫療有關問題上出現動機性推理。研究將中醫藥文化認同定義為“個體對中醫藥文化特征(事項)的接納,這種接納具體表現為人們對中醫藥文化特征內容和形式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潘小毅等, 2019)。本研究認為患方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導致其在回答中醫醫療有關題目時產生動機性推理,如果患方回答完問題之后立即收到關于其回答是否正確的信息,患方也會根據自己的中醫藥文化認同判斷該信息是否符合其預有信念,并在評價信息信任時出現動機性推理。
為此,本研究設計了一組自編題目,實驗1為二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其中參與者的中醫藥文化認同程度為被試間因素,自編題目的中醫藥正負線索為被試內因素,檢驗了中醫藥文化認同是否會導致參與者在中醫醫療估值題目上產生動機性推理;實驗2為三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在參與者完成實驗1的題目估值后馬上給出反饋信息(“高于估值”或者“低于估值”),要求其評價對所給信息的信任程度,其中中醫藥文化認同和反饋信息為被試間因素,中醫藥正負線索作為被試內因素,檢驗參與者在評價反饋信息可信性時是否也會出現動機性推理。研究要求參與者同時完成實驗1和實驗2。
2 實驗1:中醫藥文化認同與中醫藥正負性線索對動機性推理的影響
實驗目的在于利用自編中醫醫療估值題目,檢驗患方關于中醫藥文化認同的預有信念是否會導致其在積極、消極或沒有中醫線索的中醫醫療估值題目上產生估值推理偏差。
2.1 方法
2.1.1 被試
使用G*power計算樣本量,使用F檢驗中的ANOVA被試內重復測量設計進行測算,設定effect size為0.25,預計統計檢驗力1-β為0.95,按照預測因素有一個三水平的組間變量和一個三水平的組內變量,得到計算計劃樣本量為54人。通過線上實驗收集到參與者200人,平均年齡為32.97歲(SD=8.35),最小為25歲,最大為65歲。其中男性91人(45.50%),女性109人(54.50%)。
使用中醫藥文化認同量表的統計結果對參與者得分進行排序,將得分最低的25%、共50人劃為低中醫傾向組,將得分最高的25%、共50人劃為高中醫傾向組,剩余50%、共100人劃為中立組。
2.1.2 材料與工具
參考Gür?ay-Morris(2016)的研究,使用自編估值題目作為測量材料(見附錄),記錄并研究參與者根據題目線索進行估值的準確性。實驗中編制了七個題目,每個題目字數在150±7左右,根據是否有中醫藥線索及線索的性質,分為三類,其中經度估計和隨機數估計為控制題目,醫保藥品、執業人員和醫院數量題目作為中醫積極線索,不良反應題目和說明書題目作為中醫消極線索題目。
采用潘小毅等人(2019)編制的中醫藥文化認同量表測量參與者的中醫藥文化認同。該量表共18個題目,分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維度,采用5點評分,總分越高表明越認同中醫文化。本實驗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5。
2.1.3 任務和程序
本實驗為3(中醫藥文化認同:高/中/低)×3(中醫藥正負性線索:積極/消極/控制)混合實驗設計,因變量為被試對中醫藥相關題目的估計值與準確值之間的差值。通過Credamo數據收集平臺收集數據,實驗完成后參與者會收到8元報酬。
步驟1:要求實驗參與者填寫個人信息,并完成回答中醫藥文化認同量表。
步驟2:向實驗參與者依次呈現七個測量題目,要求參與者分別進行推理估計。告知研究參與者“每個題目的內容都來自真實的新聞或者報告,但其中給出的信息并不完整,需要您根據要求,結合已有知識與經驗,寫出自己估計的答案,越準確越好”。
步驟3:最后呈現七個題目的參與者估值和正確答案頁面,解釋研究目的并告知其領取報酬。
2.2 結果
2.2.1 中醫線索題目和控制題目估值差異檢驗
對研究參與者對測量題目的估計值進行統計,并計算估計值與正確答案之間的差值,將其標準化后作為偏差程度的指標,結果見表1。

表1 實驗參與者估值偏差描述統計(N=200)
分別計算中醫積極線索、中醫消極線索和控制題三類題目標準值的均分,生成三個新的變量,分別是中醫積極線索題得分(M低=-0.30,SD低=0.75;M中=0.04,SD中=0.76;M高=0.22,SD高=0.72)、中醫消極線索題得分(M低=0.20,SD低=0.82;M中=0.01,SD中=0.71;M高=-0.22,SD高=0.75)和控制題得分(M低=-0.02,SD低=0.68;M中=-0.02,SD中=0.78;M高=0.06,SD高=0.71),將中醫藥線索作為組內因素,將研究參與者的中醫藥文化認同作為組間因素,進行兩因素混合方差分析。
對本實驗估值偏差的組間差異進行檢驗,發現在中醫積極線索題目中,估值差異主要出現在醫保藥品和執業人數兩個題目上,都是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顯著高于低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在中醫消極線索的題目中,估值差異主要出現在不良反應和說明書兩個題目上,都是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顯著低于低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根據分析結果,制作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程度參與者得分差異圖,見圖2。

圖2 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在各個估值問題上的估值偏差差異
2.3 討論
不同水平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中醫積極線索和消極線索題目上,即在醫保藥品、執業人數這些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希望比例更高的題目上,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顯著高于低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在不良反應、說明書這些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希望比例更低的題目上,高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的估值顯著低于低中醫藥文化認同參與者;在控制題上則沒有顯著差異。這表明人們不同的醫療傾向對于估值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有中醫線索條件下。也就是說,參與者在有中醫線索的估值題目上出現了動機性推理。
3 實驗2:中醫藥文化認同與反饋信息對動機性推理的影響
實驗1發現參與者不同水平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影響其估值偏離正確答案的方向和程度,并且驗證了自編題目的有效性。實驗2在此基礎上,在參與者完成每次估值后馬上提供“高于估計值”和“低于估計值”兩類反饋信息,測量參與者對該反饋信息的信任情況,以進一步確證中醫藥文化認同造成的動機性推理的具體表現。
3.1 方法
3.1.1 被試
與實驗1相同。使用G*power計算樣本量,根據F檢驗中的ANOVA被試內重復測量設計進行測算,設定effect size為0.25,預計統計檢驗力1-β為0.95,按照預測因素有一個三水平的組間變量、一個二水平的組間變量和一個三水平的組內變量,得到計算計劃樣本量為72人。實驗1收集樣本200份,符合統計檢驗力要求。
3.1.2 材料與工具
與實驗1相同。
3.1.3 任務和程序
本實驗為3(中醫藥文化認同:高/中/低)×2(反饋信息:高反饋/低反饋)×3(中醫藥正負性線索:積極/消極/控制)的混合實驗設計,因變量為參與者接受反饋信息后對反饋信息的信任度。參與者同時完成實驗1和實驗2。
步驟1:與實驗1相同。
步驟2:參與者完成實驗1題目板塊要求的估計任務之后,呈現反饋板塊,在反饋板塊中進行隨機設計,隨機給予“高于”或“低于”參與者估計值的反饋,并告知其“每個題目之后都有反饋信息,告知您所猜測的數字和正確答案之間的大小關系,但是反饋信息有可能為真也有可能為假,需要請您在閱讀完答案之后根據已有知識和經驗進行評估”,要求參與者用0到10進行評價,0表示非常不信任,10表示非常信任。
步驟3:與實驗1相同。
3.2 結果
3.2.1 中醫藥文化認同與反饋信息類型影響反饋信息評價
計算研究參與者對反饋信息的信任評分作為信息信任指標,見表2。

表2 參與者信息信任描述統計(N=200)
為比較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水平的參與者在完成不同類型的估值題目后對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根據題目類型逐類分析。
(1)中醫積極線索題目


圖3 不同分組在醫保藥品問題上的反饋信息信任
對中醫執業人數和醫院數量兩個題目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評價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反饋信息主效應、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的主效應以及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都不顯著(ps>0.05)。
(2)中醫消極線索題目


圖4 不同分組在不良反應問題上的反饋信息信任


圖5 不同分組在說明書問題上的反饋信息信任
(3)控制題目
對經度和隨機數兩個題目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評價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反饋信息主效應、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的主效應以及二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都不顯著(ps>0.05)。
3.3 討論
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水平的參與者在積極和消極中醫線索類型的題目上,對于高低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存在差異。在積極線索題目上,高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參與者相對于中低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參與者,對于高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更高;在消極線索題目上,高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參與者相對于中低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參與者,對于低反饋信息的信任程度更高;在控制題目上,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程度的參與者對反饋信息的信任差異不顯著。
4 討論
本研究通過操縱中醫藥線索出現與否,發現人們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影響其在中醫醫療估值題目上的表現;同時,通過操縱估值后所反饋的信息是順應還是反駁參與者的預有信念,發現參與者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影響其對于估值后反饋信息的信任。這證實了文化認同對動機性推理的作用,展示了其在中醫醫療健康領域的具體表現形態,并對其成因進行了理論解釋。
在有目的的動機性推理過程中,人們根據不同的目標產生不同的動機,所產生的動機則通過影響信息的搜索和觀念的構建起作用。同時,人們可能會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完成這一過程,甚至陷入“客觀性錯覺”,即認為自己是客觀公正的,卻沒有意識到個人所產生的有目的的動機已經在影響信息搜索和觀念構建的過程了(Greenwald, 1980; Pyszczynski & Greenberg, 1987)。本研究正是通過有中醫藥積極或消極線索的估值題目,引導參與者調用個人與中醫藥文化認同有關的經驗,再通過估值的高低反映出其對中醫藥文化認同的程度。研究發現,中醫藥線索自身引起的動機性推理已較明確。已有研究認為動機性推理是人們在面對威脅性信息時的一種自我防衛手段(Chasiotis et al., 2021; van’t Riet & Ruiter, 2013),本研究的結果支持了這一解釋。通過在估值后提供“高于估計”或者“低于估計”兩類信息,我們發現簡單的、不加數據或者理論支持的信息就已經能夠產生威脅個人文化認同的效果,人們不能夠忍受與自己預有信念不一致的信息,而會輕易接受與自己預有信念一致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任何不一致的信息都會使人們產生威脅感和防衛心,從而抗拒新出現的、與自己預有信念不一致的信息。因此我們在進行信息糾正或者信息傳播時,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工材料,處理好其呈現方式,以最大程度降低威脅感為主要目標。
本研究結果也有助于理解現在的中西醫之爭。中醫藥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醫藥市場蓬勃發展,中醫藥產值不斷增長,也逐漸走向國際化,但是對于其功效和安全性的爭議從未中斷(Xu & Xia, 2019)。現代醫學主張通過隨機對照實驗和可靠的數據來評估療法和療效,但是中醫的理念和療法并不能完全滿足這一要求,因此中西醫之爭也常常會轉變為對科學理解能力高低的爭論,中醫的反對者和支持者都認為對立方由于缺乏基本的科學理解能力才持有目前的觀點。但是以往研究已經發現,高科學素養和高受教育程度的個體對有爭議的科學話題的看法可能會更加兩極分化(Drummond & Fischhoff, 2017),并且文化認同會導致人們在理解科學有關問題時出現能力失效(Kahan et al., 2017)。本研究就發現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導致人們在估值和信息評價中出現動機性推理。這啟發我們,提升人們的科學理解能力并不能有效彌合雙方之間的沖突,而是應該尋找途徑,切斷有爭議議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關聯,充分調動人們的科學素養和能力,促使人們對有爭議問題做出客觀判斷。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采用自編工具,在工具設計、內容表述等方面考慮不夠充分,存在信效度難以評估的問題。其次,對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劃分比較粗糙,沒有對參與者先驗觀念的強度和穩定性進行有效控制,因為美國一項關于政治信仰的研究中發現先驗觀念越強、相關知識越完善的參與者越容易受到動機性推理的影響(Taber & Lodge, 2006)。最后,從研究內容來看,分析了不同中醫藥文化認同的參與者對反饋信息的信任評價,但是對于反饋信息的內容、性質、強度、數量等變量沒有進行操縱。而美國一項關于候選人負面信息對選民態度影響的研究發現,負面信息不能有效促使人們改變原有選擇,反而可能會讓選民更加堅定自己的選擇,只有當負面信息的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選民才會開始考慮重新選擇(Redlawsk et al., 2010),因此想要達到影響已有態度、使人們接受與已有觀念不一致信息的目的,需要從反駁信息本身的數量和質量出發,這有待后續研究的進一步檢驗。
5 結論
個體的中醫藥文化認同會導致其在中醫醫療估值題目上出現動機性推理:在中醫積極線索題目上,高中醫藥認同水平參與者的估值更高;在中醫消極線索題目上,低中醫藥認同水平參與者的估值更高;在評價估值后反饋的信息時,個體更傾向于認為與其預有信念不一致的反饋信息是假的,而與其預有信念一致的反饋信息評價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