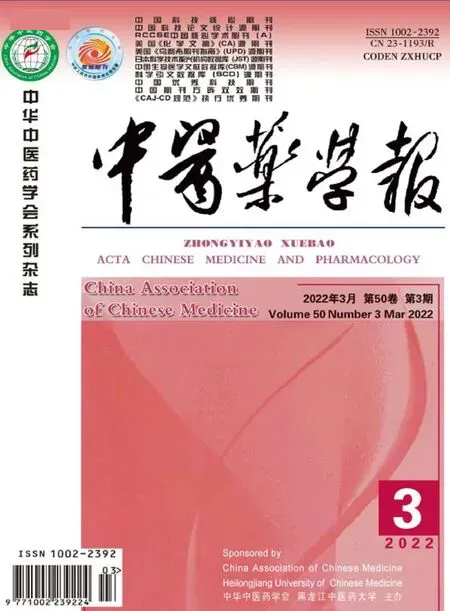“藥力”之“炮制”論
魏爽,郝峰,李冀*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 150040;2.江西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藥力是藥物本身在方劑中與它藥相比而言的能力,決定了藥物在方劑中的地位。單味藥無法評判其藥力大小,只有將其置于方劑中,藥力才有生命,才能悟衡其藥力之大小。影響藥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諸如藥性、配伍、藥量、劑型、體質、煎服法等,藥物在方中的藥力主要由藥性、藥量與配伍決定,藥性是決定藥力的基礎因素,藥量則是藥物在方中藥力大小的衡量標準。一般而言,藥物的藥性通常是不變的,但在方劑運用時若更改藥物的炮制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藥性,使其發生某些轉變。方劑中君藥之作用趨勢往往針對主要病機,君藥之藥力更易于把握,若君藥能夠通過炮制而使其藥性產生明顯的改變,那么對其在方中作用趨勢之探討就更有意義。本文試以幾首經典方劑中君藥運用不同炮制方法時其藥力之差異為基礎進行探討。
1 “藥力”探討之必要性
方劑多以“君臣佐使”為組方原則。然而,諸多醫家對許多傳世之經典方劑及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方“君臣佐使”的界定難以達成共識,難以對方子進行精準的剖析。基于此種情況,李冀教授根據“力大者為君”提出“藥力判定公式”,以“藥力”作為判斷方劑中君臣佐使地位的依據。藥物在方中的作用是由藥物自身在方中的藥力大小所決定的。這使一些方劑中藥物的君臣佐使地位更為明確,使方劑之理論研究更加明晰[1]。另外,尚有許多方劑并不是以“君臣佐使”為原則而立或不適宜用“君臣佐使”理論剖析,但藥力仍然可作為判斷方劑中藥物尤其是主藥作用力量大小的重要依據。“方無至方,方以效論”,不能因為一首方劑無法界定其“君臣佐使”而忽略其有效性,方劑有效就必然有其一定的道理,即或現階段人們不能解釋所有方劑的組方原理,也應當基于臨床承認其療效。如以“藥性”即藥物的四氣五味等為基礎的組方理論所創的方劑等,組方時并不以“君臣佐使”理論為依據,或不適宜以“君臣佐使”之理論對其進行闡釋。這時,便可通過“藥力”之判定,明辨各藥之作用趨勢,使得方劑更好地被人們所把握。方劑可以無“君臣佐使”之區分,但方中每味藥必然有其自身的“藥力”,且可通過調整藥量、配伍等影響其藥力。一首方子不論以何種原理組方,都應有其一定的作用趨勢,方中藥物配伍可使整首方劑發揮其多方面的作用,方中所用之藥都有其運用的道理,每藥必有其藥力。因此,對“藥力”之探討有其一定的必要性。
2 炮制對君藥藥力的影響
方劑中藥量變化與配伍的靈活運用是影響藥力的兩個突出方面。一般而言,藥量越大,其在方中的藥力就越大。但有時藥量亦可改變藥物之藥力,如柴胡一味,于補中益氣湯中少量應用則有升陽之性,于逍遙散中使用常用劑量則可疏肝解郁,于小柴胡湯中大量應用則透散少陽之邪。通過配伍可以增強、減弱或改變藥力。通常,作為影響藥力的基礎因素“藥性”是一定的,但并不意味著其永久保持恒定不變。藥物有其一定的藥性,多數藥物的功效具有多向性,且可通過配伍或藥量改變使其發揮其某一或部分功效。而不通過配伍或藥量改變亦可使某一藥物發揮其某一或部分功效,或改變其原有功效,這一因素便是炮制。藥力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大”或“小”的概念,藥物不同的功效有其不同的作用趨勢,藥力亦有其一定的“方向”性。藥性是探討藥力的基礎因素,藥性的可變性使炮制之探討更有意義。
大部分藥物的炮制多是為了增強療效、減低毒性,或改變其寒熱之性,或使藥物突出發揮其某一功效。亦有少部分藥物通過炮制可使單味藥呈現差異較大的藥性,這種藥性的改變是通過配伍難以影響的,如何首烏生用截瘧,制用補益精血。炮制前后,雖其本仍是同一味藥,但選擇不同的炮制方式對其在方劑中的藥性有時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進而影響其在方中之藥力,且以對君藥藥力的影響更為明顯。
2.1 腎氣丸之地黃
此方出自《金匱要略》[2],主治痰飲、腳氣、消渴、轉胞等證,又名“崔氏八味丸”,普遍認為是仲景引用崔氏之方。方名往往反映了一首方的功用,原方以“腎氣”命名,其意在圖腎氣可知。“氣”是機體發揮功能的基礎物質,腎司開闔功能的發揮主要責之于腎氣,腎氣不足則其司開闔的功能無法正常發揮,或開而不闔,或闔而不開,因而多出現小便不利或小便反多的情況,即“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及“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等。虛勞為陰陽精血皆損,病及精分為病勢較重的情況,陰陽氣血皆源于精,腎氣的充足有賴于腎精的充盛,而腎精的填補要依賴于腎氣的充養,即腎氣源于腎精而反過來能對腎精的充盛起到積極的作用,因此虛勞腰痛者運用此方可于補腎氣中達到填腎精的作用。
“虛則補之”“少火生氣”,腎氣不足者補之應以少火生氣之法,不能以大辛大熱之品,要以微溫陽氣為基礎使腎氣充盛。腎氣丸原方立意在于緩生腎氣而助填腎精。同時溫陽之品當以陰藥制約其溫熱之性,否則易生浮火。故方中以一兩桂附溫陽而以八兩干地黃微涼之品制約其溫且補陰分。腎者先天之本,腎精之充盛是五臟六腑發揮功能的基礎,脾為后天之本,五臟六腑亦賴于后天水谷的充養。故原方在補腎之基礎上兼顧后天之脾,以山藥補脾之陰分,伍桂枝又可補脾之陽,陰陽并補,脾氣亦充。腎氣不充則水濕易聚下焦,茯苓、澤瀉又使全方在補的基礎上有瀉其濁的作用。腎之陰不足則易為虛熱或浮火,故用丹皮以清虛熱退浮火,更佐地黃之功,杜其生熱之弊。丸者,緩也,欲緩生腎氣,不宜以勢峻之湯劑,是方為丸緩服,恰合丸劑減緩藥力之意,達到緩生腎氣之功。
此方明示所用之地黃為“干地黃”,當為鮮品曬干用之,即今所用之生地黃。然后學臨證運用或有以熟地黃易之者,實與仲景本意相悖。《金匱要略》成于漢代,其時,對于地黃尚無生、熟、干之明確區分,生地黃與干地黃于南北朝時期方分化,而熟地黃則始載于宋代《本草圖經》[3],故原方中之“干地黃”為“生而干者”,即今之生地。蓋干地黃較之鮮地黃,寒性稍減,清熱涼血之力遜而養陰之效佳,熟地黃則屢經蒸曬而性微溫[4]。地黃對腎陰與心陰皆有滋養作用,如炙甘草湯中即以一斤生地配諸溫心陽養血之品,在炙甘草緩急的基礎上補養心之陰陽。故而腎氣丸中在將地黃用干品的基礎上配伍諸滲瀉之品亦可引其專養腎陰,且無涼遏之弊,八兩干地黃與桂附各一兩相配而達到“陽化氣,陰成形”“少火生氣”的目的。
后學以熟地黃易之,則為益精髓之品,且熟地黃寒性幾無,用之無法制約桂附之溫燥。然而若以熟地黃易干地黃則也非全然不可,只是易后全方偏于補精助陽,無緩生腎氣之力。對此,應當理性看待,然而熟地黃與干地黃藥性之差異于此亦可見一斑。如錢氏之地黃丸則將腎氣丸去桂附并使用熟地黃,偏補腎精。景岳之右歸丸針對的是腎精不充,腎陽不足之證,以熟地黃配伍諸滋陰與補陽之品,而以補陽為主,達到陰中求陽之目的。由此也可見,仲景組腎氣丸之衷應當不為溫腎陽而設,否則景岳似不會又去創制溫腎之右歸丸。
可見,腎氣丸中地黃若用干品則功善補腎陰,配伍少量桂附以緩生腎氣,適于腎氣不足諸證;若以熟地黃易之與桂附配伍則全方之性偏溫,適于腎精不充,腎陽不足之證。
2.2 麻黃湯之麻黃
麻黃湯為治療太陽傷寒第一方,主治太陽傷寒表氣郁者。表氣被郁不得發散,因而出現脈浮、惡寒、頭項痛等癥。治療當以解表散寒為主,故以三兩麻黃發散表郁,逐除寒邪。寒邪傷人每有耗陽之慮,故伍桂枝固護陽氣且助麻黃溫散之力,又兼預培心脾之意。麻黃雖為解表之峻藥,其性燥烈,恐又有宣發太過之虞,且是證每有喘嘔之兼癥,故以杏仁潤利氣機以制約麻黃宣發之性,防其宣發太過而致衄血,且有一定的降氣平喘之效。麻杏相配,宣降相得,恰與肺之宣肅功能相合。考傷寒論可知原方中麻黃當為生品,蓋仲景用藥皆明示其炮制,此處用麻黃僅示“去節”而沒交代其他炮制,此其一。麻黃生品煎煮當有藥沫產生,正合其后煎煮法中“去上沫,納諸藥”之語,此其二。是知仲景所用麻黃湯中之麻黃當為生麻黃。故仲景諄諄告誡諸瘡家、淋家、衄家、亡血家,不可發汗,即使已經用汗法治療未愈者也不應復用麻黃湯,蓋因其發表之力峻猛,誤汗在所當忌。今人每多謂麻黃煎煮未見沫出,實皆因未用生品而是炙品。此方若將生麻黃易為炙麻黃,則其發表之力減而潤肺平喘之效增,同時配伍桂枝、杏仁等則適于治療寒性喘咳。炙麻黃雖也有一定的宣表之力,而若仍以此治療仲景所載之太陽傷寒表實者,則發表之力明顯不足,且桂枝已溫之陽無從出路,極易變生內熱或轉入陽明,即所謂“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于外,則必壅塞于內”[5]。可見,麻黃湯中麻黃若用生品,則其性專發散,用炙品則力擅潤肺平喘。
2.3 白術湯之白術
所謂白術湯,出自《圣濟總錄》,后被《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轉載時易名“四君子湯”[1]。原方以白術命名,可見對白術功用的重視程度,觀其主治“水氣渴,腹脅脹滿”可知[6]。考原方之白術,當為生白術。白術生用,實為健運之品,《本經》所謂“消食”似是指此。實則仲景亦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白術運化之功,即于“理中丸”中可見一斑,所謂“理中者,理中焦”,不因其三兩干姜而謂“溫中焦”,或因其三兩人參而謂“健中焦”,卻偏偏用一個“理”字,使不被重視的白術脫穎而出,且并沒有交代白術要炒用,可見所用者當為生品,正合“理中”之意。胃受盛飲食,“脾氣磨而消之”[7],脾欲發揮其運化之功能,脾氣充足是基礎,故配伍扶助中焦之氣的人參,使脾氣得以在“健”的基礎上達到“運”的功能。脾喜燥惡濕,又兼有水氣為患的病機,故以赤茯苓以通其水道。白術湯主治水氣為患,生白術本有利水之功,又有赤茯苓以助之,則此方中白術之藥力略強于人參可知,堪為君藥。今用白術往往以炒白術,乃取其健脾燥濕之用。
其后之四君子湯則以炒白術易生白術,使白術所發揮的藥力從“運”轉變為“健”,其與人參配伍則共同發揮健脾之功效,運脾之力驟減。雖有滲濕之茯苓,而其作用在于滲濕以健脾,更兼輔助人參之力。此時炒白術健脾之力又明顯遜于人參,僅能作為輔助人參之品,退居臣位,故四君子湯中以人參為君藥,全方以健脾補氣為主。
可見,白術湯(或謂四君子湯)中,若用生白術配伍人參、茯苓等則偏于運脾(白術湯),若運用炒白術則臣于人參而使全方偏于健脾(四君子湯)。
此外,常用藥物甘草也應當重視其不同炮制方法在不同方劑中的運用。《傷寒論》311條曰:“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此中之“甘草湯”僅甘草一味,仲景所用之甘草多以炙者,此處卻僅交代“甘草二兩”,則其為生甘草可知。所謂“咽喉干燥者不可發汗”,此咽痛蓋因邪結于咽喉局部,略有化熱之象,雖汗之病不可解,若癥狀較輕者則可以生甘草清熱解毒止痛。此證若略重者,單以生甘草一味不足奏效,則臣以一兩桔梗于解毒之中有排膿之用。病情更重者,當求它法治之。甘草生品與炙品藥性不同,炙甘草被醫家所熟悉,其有“國老”之稱,多用以調和諸藥,如麻桂劑等,或緩急之用,如炙甘草湯中蓋為緩其“心動悸”之癥。此處甘草生品之用,亦不可忽視之。
3 炮制改變中藥化學成分研究
單味中藥在方劑中發揮主要作用的成分與中藥的炮制方法及炮制輔料存在密切聯系,炮制后化學成分的改變是導致中藥藥效變化的物質基礎。傳統中藥炮制方法多是通過水、熱、乙醇等理化因素達到改變中藥的藥性,從而使其在方劑中發揮不同側重的作用,也就是說,中藥的藥性可以通過不同的炮制工藝進行改變。通過炮制改變中藥的藥性是基于中藥在水、熱、酒、醋等一定的理化因素條件下發生一系列化學反應,產生新的物質基礎,改變原有的藥理作用達到的。而處方中藥物的藥性一旦發生改變,依據藥力判定公式,則藥力必然發生改變。
傳統應用中,地黃有生熟之分,生地黃經炮制后所成熟地黃之所以顏色轉為烏黑,質地變黏,性味轉為甘溫,功效以補為主,側重滋陰補血、益精填髓,主要在于炮制后二者的化學成分有了明顯的變化[8]。趙國洪等[9]采用偏最小二乘法-判別分析模型進行研究發現,生地黃和熟地黃化學成分及代謝物含量存在較大差異:蒸制后包括單糖、環烯醚萜苷元等化合物在內的半數代謝物水平升高,氨基酸類、環烯醚萜苷類化合物等代謝產物含量降低。炮制后,5-羥甲基糠醛含量的顯著增加及氨基酸含量的顯著降低間接證明了炮制過程中美拉德反應的發生,從而導致中藥顏色發生改變[10]。另外,熟地黃中果糖和半乳糖的水平也明顯上升,且果糖在生地黃、熟地黃的分類上作用顯著,表明果糖含量可能是熟地黃質地變黏、味轉甘的原因。環烯醚萜苷類化合物是地黃的重要活性成分,生地黃炮制為熟地黃后,環烯醚萜苷類成分含量顯著下降,而環烯醚萜苷元成分含量顯著上升,可能是生地黃與熟地黃功效存在不同側重的主要原因。
發表第一要藥麻黃在《中國藥典》[11]中收錄的炮制品為蜜麻黃,(麻黃)生品以發散風寒為主,蜜炙以平喘止咳為主。可見,經炮制工藝后的麻黃在藥性和功效上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說明炮制過程中可改變作為藥效物質基礎的麻黃的化學成分。研究發現[12],與生麻黃相比,炙麻黃中的生物堿、黃酮、烯烴、有機酸4類21種化學成分發生顯著變化。生物堿類成分均有所降低,黃酮、烯烴及有機酸類成分經炙后含量上升,其中,有機胺類生物堿含量的微降,加之噁唑酮類生物堿含量的顯著升高,使得炙麻黃在保留發汗作用的同時又增強了潤肺止咳平喘作用。
前文已述,生白術與炒白術功效側重存在差異,造成此現象出現的原因同樣在于炮制,炮制改變了中藥內所含的化學成分及水平,炮制方法不同,白術功效不同。揮發油是白術的主要活性成分,且以蒼術酮含量最高[13],白術經過炒制后揮發油含量顯著降低,而白術的性“燥”主要取決于揮發油的含量。炮制后,揮發油水平明顯降低,使其燥之偏性被抑制,健脾燥濕止瀉的作用得以突顯。此外,白術炒后,β-丁香烯、β-Vatirenene、β-朱欒、r-欖香烯、6,7-二氫甲氧呋豆素顯著升高,2-Ethyl-6-(4′-methoxyphenyl)-3-oxo-1-cyclohexenecarboxylic Acid及(+)-喇叭烯成分消失[14]。由此可知,炮制可通過影響中藥的有效成分及水平影響藥性,從而改變方劑之藥力。
4 結論
臨證處方時,君藥運用不同的炮制方法有時會使全方的主治方向轉變,炮制也是影響藥力的因素之一。君藥往往代表著一首方的主旋律,其采用不同炮制方法時所體現的差異較為明顯,同時也不能忽視非君藥炮制的影響,方中每一味藥的藥性改變都對其藥力有一定影響。炮制能夠改變藥性,進而影響藥力。“方之精,變也”,臨證中對方劑的運用,其加減變化在所難免,患者病情之難以復制性使得醫家運用古方時要針對患者當下之證遣藥組合適宜之方,加減運用適宜之藥。這些運用一定要建立在對方劑靈活把握的基礎之上,熟悉方劑中藥量與配伍的同時,也應對藥性有一定的把握。通過詳細辨證,針對患者的證施以相應的藥,從而為處方發揮更好的作用提供基礎,使藥物更好地發揮其所被期望的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