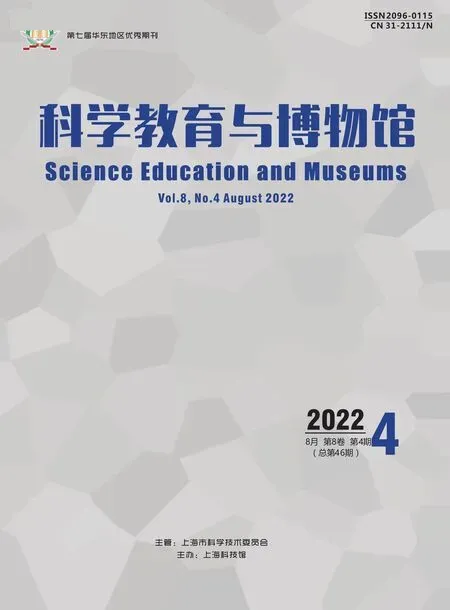親子在動物園參觀過程中的對話內容與模式調研
吳上好 沈 演 陳柯澄 顧江萍 翟俊卿
1.浙江大學教育學院
2.杭州動物園(少兒公園)
0 引言
場館(museum)指各種與科學、歷史和藝術教育有關的公共機構,如科技館、天文館、自然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美術館、動物園、植物園、水族館等[1]。其中,動物園是飼養各種野生動物,進行科學研究和遷地保護,供公眾觀賞并進行科學普及和宣傳保護教育的重要場所[2]。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運用話語分析的方法探討親子團體在自然博物館、科技館等場所的參觀體驗與學習過程,但是對親子團體在動物園中的學習過程關注較少。此外,以博物館為背景的對話研究往往缺乏對家長和孩子情感體驗的深入分析,而訪客的情感體驗正是動物園開展保護教育的根基。探討親子團體在動物園參觀過程中的對話,有助于深入了解親子如何通過言語互動建構知識,同時還能透過對話內容,剖析動物園科普教育的成效。本研究以參觀杭州動物園大象館的親子團體為研究對象,通過考察他們在參觀中的對話內容與對話模式,以探討他們的參觀學習過程。
1 研究背景
1.1 場館學習中的親子對話
學習是學習者在語言介導的社會互動中發生在知識、信念、態度等維度的積極建構[3]。通過語言,這種人類社會交往的主要手段,孩子們開始養成自己的文化思維習慣[4]。而對話作為人類利用語言進行溝通的基本形式,提供了一種腳手架式的學習機制,是知識共享與建構的工具[5]。以對話為中介的學習,發生在學校課堂,更發生在各類場館[6]。場館學習(museum learning)是一種典型的非正式學習方式,它指的是在信息刺激豐富的場館環境基礎上,個人經驗與社會團體交互作用的結合[7]。場館中的對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訪客建構知識和理解的過程[8]。
近年來,國內涌現出一系列有關場館中親子團體對話內容的研究。例如,鄧卓等人對自然博物館內親子團體的學習性對話內容進行了研究,發現與學習有關的對話發生頻率相對較低[9]。相類似的,郭子葉的研究也發現親子之間的學習性對話呈現出親子交流過程短暫,極少形成互動式的交流過程,深層次的解釋類對話很少[10]。此外,國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針對場館中親子對話模式進行研究。例如,翟俊卿等將自然博物館中參觀的親子團體對話類型分為“互動-對話型”“無互動-對話型”“互動-權威型”“無互動-權威型”[11];張月將親子團體對話模式分為“共同探究型”“啟發引導型”“指導操作型”三種親子互動模式[12]。
1.2 動物園中的參觀學習
動物園是一個產生學習性對話的場所[13]。過去,動物園常被認為是家長帶孩子出去玩的地方,并非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公共機構。但近年來其教育作用已經成為反映其社會作用的關鍵。根據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動物園參觀學習,正是受訪問動機、先前經驗等影響,并通過與同伴、動物展覽等外部交互作用、建構意義的一種學習模式。
學習是群體共同活動的過程[14],而家庭團體是動物園參觀學習的主要受眾群體之一[15]。動物園提供真實的野生動物、豐富的科普內容、自由的參觀過程,使得家長與兒童在參觀過程中發生各種各樣的互動,而這些互動機會正是發展和維持孩子對于某一話題的個人興趣與基于知識的后續興趣的關鍵[16]。因此,親子團體在參觀過程中的互動影響著孩子對野生動物的興趣發展與知識理解。已有研究還表明,與活體動物的直接接觸能喚起兒童在情感與態度上的學習結果,而情感領域的教育作用能在長時期內產生積極的認知影響[17]。此外,動物園參觀可以增強訪客與自然的內隱聯結度[18],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強訪客的保護態度,并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在環境問題中的作用[19]。
相較于國內,國外學者對于游客在動物園、動物展覽、水族館等場館的互動研究較多。Geerdts研究了參觀動物園企鵝展覽和科學博物館昆蟲展覽的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和互動方式,發現父母會根據孩子的年齡特征調整他們的語言使用。如對學齡前孩子使用更多賦予動物以社會或心理屬性的社會性話語(如“它可能很害怕”)、強調動物作為一種生物的生物性話語(如“它正在水里游泳”)和提供超出動物身體屬性之外信息的概念性話語(如“你認為它們會發光嗎”)[20]。Patrick等人[21]和Kopczak等人[22]的研究都發現,動物園工作人員的存在與他們和游客的互動會影響家庭內部的對話內容,他們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參觀家庭內關于生物多樣性威脅、保護行為的討論。
然而,以上有關動物園、動物展覽內親子團體對話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歐美國家,我國目前對于親子團體在動物園內參觀對話內容與對話模式的研究較為缺乏。動物園內親子團體之間的對話,不僅反映了家長和孩子在動物園這種非正式場所參與學習、科學推理的過程,還從側面反映了動物園的保護科普教育效果。因此,對此進行探究具有重要的價值。綜上,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問題:(1)親子團體在參觀動物園過程中都在談論哪些內容。(2)親子團體在參觀動物園時的對話模式是怎樣的。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收集
本研究開展的地點位于浙江省杭州動物園中心位置的大象館區,大象館區內包含1條大象科普長廊、內室有3間、外活動場2個,外活動場邊上有1只水泥象雕。館區目前飼養了3只亞洲象。科普長廊對于象的棲息地、習性、生態價值,亞洲象與非洲象的區別,象的世界分布,象的進化史,大象冷知識,大象的食物,亞洲象的豐容等內容進行展示(見圖1)。
本研究的目標對象是杭州動物園大象展館內參觀的親子團體。親子團體均由父母一方與一名兒童組成,其中父母的年齡不限,兒童的年齡為6~9歲。主要采取觀察法和問卷法收集數據和信息。研究者通過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招募家庭,在研究開始前均先告知他們本研究的意圖并獲得他們的同意。研究的觀察時間主要是周末10:30至15:00,該時段人流量較大,容易招募研究參與者,也與大象日常活動時間基本一致。在參觀大象展館前,研究者對每組家庭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家庭的基本信息,包括家長與孩子的性別和年齡、家長的受教育水平、家庭參觀動物園的動機與頻次等。在參觀過程中,研究者采用無干擾跟蹤錄音和拍攝視頻的方式記錄親子團體參觀大象展館過程中的互動情況。
在家庭結構上,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均為由父親或母親單方家長與孩子構成的親子團體,其中母親-孩子構成的親子團體為10組,占67%;而父親-孩子構成的親子團體為5組,占33%。在孩子性別上,孩子為男孩的親子團體為8組,占53%;孩子為女孩的親子團體為7組,占47%,孩子的男女性別比基本平衡。
2.2 數據分析
本研究的數據收集方法是將所有親子在大象館的對話錄音轉為文本。在完成速記整理和音頻轉錄后,進入編碼階段,編碼前需要確定話語的分析單位。原則上以父母和孩子連續說的表達同一含義的一個句子或者一小段話作為一個分析單位,如果這一小段話中包括多種意義,在編碼時就視作多個分析單位。親子對話內容的分析框架在借鑒已有國外研究成果的同時[23-24],并綜合本研究所收集數據的特征,對分析框架做出進一步的優化(見表1)。
3 研究結果
3.1 親子團體在參觀動物園過程中的對話內容
通過對15組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進行質性編碼和分析,我們將家長與孩子在參觀大象館的互動過程中的對話按照表1的定義進行類型分析,將對話分為感知性、概念性、生物性、聯系與情感等五大類,各類型頻次統計結果(圖2)。其中,概念性和感知性話語內容是親子對話的最主要內容,而有關物種和相應情感的對話內容卻很少出現。
在5類對話內容的細分中可以發現,在感知性對話中引用最多,吸引注意和描述特征在數量上差異不大,命名相對較少。而在概念性對話中事實提問和解釋最多,較為高階的因果提問與推理對話則較少。此外,在概念性對話中猜測也占了相當的比例,這或許說明家庭對與大象相關的知識或大象科普長廊的展牌上提出的問題并不了解,故而廣泛使用了猜測性的語言;同時他們也對動物可能出現的行為做出一定的預測(見圖3)。
在聯系上,聯系動物、聯系先前知識、聯系先前經歷三大對話間彼此差異不大。父母聯系先前經歷的對話相對孩子較多,有較多家長都提到了之前看過的相關電影。例如10號親子團體母親與女兒的對話:
媽媽:這個猛犸象是《冰河世紀》動畫片里的長毛象。
女兒:對,胖胖的象。
媽媽:它還在里面泡澡呢,在泥池里面,它跟佩奇一樣也喜歡踩泥坑!
女兒:哈哈哈!
生物性對話主要以描述大象的行為為主,而與棲息地以及動物保護相關的對話極少,其中孩子幾乎沒有與棲息地相關的對話。以下是分別為5號親子團體與6號親子團體的有關動物保護的對話:
女兒:我覺得人類很壞。
女兒:為什么要造這樣的動物園呢?
媽媽:供你們小朋友那個呀,近距離的接觸,要不然去哪里看到這些動物呢?
媽媽:但是呢,有些動物可能還是放在大自然中更好,失去自由了。
兒子:大象現在已經……野生動物現在都已經是保護類動物了
媽媽:對,大象也需要保護啊!
兒子:大象也是野生動物,所以它也是保護動物,現在看來。
在情感性對話上,我們發現積極的情感性話語較少,而消極與驚訝的情感性話語較多,主要包括在參觀科普長廊過程中對科普問題答案、展示模型、場館環境的相關情感表達,例如“哇,始祖象……哇,這個是爸爸”“這太出乎意料了”“我的媽呀,相差這么大”“這個樣子好奇怪啊……這個好恐怖”“我覺得人類很壞”。
對家長與孩子的對話內容進行對比分析,可以看到在吸引注意力上,家長對話數量幾乎是孩子對話的2.5倍;在引用、事實提問和解釋上,家長對話也較為明顯地大幅度多于孩子,結合對親子家庭對話過程的分析,可以發現在參觀科普展牌的過程中,更多地是由父母引用展牌上的問題向孩子進行提問,并對其上的知識點進行朗讀解釋;在行為上,同樣是父母對于大象行為的描述較多,這可能與孩子的視野有一定的關聯;在情感上,孩子的消極情感和驚訝情感均遠遠多于父母;而在描述特征、命名、因果提問、動物保護、聯系動物、聯系先前經歷等方面,家長與孩子的對話差異不大。
3.2 親子團體在參觀動物園過程中的對話模式
結合先前學者的親子對話模式的研究成果,在對本研究的15組親子團體對話進行深入分析后,我們從家長和孩子引起談話的話語輪數分析杭州動物園內的親子對話模式:如果一方引起對話的輪數遠大于另外一方,則說明他在對話中有更高的積極性,引導并推進著整個對話。
本研究將由一方引起的、聚焦于同一個話題的對話片段記為一輪話語。在一個家庭的所有親子對話中,若家長引起的談話輪數高于由孩子引起的話語輪數(雙方話語輪數差>3),則將親子對話模式列為家長引導型。若孩子引起的談話輪數高于由家長引起的話語輪數(雙方話語輪數差>3),則將親子對話模式列為孩子引導型。若家長引起的談話輪數與孩子引起的話語輪數差≤3,則將親子對話模式列為平等互動型。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引導型占比最高,達到60%;平等互動型占比33%;孩子引導型最少,占比僅為7%。
(1)家長引導型對話模式
以下為兩個典型的家長引導型對話模式的親子團體對話:
媽媽:你看,它的象牙好長。
媽媽:它的象牙是不是和年齡有關系啊?年紀越大,象牙越長?
兒子:應該吧。
媽媽:那為什么剛才那頭大象沒有象牙?
兒子:砍了唄。
媽媽:這么殘忍?
兒子:……(沉默)
在以上11號親子團體母親與兒子的對話中,這位母親先是吸引孩子注意大象的象牙,以及不斷地拋出問題,試圖引起和孩子的互動。然而孩子對于母親所談論的話題并不感興趣,對媽媽提出的問題,回應得較為敷衍消極,并沒有真正參與到與母親的互動中,最后母子雙方也草草結束了對話。在這樣的過程中,孩子和家長雙方其實都對于大象的象牙缺乏更加深入的認識。
爸爸:野生大象有牙齒嗎?
女兒:有。
爸爸:一般野生大象沒有牙齒,野生的大象沒有牙齒了。
爸爸:野外象群有首領,一般誰擔任?
女兒:雄象。
爸爸:年長的母象誒!
爸爸:大象怕曬嗎?
女兒:不怕,因為它們有耳朵。
爸爸:怕的,它們會用沙土,給自己防曬是不是?
女兒:那是它的防曬霜吧!
爸爸:大象有幾個腳趾,亞洲象有幾個腳趾?知不知道?
爸爸:想想看,你猜猜看,5個,我們猜5個好不好?(看展牌答案)猜對了。
爸爸:壽命我看過了,67歲,我們剛才不是看到過了呀,對不對?好,我們在這邊其他地方再看看。
在13號親子團體父親與女兒的對話中,父女兩人對于“大象冷知識”展牌上的問題進行了討論。主要是父親在朗讀展牌上的問題,女兒對問題進行回答與猜測。當女兒無法回答“大象有幾個腳趾”時,父親采用讓女兒猜的方式,試圖引導女兒說出答案。但是女兒并沒有做出回應,最終由父親直接翻看展牌,結束了對話。這說明在“大象冷知識”展牌的討論中,部分家長有時會忽視“冷知識提問”背后的動物學知識與科學推理,雖然以閱讀展牌、提出問題來引導與孩子之間的對話,但是卻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對孩子興趣點的關注,以及未能進一步啟發孩子的思考,因此親子團體的對話仍停留在答案本身,未能很好地促進孩子的科學推理能力的發展。
(2)孩子引導型對話模式
以下為一個典型的孩子引導型對話模式的親子團體對話:
女兒:大象嘴里有幾顆牙齒?
爸爸:我想應該只有兩顆吧。
爸爸:對。
女兒:因為它外面漏了兩顆,(翻開看)四顆。嘴巴里面還有兩顆。
爸爸:長在里面的。
女兒:大象靠身體什么部位接受聲波?
爸爸:它是通過什么來聽聲音?
女兒:嗯,應該是耳朵吧。
爸爸:打開看一下,耳朵和腳掌。
女兒:大象一生換幾次牙齒?
爸爸:人是幾次?
女兒:人好像亂換。
爸爸:是一次嗎?換一次,會不會?
女兒:換一次,那大象應該是也換一次。
爸爸:六次。
女兒:我天,要換六次。
在以上1號親子團體的對話中,這對父女兩人同樣針對于“大象冷知識”展牌上的問題展開了討論。其中主要是孩子在閱讀展牌,提出問題。對于孩子的提問,父親有時并沒有立即回應,而是以回問的方式引導孩子做出回答,推進了對話。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主要是孩子在提問,但是父親也很好地聚焦于孩子的興趣,以回答、回問、猜測等方式積極地回應孩子的提問。
(3)平等互動型對話模式
以下為一個典型的平等互動型對話模式的親子團體對話:
女兒:媽媽,那是喝水的地方嗎?
媽媽:應該是吧。
女兒:可是我覺得……
媽媽:大象是不是也喜歡在水里面?夏天的時候。
女兒:大草原里面的大象,一般有那種就是喝水的地方,就是這樣。
媽媽:嗯,主要沒吃的給它。
媽媽:它跑起來了!
女兒:成年大象能跳躍嗎?
媽媽:感覺應該很笨重啊它。
媽媽:它把鼻子翹起來。
女兒: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大象在同時跳了一下,肯定地球都要地震了。地球的各個地方都要地震的。你說呢?你說呢?
媽媽:然后地殼會震一震。
女兒:好恐怖啊。
在以上5號親子團體的對話片段中,母女對于大象場館的水池、大象的動作(跑、跳躍)進行了討論。女兒通過提問,吸引母親對于水池的注意,隨后他們討論了大象水池的作用,期間母親打斷了女兒想說的話。后來女兒聯系了野外大象的生活情況,分析動物園內的大象水池的作用。總體而言,他們對于大象水池有較為積極的討論與回應。在母親引發有關大象動作的話題時,女兒也聯想到了其他問題,與母親進行了探討。女兒猜測世界上所有大象同時跳躍的后果是地球地震,母親表示贊同。然而該假想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下,因為成年大象并不會跳躍。分析母女雙方的互動情況,可以發現家長和孩子都能夠聚焦于彼此提出的話題,進行激烈的討論。然而,對于孩子的提問,我們可以發現家長有時候由于知識水平的限制,無法給予正確的回答。
4 討論
4.1 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
本研究根據先前學者的編碼方案結合本論文的研究內容確定了感知性、概念性、生物性、聯系性、情感性5類對話,并對于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的進行了統計分析。
在感知性對話和概念性對話方面,數據顯示,親子團體的概念性對話比感知性對話更多。此外,在概念性話語中,事實提問、解釋、猜測的話語在其中占比較大。這與國內先前在自然博物館、科技館開展的親子團體對話研究中發現的“親子間發生的感知性對話較多,而概念性對話比感知性要少”的結果存在一定出入[25-27]。我們對該結果可能出現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與推測,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大象館區的大象科普長廊為家長和孩子提供了充足的腳手架的支持。正如Tare的一項對進化展覽上的親子團體對話的研究所示,在非正式的教育環境中也存在復雜的談話,實質性的解釋性內容在家庭談話中占主導地位。其中大量討論來自于展覽文本,家長除了閱讀展牌外,會提出問題并提供解釋[28]。由于大象科普長廊專門設有大象知識提問墻,家長與孩子常據此展開相關知識點的提問與解釋,引發了較多概念性的對話。此外,相對于感知性對話,概念性對話并不一定意味著發生的學習更加高階。事實上,此次編碼中部分概念性對話反映出親子團體在動物園內的學習仍停留在淺層次,且存在大量與客觀知識不相符的對話。
在生物性對話方面,親子團體的生物性對話主要是描述大象的行為,較少涉及棲息地以及動物保護方面,尤其是孩子幾乎沒有與棲息地相關的對話,這與我們的預期差距較大。這也表明家長和孩子在動物園內的學習以觀察動物,簡單了解動物的特征、習性與行為為主,較少涉及到野生動物的生存現狀與動物保護的重要性。結合科普展牌內容,我們發現大象長廊中有關動物保護等方面的內容較少,未能很好地引導親子團體對動物保護相關話題的關注。因此我們認為動物園應該不斷提高科普展牌質量,豐富并突出動物保護的相關內容,設置非純粹知識性的開放性提問,激發參觀者對于相關話題的討論。
在聯系性對話方面,聯系先前經歷和聯系先前知識的對話所占比例相對較高,這與鄧卓、郭子葉等人在博物館的研究結果一致。其中,家長比孩子更多地聯系了先前經歷。在情感性對話方面,我們發現,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中,情感性話語占7.8%,其中積極情感的話語占22.2%,這反映出了在動物園的大象場館內,積極的情感對話總體而言并不常發生。在大象館的親子團體的對話中,大象本身的臭味引起參觀者的反感、象足模型被誤解為截肢象足導致孩子出現恐懼心理、參觀者對于圈養大象表示出的同情是較為高頻的消極情感。
4.2 親子團體的對話模式
本研究統計了家長和孩子引起的談話話語輪數情況以及家長和孩子對對方提問與解釋的回應情況,對親子團體的對話模式進行了探究。其中,親子對話模式為家長引導型的親子團體最多,平等互動型的其次,孩子引導型最少。過去有研究顯示,在博物館的親子互動中,雖然這種親子互動可能是“流動”的,但父母可能比孩子表現出更多的“展示-說話”行為,他們往往扮演著教師的角色[29],通過自己的言語來支持家庭的學習。家長在非正式活動中的策略可能類似于教師在學校的行動,通過問更多的事實問題讓孩子參與對話,并評估他們對于某個主題的了解。
Palmquist與Crowley的研究發現,如果是對于參觀主題有一定了解且感興趣的“專家型”孩子,在博物館內更像是一個信息闡釋者,而他們的父母往往會是沉默的參觀陪伴者。對于那些“新手型”的孩子,父母會更像一個學習伴侶[30]。本研究中,由于大象科普長廊的內容更易被家長所理解,更增強了父母作為在動物園情境下的“教師”的可能性。這也說明父母在非正式場所的學習中是扮演一個講解的教師、沉默的陪同者,還是孩子的學習伴侶,其實與較多因素有關,例如家長和孩子對于參觀主題的知識掌握程度與興趣、作為腳手架的展板內容與形式對于家長和孩子的友好性等。
5 總結與建議
本研究將動物園中的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分為了感知性、概念性、生物性、聯系性、情感性對話,通過對于15組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分析,我們發現在動物園的大象場館中,親子家庭團體的概念性對話比感知性對話更多,其中引用、事實提問、解釋、猜測的話語較多,這可能與動物園大象場館的知識長廊(尤其是“大象冷知識”提問展板)為參觀的親子團體提供了“腳手架”有關。而生物性對話在親子團體的對話內容中占比較少,很少有家庭涉及到動物保護與動物棲息地的討論。意外的是,情感性對話,尤其是積極情感的表達在動物園內的親子團體對話中也并不常見。本研究根據親子對話輪數的差異,將親子團體對話分為家長引導型、平等互動型和孩子引導型。其中家長引導型的對話模式親子團體最多,平等互動型略少于家長引導型,孩子引導型對話模式的親子團體最少。
基于以上發現,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建議:
(1)動物園要不斷優化場館,增強科普展牌與導賞設施對于兒童的友好性。一方面,動物園在設計科普展牌內容時,應考慮到兒童的認知發展水平,結合兒童閱讀的偏好性,使科普展牌的信息呈現方式更易為孩子所理解。如運用動物的語態進行科普說明,對一些偏僻詞匯標注拼音與解釋等,從而更好地吸引兒童的興趣,使其更具親切感和代入感,便于兒童自主閱讀;另一方面,針對多組家庭反映的觀賞圍欄過高,影響小孩觀看視線,部分小孩甚至完全看不到大象的情況,本研究認為動物園需要在保障觀賞安全性的同時,充分考慮兒童身高的特殊性,為兒童提供更多看到活體動物的機會,例如在圍欄的外圍間隔提供觀賞臺階等。在知識展牌與長廊設計中也同樣需要考慮到兒童身高問題對其閱讀科普展牌舒適度和積極性的影響。
(2)動物園應提高科普展牌內容質量,適當設置除知識性外的開放性問題,以促進人們對于動物保護內容的討論,豐富其在動物園內的情感體驗。動物園肩負著保護與教育的目標,相較于其他博物館,生物性對話是動物園更有可能產生的對話,即通過活體動物的參觀與科普知識的學習,促使游客增長對動物生存狀況與保護情況的認知。然而上文研究顯示,親子團體的生物性對話主要是描述大象的行為。家長和孩子在動物園內的學習仍然以觀察動物,簡單了解動物的特征、習性與行為為主,較少涉及到野生動物的生存現狀與動物保護的重要性。事實上在大象場館的科普中,包含傳統普通展牌和大象科普長廊,其中有關動物保護的開放性、引導性和思考性問題均較少,更多地是知識輸出和知識傳遞。因此動物園應該不斷提高科普展牌質量,豐富并突出動物保護的相關內容。
(3)動物園應對游客在參觀過程中的討論內容與情緒感受予以重視與回應。除針對動物本身產生的情緒外,場館整體環境衛生、大象生活設施、科普展牌等系列設置也會影響親子團體的參觀感受。因此動物園應重視游客在參觀過程中的情感體驗,通過優化場館布局設置等對游客的情感予以注意與回應,不僅可以為動物提供更好的生活福利,也能夠為游客帶來更積極的參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