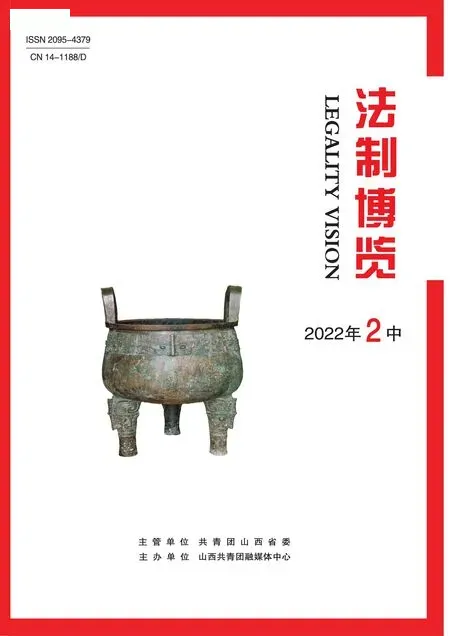“斷卡”行動中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司法實務適用難點及出路
李曉婷 樊豐琴
山西省太原市迎澤區人民檢察院,山西 太原 030000
網絡信息技術日益先進并被廣泛應用到人們的生活中,但在其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網絡犯罪也隨之而來,其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是持續高發的網絡犯罪情況。但對于網絡犯罪分子來說,其犯罪收益的占有和享用的必經途徑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因此網絡詐騙犯罪逐漸演化為層級嚴明、分工明確的產業鏈,引發許多幫助違法犯罪的活動,如替人開卡、取錢車手、碼農、販賣多卡合一等服務。2020年10月,根據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的決定,“斷卡”行動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嚴厲打擊各類電信網絡詐騙及收購販賣電話卡、銀行卡等違法犯罪活動,全力斬斷“兩卡”販賣產業鏈條,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切實維護社會治安大局穩定。根據最高檢數據顯示自專項行動以來,重點打擊專門從事非法收購、販賣“兩卡”的人員,共起訴8000余人,在懲治網絡犯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筆者根據公開文書統計分析及與承辦人員案件討論過程中發現,涉“卡”人員的構罪標準、罪名認定、一罪數罪認定等問題五花八門,最終導致同案不同判、打擊力度不夠、擴大解釋司法解釋等問題。為此筆者擬以辦案中的案例入手分析不同行為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的構罪標準、罪名選擇以及一罪或數罪的認定問題,進而探究公安機關在辦理該類案件的偵查取證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及各司法機關進一步強化打擊力度的途徑。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追訴標準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為維護網絡秩序,懲治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犯罪,維護正常網絡秩序,出臺了《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十二條①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幫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一)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二)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三)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四)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五)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六)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七)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實施前款規定的行為,確因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查證被幫助對象是否達到犯罪的程度,但相關數額總計達到前款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五倍以上,或者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應當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針對“兩卡”犯罪的追訴標準作出明確的規定,但關于該條解釋的適用問題在司法實務中同樣產生分歧,下面以具體案例說明。
案例一:B通過網絡聯系其上線A得知以1000元的價格收購銀行卡、電話卡,后B找到其朋友及親戚C、D、E以500元的價格購買十余張銀行卡、電話卡,經公安機關查證后,C、D、E名下賣出銀行卡交易金額流水分別共計120萬、60萬、300萬,三人的非法所得均不足10000元,但報案被害人被騙錢款流向僅經過C、D名下的銀行卡賬戶。在該案中根據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E的行為是否構罪?部分案件承辦人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實E的銀行卡資金系違法犯罪錢款,故不宜認定構罪。但在此處,筆者認為應適用上述解釋的第二款規定,認定E的行為構罪。電信網絡犯罪多因地域性、網絡隱蔽性等特征無法一一查實被害人,從該司法解釋的本意來看,也是針對網絡犯罪的特性才規定了第二款,故雖然現有被害人報案損失的錢款中沒有流經E的賬戶,但E將銀行卡賣給他人使用并有大額資金流水,明顯異于常理,其同期被賣的卡確實用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從行為的主觀故意到客觀危害性均符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構罪標準。
案例二:行為人A與B從網絡廣告中得知上游C犯罪集團租用銀行卡用于洗錢,并與C商定以資金流水金額3%為傭金,后A與B到C所在地將銀行卡、手機卡交給C,C租用一天后將5000余元交給A、B,后查明,當天未使用A的銀行卡,僅使用B的銀行卡,B銀行卡轉進、轉出資金共計34萬余元。多名被害人報案因電信詐騙被騙金額共計12萬余元,資金全部流經B銀行卡。該案的爭議焦點在于B是否構罪。一種觀點認為根據1997年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支付結算辦法》第三條的規定:“本辦法所稱支付結算是指單位、個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所使用票據、信用卡和匯兌、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結算方式進行貨幣給付及資金清算的行為”,支付結算金額,應包括轉進和轉出,故B的銀行卡支付結算金額超過20萬,符合上述解釋的規定。一種觀點認為支付結算金額不應作擴大解釋,只能單向計算,轉出或轉入,因此支付結算金額不足20萬,不構罪。因上述兩種觀點的對立性,有的檢察官提出,根據證據顯示,有多名被害人被騙金額12萬,超過電信詐騙數額巨大的標準,應適用上述解釋第六項“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的解釋,B的行為構罪。在2021年6月22日,兩高一部發布了《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二)》中,對上述解釋中的第七項規定的“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也作出明確規定,“收購、出售、出租信用卡、銀行賬戶……5張(個)以上的;收購、出售、出租他人手機卡……20張以上”。根據該規定B的行為也不符合構罪標準。但筆者認為上述第三種意見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從案例中可知B的主觀惡性、明顯不合理的交易價格、客觀危害后果等,B的行為確實符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構罪要求及立法本意。同時“支付結算金額”本就是金融領域的專有名詞,根據《支付結算辦法》的解釋也符合對法條的文義解釋,故無論適用第二項還是第六項均足以證明B的行為構罪。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中“明知”的認定問題
認定行為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條之二的規定中必須以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前提,同時在上述司法解釋的第十一條也列舉了認定行為人明知的幾種情形①(一)經監管部門告知后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二)接到舉報后不履行法定管理職責的;(三)交易價格或者方式明顯異常的;(四)提供專門用于違法犯罪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術支持、幫助的;(五)頻繁采用隱蔽上網、加密通信、銷毀數據等措施或者使用虛假身份,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的;(六)為他人逃避監管或者規避調查提供技術支持、幫助的;(七)其他足以認定行為人明知的情形。,但在司法實務中關于行為人的明知認定仍有分歧。案例一中經偵查查明,A又讓其老公F辦理了兩張銀行卡,F名下銀行卡資金流水100余萬元,C也讓其老婆G辦理了兩張銀行卡,并交給A,G名下銀行卡資金流水金額合計100余萬元。A、F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相互印證,證實F不知A將銀行卡轉賣的事實;C、G的訊問筆錄相互印證,證實C僅告知辦理銀行卡讓A用,幫忙走賬。A、B、C、D、E的訊問筆錄均證實上線稱是公司走賬需要用銀行卡。上述5人的訊問筆錄雖未供述其明知,但根據5人供述的以500~1000元的價格購買一張銀行卡的事實,適用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第(三)項,可以認定5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但案例中關于F、G能否認定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呢?雖然在辦理銀行卡時銀行明確告知銀行卡不得轉租、借用,但僅以此不能單一適用解釋第十一條第(一)項認定二人明知,鑒于二人與A、B的特殊夫妻關系,結合一般人的認知水平,應采信F、G的證言,對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無法預知和明知。故在本案中不宜認定F、G構罪。
三、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罪名選擇及一罪、數罪的問題
為上游犯罪提供銀行卡進行支付結算幫助,可能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也可能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但兩罪量刑差異比較大:幫信罪最高刑為三年,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最高刑為七年,因此,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準確定罪量刑非常重要。司法實踐中,往往因為偵查機關的取證程度、法院的證據采信等導致同種行為被認定為不同的罪名。
案例三:行為人A通過網絡得知上線一網絡犯罪洗錢平臺收購銀行卡、電話卡,后A通過網絡從下線人員處收購了大量的銀行卡、電話卡,并將收購的銀行卡、電話卡一部分交由上線使用,一部分留下并根據上線的要求實時轉賬。案發后偵查機關從A處查獲了大量的“兩卡”及A收購“兩卡”的下線,根據查證的銀行資金流水情況,A處查獲的“兩卡”中資金流水中有5萬元系被害人報案金額,同時查明A收購的轉交上線的銀行卡中資金流水金額上千萬。根據本案的證據情況,足以認定A的行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件的焦點問題在于A留下的部分銀行卡進行操作轉賬的行為應認定為什么罪?其兩部分行為是一罪還是數罪的問題?在202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修改了《關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將“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3000元至10000元以上的”這一構罪標準刪除后,部分檢察官認為因新修改司法解釋無法認定A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部分檢察官認為雖然司法解釋刪除了該規定,但實質是加大對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打擊力度,應認定A的行為構罪。但即使認定A這一部分行為構罪,那關于其轉賣的部分“兩卡”該如何認定,仍有爭議。部分認為應該數罪并罰,分別評價;部分認為只能認定為一罪。
筆者認為,A的兩部分行為應分別認定,數罪并罰。幫信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雖然在主觀明知、行為方式、行為對象等方面均有區別,但筆者認為在“兩卡”犯罪中,區分二罪的重點在于行為對“兩卡”是否進行操作。如進行操作轉賬則應當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如僅是買賣、出租則認定為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案例中A的行為不論從其主觀惡性還是社會危害性都比較大,從客觀行為來看,其行為并不是想象競合的問題,而是多個行為觸犯多個罪名的認定。
四、針對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偵查機關偵查取證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注意固定關于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言辭證據。現在雖然銀行等金融主管機關在行為人辦理銀行卡的過程中會簽署相關銀行卡不得轉借、出租的承諾書,同時會口頭告知行為人。但關于明知不能僅以此來認定,必須全面、客觀地收集能夠認定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所有證據,此外還要結合一般人的認知水平和行為人的認知能力,調取相關不能認定行為人明知的證據。
(二)注意調取行為人銀行卡交易流水等書證的合法性、客觀性。司法實踐中,因“兩卡”犯罪的跨地域性,偵查機關在調取銀行卡流水書證時比較困難,因此有的偵查機關將公安機關內部的數據平臺上打印下載的銀行交易情況作為證實行為人銀行卡資金結算情況的書證。該書證的合法性和客觀性往往在庭審過程中受到辯護律師的質疑。關于公安機關內部數據平臺的證據能否作為證據使用、證據的證明力等問題,需進一步探究。但筆者認為該數據平臺數據可以作為偵查機關的偵查手段,要認定行為人涉嫌犯罪仍需盡可能向銀行等有權機關調取原始、全面的書證,保證證據來源的合法性、真實性。
(三)注意加強對“兩卡”犯罪取證的跨區域協作。司法實踐中,部分行為人往往因為經偵查機關取證資金流水超過20萬未達100萬,但查證的轉賬流水中無被害人報案,無法認定行為人構罪。因此偵查機關應加強同其他地區偵查機關的協作取證,加強資金交易情況的數據比對,盡可能對應相應被害人,做到嚴厲打擊“兩卡”犯罪。
五、不斷提高司法辦案能力,嚴厲打擊“兩卡”犯罪
“兩卡”犯罪手段不斷翻新,由最初的銀行卡、電話卡已升級為支付寶、微信等網絡支付賬號,還有的已進一步升級為有價網絡游戲幣、比特幣等虛擬貨幣,雖然一年來,打擊“兩卡”犯罪成績明顯,但辦案現實也對我們司法辦案機關及司法辦案人員提出諸多的挑戰。為嚴厲懲治“兩卡”犯罪,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態勢,切實維護社會治安大局穩定,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不斷強化。
(一)強化人才培養和運用
新型“兩卡”犯罪更加依托計算機網絡,因此對偵查、檢察、審判人員的計算機網絡水平也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司法實踐中該類犯罪的電子證據海量、分布廣、收集難度大,這就要一方面要用好現有司法技術人員,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現有辦案人員的計算機網絡水平,只有這樣才能運用高科技對現有的海量數據進行準確提取、認定及運用。
(二)完善、統一各司法機關之間關于“兩卡”犯罪的證據標準
新型網絡犯罪在方式和手段上都是新花樣,給司法機關適用法律的準確性帶來極大挑戰,上述案例中也因證據認定標準不統一,不同承辦人、不同司法機關對相同案情的處理結果產生分歧,從而導致司法權威一定程度上受到影響。部分犯罪嫌疑人鉆了司法的空當。目前僅有吉林省公安廳出臺了《吉林省“斷卡”行動法律適用問題及建議》,該建議也僅適用于公安機關內部,未與檢察機關、法院聯合制定,統一標準。因此針對該類犯罪各地區有必要完善、統一各司法機關之間的證據標準,探索聯合出臺相關的辦案證據指引等文件。
(三)加強法治宣傳,從根源上遏制“兩卡”犯罪
一方面強化涉嫌“兩卡”犯罪的指導性案例和普法宣傳案例的發布,通過“以案釋法”,增強社會公眾的防范意識和法治意識。另一方面,各司法機關應嚴格貫徹“誰司法誰普法”的要求,承擔普法職責,加強與行政管理機關的聯絡,強化“兩卡”犯罪的普法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