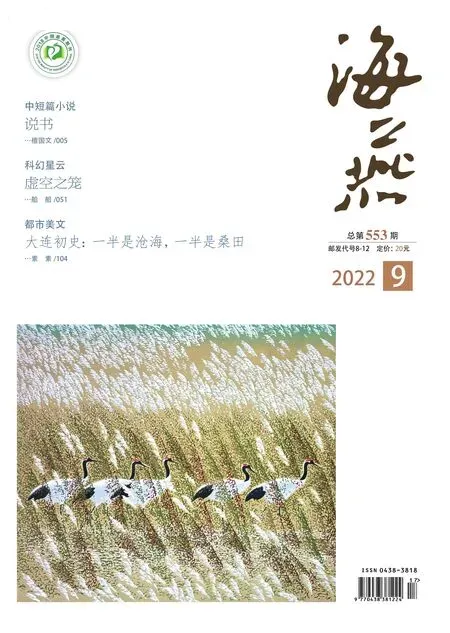大連初史:一半是滄海,一半是桑田
文 素 素
一、從龜裂石說起
從世界地圖上看中國,狀似一只雄雞,遼東半島似尖尖的喙。此刻,喙正閑著,不左觀右望,亦不低頭覓食,好像在靜等破曉而啼。
其實,從亙古開始,遼東半島更多的時光是混沌和荒涼。相對于漫長的地質演化史,遼東半島不過是某一次地質演化之后的短暫定格,正巧被今人遇見。
我居住的城市大連,在遼東半島南部,也就是雄雞的喙尖。左邊一個黃海,右邊一個渤海,南邊一個山東半島,東邊一個朝鮮半島,大連與遼東半島被夾在中間。與內陸城市相比,大連地理有一種難以復制的辨識度。自古以來,這里就是海上航線必經之處。自古以來,這里就是一個歷史過道。而且,大連從古代到近代發生的一切故事,都與它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
正因為如此,我要占用一章的篇幅,說說遼東半島的滄海桑田。也許離題太遠,但對于文化稀薄歷史并不雄厚的大連而言,這一章卻不可或缺,也無法繞過。
許多年前,我曾走近過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已經在黃海岸邊站立了6億年,以地球史有46億年計算,似乎不算什么,剛剛占了一個零頭。但是,記得那天,不遠處就是潮汐鼓噪,而它一直斜斜地靜臥在那里,當我弄懂了該石頭從何而來,姓甚名誰,它便突然激發了我對地殼變遷的興趣,對鄉土地理的好奇。
石的質地呈赭紅色,表面布滿了巴掌大小的淡綠色網格,看著就像上蒼之手畫出的謎語。石旁有個標牌,說它來自震旦紀,因狀似龜甲,被稱為“龜裂石”。它的樣子,既讓我感到陌生,也讓我充滿好奇。
于是,龜裂石成了一個標本,一塊敲門磚。我就此知道,在鴻蒙未開時代,地球大部被海水覆蓋,無數的微陸塊,如幽靈一般,在無際的水面上碰來撞去,胡亂地拼接著,無主地漂移著。
直到35億年前,“華北島”如一顆上蒼賜予的石質胎盤,成為中國這只方舟最原始的陸核。而25億年前的一場“鞍山運動”,驚醒了蟄伏在水下的遼東古陸,使它從海底褶皺里轟然隆起。自20億年前開始,則以“呂梁運動”為代表,地球時不時就會來一次或大或小的山顛海覆,而在無數的跌宕起伏中,遼東半島始終是遼東古陸甩不掉的小尾巴。當地球幽幽轉動到了10億年前,又因為一次劇烈的地殼下陷,讓遼東半島有長達4億年淹沒在親親老家般的海水里。6億年前,它才隨著地殼緩慢抬升,光鮮如美女出浴,得見藍天麗日。也是自那一刻起,大自然以時光為斧,鏤刻出這塊沉默如金的龜裂石。
然而,在這片海岸,龜裂石并不孤獨。漫長的6億年間,又發生過許多次地殼運動,許多次海陸交替。因為這里是震旦紀喀斯特地貌,因為堅固的巖體或被一次次地殼波動碾壓斷裂,或被億萬年的大風和海浪沖擊變形,最后化成了各種生動怪異的鬼斧天工:恐龍探海、貝多芬頭像、鰲灘、玫瑰園、七彩虹霓......
曾有一位藝術家在海邊駐足說,這是神力雕塑的公園。我卻有點心疼,這些崎形怪狀的巖體,不過是某一場地質運動的遇難者,一些被地殼遺棄的無用的邊角余料。只是,當龜裂石與伙伴們抱團取暖似的擁擠在這片海岸上,竟意外獲得了另一種永生。
在我眼中,龜裂石是地球史上的但丁。
震旦紀是隱生宙最后一個紀,寒武紀是顯生宙第一個紀,龜裂石恰好站在兩個宙之間。石面上那些神秘如天書的網格,我給看成了隱生宙的休止符,顯生宙的預言。如果隱生宙是柳暗,顯生宙就是花明。
事實證明,顯與生,皆拜太陽所賜。5.4億年前,地球一不小心被這位天外來客捕獲,從此以后便郞才女貌,天作之合,不離不棄,你儂我儂。顯生宙有三個代:古生、中生、新生。故曰,生命之宙。就是說,顯,即是生。
不過,太陽雖然把地球照亮了,催成了生物大爆發,卻也隨之帶來了生物大滅絕。而且,天地失色、萬劫不復的大滅絕,竟連著發生了五次。好在,龜裂石是石頭,不是花草,它一直乖得像塊狗皮膏藥,緊緊黏在遼東半島身上,從未失聯。所以,它不但看見過侏羅紀恐龍怎樣成為巨無霸,也目睹了它怎樣給那顆撞入墨西哥灣的小行星作了殉葬。
小小一塊龜裂石,竟以本自具足的神性,活得比恐龍還長壽。我想,它之所以穿越6億年時空,以6億年篤定,深情地等候在這里,就因為它相信總有一天,會與后天來到的人類相見。
卻沒想到,人類來得那么晚。
二、膠遼古陸的沉浮
在大連的地質履歷表上,可與龜裂石等量齊觀的風景,還有膠遼古陸。有人說,它形成于6億年前的震旦紀,也有人說,它形成于7萬年前的大理冰期。
或許都有道理,膠東半島屬于華北古陸,遼東半島屬于遼東古陸,膠東與遼東,打斷了骨頭連著筋,比鄰而居的兩個半島,不知有多少次拉勾上吊,直到貢獻出一個這么婉約,又這么雄渾的地理名詞:膠遼古陸。
莊子《逍遙游》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這是個由魚化鳥的上古神話,一條三千里長的大魚,因為向往自由,突然在海里待不住了,變成了一只扶搖九萬里的大鵬。莊子說了,他引述的神話出處有二,一個在《商湯問棘》,一個在《齊諧》。莊子之所以搬過來用,就為了抒己之志,為了無束無止的自由。
神話里的北冥,其實就是渤海,趕上冰期,縮成了一個湖。正因為如此,《逍遙游》不只是一篇道家經典,還是一部膠遼古陸秘史。
當然,不論是6億年前,還是7萬年前,膠遼古陸只要出現,一定是冰期來了。幾十億年地球史,不知發生過多少次大冰期,每一次生物大滅絕,都會降臨一次大冰期,怎么知道膠遼古陸不是在震旦紀那一次大冰期橫空出世的呢?
地球上最后一次大冰期,發生在新生代。
第三紀最大的事件是造山運動。喜馬拉雅原本是海洋,竟一點點長成了地球第三極,華北古陸原本是平川,東緣這一角竟慢慢凹出個渤海。
第四紀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大冰期。雖然長達260萬年,卻并非鐵板一塊,分四次冰期,四次間冰期。基本畫風是這樣的:冰期一到,膠遼古陸就要升起,渤海就退成了湖,黃海則退成了大平原;間冰期一來,膠遼古陸就要下沉,渤海湖和黃海大平原復又汪洋一片。海陸變身,冷暖交替,演得如川劇里的變臉。
四次冰期最后一次,叫大理冰期,時間在11萬年至1萬年前,不但氣候一直寒冷,還曾有過兩次極寒。
第一次在7萬年前。渤海水面下降了50多米,變成了一個內湖,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全都露出海面,白茫茫一片膠遼古陸真干凈。
第二次在2.2萬年至1.5萬年前,寒值遠遠超過了前一次。冰川厚如危崖,海面直降140多米,山東半島、遼東半島、朝鮮半島與日本列島無縫對接,朝鮮海峽、對馬海峽、津輕海峽、宗谷海峽、韃靼海峽、白令海峽、楚克奇半島與阿拉斯加十指相扣。

這也就是為什么說,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這也就是為什么說,華北古人類是印第安人的祖先。
第四紀是冰河紀,也是人類紀。有一個說法讓人類很沒面子,就是把46億年地球史換算成一天24小時,人類在最后3分鐘才登場。其實,人類要是知道地球到處冰天雪地,寒風凜冽,也許還覺得來早了呢。
膠遼古陸,仿佛是天造地設,給遲到的古人類鋪就了一條遷徙通道。高丘深谷,悉如女人胴體,整個東北亞都赤裸在地平線上。于是一支支古人類便被動物吸引著,誘惑著,義無反顧地離開華北,向東北亞大陸走去,向北美大陸走去。
彼時,在古陸上如如不動的龜裂石,應該目睹了這樣的場面:那些不倦遷徒著的古人類,曾經路過它身邊,或靠著它避風歇息,或停下來撕吃捕獲的動物。冰天雪地里,龜裂石給過他們一只手的溫暖,因而讓他們走得更遠。
也有留下不走的。他們也是古人類,或者說,他們是大連最早的先民。
據《大連通史》載,在遼東半島現身的古人類,大致有兩個來源,一是從遼河流域南下的金牛山人、廟后山人,二是從中原北上的山東半島人。其實,不如說他們都是在古人類大遷徙時代留下不走的人。
迄今為止,大連境內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遺址有兩個,一個在駱駝山,一個在古龍山。有意思的是,這兩座山都在我老家附近,這里過去叫復州,現在叫瓦房店。
在駱駝山洞穴內,出土了數萬件動物化石,其中劍齒虎和納瑪象,在東北地區是首次發現。專家說,駱駝山動物群與北京周口店動物群是同族,跟廟后山動物群反而不是近支。
在那堆化石層里,發現了疑似人工打磨的石制品,并且有疑似古人類燒過的咖啡色火塘。這個發現說明,駱駝山不是單純的古生物遺址,而是有古人類活動的文化遺址,時間在距今50萬年至20萬年。
就是說,駱駝山人的資歷,把金牛山人和廟后山人甩在了后面。當專家們把大連駱駝山與營口金牛山、本溪廟后山、喀左鴿子洞勾連起來,便畫出了一幅完整的中國東北遠古人類活動圖譜,看來看去,居然都與周口店山頂洞人有血緣關系。這說明華北古人類有的壓根沒走,有的走在半道不想走了,有的一鼓作氣走到底。留在東北的古人類,就是半道停下那一撥。
駱駝山在復州古城西南,山勢巍峨,其形如駝,故名。復州詩人張俸曾寫過一首《登駱駝山》:
萬丈云霄外,登臨意豁然。
聳肩思荷日,引手欲攀天。
滄海千尋浪,荒村數點煙。
東南遙望處,城郭小如拳。
但是,這么美的一座山,最終也沒留住駱駝山人的腳步。也許因為,他們在食物鏈上,靠追獵可食動物裹腹,動物離開了,他們就得離開,然后就忘了回來。
古龍山距駱駝山只有幾十公里,雖然也是舊石器時代遺址,時間卻近多了,距今只有4萬年至1.7萬年。
與駱駝山洞一樣,古龍山洞也出土了數萬件動物化石。當它們被拉到大連自然博物館化石庫,分門別類地擺放在開放式儲物架上,從美國和德國來的專家吃驚地問,這難道是從同一個洞穴里出土的嗎?回答是肯定的,它們都來自古龍山洞。
動物最多的是馬,而且是野馬。有200匹個體馬骨,6000顆馬牙,古龍山簡直成了它們壓倒性主場。而且,經過測定,這些馬是現在已經滅絕的獨特物種,與歐洲野馬是近親,反而和東北內陸的中國野馬親緣關系較遠,專家便給了一個命名:大連馬。
事情并沒有完。大連馬的馬骨和馬牙證明,它們正值青壯之年,死亡的原因不是自然淘汰,而是被人類圍獵捕殺,然后將它們全部拖進山洞并吃掉。專家由此推斷,古龍山人喜食馬肉,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狩獵集團,于是又給他們一個命名:獵馬人。
我曾專程去了一次大連自然博物館,并在庫房里看過動物骨化石。館里專家告訴我,他們當年發掘的只是一個岔洞,主洞已經被采石者炸沒了。從埋藏學的角度分析,這些動物骨頭是人類啃吃過的,唯一的解釋,就是他們住在主洞,把岔洞當作垃圾場。
古龍山獵馬人的蹤跡,消失于最后一次冰期結束之前。他們可真是果決,說走就走了。那一次次快樂無比的激情獵殺,一場場大快朵頤的饕餮盛宴,都被他們拋在腦后,只扔下一堆吃剩的動物骨頭,幾件剁肉用的打制石器,留給后面的人考古。
考古者當然知道,歷史更多的是混沌。面對那么多的說不清,那么多的暗角,只有盡可能的去尋找線索,然后在線索里打撈細節。
駱駝山人和古龍山獵馬人,就是這樣被打撈出來的。如果沒有他們,大連歷史是不完整的。因為有他們,這一段看似有太多空白的歷史,便具有了質感和別樣的生動。
三、稻作之路
近代地理學奠基人A.von洪堡認為,人是地球這個自然統一體的一部分。他的“人地關系”學說,隨后便成為一個著名的科學論題。
中國人也懂人地關系,在中國人嘴里,這么深奧的哲學問題,只用七個字就講明白了:一方水土一方人。
兩種觀點沒有高低,只是參照系不同。洪堡講的是地球和人,看得高遠,中國人講的是山水和人,更接地氣。
人與地,的確有一種天然的依存關系,地理是物體,人是物種。換句話說,地理是“皮”,“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左傳》里面說的。
大連地理之“皮”,就是遼東半島,但與膠遼古陸相比,遼東半島實在是太年輕了。《大連廣鹿島區域老古調查報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載:
地球上最后一次冰期結束后,氣候又逐漸變暖,海平面上升,最終形成了現在的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這樣的地理格局。
《大連通史·古代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載:
最后一次海進發生在距今9000年。在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黃渤海海峽及渤海地貌形態基本形成,遼東半島海侵達到高峰。
就是說,它成為半島是因為海侵停止在5000年前,然后形成了它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這樣一個格局。同樣,山東半島也是如此,于是才有了兩個半島如一道海上城墻,騎在黃海和渤海之間,讓渤海成了內陸海,讓黃海成了邊緣海。
寫到這里,我想用全能視角描述一下遼東半島。它其實是一脈欲斷又續的丘陵,近看是千山余緒,遠看是長白山末梢,如一柄鋒利的犁鏵,耕入浩瀚的黃海與渤海,并給它們劃出一條清晰的分界。
正因為遼東半島一脈青峰如脊,三面碧海環繞,形成了它獨特的天然肌理,那就是無所不在的曲線。
豎著看它,山是波紋樣的,北境的老帽山,中部的大黑山,南端的老鐵山,一波三折,凸凹有致,給半島帶起了性感的節奏。
橫著看它,岸是游蛇樣的,半島兩翼的黃海岸和渤海岸,像從老鐵山手里放出去的兩根風箏,一根飛落到遼河口,一根悠揚到鴨綠江口。
這兩根風箏線,長達2000多公里,線上還冰糖葫蘆般串著無數個海灣,一個海灣,就是一個漁歌唱晚的碼頭。最有名的一個,叫大連灣。后來,大連就成了半島城市的名字。
距半島海岸不遠處,還有數百座島嶼,它們就像一不小心從遼東半島項下扯掉的祖母綠珠子,星散在黃海和渤海的深藍里。這些大大小小的島嶼,還有另一個稱呼,離島。
一個離字,道盡悲歡。歲月靜好時,卻發現是天賜之美。
距陸地最近的一個離島,叫廣鹿島,屬于北黃海長山群島一員。從上個世紀初開始,中外專家就在廣鹿島作了一個世紀的考古。《大連廣鹿島區域老古調查報告》(文物出版社 2018年)載:
距今5.7億年前,遼南大陸是原始形態的古老地塊,后來地球發生造山運動,地殼出現一系列西東北南交錯的斷裂,逐漸分離為現在的長山群島諸島地貌。遼東半島南部,地質學上稱為“遼南平原中丘”,當時的廣鹿島與遼南大陸相連為一片丘陵山地。
這個時間,幾乎與龜裂石同齡,這段考證,也讓我窺見了它當年所處的天時地利。卻原來,遼南曾是一片平原中丘,因發生斷裂和分離,又變成一片丘陵山地。正因為如此,海侵之后,那些丘陵變成了無法淹沒的島。
廣鹿島也是,原本與陸地相連,在成為離島之前,就已經有人定居于此,而且在此升起了大連歷史上第一縷炊煙。如果廣鹿島是“皮”,這一縷炊煙就是“毛”。皮與毛一起,構成大連新石器時代最早的人文故事。
記得,有位專家朋友告訴我:一萬年前是舊石器時代,出土文物叫化石,一萬年后是新石器時代,出土文物叫河灘淤積。這話如醍醐灌頂,讓我一下子分清了歷史經緯。
叫河灘淤積,是因為氣候正在變暖,山野吐出綠色,人類已經走出山洞,可以選擇一個風和日麗的地方定居下來。廣鹿島最典型的河灘淤積在小珠山,它是一個有7000年歷史的貝丘遺址。那堆潔白的貝殼,仍帶著腥鮮味的貝殼,就像駱駝山和古龍山那些數不清的獸骨,也是通過人類之手,拋擲成堆。從使用工具看,小珠山先民在岸邊拾貝的同時,還向大海撈珍,叉魚、射魚、網魚,曾是他們慣用的三種姿式。
我發現,小珠山先民不光吃海鮮,也吃鹿肉。叫廣鹿島,就是鹿多的意思,因為鹿群擠擠,小珠山人便在河灘淤積里留下一座6500年前的鹿骨作坊。因為彼時海水還遙遠,廣鹿島尚未成為離島,在陸地上奔逐狩獵,仍是小珠山人熟能生巧的老本行。
然而,小珠山最讓我大吃一驚的,不是貝殼,不是鹿骨,也不是具有下遼河文化特征的玉斧,刻有之字形紋的陶罐,而是在先民的房址里,居然有可以當主食吃的蕎麥。這些蕎麥顯然不是從野地采回的植物種子,而是經過播種和收割的田間作物。
我的吃驚,是因為我聽專家說,蕎麥起源于東北,然后一點一點向更曠遠的地方傳播。在它走過的線路上,都留有蕎麥的形跡,唯獨在它的出生地未見一粒。就是說,偉大的小珠山蕎麥,將中國農業考古一個重要空缺給補齊了。
正是這個結論雷著了我,也成了我為小珠山激動不已的理由。據我所知,遠古東北土著有三大族系,東胡族系是游牧者,肅慎族系是漁獵者,唯獨穢貊族系以農業和城柵為生,而且下遼河流域新樂人,就以黍為主食。小珠山先民,應與穢貊沾邊,他們或許也吃黍了,只是沒有實證。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種蕎麥是把好手。因為有了蕎麥,而讓小珠山上空炊煙裊裊。
在小珠山之后,便是郭家村。5000年前,海侵已然停止,因為一支先民在半島最南端的老鐵山落腳,便在這里留下了另一片河灘淤積。
郭家村與小珠山一脈相承,但比小珠山更純粹。小珠山文化有一種雜然性,既有下遼河新樂,也有山東大汶口,只是與大汶口血緣更近。郭家村因為后發,本地只學小珠山,外面只接大汶口和龍山,于是灌了漿似的水靈而飽滿。
兩個千年,兩個文化層,最后都是因為一場大火燒成了廢墟。于是,焦結的紅燒土,煮飯用的陶罐,砍砸用的石斧,縫補用的骨針,捕魚用的網墜,祭祀用或給孩子玩的小陶豬等等,統統作了那兩場大火的說明書。然而,郭家村同樣讓我大吃一驚,因為在4000年前的一堵墻根下,有一簍炭化了的黍。
在這個地球上,谷物起源地有三處,西亞是小麥,美洲是玉米,中國是小米和水稻。所謂小米,即黍和粟,兩者的區別,粟是不黏的小米,黍是有黏性的小米(俗稱黃米),原產地皆在黃河流域。郭家村人吃的黍,與新樂人吃的黍,應該來自同一個地方,只是新樂人吃得更早些。
由此可知,小珠山先民嘴里咀嚼的,是土產的蕎麥,郭家村先民灶房內彌漫出的米香,是從中原舶來的黍。我猜,來到郭家村的黍,無非兩個渠道,一是中原耕夫從山東半島渡海攜帶過來,二是郭家村先民渡海過去載回來。因為4000年前,郭家村先民就制作出了一只工藝先進的陶舟,相當于現在的船模。這只陶舟的船首呈流線形,前突上翹,劈波斬浪的速度會快。船底不是一塊整板,而是多塊拼接,嚴絲合縫,能保持行駛穩定。兩舷等高,外凸,呈弧形,這樣平衡效果會好。內里是個大通艙,可以多裝貨物。如此復雜的航海器,在半島南部還是第一次發現,說明郭家村先民已經告別原始的獨木舟,改撐多木拼接而成的舢板。有這么豪華的大船,什么貨載不了呢?
在小珠山和郭家村之后,還有大嘴子。它依然屬于河灘淤積,不同在于,小珠山和郭家村是新石器時代遺址,它是青銅時代遺址。
彼時,大嘴子先民已經學會了砌墻,不是用土夯,而是用石壘,一共有三道,最長一道有30多米。環繞著村莊,建造堅固的石墻,顯然是人口稠密了,有更多財產了,石墻是一種守護,可以讓好日子不被侵犯。
比石墻更令我刮目的,或者說,再次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在一座屋址內發現了炭化的稻米和高粱,它們被分裝在六只陶罐里,整整齊齊地擺放在地上。又有兩種不同的米香,在3000年前的大嘴子裊裊升起。
稻米是水田作物,來自長江流域,高粱是旱田作物,來自黃河流域。稻米標本,在新石器和青銅時代就遍布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東北一直是個空白。大嘴子遺址的意義,在于它將中國栽培稻從北緯37度15分,刷新為北緯39度2分6秒,成為中國最北界稻作地點。
還有更爆的,中外專家一致認為,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栽培稻,最初都是從中國傳入的,歷史上從南到北,曾有三條平行東去的“稻作之路”。途經遼東半島這一條,屬于北路。有人寫過一本小說叫《高緯度戰栗》,大嘴子種的是高緯度水稻。
大嘴子太牛了,它以實物的方式,證明了自己在稻作之路上的不可或缺。因為在中國栽培水稻向外傳播路線上,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是一傳,山東半島是二傳,遼東半島是三傳。下一站,是朝鮮半島,再下一站,是日本列島。如果大嘴子自私,或懶得再往東傳,歷史就不會有這么精彩的一筆了。
寫到這里,我覺得筆下的每一個字,仿佛也都變成了一粒粒稻米,一粒粒在半島與半島之間行走的稻米。
不知為什么,高粱沒有隨稻米一起向東傳播,而是從遼東半島向北鋪去,把黑土地染得紅彤彤一片,把東北地區的高粱栽培史整整提前了1000年。于是,在東北流亡學生唱的歌里,就有了這樣的詞句: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嘴子先民用六只陶罐儲存種子,說明家口大,土地多,也說明雨量充沛,可以種大面積水田。要雨有雨,種稻得稻,說明他們趕上了一個萬物生長的好年景。
然而,從大嘴子挖出來的紅燒土告訴我,同樣是一場大火,終止了他們所有的盤算和想往。
小珠山,郭家村,大嘴子。它們是三堆厚厚的河灘淤積,更是三個人間煙火的村莊。我很任性,那里有那么多可書可寫的東西,但我只選擇了種在不同時代的米,選擇了帶著煙火氣的米。因為我喜歡它們種在地里的樣子,喜歡它們在陶罐里煮熟的樣子,喜歡它們跟著人在半島之間行走和傳播的樣子。總之,不論哪一種樣子,我都喜歡。
米是物質,能續命。也是精神,象征著生生不息。所以,即使被沖天大火燒成了炭,它們仍以炭化的籽粒,留在世間。也許,這就叫物質不滅,能量守恒。
四、青丘的背影
駐足在遼東半島,或途經遼東半島的古人類,曾經與冰期動物一起,奔走在漫長的無名時代。不管今人如何踮起腳尖,向歷史深處張望,他們的面孔與表情,仍然是模糊的。因為石器時代尚無族屬概念,只能是在哪里被發現,便以哪里人名之。
歷史在青銅時代改寫,因為從這個時代開始,大連有了一個地名,青丘;大連先民有了一個正式身份,貊人。
《大連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載:“青銅時代大連地區的居民屬于東北夷的青丘、周頭等部。”話說得很肯定,青丘和周頭都是大連居民,而且不只這兩個部。但是《東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2年 孫進己等著)一書,卻持另一個觀點,認為周頭聚居地在丹東的小娘娘城山遺址。
就是說,周頭確與青丘為鄰,但青丘在半島南部大連境內,周頭在半島東北丹東境內。那么,確切的說法,只有青丘是青銅時代的大連居民。對于大連初史,知道這一點十分重要。
我注意到,各類地方史書對青丘的敘述大都一帶而過,民間書寫者對青丘卻顯得十分在意和踴躍。因為在寫大連傳,我對青丘的態度就是一定要湊近了看,放大了看。
青丘之名,最早出自兩部典籍,《山海經》和《逸周書》。有趣的是,它們的成書年代,都在戰國至周初,不知誰抄了誰的作業。兩書的區別在于,前者是神話,后者是史書。
在《山海經》里,青丘是神話發生地,神話主角叫“九尾狐”。《山海經·大荒東經》載:“有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山海經·海外東經》載:“青丘國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
《山海經·南山經》載:“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之不盅。”
青丘是國名,也是山名。這里盛產一種仙狐,狐之魅惑,碾壓了青丘,狐之氣場,也把青丘甩出去好幾條街。青丘是舞臺,墊場的,狐是角兒,閃著光。
更有甚者,自九尾狐在《山海經》現身,就不曾在人間消失,始終搖著一叢迷人的尾巴,從上古傳說、秦漢典籍、明清小說里翩然而出。一直到現在,仍有人以《山海經》為百寶文奩,把青丘和九尾狐寫成各種仙幻類劇情。
九尾狐如此神奇,也引發了青丘究竟在何處的各種猜想,從古至今,想找到它具體經緯的人熙熙攘攘。現在去網上搜,也是有說在山東,有說在青海,有說在福建,還有說在遼西的朝陽。真真是,亂花漸欲迷人眼,爭論者的腦子,好像被九尾狐給下了迷幻藥。
要怪就怪《山海經》,把一個神話反復說了N次,仍語焉不詳,故意要噴人一頭霧水。要愛就愛《山海經》,其實它已經說得很具象了。
《山海經·海外東經》載:“亦有青丘國,在海外。”
西漢司馬相如《子虛賦》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
東漢服虔注:“青丘國,海東三百里。”
西晉孔晁注:“青丘,海東地名。”
海外,即渤海之外。海東三百里,即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的海上距離。然而,即便說得這么清楚,因為《山海經》被學界或非學界過度翻抄附會,關于哪里是青丘,仍在嘈嘈切切中。
好在還有《逸周書·王會篇》。周成王七年,正逢新都洛邑宣告竣工,作為天下共主,年輕的周成王為了給自己立威,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剪彩典禮。他是武王之子,西周第二代王,由他主辦的這次成王之會,既是他即位后第一次會盟諸侯,也是西周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全家福,史官自然要打起精神,記下明細。
在出席會議的報到簿上,光是有名有姓的東北夷,就忽啦啦來了十五個:稷慎、穢、良夷、揚州、解、發、俞、青丘、高夷、獨鹿、做孤竹、不令支、不屠何、東胡、山戎。
其實,還有一個東北夷周頭也來了,不知何故,報到簿上青丘赫然在列,周頭卻被打入另冊,只在貢品清單里露了一回臉,座次倒是挨著青丘。《逸周書·王會篇》載:“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互,煇羝互者,羊也。”
周頭與大連無關,只說青丘吧。這場王會,至少透露了兩個訊息:其一,青丘是東北夷名正言順一分子;其二,青丘給周天子進貢的地方特產是“狐九尾”,而不是“九尾狐”。
對《逸周書·王會篇》所記青丘,《中國東北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年 佟冬主編)曾作如下解釋:
東北南部的貊人,因居地或部落之不同而有不同稱呼。文獻記載,在遼東半島上有兩個貊人的小部落,一稱周頭,一稱青丘。兩部均為‘海東夷名’,并謂‘青丘在海東三百里’。這里的海指今渤海而言,所以兩部之地當在今遼東半島之上。這兩部的代表性特產,青丘是九尾狐,周頭是煇羝——毛色光亮的公羊,因此他們可能是以狩獵兼畜牧為主。
讀過此書,青丘已不再是東北夷那么籠統,地理上有了具體指向,遼東半島;青丘居民族屬也不再那么模糊,他們是海東夷,貊人。
海東夷即遠古的東夷。史載,在距今8500年前,東夷人就活動在山東和蘇北。《禮記·王制》云:“東方曰夷。”漢朝經學家孔安國《書傳》云:“東表之地稱嵎夷。”
《后漢書·東夷傳》載:
夷有九種,曰畎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為嵎夷也”。
在一張今人繪制的上古地圖上,我看見遼東半島南部和山東半島東部被涂成同一種顏色,像給渤海岸鑲了一道花邊,上面只寫了兩個字:嵎夷。
想想也是,彼時他們從一個半島蔓延到另一個半島,只有兩個可能,或是在海退之后,他們在膠遼古陸追殺獵物跑過了頭,或是在海侵之后,借舟楫之便,搖櫓撐帆,一葦以航,見岸則登。
但是,《中國東北史》對周頭所貢的羊,說得惟妙惟肖,對青丘所貢的狐,卻基本上原文照抄,有點令人費解。我認為,《山海經》里的“九尾狐”是以“靈狐”形象出鏡的,既是靈狐,何以捕捉?又怎能入貢?《逸周書·王會篇》里的“狐九尾”是以“凡狐”之貌現身的,所以它只是一種動物學意義的狐貍,青丘拿它當貢品,非以狐尾取悅,而以皮毛貴重獻之。
也許青丘確有長著九條尾巴的奇葩狐貍,但是至今也沒看到任何可以采信的記載,倒是《藝文類聚?卷九十九》更加堅定了我的猜測:“《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寫在這里的“尾”,顯然與量詞“只”同義。彼時,去給周成王上貢的東北夷,貢品大都是實實在在的地方特產,青丘怎敢如此魔幻?
我想,對青丘和九尾狐作各種猜測演繹者,或者沒讀過《逸周書·王會篇》,或者就是要臆造出什么青丘帝姬、九尾白狐、四海八荒第一美女,就是要閉著眼睛拿《山海經》來大賺票房。
可以看出,青丘之國得名于青丘之山,那么在遼東半島南部,就應該有一座山叫青丘。金毓黻自1923年開始搜集整理東北地方文獻,對東北文化系統研究,《東北通史》是1941年出版的中國第一部東北地方性通史專著。他認為,遼東半島最南端的老鐵山,就是《山海經》里的“青丘之山”。載曰:“老鐵山,其色焦黑,因以得名。”而《山海經》所謂的“海外”“海東三百里”,用的正是中原視角,而從山東半島泛海東來,首先進入眼簾的,就是老鐵山的森森之貌。更何況,站在廟島群島最前端的北隍城島,肉眼即可看見一脈青峰矗立。
不管怎么說,真要感謝那場成王之會,讓大連人知道了曾有一個名叫青丘的東北夷活躍在西周之世的大連。只是,青丘第一次出場,竟是千里萬里去朝貢。
在青丘故地,至今仍觸目可見的青銅時代遺跡,就是那些極具神秘感的石棚。
它是高大的棚狀建筑,三面豎石壁,留一口朝前,在石壁頂部,蓋一塊向四面突出的石板。這樣的石棚,在大連境內不止一座,而是幾十座,它們或獨立自處,高大威凜,咄咄逼人;或大小混處,長幼有序,尊卑分明。石棚的造型,線條粗獷,風格大氣,質感厚樸。雖經3000多年風剝雨蝕,卻不能奈它何,被史家稱之為“巨石文化”。
許多年前,我曾走遍遼南丘陵山地,一座一座去尋訪它們。記得,看這么多石棚祼然而立,感覺造它的主人并沒有走遠,抑或,造它的主人知道自己有一天會煙逝云去,便用石棚來抵抗消失和遺忘。
石棚也叫石桌墳、支石墓、姑嫂石、石廟子,等等。字面上看,顯然與葬俗有關。有專家說,它“很可能是東夷族青丘部的文化”。(參見孫進己《東北各民族文化交流史》)
青銅時代,半島南部正是青丘之地,石棚極有可能是貊人葬俗。然而,面對那一座座神秘的石棚,我確曾有過一種超出了歷史常識的困惑。
后來發現,不只我一個人困惑,許多石棚研究者也同樣困惑,直到現在,仍因為無法確認,作了三種猜想和假設:其一,它是一種巨石墳墓,意義如同埃及的金字塔;其二,它是一種宗教祭祀建筑物;其三,它是原始氏族部落舉行活動的公共場所。
我想,如果是貊人葬俗,那么作為生活在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時代的有神論群體,他們的主觀意愿不外以具象的石棚為依托,表達對天地萬物的敬畏和信仰,不外用巨石給逝去的自己筑造一座永生宮殿。卻不曾想到,幾千年后,在這一方水土之上,這些石棚居然成了無法磨滅也無法刪除的文化之廈,成了無法解讀又無比崇敬的地上文物。
其實,石棚并非遼東半島獨有。在歐洲、非洲、亞洲乃至中國許多地方,也都有石棚或與石棚相類的巨石建筑。德國人叫“巨人之墓”,比利時人叫“惡魔之石”,葡萄牙人叫“摩爾人之家”,法國人叫“仙人之家”和“商人之桌”。英語則有一個專門詞匯:Dolmen,意為“用石頭架成的史前墓石牌坊”。
有人據此認為,巨石建筑雖與墓地有關,但逝者不太可能葬在巨石內部,它的造型便像是供亡靈出入墓室的大門和通道,因為Dolmen近似于最原始的發音——道門。這個道門,有點像中國皇陵入口處那座高大的牌坊,以示神圣與威儀。這也印證了石棚研究者的猜想,石棚并非單純的墓葬。
正因為巨石建筑如此相似,有人說它應該是同一文化族群全球傳播的結果。比如英國索爾斯伯利平原上的巨大石柱群和杜靈威環石墻,比如法國被稱為“石林路”的史前巨石文化遺跡,比如黎巴嫩重量在1200噸以上巨石建造的神殿遺址,比如智利復活節島的高大石像,都與這個文化族群全球遷徙有關。
一言以蔽之,人類在探詢未知的時候,最大的興奮點就是對“起源”的追溯。巨石文化似乎沒什么神秘,看懂了人類遷徙路徑,認同了文化傳播規律,也便會心和釋然了。
中國境內的石棚,最早出在商周之際,有關石棚的文字記載,最早見《后漢書·五行志》:
孝昭元鳳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
泰山萊蕪山,古為東夷舊地。2000年前的東漢,仍有如此生動的豎石場面,說明石棚文化余緒未斷,至少綿延了1000年。
金代官員王寂巡按遼東半島時,把復州境內的一座石棚寫入了他的《鴨江行部志》:
游西山,石室上一石,縱橫可三丈,厚二尺余,端平瑩滑,狀如棋盤,其下壁立三石,高、廣丈余,深亦如之,了無暇隙,亦無斧鑿痕,非神功鬼巧不能為也,土人謂之“石棚”。
此外,他還作詩一首,“以紀其異”:
片石三丈方縱橫,平直瑩凈如楸枰。
旁榰石壁做大室,人力不至疑天成。
中國別的地方也有石棚,但以遼東半島為多,遼東半島又以大連為最。于是,石棚成了大連遠古史一個標志性文化符號。
成為符號的石棚,便有了某種說不清的親和力。有一次,當我走到一座石棚面前,竟有一絲恍然,覺得那就是貊人當年的坐姿,只不過在數千年的歲月里石化了。
曲刃青銅短劍,歷史留給大連的另一種驚艷。
每每看到它,我都會意識流似的想起石棚。質地,一石一銅;形體,一大一小。在遼東半島南部,在遠古文化體系里,它們都是一種有力度的存在,一種疊加起來的神秘。
有出土文物證明,劍主活著的時候,將劍緊握在手中,死去的時候,把劍放在身邊陪葬。因為在無數的墓穴里,都能看到曲刃青銅短劍,有的甚至經過焚燒。劍是逝者的愛物,逝者輕盈的靈魂,與凝重的劍相繞相纏,在火光中一起“升遐”了。
當然,曲刃青銅短劍也在墓外。有學者在老鐵山下那片耕地里,一下子發掘出十五柄曲刃青銅短劍。之后,在黃海和渤海沿岸,有更多的曲刃青銅短劍出土。于是就有了一個專屬命名:曲刃青銅短劍遺存。
劍是冷兵器,有不同風格,北方風格的短劍,主要有兩種形制:一種是匕首式短劍,劍柄與劍身連鑄在一起,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東南邊緣。持劍者帶著它南下中原之后,劍身也隨之加長。
另一種是曲刃式短劍,主要分布在遼河流域,日本學者叫“遼寧式銅劍”,韓國學者叫 “琵琶形銅劍”,中國學者叫“曲刃青銅短劍”。作為兵器,此劍最特殊之處,就是寬葉、曲刃。
其實,歲月漫長,劍的款式和造型,也隨時光在變。最早的劍身,只有曲刃,而無劍柄,像一個成人玩具。后來,變成一個復雜的組合,由曲刃劍身、T型劍柄與劍尾端加重器連成一體。曲刃也從寬葉變成窄葉,對劍柄還作了美化,刻有三角勾連紋飾或羽狀紋飾。于是就聽過一個說法,曲刃青銅短劍的造型和紋飾,讓人想到浪花細膩的線條,有濃重的海洋氣息。
我甚以為然,持劍者濱海而居,他們造出的劍,怎么會少了海的韻致呢?此外,一柄曲刃青銅短劍,從西周到戰國,流行了數百年時間,一支持劍者部落,瀟灑地生活在秘境般的半島南部,也算一頁文化傳奇吧?
但是,關于持劍者身份,考古界至今仍存爭議。《大連通史》(人民出版社 2007年)載:

大連地區生活著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銅短劍為主要特征的居民。……這支使用曲刃青銅短劍的居民,從西周中期開始,直到戰國后期,一直活躍在大連地區。
一支以使用曲刃青銅短劍為主要特征的居民。這個定義比較模糊,沒說明白,也許是說不明白。
我目前看到的爭論,主要有兩種。
多數人說,曲刃青銅短劍是青丘部貊人的文化遺存。他們的依據是墓葬,在各種石棺墓內,皆有曲刃青銅短劍,在那些高大的石棚內,也有曲刃青銅短劍。毫無疑問,這是同一部族、同一文化體系的葬俗。
少數人說,曲刃青銅短劍出自東胡、狄人或夫余人之手。因為中原軍隊是車戰,多以長戈為武器,游牧民族是騎兵,更喜歡短劍。所以,它流行于北方諸多游牧民族,不能將其歸屬某個特定的部族。
我更認同多數人的說法。一種劍式,原創者只能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族群,不可能由諸族共同發明。只能說,它曾被別人大量拷貝,樣式或許還作了一些改變,在北方諸族間,配戴它逐漸成了一種流行和時尚。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與石棚一樣,曲刃青銅短劍在大連出土最多。當然,更早的時候,握在青丘部先民手中的利器是石鏃、石斧、石鏟和木棍、木叉,那是為了捕殺獵物。后來,時代不同了,人與人,部落與部落,有了各自的山頭,有了利益爭斗,便造出了金屬利器,便開始手持曲刃青銅短劍,開始有了刀刀見紅的肉博。當曲刃青銅短劍造得越來越鋒利,那是因為天下進入戰國。
半島南部,終于迎來了那場你死我活的廝殺。燕國被打得粉身碎骨,青丘也跟著吃瓜落兒。但是,當風云散盡,塵埃落定,曾經拿九只狐貍去給周成王上貢的青丘,曾經用一座座石棚刷存在感的青丘,曾經鑄造出海洋風曲刃青銅短劍的青丘,仍以獨有的氣質,讓后世引頸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