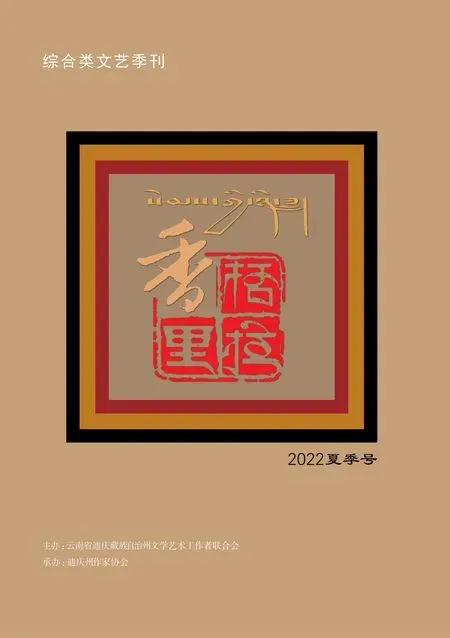草原往事(外一篇)
◎殷著虹
草原往事(外一篇)
◎殷著虹
在香格里拉高原的石卡雪山下,散落著許多藏族村落。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我中學畢業后在那里的一個村子里插隊落戶。那時,那里的一個自然村基本就是一個生產小隊。俗話說 :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我所在的村子依山傍水,還有大片的草原,真是個發展畜牧業生產的好地方。
生活在草原上的藏族人家,有著一日四餐的飲食習慣,而從早到晚的人們見面問候語是: “喝了嗎?”當然, 他們所說的“喝”是喝酥油茶。常言道: “民以食為天”,藏族人家的生活離不開酥油茶,酥油茶在他們的生產勞動中占據了重要的分量。所以藏族人家對打酥油茶所用的酥油生產很重視。酥油是從牛奶中提取而來的油脂,所以藏族人家在珍惜這種乳制品的同時,也更注重畜牧業生產。
那時我是剛走出校門的知識青年,剛到農村看到遍野的牛羊時感到很驚奇,便問:“這里怎么有這么多的牛羊呀? ”可村里的人告訴我: “這還不算多,村里的牦牛、犏牛都搬遷到雪山上去了。等到冬季來臨時,雪山上的牛趕下山來, 那才叫做牛羊多呢!”那以后我在和農牧民們一起勞動和生活中,漸漸懂得了一些畜牧業知識。
原來在高原地區, 飼養的牛主要有黃牛、牦牛、犏牛三個牛種。黃牛的性情較為溫順,適合在草原上放養,但不適宜到更高海拔的雪山上放牧。牦牛雖然野性較強,但它不懼嚴寒, 又耐粗飼, 很適合放養在雪山牧場上。而黃牛與牦牛雜交生成的犏牛, 是優質牛種,其作用和貢獻都超過了黃牛和牦牛,它有很強的飼養環境適應性,既能在雪山上放牧,又適合在草原上飼養。
犏牛有的是公牦牛和母黃牛雜交生下的后代,也有的是公黃牛與母牦牛交配后產生的物種。犏牛性情溫順,易于飼養。雖然雄性犏牛失去了繁衍下一代的功能,不作為牛種飼養,但它體格強壯、能吃苦耐勞,因而是優質的勞役牛。退役之后, 又可轉為肉牛。而雌性犏牛產仔后,具有長期產奶和產奶量高的天性,所以它是草原上的優質乳牛。為此當地牧民常說: “青稞滿架代表著年景昌 盛,犏牛遍野反映出草原興旺。”
因為犏牛有著諸多的優點,為了推進畜種的改良進步,我們到生產小隊插隊的翌年春天,村里便從四川省鄉城縣買回一頭成年雄性牦牛,大家伙都叫它“亞圖”,目的就是把它放養在黃牛場上,為生產隊里繁育出更多的犏牛。
記得亞圖由拖拉機運回來的那天,我和村里的很多人都去看熱鬧,只見它一身黑白相間的皮毛油光發亮,巨大頭顱上的兩只眼睛瞪得像兩只電燈泡,一對牛角更像古代的兩柄彎弓兵器,讓人一看就能產生畏懼。可村里的人看到它后卻都不約而同地鼓掌歡迎,待把它卸下車后, 有名望的“孜本”(牧主人)念念有詞地為它系上了牛鈴。這以后這頭亞圖種牛便威風凜凜地徜徉在草原上,儼然草原成了它的悠閑領地,它精神抖擻地護守著牛群,其它公牛和牧人都不敢隨意靠近它。
那時村里有三個黃牛場,都成了亞圖輪歇的場地,而所到之處牧主人都會對它特別關照,不僅喂它好草好料,而且還特地喂它牛奶、紅糖和雞蛋, 目的就是讓它養精蓄銳,保持旺盛的體質, 在草原上播撒更多的種子。然而精心地飼養卻讓它更得意忘形,稍有不慎它就晃動起大腦袋, 做出想頂撞人的樣子,嚇得讓人退避三舍。
藏族諺語說得好: “健壯的母牛生一頭 (牛犢) ,強壯的公牛產百頭(牛犢) ,莽撞的亞圖來到草原, 能帶來最好的小犏牛”。真是這樣的,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村里牛場上就增加了三十多頭小犏牛,這可讓村民們喜出望外。大伙說,照這樣下去,來年村里就可以增加一個牛場了,家家戶戶的茶桶里就能放進去更多的酥油。為此村里在做一年一度的表彰活動中,不僅為先進的社員和家庭送了獎品,也還在活動上為亞圖進行了披紅掛彩,大伙對此津津樂道,拍手稱快。
但這事卻惹惱了一個當時在村里下鄉的縣里干部,這位干部說: “生產斗爭必須 堅持政治掛帥,給牛披紅掛彩違背了政治路線!”之后他提出這花應該給畜牧隊長戴上,但在遭到現場群眾的一片嘲笑之后,這名干部又拉長著臉嚴正指出: “對這件事必須嚴肅批判! ”于是他不顧生產勞力緊缺,天天組織隊里干部們學習政治,直到大家怕這樣下去耽誤了生產, 只好違心地做了檢討認識,召開大會批判了“錯誤思想”,這場風波才得以平息。
這以后當地老百姓也為這名下鄉干部取了個外號,叫做: “扎果”(意思是不開竅的鐵腦袋)可這名干部似乎還很樂意接受這一外號, 他說: “做工作不光要有鐵石腦袋,還得要有鐵石心腸。”扎果的心腸確實夠鐵石的了,這以后他不允許村里的婦女們下地做活時,邊走路手中邊捻紡毛線,說公事與私事切忌要分開;不允許村里的年輕人唱情歌、跳鍋莊,說唱唱跳跳會引起傷風敗俗;更不允許村里的男人們外出做工找副業,說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等等。
但如果把“扎果”說成是不近情理、頑固不化的人,似乎又有些過分。我見過他在村里下鄉時,總是主動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有時還拿出自己的工資幫助村里有困難的人。因此村里的人對他并不嫉恨,只是說話做私事總要躲著他,生怕他抓住什么問題后又節外生枝。也就在村里人念著他好的同時,卻又把“扎果”來了!作為嚇唬小孩的話。
“有辛勤地付出,就有喜悅的收獲;有虔誠地守望,就有美好的風光。”正當村里人沉浸在悠揚牧歌聲中時,牧場上回村的人報告說,從遠方山林竄來了兩只灰狼。狼的出現, 無疑對草原上的牛羊構成了嚴重威脅。對此扎果急著去了縣城。回到村里時,他背上挎了一支半自動步槍。而當他騎上自行車打算去牧場時,那頭曾經引起披紅掛彩風波的亞圖卻突然向他沖了過來,幸虧他躲讓及時沒有受傷,可他那輛嶄新的永久牌自行車已被瘋狂的亞圖摔得不成樣了,接著亞圖再一次向他發起了攻擊。情急之下他抓起槍來就向亞圖開槍射擊,兩聲槍響劃破了草原的寂靜,亞圖倒下了,泉水般的血從它頭上噴涌而出,接著它四只牛蹄亂蹬了一陣,亞圖死了。
村里人趕來了, 都對眼前的事感到悲傷,但卻沒有人去責怪“扎果”,大家都說: “人的生命比牛的生命更為重要。”后來村里幾個年輕人剝去亞圖的皮,把牛肉分到了各家各戶,而“扎果”始終沒有要牛肉。最后是村里的一位老者把亞圖的牛鞭送給了“扎果”,至此村里人都把這事當作了笑話議論。也在那時我才聽說“扎果”結婚多年了,可是一直沒有孩子,而牦牛鞭可作為補品,能改善男人的生育能力。
草原上的狼最終在“扎果”的帶領下被民兵們殲滅了,以后他也結束了下鄉工作,回縣城去了。他走后村子里又慢慢恢復了他不允許村民做的事項,漸漸地扎果也就淡出了村民的記憶。
以后生產隊又買回了一頭更加高大威風的亞圖,村里的牛場也還確實增加了一個。但是,村民們期盼的有更多酥油的愿望卻沒能實現。相反分配到各家各戶的酥油卻在逐漸減少,甚至在草原牧草青黃不接時,人們茶碗里只能見到漂著星星點點的油花。就因為那時實行吃“大鍋飯”,原來只有三百多人的生產隊,三年中猛增到了四百多人,畜牧業的生產跟不上人口的增長, 以至于牧民的收入一年比一年下降。這也更挫傷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對此人們更期待能有新的政策取代平均分配方式。
我在這個村子四年之后離開了草原,回到了縣城里參加了工作。以后每當回想起在草原的往事時,我自然會想起“扎果”,但卻一直沒見到過他, 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單位,還真不知道他的真實名字。
“走出草原的馬駒, 最終還會走進草原;飛出雪山的山鷹,最終還會飛回雪山。”用這一藏族諺語來比喻我,確實很貼切。雖然我離開當年插隊落戶的村子已有許多年了,但時常還會回到那里去看看,回顧往事猶如夢境,卻也能使自己心境平靜、知足常樂。
也就在幾年前草原上的一個春天,我再次步行在草原的路上,看著日新月異的草原景象,真讓我感慨萬千、心悅誠服。突然一輛面包車在我身旁停了下來, “叔叔,您要到前面的村子里去吧? ”開車的小伙子主動問我。“是呀。”我回答。只見小伙子笑容滿面地請我坐他的車, 說順路送我到村子里。對他的盛情我很感激, 上車后我們算認識了。當得知我是為寫作到草原采風時,小伙子向我投來了欽贊的目光。接著他向我介紹說:“我叫尼瑪, 在鎮上做畜牧獸醫工作。”“那周末了, 你咋還奔波在草原上?”我問。“為預防牲畜口蹄疫情,我們分散到了農村搞調查。”看他對工作的熱情, 使我心里十分欣慰,還真羨慕他的青春氣質和陽光帥氣。尼瑪還對我說: “我之所以熱愛這份工作,是從小受到父親的教育,我父親曾在這片草原上工作過。”
下車時尼瑪要我給他留下個電話,說他結婚時一定要請我去做客。果然這年底他給我打來了電話,邀請我參加他的新婚典禮。而就在我參加尼瑪婚禮的這天,我才知道尼瑪的父親就是當年的“扎果”。原來“扎果”的真名叫“扎詩”,早年他下鄉工作結束后,轉崗到了縣畜牧局工作。后來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他老家農村缺乏勞力,便退職回鄉了。
我激動地拽住扎詩的手說: “大哥,您有一個好兒子啊。”可只聽他說: “年輕的 一代趕上了好時光了, 我們那個年代很艱苦,而我工作中頭腦簡單而又草率。”聽得出他對自己的過去有著歉疚,而對今天又充滿著感激和希望。
如今草原上的人們都過上了幸福生活,雖然逢人見面還是那句“喝了嗎? ”但此時的這一問候語已非彼時,聽起來能讓人感受到生活的質量和分量,更給人一種親近和愜意的味道。是啊,草原上的人早已不再為茶碗里的酥油而發愁了,看到他們美滿日子,確實讓人感到趕上好時光、好時代啊!
酥油茶
布倫村, 當年我上山下鄉當知青的地方。這個坐落在石卡雪山下半農半牧的藏族村落,當地農牧民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酥油茶。我在這個村子里待了近四年,生活和勞動和村里人是一樣的,可想而知在我身上少不了酥油茶的味道。以至于雖然我現在生活在他鄉都市,卻還在懷念那個年月每天喝酥油茶的時光。
酥油茶味美香濃。味道的凝然帶著親和的情感、和諧的氛圍。在我心里,酥油茶儼然是首甜美的牧歌,唱響著雪山草原上花開花落的歲月,滋養出藏族人家不卑不亢的人生。而相伴它的余韻悠長, 我們走過了風里來、雨里去的坎坷道路。
酥油茶的制作方式很簡單,用一個黑陶具茶罐燒水,讓茶葉在里面煮上一陣子,待上下翻滾中的茶葉蕩出茶味后,再加酥油和鹽,倒進酥油茶桶里反復攪拌,當茶水和酥油充分融合,這便就是酥油茶。記得我剛到農村后不久,為協助公社獸醫站注射防疫針水,知青們來到了村里的牧場。那時一位老牧工為我們打酥油茶做晌午,他意味深長地對我們說: “別看酥油茶做法簡單,在這沸水里少不了三樣東西:茶葉、鹽巴和酥油,三樣東西缺一不可。”
確實的。缺一不可的茶葉、鹽巴和酥油,情系著農牧民年復一年的簡樸日子,關乎到我們一日四餐的吃飯大事。記得我在村里那時,生產隊有六個牦牛牧場,家家戶戶也都飼養有奶牛。按說牛養的越多,所產牛奶也就能多,村民要想得到的酥油也就不難。但事實上村里養的牛越多, 夏秋季節倒也好辦,有寬廣的原野提供飼草。可冬春季節牧草枯萎,牛的飼草和飼料可就讓人發愁了。也就為了解決牧場越冬的飼草飼料問題,那時村里人不斷擴大耕地面積,力求通過更多種植青稞、蔓菁作為飼草飼料,以促進村里的畜牧業發展。
那時布倫村是集體化生產,是周邊農村中收入水平相對好的村落。但全村四五百號人中只有一半才是勞動力和半勞力。為了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 村里人不得不起早貪黑、加班加點地勞作。生產隊干部更是要精心調配農業、牧業和副業生產的勞力。幸好在那個“人勤勞,天幫忙”的年月中,風調雨順給村里人帶來了好年景,我們知青和藏族人家都過著安穩的生活。
每年深秋,是村里最熱鬧的季節。當地里的莊稼收拾完畢后,雪山上的牦牛場遷徙下山,草原上呈現出牛羊成群的景象。可隨著冬季的深入,一歲一枯榮的牧草已被牛羊啃食殆盡,牧人們只好用儲備的飼草喂養牦牛。而干枯的草料缺乏營養,漫長的冬季便造成了牛奶產量急速下降,而從牛奶中提取的酥油更是少之又少。
好在布倫村距離納帕海比較近,初春的牧草要比其它地方萌發得早,春風也給一籌莫展的牧民帶來了希望,他們爭先恐后地來到這一地盤放牧。于是間,數不盡的牛和零星的帳篷成了納帕海邊的壯觀景象。可新長的牧草根本禁不住牛的胃口,清晨已是見綠的草灘,可到了傍晚卻又成了枯黃。熬過了一個冬季的牛們如饑似渴地啃食剛冒芽的青綠,它們緩步走在春暖乍寒的草場上。
我到納帕海牧場是下鄉后第二年的初春,生產隊準備派我在內的 20 個勞動力到哈拉林場做副業,便叫我到納帕海籌集需要帶上山的酥油。可我轉了半天,把村里的牧場走了個遍,總共也只籌集到五斤多點酥油。回到村里作業組長對我說: “在這‘三月倒馬,四月倒牛’的時節, 能籌集到酥油就不錯了, 夠咱們吃上一陣子了。”那時我才知道所謂“三月倒馬,四月倒牛”是指三四月間,由于牧草青黃不接,隨時會出現牛馬死亡的現象。由此可見,牧人的生活并不像歌曲中唱的那樣悠閑自得,更不像詩歌里寫的那樣瀟灑自如。
隨著草綠滿了大地,牦牛牧場要搬遷上山了,要到石卡雪山上駐扎和放牧。這是因為牦牛喜歡生存在寒冷的環境中,雪山上的灌木新芽和野花野草都是它們的飼草。為了這一天的到來,村里人要穿著新裝,慈祥老人們念誦著吉祥的頌詞,祈求山恩水惠的降臨,祝愿牧業興旺帶來欣喜。而牧工們趕著牦牛,總是在悠揚的歌聲中漸漸遠去。
接下來不久,每 10 天各個牧場會派人回到村里, 上交他們牧場上新打的酥油和奶渣,同時帶去新磨的糌粑面和飼料糧等。也就在那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牧鈴聲中,聲聲牧鈴如同春天的喜訊,搖響了村里人的歡歌笑語,生動了裊裊炊煙下的童謠。人們期盼著馱來滿滿當當的酥油, 而那有滋有味的情愫,滋養著和睦家庭中的男女老幼。那時牧場上交的酥油到了生產隊倉庫后,還需要完成國家的派購任務,之后根據工分和人頭分配到各家各戶。所以牧場上馱來的酥油多與少,直接關系到每個人碗里的酥油茶質量。
就因為和農牧民在一起,讓我對酥油茶 的記憶始終難以忘懷。那時村里人有個有趣 謎語: “我家有個黑小伙, 客人一來鉆灶火。”這個謎語的謎底就是煨煮酥油茶的茶罐。謎 語不僅道出了藏家人的熱情好客,還刻畫出 了藏家人的生活習慣。我在布倫村看到,藏 族人家里都有大大小小的多個“黑小伙”, 這些煨煮酥油茶的茶罐是根據家里人多人少 選擇使用的。但無論人多還是人少,家里打 酥油茶時,只有前三罐才放有酥油,后面續 上的都只是清淡茶水。所以藏族諺語里說:“喝 了多少的酥油茶,只有酥油盒才會知道。”
喝酥油茶,還有著很多的講究,客人不能端起茶碗一飲而盡,否則主人以為你不再喝了,也就不再為你添加新打的茶。只有輕輕吹開茶碗上漂浮的油皮,喝過半碗后擱下茶碗,主人才會為你再續上新打的茶。也許正是酥油茶不同于其他任何飲料或食物,所以不僅喝茶的規矩多,就連使用的茶碗也有不同。在藏族人家里輩分高或是尊貴客人才得以用鑲銀的木碗,其他人用的都是瓷碗。
酥油茶不僅只是用來喝的,還得用它來捏糌粑團食用,糌粑是藏家人獨有的食物。糌粑和酥油茶的絕配, 構成了藏家人的主食。正是這一主食,不僅哺育出藏家人堅強生命和康健體魄,更是孕育了他們胸懷坦蕩、勤勞樸實和為人忠厚的民族氣節。我慶幸自己有過和藏族人家生活的經歷,從而讓我心向太陽和月亮, 具有了不畏艱難和挫折的品質。
我是在布倫村下鄉的第三個年頭,才到了石卡雪山牧場。記得那年村里抽調了 18 個男勞力上山去修繕牧場, 我也是其中的一員。也就在這段時間里,讓我深刻感受到牧工們勞作的艱辛。他們長期居住在陰濕低矮的窩棚里,每天卻要忙著擠奶、放牧和打奶。晴天的日子,給人感覺牧場的生活有著詩情畫意,可要遇上天陰下雪,所有的平仄詩韻都成了鏡花水月。因此村里人常說: “雪山上的天,三歲小孩的臉,一天到晚都在變。”確實高山上的氣候異常多變,給牧場牧工的生活帶來很多困難。我們一行在石卡雪山雖然只待了半個多月,也遇到了多次冰雹、雷電和狂風暴雨天氣。而牧場上的人告訴我說:“這還不算什么,最怕的是山洪暴發和遇見黑熊。”我這才知道修繕牧場是為了防范山洪暴發。
每當我喝酥油茶時,自然會想起布倫村的情緣往事。彷佛那縷縷芳香的酥油茶,是揮之不去的情深意重,茶碗中泛起的是歲月的漣漪。也許就因為如此,我離開布倫村四十多年了,卻對酥油茶篤信不疑。因而每年秋天我都要回到布倫村,向當地藏族人家購買酥油。在我心目里只有布倫村的酥油才是正宗味道,也只有喝了布倫村酥油做成的酥油茶,才能讓我服“異鄉”的水土。
歲月悠悠,時代變遷。如今的布倫村已經不是從前的布倫村了,村里人衣食住行都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每個家庭早已過上了小康生活。而當我走進牧場時,雖然山還是那個山,水還是那個水。但現代版的牧場人家,在改善了臨時住所條件的同時,還安裝上了太陽能蓄電裝備, 用上了智能手機,與外界保持著暢通聯系,同時還可以收聽收看各種信息。
也因為牧場上還使用上了手搖牛奶分離機器,于是我再也聽不到那昔日裊裊的打奶歌。但當我端起那碗新打的酥油茶時,那歡樂的小河依然潺潺流進心田。
殷著虹 云南省迪慶州政法部門退休干部,云南省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省內外多家期刊雜志以及地方黨報,曾獲省市級多項獎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