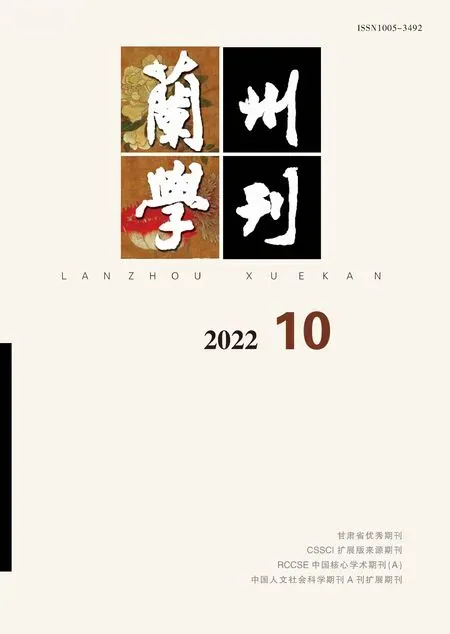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會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嗎?
——來自中國3727家上市企業綠色發明專利數據的經驗證據
陳曉華 鄧 賀 楊高舉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和資源紅利,然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及資源環境壓力的加劇,如何以更優的方式實現經濟增長成為了當今中國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1)資料來源:《工業綠色發展規劃(2016-2020年)》。為此,盡管技術創新作為主導世界競爭格局的核心理論,是減緩全球經濟下行的壓艙石及推動經濟復蘇的新引擎,但工業發展中經濟粗獷式增長引致的資源和環境問題逐漸逼近自然承受力的邊界,可見傳統的創新模式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當下綠色轉型發展的需求。基于此,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和“綠色”在內的五大發展理念,并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強調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創新體系,并推動環保和清潔產業發展。為此,綠色創新作為新型創新模式,在減小創新活動對自然環境帶來負向外部效應的同時,改善傳統創新存在的機械性局限問題,有效破除環保、創新和經濟增長三者間協調發展的瓶頸,逐漸成為中國乃至全球綠色轉型發展的重要路徑。(2)Frank Boons,et al.,“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State-of-the-art and Steps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45,No.2,2013,pp.9-19.(3)Jun Chen,et al.,“Regional Eco-innovatio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Eco-innovation Leve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No.153,2017,pp.1-14.此外,中國正處于“工業導向型”經濟轉向“服務導向型”經濟的關鍵時期,服務業發展水平逐漸成為衡量地區現代化水平及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中,作為具有高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和低環境污染特征的生產性服務業,其在一定區域內部的集聚或將成為推動企業綠色轉型升級的重要選擇。為此,《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拓寬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方向,提高生產性服務業在制造業密集區域及重點城市的集聚水平;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生產環節的核心作用。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學界有關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企業層面綠色創新效應的實證分析異常匱乏。為此,細致刻畫二者間作用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目前學界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綠色創新分別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形成以下三個方面的研究體系。
一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不僅有助于推進制造業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還是應對資源約束、環境污染及產能過剩問題的重要支撐。為此,該領域始終是學界研究的焦點。目前較為認可的衡量方法主要集中在首位度指數、行業集中度、區位熵、赫芬達爾系數、空間基尼系數和E-G指數等。(4)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9,No.12,1991,pp.483-499.(5)Ellison G,et al.,“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5,No.5,1997,pp.889-927.隨著集聚測度方法的完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經濟效應逐漸被學界所關注。如基于經濟增長視角,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促進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但低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可能不顯著;基于全要素生產率視角,二者之間存在線性關系和倒U型關系;此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可以通過技術外溢提升制造業生產效率(6)宣燁:《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與制造業效率提升——基于空間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財貿經濟》2012年第4期。,并通過知識外溢效應激發地區創新活力(7)程中華、劉軍:《產業集聚、空間溢出與制造業創新——基于中國城市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然而學界對集聚經濟效應大量而深入的耕耘局限于區域層面,缺乏對細化領域的實證分析,使得研究層面亟待深入開發。
二是綠色創新的研究。作為可持續發展與技術創新兩大前沿理念的有機融合,綠色創新對于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及企業綠色轉型升級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綠色創新的定義主要基于過程及結果兩個視角,前者定義其為綠色產品歷經技術概念到產品研發,再到產品商業化全過程(8)Klaus Rennings,“Redefining Innovation-eco-innovation Research and the Contribution from Ecologic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nomics,Vol.32,No.2,2000,pp.319-332.,后者強調其達到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的效果(9)Mirata M,Emtairah T,“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The Case of the Landskrona Industrial Symbiosis Programme”,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13,No.10/11,2005,pp.993-1002.。隨著綠色創新研究的深入,其測度指標的構建被學者所熱議。如利用因子分析法、隨即前沿分析法(SFA)和數據包絡分析法(DEA)測量的綠色創新效率,對傳統創新效率進行了優化和補充(10)Yang Gao,et al.,“An Empirical Study o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Gr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ustainability,Vol.10,No.3,2018,p.724.,不僅克服了傳統效率評價體系從單一視角出發的缺陷,還將生態環境、技術創新及經濟發展同時納入考核體系(11)Seema Sharma,et al.,“Inter-country R&D Efficiency Analysis: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Scientometrics,Vol.76,No.3,2008,pp.483-501.,進而成為刻畫綠色創新的指標之一(12)龔新蜀、李夢潔、張洪振:《OFDI是否提升了中國的工業綠色創新效率——基于集聚經濟效應的實證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7年第11期。。為進一步提升綠色創新水平,學者將研究焦點轉向綠色創新的影響因子。如學者分別剖析環境規制、政府支持、金融發展水平、外商投資和技術交易環境(13)Tuochen Li,et al.,“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China’s Provincial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RAGA-PP-SFA Model”,Mathematical Problems in Engineering,Vol.2018,No.20,2018,pp.1-13.等外部因素對綠色創新的影響作用;內部因素則主要包括企業研發投入、人力資本和企業規模等方面(14)黃奇、苗建軍、李敬銀:《基于綠色增長的工業企業技術創新效率空間外溢效應研究》,《經濟體制改革》2015年第4期。。綜合已有研究可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尤其是針對企業層面綠色創新影響研究的缺乏,使得學界無法獲悉二者間的作用機制。
三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綠色創新作用關系的研究。現存文獻從多個角度為本文研究內容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邏輯借鑒。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已有研究多從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區域層面技術創新或綠色發展作用關系視角出發,如大量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聚集通過空間溢出效應提升制造業生產效率(15)余泳澤、劉大勇、宣炸:《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制造業生產效率的外溢效應及其衰減邊界——基于空間計量模型的實證分析》,《金融研究》2016年第12期。,進而對技術創新帶來積極影響,且二者間作用效果表現出區域和細分行業的異質性,中西部地區批發和零售業以及東部地區金融業的集聚對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16)原毅軍、郭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制造業集聚與技術創新——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經濟學家》2018年第5期。;此外,適度的集聚有助于強化綠色技術創新的融資優勢(17)楊艷軍、劉夢溪:《綠色技術創新、產業集聚與企業融資約束——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湖南師范大學自然科學學報》2022年第3期。。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鮮有學者關注到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有關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層面綠色創新直接作用效應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如羅超平等(18)羅超平、朱培偉、張璨璨、陳雯:《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促進了城市綠色創新嗎——基于“本地—鄰地”效應的視角》,《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的研究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本地綠色創新的作用機制呈現為先抑后揚的U型趨勢,即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超過一定臨界值時,二者間作用效果才為顯著的促進作用;任陽軍等(19)任陽軍、何彥、楊麗波、張素庸、臧海培:《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制造業集聚對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基于中國城市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分析》,《系統工程》2020年第3期。通過動態空間杜賓模型剖析了產業集聚對工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得到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顯著提升了本市工業企業綠色創新效率,但對相鄰地區工業企業作用效果不顯著的結論。綜合上述研究結論,可以推定盡管學界已經認識到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會對綠色創新帶來顯著影響,然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的研究具有“同為研究熱點,鮮有交集”的特征,二者交互實證研究的缺乏使得學界難以科學洞察其內在作用規律,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層面綠色創新的研究是一片亟待開拓的“沃土”,這也正是本文研究內容的創新性和必要性所在。
已有文獻為本文研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作用關系提供了夯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但仍存在以下缺憾:首先是多數學者對產業集聚經濟效應的研究僅基于區域層面,鮮有學者將集聚指數與企業層面的數據相匹配,更無學者對集聚與企業層面創新水平進行研究,使得集聚的研究層面較為粗糙;其次是現存文獻多從制造業集聚、產業協同集聚和高技術產業集聚視角出發考察其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暫無學者從綠色專利視角出發考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效果,導致該領域的分析框架和理論機制存在缺陷;最后是目前多數學者分別從資源、環境和創新三個角度探究產業集聚的作用效果,鮮有學者分析產業集聚對綠色創新這一綜合變量的作用關系。鑒于此,本文嘗試以如下邊際創新點彌補上述不足:(1)將產業集聚指數與企業數據相匹配,使得對集聚經濟效應的考察下沉至企業層面,進而精琢細化集聚的研究層面;(2)從綠色專利視角出發,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的交叉領域展開探索,從而拓寬二者相關領域的研究邊界,力圖為解決企業綠色創新背后的難題提供產業集聚方面的經驗借鑒;(3)將產業集聚與綠色創新納入同一理論與實證分析框架,系統性考察產業集聚對綠色創新的作用關系,從而為產業集聚效應的研究領域開拓全新視角。
二、研究假設的提出
考慮到實現綠色轉型升級需要同時滿足綠色發展與技術創新兩方面的進步,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知識溢出效應及規模經濟效應,對實現二者協同發展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為此,從多維視角細致梳理本文研究領域的現存文獻,可以得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之間存在正效應和負效應的結論。
(一)正向效應
1.知識溢出效應
考慮到知識與技術含量越高的產業,其集聚的溢出效應越顯著。(20)Glaeser E.,“Learning in Cities”,Journal of Urban Ecanomics,Vol.46,No.2,1999,pp.254-277.為此,生產性服務業作為從制造業中剝離出來的、細分了社會分工的知識、技術和人才密集型產業,其在一定區域內部的高效集聚將通過知識溢出效應,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21)Krugman P.,“A Model of Innov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87,No.2,1979,pp.253-266.一方面,先進的知識和技術是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意識和生產效率,進而激發綠色創新活力的新生動能。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將高端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匯聚于此,有助于及時準確地把握前沿信息技術與發展動態,推動制造業產業向價值鏈高端延伸。此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通過為企業形成的多樣化網狀結構(22)楊浩昌、李廉水、劉軍:《高技術產業聚集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及區域比較》,《科學學研究》2016年第2期。,促進節能減排理念和綠色清潔技術的傳播和應用,使得企業在綠色環保領域達成默契,推進保護環境意識深入人心,從而實現企業研發重心向綠色轉型升級方面的靠攏(23)劉勝、顧乃華:《行政壟斷、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城市工業污染——來自260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經驗證據》,《財經研究》2015年第11期。,進一步有助于綠色技術的誕生與發展。另一方面,在匯聚高端知識和技術的同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吸引和留住多層次高質量人才,進而通過“蓄水池”效應,不僅提升企業間顯性知識的流動效率,還有助于隱性知識和技術的發散與傳播,即通過優化從業人員的溝通平臺,刺激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模式的誕生,為高技術人才打造綠色技術創新的最佳學習氛圍(24)Keeble D.,et al.,“W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 Small Consultancies, 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an and Southern England”,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Vol.27,No.1,2002,pp.67-90.,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引致的溢出效應,有助于促進企業透過高技術含量和高利用率的生產性服務資源,提高制造業綠色生產效率,是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重要支撐。
2.規模經濟效應
新經濟地理學認為,上游企業空間集聚的目的是發揮集聚引致的規模經濟效應,進而降低企業生產和交易成本。為此,首先,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透過規模經濟效應,實現區域內部的人才、資源和基礎設施的高效共享(25)陳建軍、陳國亮、黃潔:《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管理世界》2009年第4期。,有助于降低企業購入實現綠色發展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提升綠色資源配置和流動效率,在推動企業實現風險共擔的同時,降低企業研發、生產和銷售等各項環節的中間成本,使得企業將資金集中于技術研發環節(26)Mukesh Eswaran,et al.,“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68,No.2,2002.,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撐,有利于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去污化”(27)徐曉紅、汪俠:《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空間溢出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統計與信息論壇》2020年第5期。并舉。其次,市場競爭作為技術創新的題中之義(28)Michael Porter,“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Review,Vol.1,No.1,1990.,進一步深化規模經濟對于綠色技術創新的積極作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擴大區域內部企業的經濟規模,引致開放環境下企業間的良性市場競爭,倒逼企業提升專業化分工水平以及降低企業無效損失,實現綠色創新要素的高效配置,進而保持自身核心競爭優勢,由此可以推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引致的規模經濟效應,有助于促進企業實現綠色技術創新。
(二)負向效應
考慮到交通、資源、空間和基礎設施的限制,產業無法實現無限集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負向效應。一方面,集聚程度的深化使得空間和資源負擔過重,容易引致企業間形成惡性競爭,對企業實現綠色專利成果轉化帶來負向沖擊。另一方面,基于規模報酬遞減規律,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效應逐漸弱化(29)張治棟、秦淑悅:《產業集聚對城市綠色效率的影響——以長江經濟帶108個城市為例》,《城市問題》2018年第7期。,進一步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的積極效應。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同時存在正效應及負效應,其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整體作用效果取決于兩種作用的總方向。但基于學界大量研究結論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產業特征可以推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水平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具有促進作用
(三)調節效應
首先,適度的環境規制將產生“創新補償”效應,使得企業被迫進行技術創新,以降低其生產成本,保持自身競爭優勢,且環境規制對本地區具有“本地正外部性”效應,即嚴苛的環境規制加速不符合要求的高污染企業遠離本地區,為綠色發展帶來正外部性。其次,環境規制引致的“遵循成本”效應,提升了企業的治污成本,從而壓縮企業研發的資金投入,對綠色創新帶來負向沖擊。環境規制的“綠色悖論”效應還會使得企業為保持利潤最大化,打破市場供求均衡關系,加重環境污染和能源消耗,可見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效果取決于綠色創新獲得的“創新補償”效應和正外部效應,能否彌補其進行綠色創新活動所引致的成本增加及環境惡化在內的負向沖擊。此外,二者間作用效果可能會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不同而變化,如低強度的環境規制使得污染企業在該區域形成高污染集聚區,降低綠色創新水平;而高強度的環境規制有助于“騰籠換鳥”,為本區域高質量、低污染企業提供較大的經濟活動空間,從而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環境規制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表現為調節作用
三、關鍵變量的測度與特征分析
(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測度與分析
目前,產業集聚的測度方法主要包括首位度指數、行業集中度、區位熵、赫芬達爾系數、空間基尼系數和E-G指數等,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數據的可獲得性,筆者選取區位熵法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進行測量,具體測度方法如下:
ser_aggpt=(PSpt/PSt)/(Ppt/Pt)
(1)
其中,ser_aggpt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PSpt為t年p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人數,Ppt為t年p地區全部就業人數,PSt為t年全國生產性服務業就業人數,Pt為t年全國就業人數,該指數越高,表明該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越高。
基于《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并參照學界較為認可的劃分標準,筆者以五個行業(30)五個行業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服務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其中,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其余為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作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考察對象,測度了2014—2019年中國省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同時計算出全國范圍的平均水平。表1報告了31個省級區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具體數值, 綜合分析表格數據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全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均值保持在1左右,其中,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及黑龍江分別以2.62、1.91、1.28、1.14及1.13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均值排在全國前五名,由此可以推定:經濟水平較高和基礎設施較為完善的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整體程度較高。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斷層領先”的區域較少,使得中國整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不高。為此,中國政府仍需進一步深化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重視程度,正確引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在適當區域內形成有效的產業集聚。

表1 2014—2019年中國31個省級區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
(二)企業綠色創新水平
學界關于綠色創新水平的衡量主要從投入和產出兩個視角出發,首先,投入視角主要包括研發人員數量和研發經費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之比等,該方法往往由于企業創新過程的不確定性使得測度結果存在偏高的可能;其次,產出視角則主要包括新產品產值占主營業務收入之比和專利的申請及授權等方面,該方法克服了投入視角下的測度缺陷。其中綠色專利包括綠色發明專利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而發明專利技術性及創新性更強。由此,本文從產出視角出發,選取上市公司綠色發明專利授權量(lsfmsq)作為企業綠色創新的代理變量,并利用上市公司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授權量(lsxxsq)和綠色專利授權總量(lssq)分別作為綠色創新水平的替換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
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局(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SIPO)綠色專利數據,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企業各項指標作為研究對象,筆者整理并測度出2014—2019年間企業綠色創新水平多維度相關變量。根據圖1報告的2014—2019年間中國企業綠色發明專利、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及綠色專利授權總量的變化趨勢可知:首先是中國綠色發明、綠色實用新型及綠色專利授權總量均在整體上呈現出穩步上升趨勢,可以推定中國綠色創新水平正在逐年提升;其次是綠色發明專利授權總量始終較低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可見中國技術與創新型綠色成果的產出仍存在較大進步空間;最后是相比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中國綠色發明專利增幅較大,且其與綠色實用新型專利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企業已經逐漸意識到綠色發明專利的專業性及重要性,且正不斷提升自身以綠色發明專利為核心的綠色創新水平。

圖1 2014—2019年中國企業綠色發明專利、綠色實用新型專利及綠色專利授權總量
圖2進一步報告了2014—2019年間中國七大類型(31)“國際專利分類綠色清單”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綠色專利進行了七大分類,分別為:替代能源、運輸、節能、廢物管理、農林管理、行政監管設計和核能發電。綠色發明專利授權量變化趨勢,分析可知:一方面,綠色發明專利整體浮動變化較為平穩,其中,替代能源、運輸、節能、廢物管理、行政監管設計及核能發電領域發明專利授權量整體表現出穩步上升趨勢;另一方面,節能專利授權量增幅較大且逐漸占據領先位置,專利授權水平較低且變化較為緩慢的領域分別是運輸、農林管理、行政監管設計及核能發電,可見增加替代能源、節能及廢物管理領域綠色發明專利的產出,對中國整體綠色創新水平提升以及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筆者篩選整理出2014—2019年間,中國各地區上市企業綠色發明專利授權總量均值,并按從高到低的順序排列。圖3報告了排名前十五位地區的具體占比情況,綜合分析可得:綠色發明專利授權總量排名前十的區域分別為:北京、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上海、河南、安徽、福建及湖南,且前十位地區綠色發明專利授權總量約占全國90%以上,可以推定擁有良好經濟基礎和完善公共治污基礎設施地區的綠色創新整體水平相對較高。

圖2 2014—2019年中國企業七類綠色發明專利授權總量

圖3 2014—2019年中國各地區企業綠色發明專利授權量均值占比(%)
四、計量結果與分析
(一)計量模型設定及變量的選取
1.計量模型的構建
本文構建如下基準回歸模型分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機制:
lsfmsq=α1+α11ser_aggpt+β1Xt+γp+γi+γt+εipt
(2)
其中,lsfmsq為企業綠色創新水平;ser_aggpt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Xt控制變量;γp、γi及γt分別表示省份、個體及時間三個維度的固定效應;εipt為隨機誤差項,且均采用穩健性標準誤;α1、α11及β1分別表示常數項、核心解釋變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系數及控制變量的系數。
組網設計需要與住宅結構相結合,不同住宅其組網的設計也不同,在進行組網設計的過程中,必須要進行充分的考慮,特別是在使用無源光網絡時性需要對其傳輸的距離進行考慮,有效的將分路器級聯進行控制,使其始終保持在二級以內。
2.控制變量的選取
基于現存研究,本文從多個視角出發考慮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因素,并選取省級層面及企業層面的相關數據作為控制變量。省級層面:數字普惠金融指數(int):數據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32)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濤、張勛、程志云,《測度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編制與空間特征》,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19年。;企業層面:企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由LP法測度結果表示;企業規模(size),由企業總資產對數表示;企業成熟度(age),由企業成立年限對數表示;企業管理費率(mfr),由企業管理費用占營業收入表示;企業杠桿(debt),由企業資產負債率表示。
(二)基準檢驗與分析
基于上述計量模型,表2報告了控制年份、區域和個體固定效應下的基準檢驗回歸結果,隨著控制變量的逐步加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系數顯著為正,且通過了至少5%的顯著性檢驗,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上述結果出現的原因可能是:首先是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作為具有知識、技術和人才密集型特征的生產性服務業,其在一定區域內部的集聚可以將前沿技術和高質量人才匯聚于此,在激發先進技術之間有效碰撞,創造新思想與新技能的同時,通過人才的“蓄水池”效應,促進顯性與隱性知識的溢出效應,不僅有助于提升企業員工的綜合素養及環保意識,使得企業綠色轉型升級理念深入人心,還促使企業及時準確地掌握前沿知識和技術,從而對綠色技術創新帶來積極影響,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將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 其次是專業化效應。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推動企業專業化分工及協作水平提升, 從而降低中間品無效投入帶來的損失及綠色資源的浪費,在實現企業間基礎設施、資本、信息和人力等要素資源共享的同時,提升資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和企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對企業綠色專利成果轉化、應用和推廣能力的提升帶來積極影響,有助于深化企業綠色創新水平;最后是成本效應。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擴大行業規模,從而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使得企業綠色研發、生產和銷售等各項環節的中間成本顯著降低,有助于企業將資金集中于綠色研發領域,為企業綠色創新提供重要的資金支撐。此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將激發企業間的良性市場競爭,進一步倒逼企業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綠色資源利用效率,使得核心競爭優勢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基于此,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利于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去污化”并舉,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由此,本文的假設1得以驗證。

表2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回歸結果
(三)內生性檢驗
考慮到本文刻畫的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實現地區環境優化與技術進步,從而吸引更多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匯聚于此,使得該地區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進一步提升,即該模型的兩大核心變量間可能存在互為因果關系的內生性風險。為此,該部分利用兩種工具變量以及能夠克服內生性問題的聯立方程法,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內生性檢驗。首先,筆者選取以下兩種工具變量:其一,Bartik(33)Bartik Timothy J.,Who Benefits from State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Upjohn Institute,1991.提出了利用份額移動法(Shift-Share IV,SSIV)構建工具變量,本質是基于核心變量的初始份額結構以及其總體層面的增長率構造出同時滿足相關性與外生性的工具變量(以下簡稱:Bartik工具變量),該工具變量在與核心解釋變量高度相關的同時,與其他殘差項不相關。為此,透過Bartik工具變量進行模型內生性問題處理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認可和使用。借鑒張濤等(34)張濤、司秋利、馮冬發:《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空間溢出與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求是學刊》2022年第2期。及趙奎等(35)趙奎、后青松、李巍:《省會城市經濟發展的溢出效應——基于工業企業數據的分析》,《經濟研究》2021年第3期。的處理方法,基于本文研究的五類生產性服務業各行業初始年份(即2014年)就業份額以及全國該行業就業增長率,構造處理內生性問題的Bartik工具變量1(Bk_iv),具體測度模型如下:
(3)
式中,Bk_ivpt為p地區t年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Bartik工具變量1,P_aggipt0表示p地區初始年份t0年(即2014年)生產性服務業i的就業份額,Git表示全國層面生產性服務業i在t年的就業水平相對于初始年份t0年的增長率。可見該模型利用初始狀態P_aggipt0與具有外生性特征的全國增長率Git的交互項,建立基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估計值的工具變量1,一方面,其與核心解釋變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高度相關,另一方面,同時滿足了工具變量獨立性和外生性的要求,進而推定透過該工具變量檢驗內生性問題具有較強的客觀性及科學性;其二,以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一期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2(ser_agg_iv),以進一步保證內生性檢驗結果的穩健性。其次,更換回歸方法為同樣能夠克服內生性問題的聯立方程法。筆者選取就業人員中受高等教育(大學專科及以上學歷)人員占比和各地區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分別作為人力資本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的代理變量,并以式(2)為聯立方程的第一個方程,以ser_aggpt=β1+β11lsfmsq+μ1Lt+εipt為第二個方程,式中Lt為控制變量,即人力資本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β1、β11和μ1分別表示常數項、綠色創新水平的系數及控制變量的系數,其余變量含義均與前文保持一致。
1.工具變量法
表3報告了在更換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表示方法見后文說明)條件下,分別基于工具變量1和工具變量2的2SLS回歸結果,LM檢驗及KP W rk F檢驗均表明該模型不存在過度識別和弱識別的情況,證實了該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此外,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積極作用在至少1%的顯著性水平下穩健成立,由此,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本文結論的作用機制依舊穩健。

表3 企業綠色創新的內生性檢驗(2SLS,更換被解釋變量)

(續表)
2.聯立方程法
表4報告了更換計量方法為聯立方程組且更換被解釋變量后的回歸結果,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有效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提升,與前文檢驗結果一致,進一步表明了在使用多種克服內生性方法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之間的機制依舊成立。

表4 企業綠色創新的內生性檢驗(聯立方程法,更換被解釋變量)
(四)穩健性檢驗
1.更換測度指標
表5中(1)—(3)列和(4)—(6)列分別報告了更換被解釋變量為上市公司實用新型專利授權量和綠色專利總授權量的回歸結果,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表現為正,且分別通過了至少1%的顯著性檢驗,可見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穩健成立的。

表5 企業綠色創新的穩健性檢驗(更換被解釋變量)
2.加大約束力度
表6中(1)—(2)列、(3)—(4)和(5)—(6)列分別報告了在加大約束力度并更換企業綠色創新指標的回歸結果,可見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及顯著性均與前文基本一致,表明在加大約束力度的條件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效果保持不變,即該結論通過了以上多種穩健性檢驗,進一步驗證了假設1。

表6 企業綠色創新的穩健性檢驗(加大約束力度,更換被解釋變量)

(續表)
(五)異質性檢驗
為充分考察異質性條件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機制,本文從生產性服務業行業異質性及綠色創新發明專利異質性雙重視角出發展開探究。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可以劃分為高技術和低技術型,綠色發明專利可以細分為七大類。
1.生產性服務業異質性
表7中(1)—(3)列和(4)—(6)列分別報告了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high_seragg)和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 (low_seragg) 對更換被解釋變量后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回歸結果,可見異質性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依舊有效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進而驗證基準檢驗結論的可靠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綜合比較以綠色發明專利授權量(見表7的方程(1)和方程(4))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授權量(見表7的方程(2)和方程(5))為被解釋變量的計量方程,可以發現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在前者中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均大于其在后者中的顯著性水平,且兩類集聚作用系數絕對值的大小也與上述強弱關系非常相似,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比于綠色實用新型專利,高技術生產性服務業和低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均對綠色發明專利具有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

表7 生產性服務業產業異質性檢驗(2SLS,更換被解釋變量)
2.綠色創新發明專利異質性
表8報告了七類異質性發明專利授權量作為企業創新代理變量下的回歸結果,其中,(1)—(6)列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該六項發明專利的作用系數均顯著為正,第(7)列顯示解釋變量對第七項發明專利,即核能發電專利授權量的回歸結果并不顯著。出現該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考慮到核能發電企業的工作重心在于發電,而發電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問題。基于此,為滿足充分保證核安全的要求,核能發電企業往往不會輕易使用新技術或新方法(36)李上元、謝岱良、李鴻飛:《核能發電企業科研管理創新的思考》,《大眾科技》2018年第9期。,使得核能發電企業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綠色創新作用機制的敏感度較低;此外,涉及到核能發電領域的企業相對較少,進一步引致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核能發電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作用效果并不顯著。

表8 企業綠色創新發明專利異質性檢驗(2SLS)
五、進一步拓展分析
如何實現人民對“綠色生活”和“高質量生活”的雙訴求始終是政府和學界思考的主要問題,然而,市場機制依靠自身調節功能實現二者同步發展的難度較大。為此,政府對環境治理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和干預政策,以確保企業在發展自身經濟的同時,減緩其為環境帶來的負外部性。其中,政府環境規制為企業帶來外部壓力及成本增加效應,迫使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升級,或將成為同時實現“綠色”和“發展”的一種有效手段。這不禁引發了筆者的進一步思考:環境規制是否會對本文所研究的生產性服務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關系帶來影響呢?探究環境規制在前者對后者作用間的影響機制,是有效發揮集聚經濟效應的可行之徑。此外,從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源頭視角出發,可知其重要影響因子之一是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升級的基本落腳點是產業集聚,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空間集聚水平的提升。為此,生產性服務業對中國主要高技術就業人員的吸收和聚集,使得其產業內部結構逐漸優化升級并不斷發揮集聚的積極效應。可見,系統考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作用關系,對于實現環境質量與經濟增長質量雙重優化具有重大意義。
(一)環境規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作用關系的調節效應
基于前文理論研究,環境規制對綠色創新可能產生促進和抑制兩種作用效果,總體作用方向則取決于二者的強弱關系,且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作用機制會受到環境規制強度變化的影響。由此,筆者將工業污染源治理完成投資占主營業務成本的比值作為環境規制(hjgz)的代理變量,并在模型中引入環境規制、環境規制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交互項(ser_agg×hjgz)以及二者的二次項,進而考察環境規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作用關系的調節效應。
表9中(1)—(2)、(3)—(4)和(5)—(6)列分別報告了在更換被解釋變量條件下的回歸結果,可見環境規制及其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交互項的水平項均顯著為負,平方項均顯著為正,且通過了至少1%的顯著性檢驗。該回歸結果表明:一方面,環境規制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作用機制呈現為U型,即隨著環境規制強度的增加,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表現為先降低后升高的趨勢;另一方面,環境規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作用效果的影響機制為U型,即環境規制的存在使得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表現為先抑制后促進,證實了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的作用受到環境規制的調節作用。該現象產生的原因在于:首先是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未達到一定門檻值時,環境規制對綠色創新的抑制作用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環境規制的加強,高污染企業集聚于環境規制相對較弱的區域,進而增加其對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消耗,為集聚地帶來負向外部效應,不利于企業綠色轉型升級;其次是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超過一定門檻值時,集聚產生的專業化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占據主導地位,進而促進企業綠色創新水平顯著提升。由此,驗證了本文的假設2。

表9 環境規制的調節效應檢驗(2SLS,更換被解釋變量)
(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經濟增長
本文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lnPgdp)作為經濟增長的代理變量,在能夠克服內生性條件下,考察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及企業綠色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并進一步利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對數(lnincome)表示經濟增長,進行替換被解釋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表10中(1)—(2)列及(3)—(4)列分別報告了在更換被解釋變量的情況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結果,可見隨著控制變量的加入,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穩健為正,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水平提升。上述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在于:首先是專業化效應。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發揮產業內集聚效應,促進專業化人才和資源的集中與流動,發揮集聚的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使得分工體系的專業化程度得以提升,進而保證了經濟發展水平的穩步推進;其次是多樣化效應。集聚帶來的產業間集聚效應,有助于實現行業間信息、基礎設施和知識的高效共享,企業跨產業間相互交叉碰撞、取長補短,進而形成高效協作和細化分工的多樣化網絡,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最后是競爭效應。產業集聚推動企業間形成開放共享環境下行業內和行業間的良性競爭,進而提升企業勞動生產率,以保持其核心競爭優勢,使得集聚的專業化效應和多樣化效應得以充分發揮和深化,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表10 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回歸結果(2SLS,更換被解釋變量)

(續表)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經濟新常態背景下,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典型特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推動中國制造業結構轉型升級。此外,綠色創新能有效破解可持續發展、技術創新及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瓶頸,逐漸成為調整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突破口。為此,發揮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的提振作用,助力中國躋身創新型國家行列,并推動經濟實現綠色轉型升級,是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重要舉措,可見細致剖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影響渠道具有深遠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基于此,在科學刻畫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指數和企業綠色創新水平的基礎上,首次從企業綠色發明專利視角出發,將產業集聚指數下沉至企業層面,細致剖析前者對后者的作用機制,得到的結論主要有:首先,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該結論通過了基準檢驗、利用移動份額法構建Bartik工具變量等的內生性檢驗、加大約束力度及更換被解釋變量等多視角的穩健性檢驗,可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之于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和激發企業綠色創新活力,進而推動制造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為此,進一步引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有機”集聚,是中國順應可持續發展戰略,躋身全球創新型國家行列的關鍵之舉。其次,環境規制在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企業綠色創新作用間表現出“先抑后揚”的U型的調節效應,可以推定:加大可持續發展相關政策的力度,創新監管及政策組合形式,可以成為激發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綠色創新效應的重要途徑及動力源泉。最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增長,這進一步表明本文刻畫的經濟變量是中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為此,提高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推動企業實現綠色轉型升級,不僅能有效破解綠色環保、技術創新及經濟增長所面臨的瓶頸,更是促進中國目前及未來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本文不僅從企業綠色專利視角為考量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對綠色創新水平的作用效應提供了細致的經驗證據,還具有以下重要的政策啟示:首先,考慮到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有助于促進企業實現綠色創新發展,一方面應提升與地區比較優勢相匹配的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水平,引進高技術人才,形成多元化和高水平的產業集群;提升地區配套基礎設施水平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打造優良的營商及綠色創新環境。另一方面,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互聯網等前沿技術融合發展,打造智能化產業鏈,為企業實現綠色專利成果化和產業化搭建數字化橋梁。其次,考慮到環境規制的U型調節機制,應提升環境規制水平,打好多元政策的“組合拳”。其一,在優化綠色創新發展模式及標準化監督管理體系的同時,加大對違反規定企業的懲處強度,進而實現“創新補償”效應為企業帶來的綠色轉型升級。其二,在強化環境規制政策的初期,應同步提高對企業各項補貼政策的力度,緩解企業在順應環境規制時“遵循成本”效應的負面沖擊。最后,鑒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綠色創新效果存在細微的異質性特征,一方面,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在穩固區域比較優勢的同時,繼續加大教育及技術研發投入,發揮集聚的知識和技術溢出效應,輻射帶動其他地區產業向綠色和高附加值生產模式轉變。另一方面,引導缺乏比較優勢的區域建設多元化高技術產業園區,發揮各高校及科研企業的技術研發優勢,助力低端產業向高技術產業的生產模式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