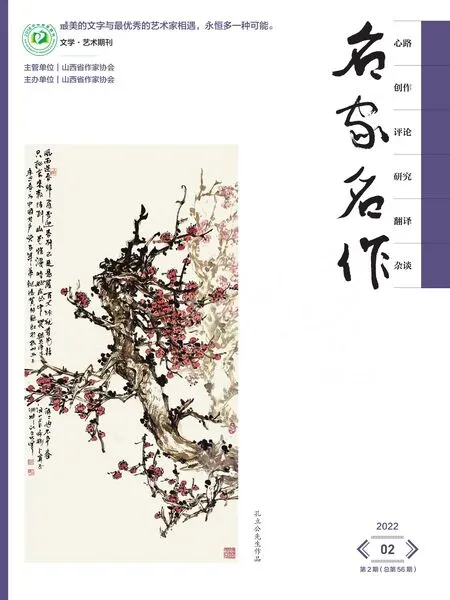波茲曼《娛樂至死》中的后現(xiàn)代文化邏輯演繹
張雯雯
一、從現(xiàn)代到后現(xiàn)代
在詹姆遜看來,“美感上的民本主義”最強(qiáng)烈地體現(xiàn)于建筑藝術(shù)中。從代表精英主義和權(quán)威主義的“龐然大物”,到接近民生的“鴻運(yùn)大飯店”,高等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美感差異與界限在不斷消逝溶解。發(fā)軔于對建筑藝術(shù)的爭論,自20世紀(jì)五六十年代,后現(xiàn)代主義的浪潮逐漸波及各個(gè)領(lǐng)域,成為現(xiàn)如今的主流文化邏輯,呈不可逆轉(zhuǎn)之態(tài)勢。
現(xiàn)代主義盛行的時(shí)代里,資本的邏輯與文化的邏輯兩者尖銳對立,后者拒絕被前者同化。而后現(xiàn)代主義誕生于資本與科技的搖籃之中,與之共謀。用詹姆遜的話說:“后現(xiàn)代主義是資本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產(chǎn)物,這一時(shí)代的主要特點(diǎn)在于,現(xiàn)代技術(shù)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特別是信息傳媒技術(shù)的發(fā)展,以及世界經(jīng)濟(jì)、文化全球化的社會(huì)背景。表現(xiàn)在文化上就是文化日益商品化的趨勢,商品化的趨勢全面滲透到文化領(lǐng)域,文化生產(chǎn)形成產(chǎn)業(yè)機(jī)制,從以往的生產(chǎn)本位轉(zhuǎn)向消費(fèi)本位,完全迎合市場和消費(fèi)大眾的需要,以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為宗旨。”資本運(yùn)作是文化的背后力量,而文化背后的真相,“就是血腥、殺戮與死亡”。
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在詹姆遜的眼里是缺乏深度的,沒有典型,堆砌在文化世界中的是大量運(yùn)用剽竊、抄襲、擬造、戲仿等手段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作品。事實(shí)如此,相比于歷史不同階段里風(fēng)格自成一派的人物來說,當(dāng)下文化的主體風(fēng)格淡薄,真正的個(gè)人風(fēng)格也是鳳毛麟角。就好比談及后現(xiàn)代的文學(xué),流派是醒目的字眼。“垮掉的一代”彰顯著一眾人的狂放不羈、頹廢墮落;“黑色幽默”在放松滑稽中沉悶與絕望;而“荒誕派戲劇”中的戈多似乎永遠(yuǎn)不會(huì)出現(xiàn)。文化流派現(xiàn)狀“只有多元的風(fēng)格,多元的論述,卻不見常規(guī)與典范,更容納不了以常規(guī)典范為中心骨干的單元體系”。 換句話說,縱使人們用不同的標(biāo)簽去定義這些不同的流派風(fēng)格,但是真正核心的價(jià)值體系卻無跡可尋,并且流派對應(yīng)下來的個(gè)人風(fēng)格,在詹姆遜眼里,也是矯揉造作的,有嘩眾取寵的嫌疑。
不僅是文學(xué)領(lǐng)域,社會(huì)體貌的方方面面也在迅速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常規(guī)在解體,最初的典范也淪落為至今那些“中立、呆板、僵化、物化的‘媒介語’”。各行各業(yè)有其專門的語言,而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信息傳媒也在奉行著后現(xiàn)代主義的這一套話語系統(tǒng)與文化邏輯。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所揭露的一系列文化現(xiàn)狀,正是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演繹。從新的媒介,到新媒介表達(dá)文化的手段,再到新媒介所承載和輸出的文化內(nèi)容,波茲曼所拋出的問題,似乎在詹姆遜的言論中都能找到相應(yīng)的聯(lián)系和對應(yīng)的答案。
二、文化邏輯演繹的具體法則
(一)拼湊法與碎片化
從“讀文時(shí)代”到“讀圖時(shí)代”,圖像不再滿足其原本的地位與作用而開始越俎代庖,試圖“把文字驅(qū)趕到背景里,有時(shí)干脆就把它驅(qū)逐出境”。 波茲曼在談及此問題時(shí),首先對電報(bào)給印刷術(shù)帶來的威脅進(jìn)行了審視。他認(rèn)為電報(bào)的出現(xiàn)使得信息開始淪為一種商品,就像詹姆遜所言文化開始淪為資本附庸被投入市場,用途與意義被棄之不談,有無商業(yè)價(jià)值才是其存在或者消失的標(biāo)準(zhǔn)。同時(shí),電報(bào)使話語內(nèi)容開始無聊,表現(xiàn)無力以及形式散亂。經(jīng)由電報(bào)傳輸出來的文字信息,有趣更容易被人們接納,而無趣或者太過嚴(yán)肅,便會(huì)淡出大眾視野。這里并不存在什么矛盾,因?yàn)樯铄涞男畔⑹浅H穗y以理解與消化的,因此便會(huì)歸為無趣一類;而大眾喜愛的有趣信息,通常便是無聊的內(nèi)容,然“有趣”也只是低級(jí)趣味一類而已。在買賣的用途上,“有趣”的信息更具市場,自然真正有趣的內(nèi)容要委曲求全,而變得無聊松散。誠然,即使電報(bào)只能傳遞文字,還不具備圖像生成與傳播的功能,但其“分割語境”、追隨市場價(jià)值、娛樂功能大于實(shí)用功能的特征,正是在暗示隨后而來的圖像時(shí)代的發(fā)展道路,它給未來圖像對文字的沖擊埋下了伏筆。
于是,相機(jī)的發(fā)明與照片的盛行加快了這一進(jìn)程。和脫離語境的電報(bào)信息一樣,照片開始把世界再現(xiàn)為一系列支離破碎的事件。動(dòng)態(tài)的世界被定格成一幅幅靜態(tài)的、不連貫的、碎片化的圖景。攝影的手法是碎片化的,生成的圖片也是意義的斷裂式表達(dá)。它采用的是摹仿的手法,它可以定格一個(gè)人或者一棵樹,將其稱為自然的畫作,卻不是真正的自然。因?yàn)檫@一媒介試圖將形形色色和變化多端的種種狹隘簡單地分類,之所以斷定其狹隘,是因?yàn)樗苡涗浀闹皇翘乩选O啾扔谡Z言以概念的方法表達(dá)世界,照片只是將世界表現(xiàn)為一個(gè)缺乏靈魂的死物,在詹姆遜眼里,只是“一種空心的摹仿——一尊被挖掉眼睛的雕像”。歸根到底,“插圖”“配圖”的限制意義在于,照片原本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修飾與補(bǔ)充。并且照片本身所賦予的意義是不完整的,它無法像語言那般能夠輕易地詮釋、理解和驗(yàn)證現(xiàn)實(shí)。然而現(xiàn)實(shí)卻是,人們甘愿掉進(jìn)這一陷阱,生活在以碎片拼湊的圖片世界中,難以體會(huì)最真的本質(zhì)。
電報(bào)傳遞文字信息,照片表達(dá)圖片理念,電視則是圖文并茂并兼具傳聲功能,其展現(xiàn)出來的內(nèi)容也由靜態(tài)轉(zhuǎn)向動(dòng)態(tài),更加栩栩如生,以至于欺騙大眾說全世界就藏在這一小塊熒屏背后。電視的發(fā)明具有劃時(shí)代的意義,它在《娛樂至死》中,也是波茲曼傾注筆墨的主角。它的出現(xiàn),可謂標(biāo)志著真正的“娛樂業(yè)時(shí)代”的來臨。依波茲曼所言,電視本是無足輕重的,它只是一種修辭的工具,最多作為一種全新的媒介出現(xiàn)在人類的生活中。然而知識(shí)分子和批評家卻對此強(qiáng)加最高使命,最終將電視置于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文化對話載體之地位。事實(shí)上,電報(bào)信息試圖改寫人類思維模式,圖片信息滿足感官刺激,甚者電視文化的核心要素即是通俗易懂的“平白語言”,要能在短時(shí)間內(nèi)滿足視覺和聽覺的雙重享受。因此電視文化需要大量的碎片素材,更需要專業(yè)精良的拼湊(剪輯)手法,從形式到內(nèi)容,已經(jīng)完完全全地碎片化掉了。“無聊的東西充滿了意義,語無倫次變得合情合理。”大眾可以經(jīng)由電視獲取各個(gè)領(lǐng)域的消息動(dòng)態(tài)和不同專業(yè)的文化知識(shí),卻只是一味地接收,碎片文化的雜亂堆砌,思維難成系統(tǒng)。最終的狀況就是“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喝”,人們在信息的海洋中迷失了自我。
由于時(shí)代的局限性,波茲曼沒有預(yù)想到互聯(lián)網(wǎng)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這一媒介進(jìn)一步打破時(shí)間和空間的束縛,印證著“娛樂至死”的當(dāng)下。電視更多是文化的單向輸出,而網(wǎng)絡(luò)充斥著回應(yīng)的聲音,不同的價(jià)值觀縱橫交錯(cuò),盲目的追隨者絡(luò)繹不絕。如果說電視的觀眾只是文化的被動(dòng)接受者,他們作為主體的能動(dòng)性被支離破碎的時(shí)間和被割裂的注意力所抹煞了,那么在網(wǎng)絡(luò)里,清晰的主體卻更加難以找尋。因?yàn)樵谶@里,剽竊、拼湊的手法更為高超,碎片化信息組合的能力更加強(qiáng)大。抄襲者或謠言傳播者可能是一個(gè)人,可能是一個(gè)團(tuán)隊(duì)、一眾人,也可能是一個(gè)指令,甚至可能只是一個(gè)機(jī)器思維系統(tǒng),它利用大數(shù)據(jù),制造人們可能感興趣的話題。大眾每天接收花樣繁多的信息,依靠自身的常識(shí)或經(jīng)驗(yàn)、對事物的偏好判斷真假,而對真的“真”、真的“假”不管不顧,更不會(huì)去探尋背后的邏輯與原因。信息的制造者和接受者都沒有明確的主體性可言,因?yàn)樗麄兊膬r(jià)值觀都是被大環(huán)境閹割掉了的殘次品,或是衍生出來的千篇一律的“復(fù)制品”。意義不再完整,從形式糜爛至思維深處。就如詹姆遜所言,“今天一切的情感都是‘非個(gè)人的’,是飄忽忽無所主的”。
文化拋棄傳統(tǒng)的闡釋模式,依賴于電報(bào)、照片、電視、網(wǎng)絡(luò)等媒介,將“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為影像,讓時(shí)間斷裂成一系列永恒的現(xiàn)在”。信息處理方式的拼湊法與內(nèi)容的碎片化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就是,智力的功能只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真正理解它們。人該有的“富有邏輯的復(fù)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于自相矛盾的憎惡、超長的冷靜與客觀以及耐心等”特質(zhì)統(tǒng)統(tǒng)被拋棄了。人們不再低頭沉思,而是在歇斯底里中跌入娛樂的深淵。
(二)娛樂先行
當(dāng)圖像開始占據(jù)文化中心之時(shí),就意味著人們在對事物給予關(guān)注時(shí),將重心從大腦的深度思考轉(zhuǎn)向了膚淺表面的感官享受。詹姆遜表明,“新潮作者在拼湊之余,的確還能設(shè)法使我們身處的日常文化現(xiàn)象浸透著一份幽默感。”而這份“幽默感”就是文化的娛樂先行主義。大眾在“自我陶醉的映像世界中”,迫使文化邏輯從嚴(yán)肅轉(zhuǎn)向戲謔,使自我理性讓位于情感的過度狂歡。
縱觀當(dāng)下的文化狀況,絕大部分內(nèi)容的確正由嚴(yán)肅轉(zhuǎn)向戲謔,充斥著娛樂的聲音。波茲曼擔(dān)憂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xiàn)一切經(jīng)歷的形式。娛樂可表達(dá)自身,但當(dāng)所有內(nèi)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文化邏輯本身就出現(xiàn)了問題。在政治領(lǐng)域,總統(tǒng)競選被關(guān)注的是競選人的外表、眼神、微笑、俏皮話,而不是表達(dá)觀點(diǎn)時(shí)是否運(yùn)用了復(fù)雜的措辭、充分的證據(jù)和邏輯。 新聞節(jié)目開始蒙蔽觀眾,被娛樂過度包裝,剝奪大眾獲取真實(shí)信息的權(quán)利。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已不合時(shí)宜,有趣味的課堂才受學(xué)生歡迎。教育的宗旨也發(fā)生了改變,原本是為了讓學(xué)生擺脫現(xiàn)實(shí)的奴役,如今卻使他們?yōu)榱诉m應(yīng)現(xiàn)實(shí)而改變自己。商業(yè)廣告違背原則,用圖像代替語言,使企業(yè)從生產(chǎn)有價(jià)值的產(chǎn)品轉(zhuǎn)向設(shè)法使消費(fèi)者感覺產(chǎn)品有價(jià)值。一切都以娛樂為原則,嚴(yán)肅的公眾話語開始失去價(jià)值、失去信服力。人們被這種愉悅感麻痹了神經(jīng),把娛樂當(dāng)成最后的避難所。大眾在娛樂所創(chuàng)造的虛假自由幻象里,一味地鼓掌,而放棄了反思。
娛樂性的背后犧牲的是文化的歷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所謂的娛樂至死就是物極必反,在過度強(qiáng)烈的個(gè)人情感中直至最后的“消逝”,在欣喜若狂中自我毀滅。個(gè)人的理性讓位于情感的狂歡,最終“自我”不復(fù)存在,真正的情感無所寄托。
三、結(jié)語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語境之下,人人皆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消費(fèi)者,并能切實(shí)感受到貫穿其中的文化邏輯之精粹。“娛樂至死”的文化現(xiàn)狀即是人們沉浸在碎片化與拼湊的圖像單元中,追求日常生活的狂歡與“歇斯底里的崇高”,嚴(yán)肅不復(fù)存在;又迷失在空間的維度里,忘記過去與歷史,主張當(dāng)下即是永恒。
當(dāng)碎片化的讀圖模式取代系統(tǒng)深層的文字闡釋模式,語言中心轉(zhuǎn)向視覺中心時(shí),人們在感官享樂中消磨著最后的理性思考。縱觀當(dāng)今的文化現(xiàn)狀,人們多是以消費(fèi)的態(tài)度接收傳媒信息,以享樂作為最終目的。大眾的側(cè)重點(diǎn)轉(zhuǎn)向了消費(fèi)文化而不是理解文化本質(zhì)或自身創(chuàng)造文化。圖像雖打破了文字線性排列的時(shí)間局限性,進(jìn)一步獲得在空間中生存和傳播的可能,卻也在淡化時(shí)間感的進(jìn)程中逐漸將歷史遺忘,使得大眾成為奉行當(dāng)下主義的娛樂動(dòng)物。歷史特性在娛樂至死的時(shí)代大大消褪,大眾處于危險(xiǎn)的境地,淪落為無根無源的浮萍,空剩下一副娛樂的軀殼,丟失了“歷史中的人”之身份。理性深度和歷史深度的雙重缺失,人在后現(xiàn)代的文化邏輯體驗(yàn)中,未來的命運(yùn)和發(fā)展又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