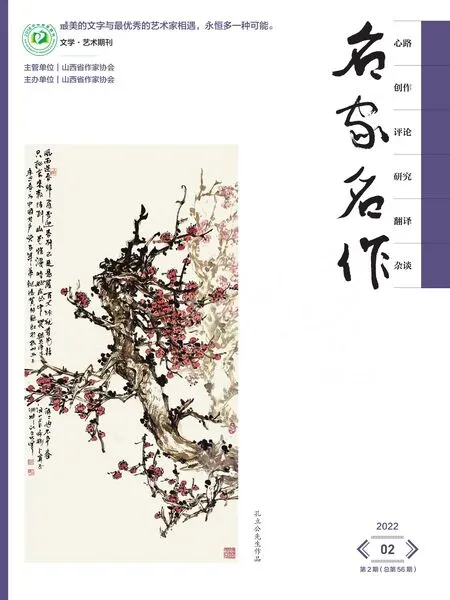從《個人的體驗》分析大江文學中的存在主義
黃馨靚
大江健三郎是繼川端康成后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歸納了大江創作的總體特征:“人生的荒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這些大江從薩特獲得的哲學要素貫穿作品的始終。”毫不夸張地說,要想真正理解大江,就必須先理解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
從學生時代開始,大江就大量閱讀了薩特、加繆等人的存在主義文學和理論書籍,此時的大江的創作帶有明顯的模仿薩特作品的痕跡。總體來說,大江這一時期的作品文筆較為稚嫩,對存在主義的理解有生搬硬套之嫌。步入社會以后,大江的創作開始有了新的轉向,他通過性來探討人的存在問題,試圖為我們揭示戰后日本文化的本質特征。日本戰后是一個特殊時期,是很多日本作家創作的時代背景,大江健三郎也不例外。當時二戰結束后,日本社會開始進入休養生息的階段,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但與此同時個體的存在卻面臨著諸多矛盾和困境,如核武器對人的威懾、個人理想與現實的沖突等。因此,這一時期的文學較之以往也要發生轉變,從僅僅關注戰爭和戰后生活轉向對日本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關心。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大江熱衷在作品中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危機和核威脅之下,人的孤獨與選擇難題,以及人與人的隔閡與扭曲關系,以存在主義思想為探索問題的手段,并且使存在主義思想成為探索的最終目的。
從這一時期的創作可以窺見,大江在積極消化薩特存在主義后融入了個人的思考和理解,即日式的曖昧的態度。《性的人》就是大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但這部作品發表不久后,大江創作走到了一個平臺期。正當他思索接下來的創作方向時,發生了兩件對他有重大影響的事,這兩件事也直接影響了大江之后的創作。一是他的兒子患有先天性疾病,這讓大江體會到了人生突如其來的不幸與選擇的困境;另一件事是“廣島之行”,這次旅行讓大江看到經歷了巨大災難的普通人民仍然選擇直面慘淡的人生,以堅韌不拔的意志對抗生活的不幸,“清楚地顯示著作為日本人的威嚴”。正是在體驗了這樣的生活“震顫”后,大江決定通過寫作實現“個人的救濟”,他“從個人的具體性出發,力圖將它們與社會、國家和世界連接起來”。
《燃燒的綠樹》和《個人的體驗》都是聚焦作者與患有腦疾的兒子之間共生的感情,書中體現了個人痛苦與民族苦難交織的雙重體驗。大江通過對個人命運和普遍人類命運的思考,以一個新的眼光看待人類世界的種種不幸和荒誕,并以這種思考和反思來規劃自己和主人公的行動。《個人的體驗》通過塑造“鳥”這樣一位經歷了痛苦和絕望,仍然選擇承擔父親的責任從而實現自己與新生兒的“再生”的人物表明薩特存在主義哲學的深刻價值,而大江高歌的“戰斗的人道主義”的行動更是對薩特存在主義的一種豐富和發展。
一、絕望困境下的“鳥”
在《個人的體驗》中,“鳥”從一開始就是以一個極其孱弱、神經緊張的形象出現的,他不僅身材像“鳥”一樣“矮小瘦削”,就連眼睛也像“鳥”一樣“溢滿膠液般遲鈍的光”,嘴巴也總是緊繃著。而且,主人公“鳥”的內心也像鳥一樣敏感而膽懦,時常伴隨著“激烈痙攣般神經過敏式的謹慎”。“鳥”在不安與從容的復雜情緒中等待著生活啟示的應驗——“疲憊老朽、備受子女拖累的‘鳥’呵”。在“鳥”的心中,一直有“最后一個充滿激動、緊張的機會”——非洲探險。然而,現實生活的種種困境阻礙了他夢想的實現。如果說家庭是禁閉“鳥”的牢籠,那么腦疝兒的降生就是關緊“鳥”生活牢籠的籠蓋。此時,他的人生陷入了極其痛苦的困境之中,即使“鳥”還在作麻醉自我的掙扎,他的“非洲探險”計劃仍像他心儀的貨架上的世界地圖一樣,只能被無限期擱置。這一時期,“鳥”的生活重心由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轉向了生與死的選擇之中,是選擇承擔腦疝兒的“生命之重”還是決絕地放棄他的生命?一開始,“鳥”儼然將自己置于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自己可以決定孩子的生命,畢竟孩子的生命源于自己。但這一設想不能讓“鳥”心中的道德重負有一絲一毫的減輕。“鳥”的內心發生了激烈的爭斗,實際上,“鳥”面臨著那個自由時代所有人都可能會面臨的困境。在一個自由選擇的氛圍和思想包圍之下,人類實際上逐漸被賦予了很多潛在的自由,因此人的選擇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自由選擇。但是欲望之外仍有道德的底線在不停徘徊,倫理道德的規范使“鳥”難以推卸責任。所以,他寄希望于嬰兒的自然死亡。一番斗爭未果的“鳥”被孤獨感和無力感包圍,無法自解,也無法與任何人訴說自己的苦痛。他深知自己是“無法擺脫那種整個的和重大的責任感的”,因為一旦他選擇承擔責任,也就選擇了自己將來的生活,“而且通過這一行動同時成了為全人類做出抉擇的立法者”,此時的“鳥”還不是“未來的人”,仍處在探索人的本質的階段。所以出于對腦疝兒的“惡心”,以及對荒誕人生的抗拒,他還是選擇了逃避這一切,去火見子家通過所謂的性愛療傷,用“做夢”代替現實。
二、從逃避到認識自己
院長“隱藏著某種陰謀”的建議一直在“鳥”的內心騷動著,面對植物人似的嬰兒,“鳥”時而看到這個異形的存在對自己的威脅,時而又對“負傷的阿波利奈爾”(兒子)感到蜜似的悲哀。盤踞在“鳥”內心深處的愧疚和恐懼加劇了他逃避的意識,他把對兒子的義務投向虛無的良心譴責之上,而非主動承擔責任的實際行動。
岳父拋出的酒精的誘惑讓“鳥”再次想要陶醉在酒精的世界里,于是“鳥”找到火見子當酒伴,火見子的“多元宇宙論”狡猾地把他引向道德負極,但卻減輕了“鳥”的負罪感,他感到自己在與這個世界和解。酒醒后的“鳥”發現孩子不僅沒有死亡,還對他的生活開始了強有力的攻擊和壓迫,這種恐懼心理上的“惡心”驅使“鳥”產生了過度的自我防衛。陷入極端利己主義的“鳥”意識到,“自己向卑劣的墮落之路跨出了第一步”,因為他是滿懷著羞恥和熱切的心情渴望著兒子的死亡。而這時,醫院中偶遇的矮個子父親呼喊著“斗爭,要斗爭”,這種“獨特的哀傷和弱者的威嚴神情”刺激了“鳥”,似乎開始把他引向了道德的正極。
在這個主觀性林立的世界里,從火見子對丈夫自殺的選擇性遺忘、矮個子男人對孩子的堅守中不難看出,人類有著普遍性的處境,“一切早先就規定了人在宇宙中基本處境的限制”無時無刻不在挑戰著人。“鳥”從“我思”中不僅發現了別人,也發現了自己,而關于自己的親切發現同時也揭示了別人的存在。“面對著我的自由是他的自由”,因此諸如火見子和矮個子男人的思想和意志都在指引著“鳥”,此時的“鳥”處于道德的中間地帶。
三、從懦夫到英雄
薩特表明,“選擇是可能的,但不選擇卻是不可能的”,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鳥”企圖讓孩子在等待手術的過程中死去,也就是說,他既不選擇放棄治療從而背上道德的羞恥感,也不選擇積極治療,來承擔養育一個植物人的責任。妻子提到的舊人菊比古喚醒了“鳥”的噩夢,因為“鳥”曾經像現在拋棄同是弱者的嬰兒一樣拋棄過菊比古。
解雇事件讓“鳥”第一次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他本可以假裝食物中毒,但是他說“那是我的責任”,這是“鳥”責任意識覺醒的開始,預示了“鳥”會選擇拯救孩子的光明結局。真正讓“鳥”無法自我欺騙的是戴爾契夫的話,他一語道破“鳥”一直在畏懼的東西——責任,“鳥”是以完全利己的姿態去拒絕他人(孩子)的生命,只因為他是孩子的父親,此時孩子是“鳥”用來對抗生活、繼續“做夢”的手段。
火見子和“鳥”最后的性交讓“鳥”擺脫了一直以來對女性生殖器官的恐怖記憶,他感受到單純的性享樂所帶來的踏實和滿足感,這與和妻子性交時的萎靡不振完全不同。為了延續這種不會長久的平安,“鳥”決定通過火見子的醫生朋友不留痕跡地殺死嬰兒,即使這樣會臟了自己的手。在去往醫院的途中,火見子因為不想軋到死去的麻雀,差點將車開進坑里。這也證明,即使多次慫恿“鳥”踏入充滿誘惑的地獄,火見子內心深處仍然保持著對生命的敬畏之情。在同性戀酒吧里,“鳥”與菊比古的重逢喚醒了他曾經的救人回憶,菊比古讓他明白看似徒勞的選擇也不是毫無意義。他終于發覺,自己一直缺少一種直面慘淡人生的勇氣。這時,他感覺“突然有種相當堅固巨大的東西驀的站起來”,也發覺自己一直捍衛的所謂自由和夢想不過是零。所以,“鳥”說,直面的方法只有兩個,“或者用自己的手親自殺死,或者接受他把他撫養大”。
“鳥”明白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責任完全有自己擔負起來”。在結尾的時候,“鳥”決心重新開始生活,承擔起父親的責任,這不僅是對自己的人生負責,更是對孩子和家庭負責。“鳥”也通過新生兒,實現了自己的再生。正像教授所言,“鳥”和他有點孩子氣的外號已經不相稱了,他蛻變了。
“鳥”從退化再到找尋的過程是“他(從無到有)從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為的那樣”。他從一個懦夫到英雄的過程,經歷了痛苦的掙扎和游離,最后仍然在關照他人的時候,聽取內心真實的聲音,做出了戰斗的人道主義的選擇,由此,“鳥”才“把自己推向未來”,在企圖成為一個好父親的時候,獲得了存在感,拋開虛偽的自我欺騙,以積極治療和養育孩子的行動宣誓著對生命的熱愛。
“鳥”的個人經歷又不全是個人的體驗,許許多多的“鳥們”都在經歷著生活的困境,而“鳥們”在選擇的過程中,也就制造了某種普遍性的價值觀,即“自由承擔責任的絕對性質”。
四、結語
大江健三郎中期創作的《個人的體驗》是他作品中獨特的存在,個人生活的不幸與民族苦難的遭際帶給大江健三郎全新的人生體驗,而這些體驗又成為《個人的體驗》創作的直接源泉。大江將自己的哲學思考與薩特存在主義哲學思想融合,并通過“鳥”這一具體形象的所思所想來展現他的思考。主人公“鳥”在經歷了“痛苦”“聽任”“絕望”后,實現了由懦夫到英雄的蛻變,而“鳥”這個人物的蛻變和選擇正是薩特“希望的”存在主義與大江式存在主義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