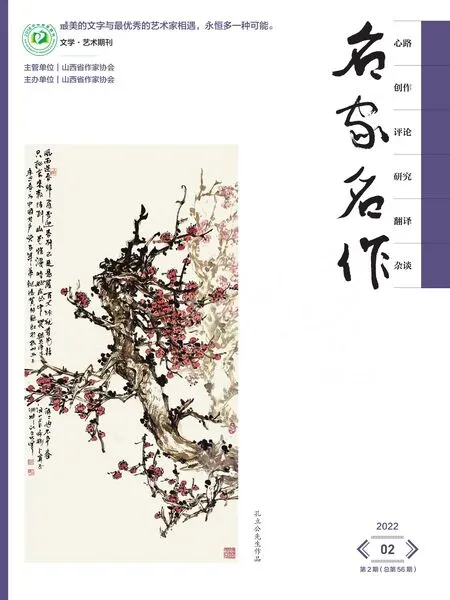詩歌·王位·太陽
趙嘉程
海子,1964年3月24日生于安徽懷寧,1989年3月26日卒于山海鐵軌。
——題記
1984年的秋天深倦難耐,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
火車飛馳,車廂末節,他臨窗而坐,啟程返鄉。車窗外火紅的葉成為肅秋最炙熱的迸裂,多像初戀女友與他相遇時嬌艷的面容,熱戀如花綻放,如收獲之果,充盈而美好,而如今花已開在高高的樹上,可果卻結在了深深的地下,當年的戀人分離相別,她已在異鄉組建了家庭。
他不時整理蓬亂的頭發,來回摸索短胡,食指反復揉搓微微泛紅的鼻尖,再顫巍地抬起右臂,側身輕靠在冰冷的車窗上。
雙膝如木,視線所及之處都是河流雜草幽幽的眼睛,呼吸之間,沉默的是車下的土地,也是曾郁郁蔥蔥的心靈。窗外,樹上數不盡的楓葉織成一張紅棕色的大網,撒滿了他的面頰,難以掙脫,也不再掙脫。耳邊人聲瀝瀝,切斷了他的思緒,他劃破密網,獲得短暫喘息。
車上兩個孩童追逐著、吵鬧著,孩子母親對著內坐的他投來歉意的目光。他注視著孩子,真真切切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月夜,獨自躺在屋前的麥地里,借著微弱的星光,望著連夜種麥的父親。父親微微曲駝的背上,仿佛流淌著流金般的美好。故鄉的風,家鄉的云,也曾收聚成最輕柔的翅膀,安恬地睡在他的雙肩,對他無限贈予。
漸漸地,車廂里,孩童的嬉鬧聲寂了,偶有男人此起彼伏的鼾聲。他摘下黑框眼鏡放在衣服右邊的口袋里,閉眼靜思。五年前,他站在村頭的包谷地旁,無比篤定。告別故鄉的木屋與清水、星月與羊群、鮮花與麥地。帶著遠方的夢,一路向北。
從小城懷寧到首都北京,他像巨樹一般,向往著高處的陽光。可他的根卻伸向了黑暗的地底。遠方的夢在孤寂中成了野花一片,歲月在時間里已塵埃無邊。想到這里,我漸合上了書頁,嘆息不已。
1984年,才二十歲的他,就寫出了《亞洲銅》和《阿爾的太陽》,轟動全國。后來更是一發不可收,在七年的時間里竟然創作了近兩百萬字的詩歌。每一首詩中都藏著他對人生的思考和靈魂深處的瘋狂,而這些思考和瘋狂也不斷折磨著他,使他走向了人生的另外一個極端。現實像一把閃閃發亮的斧子,血刃著孤獨的靈魂;或許它就是那一輛拉著被囚禁且失明的詩人的車,攜帶著他奔向最后的法場,那時的他已暗慘得可怕。
因為練氣功“走火入魔”,他已經長時間地處在精神錯亂的崩潰中,經常出現幻聽。1989年初春,大地在張裂的痛苦中哀鳴,空氣中彌散著空虛和寒冷。那個黑夜的兒子,早已來不及觸摸春的詩花,他多愿沖破濃密,像春光像火焰,奔向太陽。可他確信要走,在三月的詩尾,火把燃燒的最后一夜。
老人們在巨大的悲痛中再沒有任何話語,木然地捧著他曾來到人間的證據回到查灣。有人來訪,老人時而不發一言,時而語無倫次:“害在氣功上,害在氣功上,當初要是去海南可能就不會這樣。”偶有幾個與他年齡相仿的青年前來探望,老人緊緊盯著,再不舍得松下眼眶,臉上多了幾十年的蒼老,撕心裂肺的痛苦,需要時間才能慢慢釋放出它的毒性。最后,無人打擾的,他睡在了松林掩映的山坡上。
他的一生早已是一壇發了酵的老酒,隨著歲月的流逝,靈魂的濃度越釀越陳,陳酒味彌漫,讓每一位知道他一生的人在扼腕長嘆之外,感受著自己青春時代相同的夢想和不同的命運結局。淚水漣漣中,我似乎又看到他復活了,詩歌之魂陪伴著他,他靜靜地躺在高高堆起的谷堆旁,望著父親,淺淺哼唱;時而,他發出低低的怒吼,在黯淡的道路上瘋狂奔馳,塵世扯亂了他的發,漆黑無光。最后他毅然再次點起火把,燃燒了自己,熔鑄成了太陽,身骨葬于山頂,靈魂沉睡麥鄉。
“你為何無法走出靈魂的苦井?”
“我必將失敗,但詩歌本身以太陽必將勝利。”透過窗外模糊的暗影,我仿佛聽到他這樣凄然地答道。
查灣的農舍被加固成了他兒時夢寐以求的書屋,三間平瓦房守衛著他生前一一碰觸撫摸過的書冊,瓦屋木門、綠樹映日,年年歲歲,探訪的人絡繹不絕,來來往往間總能給予老人些許的安慰,總還有人記得他們珍愛的孩子,對詩歌的眷戀,詩歌之魂在人來人往中延續著。他們在唇齒與心靈的律動中體會著詩歌帶給他們最初的悸動,無數低回的傾訴匯成聲浪,成了查灣屋舍前新芽破土時清脆爽朗的聲響。
耳邊的磕噠聲時顯時隱,車身漸趨平緩,我慢慢收起思緒。
“山海關將要到達,請各位旅客帶好隨身行李。”火車里傳來播音聲,車站內陽光熾烈。我鄭重地合上詩集,攜著他的文字,啟程前往山海關,試圖抵達他那顆沉睡在春天里永遠年輕著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