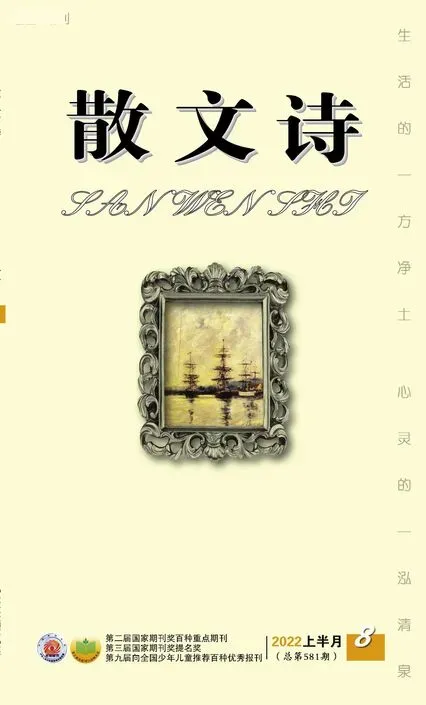非命名
◎舟自橫
失蹤者
我曾愛過她。秋天海浪河’又流回靜寂遠古。野果身著小羅裙’把持空曠’向四周擴散。
人影’飄浮而空虛’漸漸回到樹身’回到石頭’回到干凈的云朵。
我對她耳語’“向上看’天空是你獨有的鏡子。”打開她的發(fā)髻’黑瀑布流下來’掩藏草香’發(fā)絲的枝頭上’蘋果搖曳。
——如果能夠繼續(xù)。她的眼睛有些迷茫’最先從遠方帶回清霜。
我把她的腳’埋在沙灘里。我是牧羊人。把手伸進沙子里’如伸進黑夜。
細數(shù)我的小羔羊’從一到十’從十到一。
小羔羊早已失蹤。從此之后’我便埋掉了我的草場。僅僅記得’一個虛構(gòu)的地址。
盜火者
雨季來臨。
除了云層之上的神’誰能獨善其身?
茅草變身蓑衣。
野果掉落’風(fēng)卷時的曲線’讓它跌倒時獲得了少女腰身。
釀酒的漿汁’已經(jīng)背叛戎與祀。嘴唇’唯一的容器’被閃電打碎。也只有異人或許能夠獲取另類密碼。盜火者’是石頭委身于另一塊石頭。他的生命如先賢’誕生于巖漿。
或許’他在身體里拿出肝膽’逐日而行’被聚焦之光吹成火苗。這些’僅僅局限于假設(shè)。
我所認定的真相是’一夜之間’盜火者讓全世界的女性成為母親。
狩獵者
鵝毛大雪落到松嫩平原’落到我與四舅身上。隱藏或偽裝’狩獵者最懂得為身體和呼吸’披上形容詞。
樹后’四舅手中獵槍指向他最熟悉的“兔道”。兔道被覆蓋’暗藏的小腳印仍舊柔軟。
其實在夏天’也為人間’落過雪。
雪有融化的時候。我在逯家溝西側(cè)柳樹地’用鐵夾子捕過一只最小的鳥。
小身子與柳枝相仿’柳枝傳來戰(zhàn)栗。
多年后居住山區(qū)’發(fā)現(xiàn)樹葉都學(xué)會了人聲。
那些動物留下一張白紙。不是用來填充筆墨。我不知道’夜露與白樺樹的眼睛’是否還有幻覺。
對弈者
“白戰(zhàn)不許持寸鐵”。閃開無數(shù)影子’豈不知’戰(zhàn)場背面’寂靜被一座宮殿獨占。
兩個人’或一群人’只能以風(fēng)聲縫制軍中大帳。先謀劃好’兔子與老虎的關(guān)系。互換位置’亦有可能。
沒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如身邊溪水’曾經(jīng)背對千里之外的大海’養(yǎng)育了逯家溝的炊煙。
哪個更重要呢?不論怎么說’我只能紙上談兵。
久在人間’但計謀尚淺。高人為一粒漢字’洗心革面’找到新出路。
圣手用自己左眼審視右眼’逐漸敲到心臟。
野餐者
麻雀蜜蜂值得學(xué)習(xí)’野草樹木也值得學(xué)習(xí)。它們聚會或分離’不在盡頭留下墓碑。
我們也一樣。
坐在鐵軌南側(cè)草地上。空曠的句子’接納另一個句子。這樣的空間’表達出春天完整的意圖。
蒸汽機車轟隆隆鉆出隧道’像脫下棉衣的愛情仍在飛。
為山命名’姓馮。為翅膀命名’姓楊。留下余溫’是一塊被史詩遺忘的石頭。
酒杯既敘事也抒情。我的經(jīng)歷照亮你的臉。漫長的成長’委身蘸大醬的蔥段。
二十多年過去了。那段光陰綿延’我們留下山口’讓風(fēng)繼續(xù)吹來’不曾凋落的手勢。
獨行者
坐在徐霞客故居’蟬聲的大浪把我淹沒。出行的木船’再也找不到解纜的雙手。
身影嵌入大自在’呼吸繼續(xù)吐納流水與流云。游記里文字如刀’把江山刻進石碑。
我來拜謁與追思’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嗎?飛機來飛機去’翅膀是模擬的’眼睛是大眾的’一顆心也被仿古’刷了舊油漆。
曾寫下那么多風(fēng)光或人文殘詩’我也只是過客。
獨行者’要找到寸關(guān)尺的脈象’用腳與大地相互撫慰。刪除所謂隱喻’從人群里走出來’便會發(fā)現(xiàn)’一塊普通石頭’也是隱居人間的星辰。
雕塑者
一切夢想’從故鄉(xiāng)逯家溝開始。向上虛弱的小梯子’追隨著鳥影。
孩童’堪比造物主。
之后仰望與俯視。無盡之處’沒人能夠為淺灘停留。
青春’窺探一張女人的臉’在廊柱間半掩。琵琶或葡萄’皆可釀酒。
風(fēng)繼續(xù)吹’其實是自搏術(shù)’目光推高大浪’帶回大浪’淹沒自己。
多少年啊!頭發(fā)花白了。發(fā)現(xiàn)哪一縷都是故鄉(xiāng)的炊煙。炊煙之下’野草野花日夜加工大地軟床、人子歸途。
燈火不過是姓氏的假象。如今’道路消失于纏繞的蠶絲。
從青銅到石頭。肋骨握緊刀柄’抵達黑白木刻的碎屑。
建設(shè)者
身體里的漏洞’該修補了。
詩人用詩’鐵匠用鐵。
我用故鄉(xiāng)黑土地的使者小螞蟻。星光下’它引我站在任何一塊方言上。
“我們都是土粒’首先要把自己揉碎”’人間淚與無名氏草根’組成合作社’和泥’脫坯’在人跡罕至之處’建一所房子。
骨頭還能當梁柱吧?擠出肝里的酒精。把言不由衷的紙張’掛在門楣上。
在照妖鏡里分清自己。
白天蓋’晚上拆’有我無我’皆為常事。
如果一言不發(fā)’陽光也是先知’只為選擇走出影子的人。
伐木者
在小興安嶺’我看過一株風(fēng)倒木’腰身彎曲成拱門’不卑不亢’任由大風(fēng)偷盜松籽’欲墜的鳥巢’無數(shù)次經(jīng)過。
另一次是大興安嶺漠河’看見一片幸存的松樹林。不知那年’哪些飛卷的火焰大發(fā)慈悲。
又到十八站貯木場。空蕩無人跡。
幾百公里之外’故鄉(xiāng)逯家溝的鋸子斧頭’從深雪里取出灶火。曾經(jīng)在此驚天地’泣鬼神。
我沒看過伐木場景。我僅知道’伐木者大多身居陋室’家具也四分五裂。
僅這一點便與杜甫相似。杜甫伐字’最后’沒有帶走一首詩。
浩蕩天宇面對他的詩篇’如我’不知如何為其嫁接新意。
囈語者
古榕與古松’對我有過蔭庇。
對根如何深入邏輯學(xué)、心理學(xué)’尚無了解。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散漫’召集鐘聲’必須區(qū)分土壤與水分的輕重。
囈語者處于失衡狀態(tài)。這么斷言’似乎毫無學(xué)理根據(jù)。也無雞湯熱氣。
干癟啊。誰都沒留意那些秋霜’附于屋頂葉子之上。瞇會眼’有人在光里’撿回自己的一根青絲。
遲鈍者
籽粒離開向日葵’成家立業(yè)多年。冥思苦想的磨盤’不知怎樣為老屋續(xù)寫家譜。
地平線老眼昏花’剩下逯家溝的柳樹籬笆墻上一只蹲伏的鳥。
鳥’也活在自己的影子里。
糧倉’記憶的玉米’一日少似一日。
還奔赴什么?云朵’至今才肯命名鄰居二丫的眼睛。
那些泉水啊’把落葉熬制的膽汁咽進肚里。突然間’想起童年時姥爺曾追趕著我:“小兔羔子’你往哪里跑!”
落伍者
“人是落伍者?未來的文字與聲音’也能追隨屈原李白吧?”問我話的’先是現(xiàn)實主義’后是魔幻主義。我被夾到中間’慚愧’撥弄手機里虛擬的古琴。
手指已被舊植物收藏’眼神里’多年沉默之鐵泛起小波瀾。不是老了’是我落伍了。嘴唇之鎖已銹。
只記得幾個名字’卻還常常走失。坐下來吧。懷抱殘簡’看見石頭剪子布’剛剛從大海上岸。
遠方看透我青春時代的假象。假象在稿紙上寫好這首詩’被養(yǎng)育成人的字詞’又被灑下的雨領(lǐng)走。
旁觀者
寫首詩’總覺得先賢文字’在旁觀。
先賢們銀兩不多’與店招日夜縱歌。
如果再親近些’就把他們置于冬天的松嫩平原。天空蒼白’至今不忍著墨。
我也是旁觀者’在病院走廊里。寓言稱半夜有人捉鬼’其實是我’躡手躡腳到衛(wèi)生間吸煙。
鏡頭再推近:我也仿佛進入院內(nèi)。偷窺與暗示’不停地咳嗽。
夜游者
比如一朵云的呼吸’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從夢里脫離。
它是我’我能對它指認。語境太緊密了。舌頭是復(fù)制的’需要穿過肉體叢林。也取決于路徑。
翻過舊墻’老屋與高樓傳來無數(shù)囈語。
它’或消散’或凝聚’成為夜色本身。稀釋詩篇’藥劑清湯寡水。小燈火弱不禁風(fēng)’
如此這些’只能看作救贖而不是救命。病歷上寫道:殘雪得了哮喘。樹芽尋找替身。
那些道路’沒有熬過倒春寒’終止于喑啞的子規(guī)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