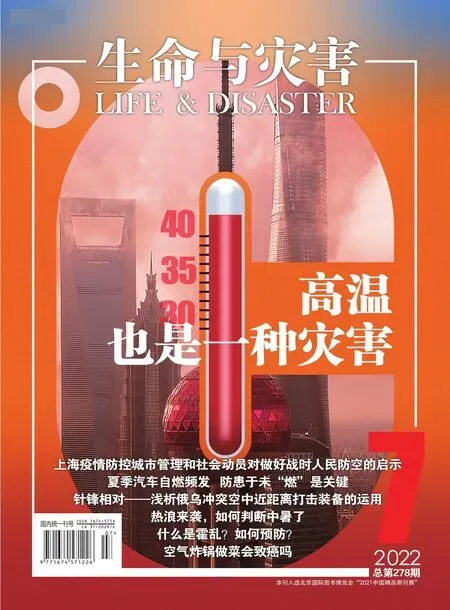盤點蘇東坡詩詞中的“天氣”莫聽穿林打葉聲!
葉奕宏
有這么一個人,在他留下的2 700多首詩、300多首詞、4 800多篇文章里,一定有一句讓你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會心一笑,這個人就是蘇軾。他的妙筆碰上天氣,又會撞出怎樣的風雅才情?跟著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風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
掛帆卻西邁,此計未為非。
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
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
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違。
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
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
我行無南北,適意乃所祈。
何勞弄澎湃,終夜搖窗扉。
妻孥莫憂色,更有篋中衣。
在湖上,遇大風,想走走不了,常人或許氣得半死,但蘇軾卻看到了行程有變背后的別樣風味。
他酒后睡到自然醒,惦念的是明天到淮陰,應該可以吃那肥美的白魚。就連半夜風急浪高,他也覺得是湖神太看得起他了,跟粉絲一樣扒窗子搖門可太沒必要!看老婆孩子嚇得不行,他兩手一攤:別怕,我們帶了厚衣服!
他說:管他東南西北,順心就好!
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
落日繡簾卷,亭下水連空。知君為我新作,窗戶濕青紅。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 一千頃,都鏡凈,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蘇軾見江面上初是水平如鏡,倏爾浪起,白頭漁翁駕著一葉扁舟卻沒有被掀翻,而是隨水勢而“舞”,不由得心生感慨。
最妙的一句為“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一個人只要具備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就能在任何境遇中都處之泰然,享受無窮快意的千里長風。
雨
飲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晴姿雨態,是西湖美的不同側面;就好像是耶非耶、起起落落也不過是人生的一站風景。“西子”之比更為湖光山色注入靈氣,被后人稱為“西湖定評”。
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此時,蘇軾正經歷人生從高臺上跌落的痛苦,就好像遭遇這場急雨卻沒有雨具。若是狼狽應對,就只剩下狼狽;若是從容自若、任天而動,那什么風雨斜陽都不過是前行路上的陪襯。
雪
江神子
大雪,有懷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此以寄之
黃昏猶是雨纖纖。曉開簾,欲平檐。江闊天低,無處認青簾。孤坐凍吟誰伴我?揩病目,捻衰髯。使君留客醉厭厭。水晶鹽,為誰甜?手把梅花,東望憶陶潛。雪似故人人似雪,雖可愛,有人嫌。
也許是因為寫給密友,行文十分跳脫,幾乎自帶“表情包”——震驚!昨天傍晚還是細雨紛紛,今天早上一掀簾子,怎么雪都快和屋檐齊平了!一個人凍得歪歪倒倒地吟詩,像個沒有人陪的“大可憐”,再一想著朱使君你呀,那邊是不是正大宴賓客呢!這水晶鹽一樣的雪,是因為誰變得甘美呢?
可見呀,雪花就像故人,可愛是可愛,就怕還是有人嫌棄呢!
和子由澠池懷舊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嘉祐六年(1061)冬,蘇軾在去陜西鳳翔任職的路上,再一次經過了和弟弟一起到過的澠池。兩兄弟見同一片“雪泥”,蘇轍想的是人生艱難,蘇軾想的卻是世事無常。
把眼神從當下拔出來,于是生命中看似深刻的印痕,只不過是萬里飛鴻偶然在雪泥上留下的爪痕。
末四句看似悲涼,但代入蘇軾彼時情境——去往仕途第一站,又未嘗不是另一種豪情:此一時人困馬乏,誰說彼一時就不能春風得意!
延伸:元豐二年(1079),“烏臺詩案”讓蘇軾遭遇人生第一個“生死劫”。貶謫黃州第二年,蘇軾得到了他的“東坡”,并于次年一月大雪時節在東坡處建“雪堂”。
此時,蘇軾在“出世”和“入世”的十字路口徘徊不定,作《雪堂記》,以主客對答的形式層層剖白復雜的內心世界。
他說:“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
他悠然自得,在萬物萌動、太陽升起時,輾轉間抬頭見一線天光中飛揚的塵粒。
順其自然而已。

攝影:揚帆
雷電
有美堂暴雨
游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云撥不開。
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
十分瀲滟金樽凸,千杖敲鏗羯鼓催。
喚起謫仙泉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
詩作前賦后比,首聯生動形象地刻畫了雨來勢洶洶的前兆——一聲驚雷好像在腳底炸開!黑云壓城,風吹浪立,浙東飛雨踏浪而來!
蘇軾將雨勢、雨聲與眼前宴席上的金樽、羯鼓作比,甚至更發散想到,如果李白在此,暴雨一澆,字字珠璣的詩篇是不是也能一瀉千里?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云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
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標題比詩還要長啊……有個叫唐道人的說,自己在天目山上哪怕聽見大雷電,也只覺像嬰兒哭。蘇軾由此感慨,為什么離雷電近的人能泰然處之,離雷電遠的人反而嚇得筷子都掉了?
想來想去,是因為站在山頭的人不求名利,有一個自然而超脫的靈魂,而站在山下的人心有未安,總是“以物喜、以己悲”。
因此,這首詩看似說“雷”,實則說的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