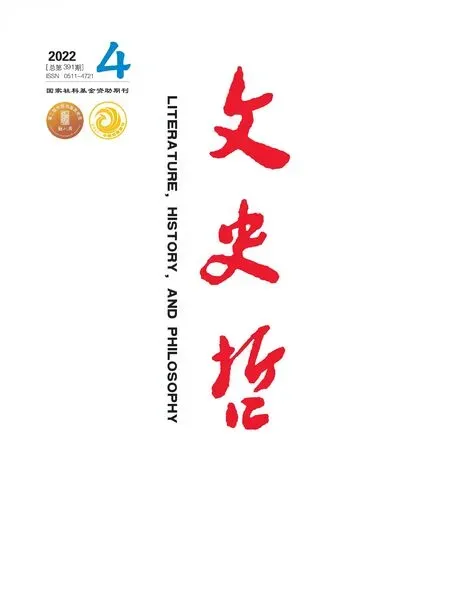“儒家”與“哲學”:錯位的話語和歧進的路向
——兼論作為情感主義思維方式的“儒家哲學”
崔 罡
近年來的儒學界確實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喜人態勢,但同時亦蘊藏著分歧層出不窮的局面。正如黃玉順指出的:“如今的儒學,既有原教旨主義的儒學,又有自由主義的儒學,還有馬克思主義的儒學。……儒學已經分裂了。這種分裂并非古代那種‘儒分為八’的分裂,而是基本的價值觀念、價值立場的分裂。今日儒學唯一的‘共識’,就是大家都自稱為‘儒家’。”
此種狀況迫使我們不得不對“儒家哲學”觀念本身進行反思。道理顯而易見,根據現代學術的基本規則,倘若儒家哲學真如學者所以為的那樣具有內在系統性,分裂的狀況便必然是由基礎概念的分歧導致。但是,只要稍加推敲,我們就極容易提出一個基礎性疑問:“儒家”與“哲學”是怎樣實現兼容的?“儒家哲學”這個概念又是如何吊詭地成了現代儒學的核心語詞?
本文試圖闡明如下真相:“儒家”與“哲學”是兩種相互錯位的話語,前者是前現代的,而后者是現代的;錯位的話語導致了歧進的路向,也就是說,當前被冠以“某某儒學”的形態,從現代性的角度來看,是種種彼此沖突的立場之表達,根本不能也不應被視為某種自洽的哲學。最后,本文還將嘗試性地提出,儒家哲學應是一種不同于歐洲理性主義傳統的現代性思維方式,也就是儒家情感主義。這才是儒家哲學在這個時代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一、儒家與哲學:兩種相互錯位的話語
綜觀先秦至漢初所有學術史文獻,如《荀子·非十二子》《荀子·解蔽》《韓非子·顯學》《莊子·天下》《呂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等,沒有任何一例在學派的意義上使用“儒家”概念。“家”被賦予“學派”的含義最早見于《莊子·天下》,文中提到“百家之學”“百家眾技”“百家往而不返”,凡此三例。盡管《天下篇》“在‘家’的概念的形成、發展過程中,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但全文仍然是以松散的學術史觀來討論“道術為天下裂”的學術態勢。先秦有儒者、儒士、儒生等用例,但前述文本至少表明,在中華帝制時代之前,“儒家”觀念與此后習以為常的理解絕不相同。
在嚴格區分“道家”“墨家”“陰陽家”等各家意義上使用的“儒家”,真正成型于《論六家要旨》:“《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這段話嚴格符合“屬加種差”的概念定義原則。在司馬談看來,天下所有的思想歸根結底都在討論同一個問題,即如何治理天下(此其“屬”),在此前提下,根據其立場和觀點的不同(此其“種差”),天下學術被分為了六家,而儒家是其中之一。學術是否真的只是圍繞此唯一問題展開,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關于《論六家要旨》的歷史事實是:其一,它是典型的中華帝制前期生活方式的顯現,是第一次社會大轉型完成之后“大一統”現實訴求的反映;其二,它被保留并整合為“諸子出于王官論”,并隨著從《漢志》系統到《隋志》系統的更新換代,成了漫長的中華帝制時代“天經地義”的觀念。也就是說,“儒家”首先對應的是經(六藝)子(諸子)之分,它屬于子學;在子學中,它又對應“道家”“墨家”各派。“儒家”概念在中華帝制時代保持了基本的一致,它的背后是一整套彼時的生活方式、世界觀和價值系統。質言之,“儒家”是前現代話語。
漢語學界使用的“哲學”是舶來詞。在西方語境下,它至少具有三個不同的含義:philosophy,這是愛智慧的行動;metaphysics,形而上學,這是愛智慧的產物;knowledge of metaphysics,這是關于形而上學的知識,亦即哲學專家處理的知識領域。哲學在西方傳統中的語義變遷非本文所能討論,但需要指出的是,在19世紀中后期之后,學者已經習慣性地、不加區別地使用這三層含義。
“哲學”概念經由日本傳入中國時,時人承接了彼時西方流行的哲學觀,普遍將“哲學”理解為“統合之學”,也就是metaphysics。例如,發表于1901年的一篇文章認為:“上下古今縱橫,宇宙自洪荒最初之點迄世界大同之場,其所以綱維人類主宰事物而有莫大之勢用者,學術也。然事物有萬變而學術亦有萬端,于紛歧復雜之中而有一至理貫徹之、綜合之,使無不明之事物、無不達之知識者,惟哲學。”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人們既亦將哲學視為知識門類之一。王國維在1904年即討論過戴震與阮元的哲學。程樹德稱荀子為“哲學大家”。更早的例子是1898年譯介的日本學者大橋鐵太郎的周敦頤張載哲學。直到科玄論戰,學者們依然不加區分地使用“哲學”和“玄學”,并習慣性地用metaphysics補充標注。
“哲學”概念開始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被大量使用是在20世紀的最初十年,且其使用量呈爆發式增長趨勢。彼時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覺醒時期,也是救亡圖存三階段論的成型時期,還是中國現代學科的初建時期。“哲學”概念在進入中國之初就被視為一整套近代以來西方世界觀和價值系統的象征。這不僅是教育系統的轉變、知識系統的轉變,更意味著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動、社會秩序的崩潰和重建。這個轉變,通常被視為晚清現代化的重要現象之一。這清楚地表明,“哲學”在進入漢語學界之初就與“現代化”聯系在一起。質言之,哲學是現代話語。
因此,嚴格來講,“儒家”和“哲學”是基于兩套完全不同的話語體系的彼此錯位的概念——前者是前現代的,后者是現代的。合乎邏輯的推論是:現代化就要反傳統(因為現代與傳統互釋),反傳統就是反儒家(經學也被視為儒學)。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許多持有儒家立場的學者都會被理所當然地貼上“文化保守主義”的標簽。不論國人對自己的傳統還有多少香火情分,在新式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幾代人對儒學陌生已是不爭的事實。在哲學領域更是如此。例如,大量嚴肅地專業從事西方哲學研究的學者,在平時可以和儒家形同陌路,但一旦在某個具體問題上與儒學遭遇,就會迅速爆發激烈的爭論。最近的例子是關于“父子互隱”的大爭鳴。
但“儒家哲學”是中國哲學界的最核心話語之一,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這意味著什么呢?不假思索的判斷是,儒學發生了現代轉型。這自然沒錯,同時亦表明,只要不否認“哲學”的現代性意涵,那么,就必然是儒家“被哲學化”了。不過,事實絕非如此簡單。
二、“儒家哲學”與歧進的路向
“儒家哲學”最早被使用應該是在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只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不過全書也僅此一例。這個概念被正式用作著作題名是1922年梁啟超的《儒家哲學及其政治思想》。1926年,梁啟超在題為《儒家哲學》的講座中表示:“‘儒家哲學’四字大家都用慣了。”由此可見,“儒家哲學”已成為學術討論中的常用詞。
那么,“儒家哲學”是在什么意義上被使用的呢?
根據陳來先生的觀點,“儒家哲學”有兩個大的分別:“一是指對傳統儒學的學術研究,即把握儒學歷史發展演化的脈絡,梳理儒學理論體系的內部結構,清理儒學概念的意義及演變,研究儒學在不同時代與社會、制度的聯系,澄清儒學的思想特質和價值方向等等;一是指儒家思想的理論建構與發展,即20世紀面對時代、社會的變化、調整和挑戰,發展出符合時代處境的儒家思想的新的開展,開展出新的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學、新的發揚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學,以及從儒家立場對世界和人類境況的普遍性問題給出指引的哲學。”要言之,儒家哲學不外乎兩類形態,一是知識化了的儒學,也就是按照現代學科分類標準將傳統儒學分解和重組;一是資源化了的儒學,也就是批判繼承儒學思想資源,回應當下的問題。
在更嚴格的意義上,我們還可以將“儒家哲學”分為三類:一是“儒學中的哲學”,一是“儒家化的哲學”,一是“儒家式的哲學”。
所謂“儒學中的哲學”指的是,按照西方哲學的分類體系,將儒學中與之符合或類似的內容單列出來,納入哲學學科的研究對象之中。其下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以胡適為代表的“以西律中”;第二類是以郭沫若、蔡尚思等為代表的“以馬律中”。從數量上來講,這種用法是此后各種儒家哲學研究的典型范式,其價值或如蔡元培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評價:“把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由此帶來的爭論是,儒家是否有形而上學(metaphysics)?
所謂“儒家化的哲學”指的是,運用儒學的思想資料,積極建構儒家的哲學體系,但參照的仍然是西方哲學的標準。賀麟說:“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蓋五花八門的思想,不同國別、不同民族的文化,漫無標準地輸入到中國,各自尋找其傾銷場,各自施展其征服力,假使我們不歸本于儒家思想,而加以陶熔統貫,如何能對治這些分歧龐雜的思想,而達到殊途同歸、共同合作以擔負建設新國家新文化的責任呢?”由此帶來的爭論是,中國哲學是否合法,或中國哲學的失語癥問題。
所謂“儒家式的哲學”指的是,持有儒家的立場、建構儒家式的哲學體系。其下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化樣態說,代表觀點見于梁漱溟《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所謂哲學就是有系統的思想,首尾銜貫成一家言的。”在梁先生看來,哲學乃是思想,而思想即是文化。“文化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一類是人生哲學說,代表觀點見于梁啟超。他認為儒家哲學的范圍要遠遠大于西方哲學的范圍,是不能簡單地采用現代哲學來對其解釋的,因為“我們所謂哲,即圣哲之哲,表示人格極其高尚,不是歐洲所謂Philosophy范圍那樣窄”。此一類的前提是對哲學另做解讀,但其所持是否如論者以為的儒家立場,則存爭議。
無論二分抑或三分,都未根本性地扭轉話語自身的錯位性。知識化的儒學不可避免地被現代學術分解,至少被分到了歷史學和哲學兩個一級學科門類之下。那也就意味著儒學不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獨立性,且其哲學品質總體上不被高度認可。
資源化的儒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轉型后的哲學形態。如此一來,被冠以“現代儒學”之名的種種儒學的提倡者們,一直以超乎尋常的熱情積極參與新潮的、時尚的、通常是西方學者率先發起的話題。請注意,這意味著“現代性”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很容易令非儒家學者詬病的是,凡是有一種西方的哲學流派,就幾乎會有一種與其對應的儒家哲學,諸如康德式的儒家、黑格爾式的儒家、現象學式的儒家、詮釋學式的儒家等等。擴而言之,現代思想中但凡有一種主義,就會有該種主義的儒家。所謂“主義”指的無非是就公共生活“所具有的信仰和行動”。這顯然意味著各種主義之間的界限本來、應當是分明的。“主義”的背后,是關于現代性諸問題的立場對立,且這些對立是實然的,甚至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引發了流血沖突。儒家哲學居然能夠逍遙乎其中,這簡直太荒誕了。
在“主義”的意義上,中華帝制時代的儒家確實可被理解為“某種主義”。但問題在于,面對當下的狀況,儒家究竟算何種主義?倘若存在儒家主義,那么,它是什么?它又如何與其他種種立場相區分?倘若不存在儒家主義,儒家是否就必然消融在各種現代性的主義之內,而僅僅是思想資料和話語工具?如此它又憑什么獲得自身的獨立性?
總之,當下的儒家哲學以某種奇異的方式存在:它似乎無處不在,但又無處安身。歧進的路向背后是錯位的話語,換言之,當下的狀況是由“儒家哲學”觀念本身混亂引發的。既然如此,只要不對儒學進行全盤否定,就應從根本上闡明“儒家哲學”的現代意涵。
三、情感主義:儒家哲學的現代意涵
“儒家”作為一個偏正語詞,“儒”是種,而“家”是屬,這樣就必然存在與“儒家”并列的別家。孟子“拒楊墨”,楊、墨即與儒家并列;司馬談分六家,其余五家即與儒家并列;宋明“辟佛老”,佛、老即與儒家并列。無須贅言,這些并列方式、理論對手、問題指向,在今天早已不復存在。例如,梁漱溟和熊十力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佛學資源,這在宋明理學家看來是犯了大忌的,卻絲毫無損梁、熊二先生在現代新儒家中的開山地位。尋求“儒家哲學”的現代意涵,即要明確它在現代哲學中的并立之學。
“儒家哲學”首先是哲學,這是其“屬”,它與其他哲學的差異即是其“種差”。“現代哲學”作為學術分工之一種,即是對現代性諸問題的一般性、根本性闡明。考慮到20世紀以來鮮明的“去形而上學”傾向,考慮到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學科對此前原本下轄于哲學學科諸問題的分有(此種分有乃人類學術史的常態),哲學愈發地表現為對諸學科形而上學承諾的審慎反思,亦即,它愈發地表現為某種思維方式。
那么,什么是思維方式呢?蒙培元先生對此進行了界說。在他看來,首先,思維方式是廣義的認知,也就是認識生活、理解生活、安置生活的致思進路。其次,思維方式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客體的對象性認識”或“自覺的理性認識”,即理性主義(rationalism)思維方式;另一類則是“主體論的存在認知和評價認知”或“非自覺的非理性認識”,即情感主義(emotionism)思維方式。
縱觀人類歷史,自軸心期以來,在安置公共生活問題上,主流的、基本的思維方式都是理性主義的。無論這里的理性指代的是自然哲學的自然規律,還是先驗哲學的義務論,或是宗教哲學的神命論,其本質是完全相同的。它在歐洲中世紀表現為亞里士多德主義,特別是托馬斯·阿奎那的卓越工作;在中國傳統帝制時代則表現為漢唐儒學的“天”或宋明儒學的“天理”觀念。此種歷史事實有其正當性。因為情感一定是個體的情感,而公共生活又必然是非個體的。個人情感的反復無常自然會成為公共生活中嘈雜的聲音、不協調的旋律、令人厭煩的擾亂者。因此,在哲學史上,對情感的基本態度要么是道德哲學式的“給這些放縱無度的渴望套上轡頭”,要么是政治哲學式的“可以怎樣被塑造和被影響,來促進我們的正義目的”,也即傳統儒學的“發而皆中節”的倫理要求。
在理性主義的原則之下,人類打造出了高度組織化、高度模式化的現代社會。在此社會中,“作為自然或歷史發展的法則的近代形式的普遍法,成為運作的原理,不斷保證人為的實定法的規則和規范體系的有效性”。此種思維方式潛藏著巨大的危機,19世紀人文主義的先驅者們對此早已發出了警告。但這些“不合時宜”的諫言被淹沒于工業革命帶來的理性主義狂熱之中。
因此,現代性諸問題帶來的真正焦慮在于:我們已然無法確信現代性是否會必然帶來美好生活。于是,對理性主義的警醒就成了20世紀哲學的重要傾向。再進一步的追問是:公共生活一定是理性的,但安置公共生活的思維方式就只能是理性主義的嗎?
談到理性,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亞里士多德的著名格言:“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也是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最核心的價值之一。“理性”用拉丁文來表述是“rationale”,而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那里的表述則是“logon”,直譯為“人是邏各斯的動物”。這里顯然存在著ratio與logos之間的差異。“古希臘語中,logos具有言語和理性的雙重意義,表達這種保證對話能力與思維能力的統一性的用詞,后來就變成了ratio。從政治的觀點來看,兩者是不同的。后者先是在理性的個體內存在,與個人有關系,以后,成為個人向他者表達自己的想法所使用的言語。但是,前者根本上與他者有著聯系,因此其本性是政治的。”從漢語的表達習慣來講,logos既是指“說道”,也就是人類運用連貫的思想和表達能力對存在者的言說,通常被理解為人性天賦的理性能力;還表示“道說”,也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的自我顯現,通常被理解為客觀的規律、規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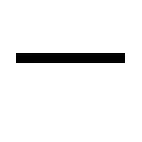
儒家情感主義則提供了一種徹底的“由情及理”的思維方式。蒙培元指出,“將情感作為真正的哲學問題來對待,是儒家哲學特有的”。“這里所說的‘哲學問題’,不是指哲學中的某一個問題,或哲學中的一個分支(比如美學和倫理學),而是指哲學的核心問題,或整個的哲學問題。”
蒙培元的工作是對先秦儒學,尤其是孔子儒學的重新發現與復歸。在孔子那里,有一個更為源初的“情—理—情”結構。《論語·泰伯》記載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在這個框架性結構中,“《詩》以道志,《禮》以道行,《樂》以道和”。“志”即是情感的意向性,而“和”則是情感的滿足。這就是說,問題生發于情感,其最終的歸宿也是情感。在發生與歸宿之間,則是“理”的環節,是訴諸公共性、連貫性的能力,落實來講,可以是禮樂制度、禮樂文化,抽象地說,則是一般性的理性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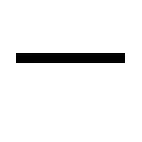
情感主義則不然,其基本的判斷是因為有如此這般的情感樣態,故而人被視為如此這般的存在者。質言之,不是理性駕馭了情感,而是情感生成了理性,理性是且只是情感的工具。
再次申明,理性主義和情感主義都是用以應對如何安置公共生活的思維方式。既然公共生活必然是理性的,問題就在于如何看待“情感與理性”的關系。由此可以導出一些情感主義的基礎性立場:其一,安置公共生活的方式不是來自某種形而上學設定,而是來自個體情感的訴求,來自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溝通以及公共善(public good)的約定。其哲學化表達是“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問題與回答。其二,倘若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生活是實然的,那意味著不同世界觀、不同價值觀、不同文化觀之間的溝通乃不爭的實情。紛爭不斷不是因為彼此天然的隔閡,恰恰相反,而是彼此溝通不足所致。討論至此,儒家哲學的現代意涵已然呼之欲出。作為現代哲學的形態,儒家哲學不同于任何哲學的根本性特質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徹底的情感主義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