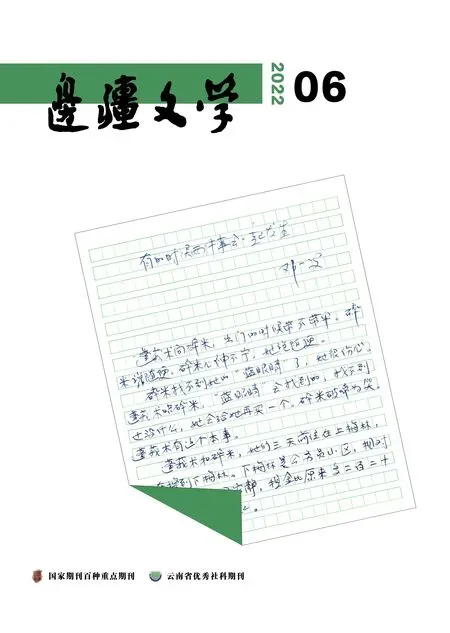張常美的詩
張常美
烏有鄉
能不能這樣填寫自己的籍貫:
烏有鄉。或,桃花源……
我愿意操著你們聽不懂的鄉音
永遠都漂泊在外
桃花開了,又落了
我的故鄉在左,在右……
在不得返回中。起風了
我愿意吹著每一場
自故鄉吹來的風
懷想它。花的味道,桃子的味道
我蹲在別處的云泥里
看著別處的螞蟻,那些
終身都在故土忙碌著的螞蟻
它們搬運著一枚落葉
也像是為了搬運我的故鄉努力著
農夫與蛇
講出這個故事的人一開始就沒安好心
想想那條凍僵在路上的蛇
想想那個背著柴
或兩手空空回家的農夫
兩個落難者為什么一定要遇見
為什么不能是個好天氣
農夫輕松而愜意
哼著歌兒,路過打盹的蛇
彼此沒有察覺。或者
假裝沒有察覺,各自避開了對方
與世界的對峙中
大部分時候,我都是心虛的
越是毫無勝算
內心的鼓聲擂得越響
密布在我周遭,探出枯指
撩撥我的,依舊是
曾伏在我童年肩膀上的
影影綽綽的樹嗎
我已試過妥協。但并不徹底
我伸出的手又總是
迅速從狗爪、從灰燼中抽出來
唯有戰栗,是最熟練的動作
像是天賦。將恐懼藏得滴水不漏
是畢生的難題
以至于,上天為我安排了
妻子和孩子……那么多親人
在為怎樣安撫她們的
每一次尖叫和抽泣而焦慮時
更多也像是為怎樣
安撫自己而耐心練習著
早春或暮冬
貿然闖進早春的白蝴蝶就像
一片遲緩的雪。落在你肩膀上
那一刻,幾乎無需回頭
你就篤定
自己要開花了
盡管這太危險,但不妨冒險試試
為了配得上選中你的
這只蝴蝶,或這片雪花
催眠曲
倒坐進一輛慢車里,風景
從眼前退出,又自身后
徐徐展開。幾乎一樣的房子,樹木……
一樣的荒野和城市
是不是會一直永不知疲倦
復制下去。我小瞇,也假寐
有時把頭埋進同樣令人厭煩的手機里……
同樣的悲歡離合,也在那里次第展開
火車拐彎的時候看見
后面,一節節車廂
同樣在復制著自己
大概是為了能穩妥經過
剛剛從我眼中消逝的風景
終于在疲倦中沉沉睡去
又醒來了。抬頭的瞬間,我才知道
自己多么愚蠢
在我并不漫長的睡眠中
世界好像也自責過
每一個窗口都掛滿悔恨的淚滴
淚滴后面,布置出了我想象之外的青山和綠水
婦女節
屬于所有女人們的,也應該
屬于我的母親,我的姐姐
屬于我的妻子。屬于高跟鞋的
也應該屬于解放鞋
屬于正攪拌著的
咖啡的。也應該屬于混凝土
屬于那些讓男人亢奮的
也屬于被鮮花遺忘的
屬于歡笑,也屬于哭泣
還沒有長大的和日益干癟的
我無法一一祝福的女人們啊
之所以我還要祝福
就是因為這世界的一半
還在孕育。是因為
從來沒有被祝福過一次的
母親,至死,對活著都很有耐心
準備好的死
那些落滿了灰塵,又一遍遍擦亮的
壽材。在太陽下翻出來
又疊回柜角的壽衣。讓
尚在人間熬著的
逝者,安心熬著。每一次展開
好像就是給死神炫耀的——
只有沒準備好的死
才會讓人唏噓
一個兒子,走了。匆匆忙忙
披上了父親準備好的衣衫
像是替他的父親赴宴去了
而那個令死神又一次撲空的
影子,伏進一具衰老的身體上
一拳,一拳,像是替死神狠狠捶打著
大夢三題
(一)
真讓人羨慕。一頭倒進
一座正在施工的
樓宇的陰影里,呼呼大睡的那個人
差點就想貼著他
也躺下來。像兩個落魄的神仙
在南廣場的車水馬龍里
做自古以來的
那唯一的夢
真想叫醒他的不是攪拌機、水泥漿……
是遙遠深林中,那閑下來的
一兩聲嘰喳,或叮咚
(二)
夢中喊了很多遍的名字
無人回應。夢中亮堂的屋子
醒來后,又陷入黑暗
夢中去過的地方,隔著千山萬水
夢中的鞋就脫在夢的外面
落著夢里從來沒有過的灰塵
夢中,我隨手撿了一朵落花
插進自己的鬢角
明知到已經化作一滴眼淚
我還是禁不住想摸到它的余溫
(三)
月亮推醒我兩次
從它鋪排開的景致
我斷定,第一次是古時候
那只白天聞其聲,卻不得見的鳥
正一遍遍忙著拾揀月光
不知道,是用來搭建分娩的巢穴
還是過冬的柴火
另一次醒來卻像長筵已盡
帳篷外,世界閑置很久的樣子
布滿灰燼的天空中
捂著的一枚月亮,也像空蛋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