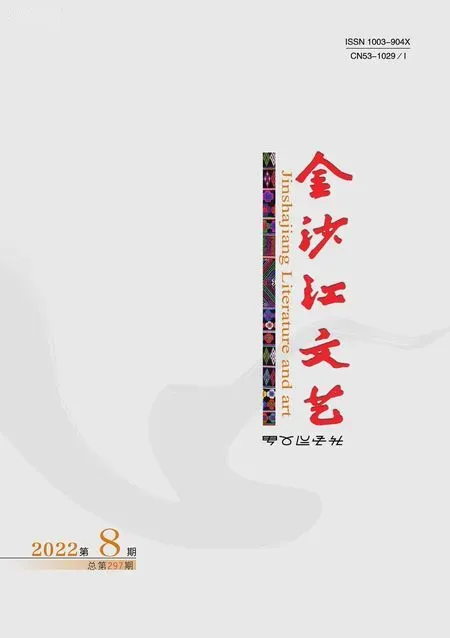父親教不會的牛(外一篇)
◎王勝華
誰也沒有料到,跟隨父親征戰貴州、四川、廣西從無敗績的牛王會在本村的牛場被鄰村一條不起眼的小嫩牛偷襲,不死不活半價賣給了山下那家牛肉店。自那以后,父親就像一根漚了水的老木炭,整天黑黢黢的,看不到一點人樣。
父親常常獨自去牛王“大意失荊州”的那個牛場上看看,每一次去,他都要在牛王倒下的地方獨自靜坐,獨自默哀,獨自流淚,人蔫得像一個摘久了的茄子,表面看上去飽鼓光鮮,但手指一按,就窩了,窩得再也飽不起來。
直到有一天夜里,家里那條被牛王“霸王硬上弓”的母牛下崽了,父親那張“木炭臉”才透出一絲絲喜色,點著發黃的手電筒趕忙跑過去看看母牛生的是公牛還是母牛。父親繞著在地上濕漉漉蹬踏的小牛看了幾圈,結果驚喜地發現,自己不曾喂過一把青草,自己不曾喂過一抔糧食的那條母牛竟然給他生了一條小公牛,而且毛色和花點跟牛王一模一樣。從來不喂母牛不養母牛的父親滿滿地調了一盆苦蕎面湯給母牛喝下去,好讓母牛有充足的奶水來喂養這條生下來就沒了爹的小公牛。
斟酌了好幾天,父親才給這條小公牛起名“牛牛”。在父親看來,“牛牛”這個軟硬軟硬的名字,有牛中之牛的意思,他決定用自己的后半生來喂養牛牛,來訓練牛牛,讓牛牛再度成為牛王,去牛場上為父報仇。
從牛牛站起來拱奶吃的那一天起,父親就像牛牛的爸,一刻不離地陪伴在牛牛的身邊,想方設法去親近它、討好它,常常趁牛牛吃奶的時候從后面悄悄地伸手過去,摸摸牛牛的卵卵坨。有幾次父親摸著摸著,牛牛舒服得竟然忘記了喝奶,回過頭來,像兒子看父親那樣兩眼出神地看著我的父親。有幾次,父親在牛牛的卵卵坨上摸到賴賴的蜱子蟲,父親就像摘蓖麻籽那樣,把蜱子蟲一個一個摘下來,用石塊去碾壓,讓蜱子蟲啪啪啪地炸開,付出血的代價。有一次,也許是父親摸得太賊了,牛牛突然朝著父親兩腿中間那個微微凸起的地方就是一猛腳,父親痛得眼冒金星,伸出去的手,像一條打折了七寸的蛇,立即縮回來,無力地捂住那個微微凸起的地方,蹲在地上,雙目失色了好大一晌才站起來說:“牛牛啊,我摸你都好多回了,你才摸我一回,咋就這么用力?……哎唷……哎唷……”
牛牛學會吃草以后,父親就更加上心了,冬天山上沒有青草,父親就到十幾里以外的山腳田壩有水的地方割青草背回來,焯水以后和在干草里撒上苞谷面來喂它。有一個暑期我放假回來,恰好在山道最艱難的路段趕上背著牛草蝸行的父親,他滿頭大汗,全身濕透,氣喘如牛,一步一步負重前行的模樣極像背著重殼爬行的蝸牛。我把父親和草籃扶在路坎上歇息,用力替父親頂著草籃,讓父親全身都得到輕松。有我頂著牛草,父親就脫下浸滿汗水的衣服,站在風口讓風吹著身子,此時我看見父親的肩頭被繩子勒出兩道深深的勒痕,勒痕陷進肉里去,像血槽。我使勁抹了抹父親身上那兩道勒槽,可父親的身子就像一張皺紋紙,怎么也抹不平。我替父親背著牛牛的糧食艱難地走著,結果還沒有翻過眼前那道山梁,我就累得像父親一樣,滿頭大汗,全身濕透,氣喘如牛,移不動腳步了。父親換下我,背著牛草走在前面,到了家里,他先舀幾瓢冷開水給他的牛牛飲了,自己才舀一瓢冷水咕咚咕咚地灌下,澆滅喉嚨里的火。
父親天天割草和面來催牛牛,要把牛牛的肩包盡快給催出來,催得像一座山那樣聳立在牛牛的肩頭上,牛牛就可以像它父親那樣在牛場上叱咤疆場了。父親真的迫不及待,為了讓牛牛盡早具備戰斗力,他把家里沒有人吃的臘肉肥坨煮熟后塞給牛牛吃。一到晚上,父親就離開母親,睡在牛牛身邊,不時地給牛牛添草上水。父親吃鹽較重,尿液的鹽分高,牛牛特別喜歡吃有鹽味的草料,夜里尿急,父親就站在牛槽旁邊將自己的尿撒在牛草上,讓牛牛吃。為了讓牛牛野性十足,充滿戰斗力,父親不像別人養牛那樣穿牛鼻子,要拉牛牛出去,父親就整一個活扣套在牛角上。有時候父親忙不過來,我們也去拉牛牛,可牛牛欺生,常常朝著我們吹鼻子,瞪眼睛,刨地抓土,怪嚇人的。
父親常常拉著牛牛出去遛彎,走到村里的牛群都喜歡擦身撓癢的土坎,父親就學著牛的模樣趴下身子,用頭去頂頂去撞撞那個一人高的土坎。一來二去,牛牛果真學著父親那樣用頭去猛力頂撞那個土坎,將一塊塊土垡和石頭掀下來。
半年以后我再次放假回來,牛牛的肩包果真已經微微地凸起,有半個籃球那么大了。有時候,我也摸摸牛牛的肩包,我感覺,那是牛力的象征。
長了不好用,短了不夠使,牛牛兩歲的時候,兩只牛角像兩把鋒利的鐮刀,角根粗壯得像兩根長在斜坡上的竹筍,硬扎,有力,不論是長度、彎度還是圍度,都極符合牛王的標準。六月二十四火把節那天,村里在牛場上舉辦兩年一屆的牛王大賽,邀請了遠遠近近幾十頭牛一起來爭霸,偷襲打傷了牛牛父親的那頭牛,也在受邀之列。父親拉著牛牛想去練練膽子,一出門,牛牛就氣勢磅礴,刨土抓地,仰天號叫,那種不可一世的氣概像極了它的父親。父親似乎看到了新一代牛王,心里喜滋滋的,不舍得罵它,更不舍得打它。
聽說牛王有后了,七村八寨喜歡玩牛的人都圍攏過來,對著牛牛嘖嘖稱奇,都說:“像,跟它爹一模一樣……”
圍觀的人群中就有打傷牛牛父親的那頭牛的主人,父親看著那個七老八十的牛主人,臉紅脖子粗,恨不得上去就和他拼命,為牛王報仇,他心里想:我的牛不幸輸給你的牛,如果允許我倆替牛打架,我可不會輸給你,我比你年輕……
可是,人怎么能夠去替一條牛報仇呢?牛的仇,就讓牛去報吧!
一進場,牛牛就聞到牛場上那股你死我活的血腥味,屁股就直飚稀屎,像水泥澆灌車倒水泥漿一樣,稀屎啪啪啪地砸在場子上,隨著牛牛尾巴的左右甩動,稀屎涂滿了整個屁股。父親小心地牽著牛牛走到它父親栽跟頭的地方,牛牛似乎聞到了什么,將頭插得很低,朝著地上號啕大哭,甩頭掙脫了父親手里的繩子,沖出牛場,消失在來時的路上……
“這是牛王的后代嗎?”
父親的臉唰地一下變黑了,像一坨潑了冷水的木炭,情緒一落千丈,他沒有看牛王爭霸,像融雪一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牛場上。
父親回到家里的時候,牛牛已經自己在牛舍里嚼著青草。
父親更加郁郁寡歡了,他常常央求似的對我說:“兒呀,回來幫我養牛喂牛吧……”我知道父親的意思,但我沒有答應父親,也沒有回絕父親,我不想放棄讀書,又不想讓父親的希望在我面前就這樣熄滅。
誰知道,第二天父親就叫來村里的男人,在牛牛的臉上蒙上一塊黑布,讓牛牛的前途黑了下來,一擁而上,將牛牛摁倒在地上,在牛牛的卵卵筋上裹了一層紅布,墊上木墩,用斧頭一樣的木楔子對準卵卵筋,揮起重錘,用力砸下去……
“哞—哞—”
我站在牛牛的近旁看著、聽著,牛牛的叫聲死去活來,我心里有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轉眼,春耕在即,父親突然對我說:“走,不想回來養牛就跟我馴牛去。”父親拉著只會低頭吃草,不會抬頭看天的牛牛默默地走在前頭,牛牛跟著父親,我跟著牛牛,向著村里專門馴牛的那塊荒地走去。
荒地上,我在前面拉著牛牛,父親在后面使著牛牛,牛牛不想走的時候,父親就揮舉著青竹竿說:“別人的牛三歲就苦吃苦喝了,莫非你三歲還學不會拉犁踩溝?我就不信教不會你!”不知是有意還是失誤,父親教牛的青竹竿一下子脫手,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與馬蜂修行
馬蜂有與生俱來的稟性,需要修行,人也是這樣。
下班回來,我剛把煮熟的肉從鍋里撈出來涼在飯桌上,一粒紅彤彤的“火炭”隔著玻璃窗對著我那熱氣騰騰的肉,來回運動,不肯離去。我悠悠地推開窗子,想看看這粒“火炭”究竟是怎么回事。結果窗子一開,更多的肉味就關不住騰了出去,那粒“火炭”就從我推開的窗子飛了進來,在熱氣騰騰的肉湯和肉的上空游弋著。待我看清楚了這粒“火炭”是一只能夠致人重傷、致人重殘、致人死亡的馬蜂之后,我開始后悔為什么要推開窗子,讓它進來。我不敢聲張,不敢出大動作,做賊一樣偷偷地摸起桌子上的筷子,朝著這只火炭一樣紅的馬蜂輕輕一揚。沒曾想到,這筷子竟然長了眼睛,準準地撣在這只馬蜂的翅膀上,讓這只馬蜂在空中踉蹌了一下。
這回,我更加后悔了,我后悔之一是怕這只馬蜂蜇我,讓我不死也傷;我后悔之二是怕這只馬蜂不小心掉進我的肉湯里燙死,我就成了有罪的人。我在心里懺悔:“完了完了,我今天干壞事了!”
幸好馬蜂是昆蟲界里的“肉食者”,有超強的平衡能力,趁我的眼睛發生一點小小的故障模糊不清的時候,這只馬蜂輕盈地來了一個沒有被我看清楚的鯉魚打挺,繼續飛舞著,可翅膀振動的頻率明顯翻倍了,發出的聲音像殲擊機的聲音一般刺耳了,顯然是我阻礙了它,得罪了它,惹怒了它。我害怕到了極點,心里默念道:“著了著了,馬蜂生氣了,它要蜇我了……”我雙手蒙著臉,眼睛只能通過手指間的縫隙窺視這只馬蜂的舉動,等待著這只馬蜂賜給我一個胖乎乎的腦袋,等待著這只馬蜂賜給我一只腫乎乎的手……
可是,這只馬蜂并沒有把我的莽撞產生的惡果還回于我,它在空中翻了個身,旋即飛出了窗外。
窗外是如筍的高樓,一棵可以筑巢的樹也沒有,一塊可以覓食的草地也沒有,這只馬蜂還能去哪兒呢?
我拍手站起來,慶幸自己沒有被那只馬蜂蜇,也慶幸那只馬蜂活著離開了這個充滿誘惑的險地。我這么龐然,而馬蜂那么微小,我始終認為馬蜂是被我趕跑的,我始終覺得我是一個勝利者。
正當我余興未減地陶醉勝利中的時候,那只馬蜂又來了,顯然是被肉味誘惑著,它才不甘心于剛才那一番踉蹌。
這是我的地盤,給不給它進來,我說了算,我心里矛盾極了,如果不給它進來,我只要把推出去的窗子重新拉回來,那只馬蜂就永遠被我隔離在窗外了,那股極香的肉味對它來說是永遠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我也不會存在任何傷亡的危險了。正當我猶豫不決的時候,那只馬蜂從剛才飛出去的地方又飛了進來,繼續在那砣肉和肉湯的上空游弋著,越來越低,馬蜂越是接近它想要達到的目的,我就越是擔心。
初次相遇之后,我正在為自己的莽撞買單:我對它的害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想到這一次它可能是有備而來,我就愈加恐懼,但我又想看看它究竟想要干什么。我用笨拙的左手遮住半張臉,斜著眼睛觀察它;那只靈活的右手高高地舉起來,時刻準備著,假如這只馬蜂膽敢撲向我,即使忍著被蜇的疼痛,我也會毫不猶豫一巴掌拍過去,把它拍碎在桌子上。從手指的縫隙間看得出,這只馬蜂也怯我。這是一只被稱作“黃腳”的馬蜂,黃腳蜂是馬蜂界的精英,它們在空中的轉旋能力超強,能夠在空中截殺飛翔的飛蛾、蝴蝶、蜻蜓和蜜蜂,蜇人的時候,速度快得像槍膛里射出來的子彈,被它蜇過的地方就會爛掉指甲大一塊肉,要個把月才會好,好了之后仍然留下一個黃豆大的疤痕窩坑,黑黑的,十分難看,就像冰雹打過的蘋果,再漂亮也留下一個永遠抹不平的疤痕。黃腳馬蜂對來犯者,即使是龐然大物也毫無畏懼,一旦家園遭受侵損,它們就一撥接一撥發起攻擊,赴湯蹈火。如果來犯者將身體保護得嚴嚴實實,蜇不進去,它們就對著來犯者的眼睛飆毒液,毒瞎來犯者的眼睛,讓來犯者失去抵抗能力。
經過長達三個多月的冬眠,驚蟄之后,黃腳馬蜂先在溫暖的土洞里繁衍,進入夏季,土洞潮濕陰冷,它們就要搬離土洞,到廣闊的野外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它們不停地啃咬樹皮和朽木,將樹皮和朽木咬碎嚼細,和上蜂膠,在空曠的樹枝上、崖壁上、人家的房子上建造新巢。黃腳馬蜂葷素兩食,沒有脂肪的螞蚱肉和花蜜,是它們最喜歡的美食,它們天天尋找這些美食,供養幼蛹,讓幼蛹長大,參與建設家園。一個黃腳馬蜂巢,蜂房多到十五六層,少的也有八九層,富麗堂皇如人類的皇宮,層層疊疊,能夠容納成百上千個職蜂在里面上班:在公安部上班的,專門負責蜂巢的警衛和安全;在水利部上班的,專門負責蜂巢的防洪和供水;在糧食部上班的,專門負責蜂巢的糧食供應;在建設部上班的,專門負責蜂巢的規劃和擴建;在生態環境部上班的,專門負責蜂巢內部的衛生和防疫;那些剛剛羽化出房的青年職蜂,它們專門負責蜂巢里的保育工作……馬蜂王國里沒有設立紀檢監察部,它們既有分工,又有協作,個個都能各司其職,風雨無阻,無欲無貪,一旦天敵來犯,它們都放下手里的活計,團結一致,眾志成城,一致對外。黃腳馬蜂有超強的認點定位能力,即使在廣闊的天宇下,經過在空中盤旋認點之后,它們就能夠準確無誤地再次回到原來的地方。如果在野外找到一次性帶不走的食物,它們就像人一樣進行多次搬運,直至把食物完完全全地帶回蜂巢,分給蜂寶寶們享用。黃腳馬蜂和所有馬蜂一樣,它們不會積攢食物,因此每一次食物都是新鮮的,它們起早貪黑的勤勉程度遠遠超過了人類,絕無一天閑著,也絕無一刻閑著,對工作的量與質,無須做任何攤派,也無須進行任何監督。
我擔心這只馬蜂飛著飛著突然就落在肉湯里燙死,我就輕輕地把滾燙的肉湯端起來,放進櫥柜里去。當我轉身回來的時候,這只馬蜂已經落在那砣煮熟了的肉上面,用力地啃嚙著,饑餓而貪婪。
它的刀很鋒利,很快就割下一砣肉,抱在胸前,在空中盤旋認點之后,急匆匆地往窗子的右邊飛去了。
我默坐在飯桌旁瞎想、瞎操心:這肉,我是放過鹽的,微咸,馬蜂吃了會不會傷腎?會不會患高血壓、冠心病和心律失常等疾病?這些只是慢性病,比不上我對這只馬蜂死活的操心:這只馬蜂會不會因為吃了放鹽的肉而立即死去?
按理來說,這只馬蜂如果不死,它是還要回來的。
兩分鐘過去了,四分鐘過去了,六分鐘過去了……那只馬蜂一直沒有回來,因為沒有理論根據,我不敢肯定,但只要那只蜂不回來,我的心就一直為它懸著。
我整整等了它十分鐘,這十分鐘就像過了一個世紀那么漫長,漫長得我的眼睛有些濕潤了。第十一分鐘剛剛開始,一粒紅彤彤的“火炭”從遠處彈了回來,差一點撞在玻璃窗上。等我定睛細看,那粒紅彤彤的“火炭”正是我等了一個世紀的那只馬蜂,我興奮得不得了,用拇指和食指捏著一塊瘦肉,在空中遞給那只馬蜂。那只馬蜂顯然是心存疑慮的,畢竟剛才它飛走的時候,認點定位的肉是在桌子上的盤子里,現在怎么突然在曾經用筷子來給它使絆子的我手里了?它幾次試著接近我手上的肉,卻又幾次離開,即使已經爬在我的手上,也微微地扇著翅膀,隨時做好遇險即離的準備。它肯定在想:眼前這個遞肉給我的人,該不該信任?經過幾次試探確認安全之后,它收起翅膀,收起懷疑,斂起稟性,穩穩地站在我的手上,啃著我兩根手指捏著的肉。
此時,它屁股上的毒針離我只有一張60克紙那么厚的一點距離,它完全可以給我一個鉆心的疼痛,通過針管把毒液輸到我的皮肉里,讓我疼,讓我受傷,讓我去死,對它來說,現在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世間萬物的關系總是相互的,這么短的距離留給我殺死它的機會也是同等的便捷,若想要它的命,在它毫無防范的時候,只要我的兩根手指閃電般用力一搓,這粒紅彤彤的火炭就得熄滅。
或許是餓壞了,或許是家有待哺的娃,也或許是與人為善,這只馬蜂毫無戒心地把我的手當作一個沒有仇恨的木頭砣,穩穩地站在上面,專心地啃嚙我手里捏著的肉,然后又像剛才那樣,再次認點定位之后,飛走了。
我知道,這只馬蜂還會再來,我們之間的修行還要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