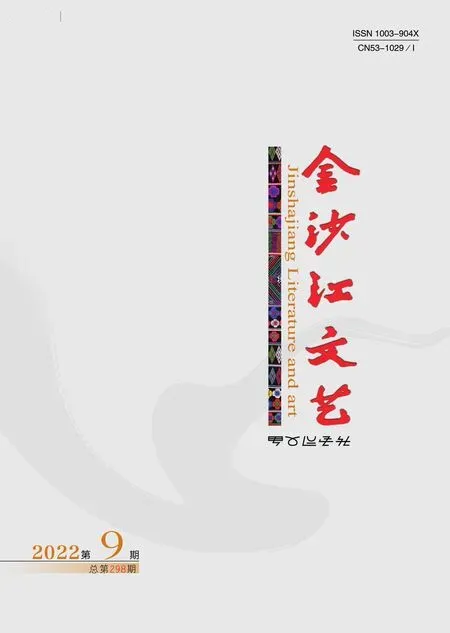我的番茄男友
◎武成勇
薄暮時分,我到達縣城。一下班車,一團燥熱的氣息就把我包圍了,這種熱氣不像牛城那樣的沾滯黏稠、濕漉漉,而是一種肆無忌憚的燎烤、一種赤裸裸的撩撥,點燃你內心暗藏的情欲。我環顧四周,周圍穿著短褲拖鞋的人們已經四散開去。我長吁一口氣,摸出墨鏡帶上,小城散發出了一種神秘的氣息。
我加快步伐走出候車大廳,眼前密密麻麻的車燈在閃耀。我站在路邊看著來來往往的車流,努力搜尋一輛車牌“云Exxxxx”的面包車。
“滴——滴——滴,滴——在這里,在這里!”一個瘦小的男人,從駕駛室里伸出半個身子,手搖得像風擺柳一樣。
我趕緊走過去。
面包車停在一棵小葉榕下面,車身被擋住了,我只看得到“五菱”標識的車頭。
“快上車!快上車!”一個胡子拉碴的削長臉緊張地催促著。
看著這輛灰撲撲的面包車,看見這個胡子拉碴的男人,我頭皮一陣發麻,心里發怵。
“你,是陳哥?”
“是呢,是呢,我是陳眼鏡。是你胖哥讓我來接你的。快上車,快上車!”
我屁股剛落地,面包車就“嗡”地沖了出去。
“到處都在整治!我這個月著兩張罰款單了。”
面包車駛離汽車站,轉入一條寬闊的大街以后,男人把臉轉向我,帶著諂笑向我解釋。
“麻煩陳哥了,我聽趙本耕說你今天要到他的基地,讓我搭你的車子進去。”
“不麻煩,不麻煩。小胖么,腳受傷了,兄弟么,我肯定要幫他啰。”
“趙本耕的腳怎么樣了,他只說腳破了,不大事吧。”
“什么不大事!腳底板都被戳穿了,站都站不起來!”
“啊,這么嚴重吶!”我一陣心跳。
“他沒跟你說啊”陳眼鏡瞟了我一眼,又趕緊盯著前方。
面包車駛離了縣城,穿過了一個村莊,四周影影綽綽都是各式小洋樓。
我坐立不安,心里火燒火燎,恨不得一下子飛到耕的基地,將他摟進懷里,撫慰他,減輕他的痛苦。
“陳哥,能不能開快一點?”
陳眼鏡開車有點奇怪,雙手不是握著方向盤,而是小心翼翼地捧著,身子前傾,頭微微昂著,眼睛盯著前方,一副神經兮兮的樣子。
“開不快啊,都是山路。”
“小胖真的沒有跟你說他受傷的事?”
面包車“咚”地一跳,我們在座位上跟著彈跳起來,安全帶勒得我胸口一緊,有點喘不過氣來。
“交稅交稅收費收費!路爛了也不修修!”陳眼鏡更加小心地看著路面,身子幾乎要傾到方向盤上。進山的水泥路很窄,一段一段的被車子壓的凸凹不平。
我不知道說什么好,心里空蕩蕩的。這半年來我們聯系越來越少,一年前每隔一個多月,耕還會到牛城一趟,然后兩人泡在一起,整個人都鉆進他的身子里去。分開的日子里,我們經常打微信視頻,我總把自己收拾利索了,頭發認真梳過,描眉上粉點唇,嬌嫩欲滴,臉頰緋紅,耕卻越來越邋遢,經常胡子拉碴,頭發蓬亂,說不了多久,要么說要滴水啰,打藥了,要么說太累了——往往聊不了幾句就關了。我握著手機的手慢慢地在僵硬、痙攣,臉頰在變冷,有時候大熱天全身卻像被寒霜覆蓋著。以前的耕手臂緊實,肩膀寬廣。“我可愛的姑娘,你怎么這么黏人喔!”耕黑發覆蓋我的時候總會這樣說。
在人前我喊他趙本耕,或者本耕。就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就喜歡喊他“耕”,不止是因為他的名字里邊有這個字。
想到這兒,我胸中似有一只小鳥,呼吸難耐,臉頰火辣辣的,喉嚨干燥,熱氣蒸騰,四面八方都是焦躁的氣息。
“哎呀,扎得真深吶,血流了一地!”男人說。
“啊,什么血流了一地!”
“十天以前,我送化肥去給小胖,他的硝酸鈣鎂不夠了。”陳眼鏡慢吞吞地給我講趙本耕受傷的原因。“硝酸鈣鎂是一種肥料,提苗補鈣的,還有番茄生長期全程都要養根,養根素不能少,轉色期膨果增色硫酸鉀也少不了——”
“本耕是怎么受傷的?”
“我這不是正在說嘛,小胖,兄弟么,我不幫他誰幫他!”
“我送肥送藥給他——連今天晚上送的他總共欠我八萬八千三百二十元了!”
“他答應賣番茄就付我農藥化肥錢的——前星期已經看得到紅了一個半個了,馬上可以賣錢了。”
我怎么感覺面包車里的氣味怪怪的,原來車廂里還拉了化肥農藥,有一種酸味,還混雜著大蒜味,怪不得我一路上一直想打噴嚏。
“小胖不容易,我陳眼鏡也不容易,這家欠幾千,那家欠幾萬,有些欠了一兩年,就是賴著不還——我不是說小胖啊,小胖有你這么一個在大城市的白領媳婦,一年工資都是幾十萬,是小胖的福氣啊。”
幾十萬,搶人啊!這個人正題不說,就只會繞來繞去的。
“陳哥,我和本耕只是朋友,我不是他媳婦。他欠你的化肥錢他會還你的。”
“是啊,是啊,幾萬塊錢么對你們來說是小意思啦。你和小胖,遲早的事么,等小胖這一茬番茄賣了,你們就結婚,去大城市買一套房,想回來就回來,不想回來,就在城市里面享清福。”
“本耕是怎么受傷的?”
“本耕?哦,小胖。他也是急啊,五包硝酸鈣鎂成了豆腐渣,五百五十塊錢飛天了!”
“什么豆腐渣?錢怎么飛天了?”我一頭霧水。
“農用的鈣和硫酸鉀是不能兌的。小胖基地的工頭老張在兌化肥的時候,池子里前次用剩的硫酸鉀殘渣還在,他又把硝酸鈣鎂倒進去了,高濃度的肥料原液就起化學反應了,變成像豆腐渣一樣的,有些變成了像石頭一樣的砣砣,要不成了!”
“小胖打電話給我,說我拉給他的化肥是假化肥。我一聽就鬼火冒,我陳眼鏡賣農藥化肥這么多年,坑過誰?害過誰?有一些賠慘了的基地老板,就會使各種陰招賴賬,說化肥農藥假啊,說工人出了人命啦,兩口子離婚了,基地被老婆要去啰……兩個月前,一個包土地種葡萄的外地人跑路了,頭天晚上都還好好的,第二天起來,一家人都跑得一干二盡,留下幾十個工人,你瞅我我瞅你,亂成一團,哭成一窩,一年的工錢飛天了。那個牛哄哄的王大頭,號稱自己一年賣五千萬的農藥,一下子就陷進去了300多萬,我估計他這一年就要白苦了。趙本耕,他每一筆都有欠條的,按有紅手印,有法律效力的!當然,小胖么,不像那些人種幾百畝、上千畝。他是講信譽的人,不至于。他還有你這么一位年收入幾十萬的媳婦。小胖么,兄弟么,我不幫他誰幫他!”
“哎呀,扯遠了,我繼續跟你講小胖受傷的事啊。”
我沉默著,盯著車窗外,偶爾有燈光閃過,好像是一些彩鋼瓦房子。
我在黑暗中能感覺到他的頭轉向我,獻媚地向我笑了一下。
“這些是基地老板的工棚,有種番茄的、葡萄的、三月瓜的,還有一些是種水果,芒果、大青棗、釋迦之類。”他見我盯著窗外的房子,補充著說。
“我繼續跟你講小胖啊。”
廢話!我能感覺到他又獻媚的向我笑了一下。我把手緊緊地摳住膝蓋,擔心控制不住,一巴掌向那張瘦臉甩出去。
“我到了基地,問了情況,跟他說了是鈣和硫酸鉀起的反應。”
“他就罵工頭,說老張是豬腦殼,是吃屎長大呢,七七八八罵了老張一些難聽的話。”
“那老張是一個火爆脾氣,也不是一個好惹的貨,又是旁邊村子里的人,膽子大!”
“老張就跳起來回罵胖子,說我忍你好久了,不要動不動就罵,動不動就擺老板架子,你算什么老板,花子,差人家化肥錢、地租錢、我們的血汗錢,你這種花子老板,隨便到大街上一掃,可以拉幾汽車!小胖哪里聽得,跳上前去揪打老張,地上有一把剪化肥口袋用的剪刀就插進了小胖的腳丫,他那天穿的是拖鞋,一下子就戳穿腳背了。小胖動作太快了,我才想抱住小胖,小胖就已經踩上去了。”
“哎呀,馬上那個血啊就流了一地!老張見小胖受傷了,知道事情有點大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辭工了。他說,老子不干了,你不仁我不義,花子老板,一個月的工錢我也不要了,送給你當裹尸布!小胖還想站起來打老張,我一把把他按住了。小胖咬著牙幫子看著老張把自己的鋪蓋栓在摩托車后座上,看著他屁股冒煙,像戰斗機一樣轟著油門沖出去,咬牙切齒的說,滾!全部滾!去滾金沙江!去跌巖子!我趕緊叫攏那些嚇傻了的小工,讓兩個男工拆了一副門板,抬小胖去村委會醫務室包扎。”
“耕啊,你還對我說就破了一點,原來傷得這么重!”我雙手壓住臉,有溫熱的液體被擠出指縫,在我冰涼的臉上流淌,心臟縮成一團。我像吃了耗子藥的老鼠,盡力將背弓起來,減輕心臟痙攣的痛苦。
“沒事的沒事的,現在小胖已經可以扶著拐棍站起來了。唉,小胖真的不容易。前天晚上小胖打電話給我,向我借錢。小胖沒跟你說嗎?”
“說什么?”
“錢啊!”
“什么錢?”
“交村上的地租錢啊!”
“他沒說啊。”
“哎呀,這個小胖,火燒眉毛的事情都不跟媳婦說!”
“本耕遇到什么火燒眉毛的事情啦?”
“村長來逼錢!唉,還不是那個工頭點的水,本來小胖的土地是簽了三年的合同,地租一年一付,他已經付了一年了,下一年的地租本來要到一月一號才付呢,現在才11月初嘛,不到時間呢嘛。那個老張回去以后在村子里撒浪藥,說小胖差人家農藥化肥錢,差人家水電費,差人家工錢,都沒有小工來幫小胖干活啦,天天都有人找小胖要錢啰,小胖要跑啰,亂七八糟地說一些。根本不符合事實嘛,小胖工錢才差了小工一個月,農藥化肥錢,只差我一個嘛,我也沒逼小胖不是,我只說番茄開始賣錢才還我嘛。”
“是啊,本耕的番茄不是馬上要賣得了嘛,這些人急什么,像催命鬼一樣!”
“催命鬼催命鬼,是啊,像催命鬼!”
“原來很好打交道的幾個廠家,都鬼精鬼精起來了,都要先打款后發貨。有幾家么徹底倒閉了,環保不過關,關了。有一家說好的年底再打款,現在像催命鬼一樣,今天一個電話,明天一個電話,煩死了。”
“你那個本耕哥也遇著催命鬼了,小胖跟我說,前天,村長開了一臺挖機,帶了二十多個人,二話不說,梆梆梆地就把基地的路挖斷了,說三天之內不付錢,這條路就要拉石頭來把它砌起來,讓狗都跳不出去!”
我倒吸了一口涼氣,這不是欺人太甚了嗎!
“本耕的番茄不是馬上賣得了嗎,番茄一賣,都能付嘛,而且合同上不是寫著一月份才付嘛,這些人還講不講理啦!”
“講理?講不清啰,我們今天也要走路進基地了。”
“現在種基地多跑路了這么多,誰不怕!我都要天天盯著呢。”
“種基地的為什么要跑路?”
“為什么跑路?賺不著花花紙啊!”
“地租要錢,種苗要錢,架材要錢,吃飯要錢,小工要錢,水費電費,那樣不要花花紙去付。等到蔬菜水果一上市,遇著爛市,哦豁,竹籃打水一場空。收地租的來了,收苗錢的來了,小工要逼工資了,當然,農藥化肥錢也要付呢,像我這樣的小本生意,哪個欠我十萬八萬的,我就倒馬了,娃娃要供書呢不是?”
“本耕的番茄肯定好賣的,我回來的時候到超市問了一下,標價都是八塊多九塊一公斤呢。”
“哼,八九塊,八九毛還差不多,現在的收購價,精品一塊五,中等貨一塊,差一點的八九毛!”
“啊,怎么差距這么大,那些二道販子不是賺大發了?”
“也不一定,你的本耕哥就做過蔬菜生意嘛,是搞蔬菜批發不好搞才來種番茄的嘛。”
耕在牛城跑了兩年業務以后,他說看到了一個市場機會,兩年前辭了營銷總監的職務去做菜生意,從云南四川倒騰一些番茄、萵苣、白花菜、西蘭花、上海青去大東南市場批發,剛做了一年,城市環境整治,大東南市場被拆遷,要求商戶都搬到政府統一規劃的室內批發市場去。但市場被一家集團公司買斷了經營權,租金死貴,耕說,我才不讓這幫小子吸我的血呢,我已經發現了一個更好的市場機會,我要做現代農業,當新農人!
耕雙手在我腰間一叉,我就像小鳥一樣飛起來啦,我雙腳亂蹬,他哈哈大笑。
“我調查過了,這兩年搞現代農業很有出路,各地政府積極招商,提供方便,種基地的都發了,一畝賺三萬五萬很輕松,有的一畝賺十多萬也不稀奇!”
“再過兩年,我三十歲,你也二十八了,那個時候,我會開著大奔迎娶你的,我要讓你做世上最美的新娘!”
我還能說什么呢,耕跑業務是高手,做蔬菜生意也賺了幾十萬,他強壯,激情四射,生機勃勃,我相信沒有耕跳不不過去的坎,跨不過的山。
但現在,我害怕,害怕耕真的難應付這么多的事。
“那,本耕借到錢了嗎?”
“曉不得。你不知道我有多難,兩個讀書娃娃要供,媳婦在鄉政府,領的是死工資,我這個小本生意,賒賬大,只要有一筆賬要不回來,我一年就白干了——我讓小胖到別處借借看,我還等著他賣番茄還我的化肥藥水錢,白天我去接你之前,廠家業務員又催債了,說再不還錢,就要到我家來,跟我同吃同住,這個草狗!”
“那明天不是就到村長規定的最后期限了嗎?本耕還有其他朋友嗎?”
“應該沒有了吧,除了我之外,他還認識幾個做基地的,好像也不太熟。”
“他欠地租是多少錢?”“十四五萬吧。”
我盤算了一下,余額寶里面有五萬,工資卡里還有三萬多一點,全部加起來也才有八萬多一點。
眼鏡好像也知道我在盤算錢,他突然高興起來。
“妹子,這下好了,小胖的救星來了。五六十萬存得有吧!”
“哪有那么多,城市生活成本挺高的。”
我不愿意讓他知道我壓箱底的錢才有八萬塊。
“三四十萬也可以了,小胖的番茄不是馬上能賣錢了么。你先墊點給他,把村子里面的地租付了,順帶把我的化肥錢也付了,廠家催得緊。”
“哪有那么多!”我驚奇這個人怎么會如此一廂情愿。
“那就只有十多萬了。”眼鏡沉默了一會說。
我能感覺到他在黑暗中擺了一下頭,瞅了我一眼,惡狠狠的,肯定!
八萬塊能干什么,在牛城能買十平方的小區房,而且要在五環以外,在牛城能租個小公寓兩年。但是,林草說,她參加了一個派對,一晚上就花了八十萬,這個萬花筒一樣的牛城!
林草失蹤了,她參加過八十萬一晚上的派對,而我沒有,他上過很多男人,而我只有耕一個男人。
她失蹤前的半年,我們還是室友,我們四個女孩曾經擠在一個套間里:林草、云、璐璐和我。
現在林草失蹤了,云去了日本,只有璐璐和我住在一個二十層高的有八十平方的一個大套間里,我每天早上起來都覺得太幸福了,靠在窗臺上,陽光燦爛,看著寬敞的客廳,想象著耕和我擁有這樣一個家,我們相擁在客廳沙發上,幸福纏綿。
我們合租的時候,好像約定俗成一樣,誰也不打聽誰的私事,誰也不能帶男人回來,包括林草也沒有。一年前,有一次耕來看我非要到我們的公寓看看,我偷偷摸摸的帶他進去過一次,耕非要在房間里親熱,我堅決不同意。雖然他們都不在,但我總感覺她們的三雙眼睛都在亮晶晶地盯著我。
林草換男朋友就像換馬燈一樣,而且每一個都是林草蹬的對方。有一次,我們剛走到小區門口,一個白西裝突然向我們奔過來,撲通一下就跪在林草面前,痛哭流涕,說:“你原諒我吧,我不能沒有你啊,這是車鑰匙,這是房子鑰匙,這是銀聯卡,上面有三十萬,都給你。”
林草不屑一顧,拂袖而去。把我們幾個羨慕得要死。問她怎么能把人家搞得這么神魂顛倒!林草輕蔑地一笑:“這算什么呀,一個要破產的小老板,還跟我裝大款,千萬資產都有不起,你們說氣人不氣人!”
沒有搞不定的男人!這是林草的口頭禪,我們深以為然。他有著飄逸的長發,勾魂的眼睛,潔凈的臉龐,高聳的乳房,再加上蜂腰、翹臀、高挑個,很讓同類的我們自慚形穢。
兩個月前,林草搬了出去,搬到未婚夫家去了,說未婚夫,是男方和他扯了結婚證。男方我們見過,請我們去五星級酒店吃過兩次大餐,肥頭大耳,頭發锃亮,很寵林草,LV包包都為林草買了六七個,聽說還準備買一輛寶馬給林草。
一星期以前聽林草的一個親戚說,他從男方家搬出去了,還沒有舉辦結婚儀式就離婚了,他們在辦結婚證以前訂有婚前財產公證,林草凈身出戶,被掃地出門了。
我打林草的電話,關機了;微信也被她拉黑了,包括身邊的所有和林草相識的人都沒有她的信息,林草在這個城市蒸發了,不知所蹤。
云在林草失蹤以前就去了日本留學,她老爸有錢,供得起她。璐璐在一家商標事務所上班,天天上班就是打電話:“老板你好,請問要不要辦理商標注冊、商標轉讓。”經常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對方掛了。她被人拒絕也不生氣,換一個電話繼續打。璐璐一個月一般能領三千多大洋,有時候能領到五千多,工資一打到卡上,就馬上去還信用卡。她平時就買買化妝品,去找好吃的小吃,實在沒錢了,就連續煮幾天面條吃,面條吃不住了,就建議我去“外婆家”搓一頓,當然是我請客了。
璐璐平時有錢沒錢都是樂呵呵的,只有一次看見她憂愁了半個鐘頭,那次我倆在小區的水果攤前經過,看見一對夫婦在買水果,男人稱了一兜發黑的處理香蕉,女人拿了兩個蘋果放上去,男人把蘋果揀出來,婦女又把蘋果裝進去,央求男人說:“我想吃,就兩個。”“吃什么吃,你還吃得高級呢嘛,路邊呢狗屎你怎么不吃!”男人忽然發怒起來,用當地土話高聲地咒罵女人。女人不再堅持,默默地跟在男人后面走了。
我和璐璐對望了一眼,懨懨地回公寓,在回公寓的路上,我兩誰都不想說話。回到公寓,璐璐癱坐在沙發上,喃喃自語:“怎么辦啊,怎么辦啊,如果我將來嫁一個窮男人,那我豈不是連蘋果都吃不起嗎?我的小龍蝦啊,我的大閘蟹啊,我要吃啊!”
她見我不吱聲,站起來,在客廳里轉了一個圈,點著頭說:“對了,對了,只要不結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誰也管不著!”
然后,璐璐又高興起來了。
我也被璐璐感染,努力讓自己心情舒暢,有時候看著寬敞的公寓,在窗臺上曬著太陽,覺得幸福極了。天天上班、下班,周末窩在窗臺上看看書,逛逛超市,夢想著有一天,耕會開著大奔來迎娶我。
但最近半年來,耕都不常來看我了,電話也聊不了幾句就掛了。連璐璐都看不下去,說:“他再不來看你,你就找別的男人去!”
我不是沒有男人要,偶爾也會和別的男人去吃頓飯,看看電影,但這些男人都太直接,一個胖子第一次見面就和我討論結婚的婚禮要怎么辦;有一個相貌堂堂的,本來還想備胎一下,吃了兩頓飯,聽說我還要考慮考慮,就再也不請第三頓飯了;有一個運動健將,請在一個酒吧見面,從酒吧出來,下起了小雨,他說去我車里避避雨吧,沒想到一關上車門,就要往我身上摸,我擋開他,說是不是太快了一點,他說,都是成年人,裝什么裝啊!
我不想裝,但一對男女要有親密接觸,至少要有一點喜歡吧,不然和畜生又有什么區別?
最近一直在做噩夢,一會兒耕牽著別的女人的手,目不斜視地走過,一會兒是耕結婚了,新娘卻不是我……
現在,我終于來了,一個馬上三十歲的老女人,像少女懷春一樣來投奔自己的情人,然而,我卻幫不了他什么忙。
“只有十多萬啊!”陳眼鏡說完這句話以后就不愿意和我多說,一直冷冰冰地開車。
只有十多萬,我十多萬都沒有啊,耕哥!眼鏡!
我掏空全部家底只有八萬塊,把我賣了吧,鞋子賣掉、襪子賣掉、褲子賣掉、外套賣掉、胸罩賣掉、內褲賣掉,把我整個人拿去稱斤湊兩賣掉,去湊十萬塊!
面包車在盤山路上繞來繞去,我胸口沉甸甸的的,呼吸困難,張開嘴呼吸,胃里又一陣翻江倒海。
“陳哥,能開慢一點嗎,要不,停一下。”
“開不慢了,正在爬坡,更不要說停了,除非我們一起找死!”
面包車轟鳴著爬行在盤山道上,昏黃的車燈焦躁地左右搖擺,我們好像雜耍舞臺上的兩個小丑。
我強忍著,好了!馬上就好了!爬上這道山梁,就會有平坦的道路,有美麗的風景,有怡人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