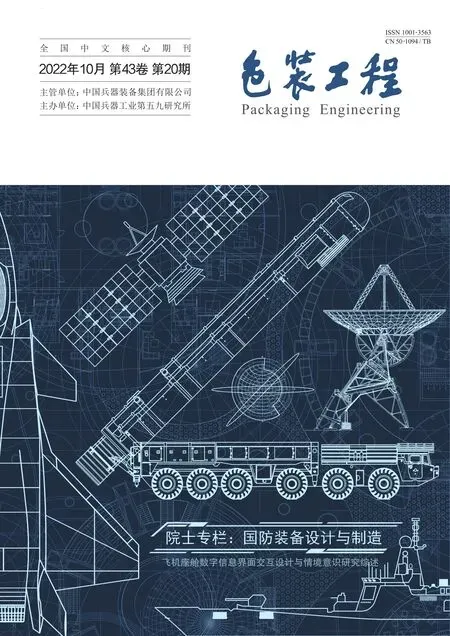戰(zhàn)國“山字紋”銅鏡設計研究
董岳,鄧莉麗,韓貝貝
(1.上海工藝美術(shù)職業(yè)學院 上海 201800;2.澳門科技大學 人文藝術(shù)學院,澳門 999078;3.江蘇大學藝術(shù)學院,江蘇 鎮(zhèn)江 212000;4.淄博市博物館,山東 淄博 255000)
“山”很早就是人們猜測和崇拜的對象。《釋名》載:“老而不死曰仙,仙者遷也,遷入山也。”認為山是神仙遷居之所,且“山”作為仙界符號,是求神問道的圖像信仰。戰(zhàn)國時期,原始宗教吸收陰陽思想,將“山”看做通往天神居所的道路。以“山”作為符號依附鏡中,傳承了人們早期和原始宗教的認知痕跡。“《戰(zhàn)國策·齊策一》載:‘朝服、衣冠窺鏡’;《楚辭·九辯》:‘今修飾而窺鏡兮’。[1]”可見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75 年—前221 年)使用銅鏡正衣冠、做飾物的習慣已較普遍。其中“山字紋”銅鏡最富特色,因在戰(zhàn)國楚地較流行,故又稱“楚國鏡”。
1 山字紋設計緣由
李學勤先生認為:“從戰(zhàn)國晚期出現(xiàn)的動物紋山字鏡看,表現(xiàn)出山間狩獵情形,稱‘山字紋’是沒錯的。”特別在戰(zhàn)國秦漢時期,“動物活躍其中則表示山峰的遙遠。”[2]但究竟哪些因素對銅鏡中“山”字的設計發(fā)展產(chǎn)生影響?設計寓意眾說紛紜。筆者嘗試從文獻及器物圖像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
《說文》載:“山有石而高,象形也”;《國語》載:“山者,土之聚也”;《荀子》載:“積土為山”。[3]從“山”字形象及字形衍化看,均反映人們對土地存在形式及山的定義。日本學者駒井和愛在《中國古鏡的研究》中提到,甲骨文、金文的寫法與現(xiàn)代“山”字幾乎沒有差別,隸書書寫特征與山字架構(gòu)造型更為相似,見圖1。還有指出山字紋源于甲骨文中的火字(見圖2),是“火字”的變形。同時,“河北平山戰(zhàn)國中山國王墓葬出土的山字形銅禮器,以及湖北江陵雨臺山楚墓出土的竹編器物上的山字形紋飾可以看出古人祭山拜山的習俗。[4]”體現(xiàn)出山形(字)對習俗信仰的使用淵源和裝飾符號。

圖1 “山”字的書寫變化Fig.1 Writing changes of the character "山"

圖2 “火”字的書寫變化Fig.2 Writing changes of the word "火"
從青銅禮器紋飾看,春秋末年禮崩樂壞,青銅文化式微,尊祖崇巫信仰坍塌。“器型與器類中,‘復古’之風對周文化傳統(tǒng),多見于較高級別銅器群中,似乎禮制乃至思想意識較為保守的社會階層,往往是地位較高的貴族階層。”[5]且當時楚國貴族和士人集團成為青銅文化的推動者,把持著青銅器(包括銅鏡)的命運,傳承創(chuàng)造出獨特的“山”字銅鏡。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的霸伯山簋(見圖3),山簋指山形及山形紋;器蓋一圈連山,8 個山形鈕,大小相錯,大鈕居四隅,小鈕居四正,紋飾凸起,兩側(cè)起棱,如峰巒。再如西周后期竊曲紋簋(見圖4),四面紋飾均同,每面均飾波浪狀竊曲紋,專家認為是山字紋。這表明“山”的形態(tài)在青銅中早有應用。還有學者指出“山”字是繼青銅器中“T”形勾連云雷紋演繹而來,以勾連雷紋為一個單元,并推論勾連雷紋由古代陶器中蛙紋演變而來,且“山”字的源頭是蛙紋。從形態(tài)上看,古蛙紋與“山”紋有相似之處,蛙作為水陸兩棲動物,具有強大的繁衍能力,是古代生殖崇拜文化的體現(xiàn)。

圖3 霸伯山簋Fig.3 Baboshan Gui

圖4 竊曲紋簋Fig.4 Qiequwen Gui
從上述文獻和圖像信息看出,“山”“山紋”“山”字的設計緣由和解釋均有依據(jù)。另有學者指出,“山”字是模仿新石器時期良渚文化三叉形器(見圖5),因器物上端并列3 個枝叉造型而得名,在墓葬中安置于死者頭部,亦與墓中出土的覆蓋于人臉面部的銅鏡功用相似。那么,從“山字紋”銅鏡的出現(xiàn),并結(jié)合戰(zhàn)國時期疆域遼闊且地貌多丘陵山地的特征,表明“山”的形象用于器物裝飾,是集歷史、信仰、文化、形式于一體的幾何紋樣符號。“山字紋”銅鏡既具有神性特征給人以寄托,又是文化傳承中特權(quán)階層禮儀、功用、享樂的尤物。

圖5 神人獸面紋玉三叉形器Fig.5 A jade trident with sacred, human and animal face
2 “山字紋”銅鏡設計特征分析
“梅原末治則認為,早期鏡子以饕餮紋和羽狀紋為主,后在羽狀地紋上置以‘山’字,出現(xiàn)較晚,但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紀”[6]。即說明羽狀紋是地紋裝飾基礎,后來增加其它紋樣作飾。學者鄧秋玲則根據(jù)銅鏡出土的墓葬年代、與墓中其他器物作對比,以及山字銅鏡的地紋裝飾變化來判斷山字紋銅鏡的分期,具有一定代表性[7];但文中提供的銅鏡圖像模糊不清,且筆者發(fā)現(xiàn)銅鏡中的山字形態(tài)、地紋裝飾及整體形式從不同視角分析各具特色,僅從一個方面難以作為確切的分期考據(jù)判斷。基于此,在考古分析的基礎上,依據(jù)“山”字數(shù)量、山字形態(tài)特征、組合形式變化與地紋裝飾變化進行綜合研究。
2.1 三山紋鏡
三山紋鏡出土少(見表1),較為罕見,均圓鈕座,多三弦、四弦鈕,鏡緣上卷。

表1 三山紋鏡Tab.1 Three-mountain pattern mirror
2.2 四山紋鏡
四山紋鏡出土較多(見表2),多方鈕座,三弦鈕較多,有單弦和雙弦鈕;出現(xiàn)形制罕見的方形銅鏡,方鈕座、三弦鈕,平緣。從出現(xiàn)的不同花葉紋裝飾及變異形式的山字紋看,圖案裝飾性更強。從鏡鈕與山字排列方式看,“山”字方正,故多用方形鈕,另有其它排列形式。可見,四山紋銅鏡的構(gòu)成形式和山字變化較為規(guī)則,且紋樣的設計裝飾更成熟豐富,并存在差異。有的四山紋山字粗短外擴,地紋裝飾弱,如四山羽地紋鏡[8],有的則地紋中花葉豐富,如十二葉四山紋銅鏡[9]、十六葉四山紋鏡[10],但整體裝飾性較強,并與鏡鈕發(fā)生形態(tài)動勢變化。

表2 四山紋鏡Tab.2 Four-mountain pattern mirror

續(xù)表2
2.3 五山紋鏡
五山紋鏡多圓鈕座(見表3),三弦鈕,也有單弦鈕,鏡緣有平有卷,鏡面尺寸變大。山字多呈修長纖細之態(tài),山紋動勢強烈,地紋中羽狀紋細密,花葉紋變化多樣,構(gòu)圖飽滿,裝飾性更強,在制作工藝上,出現(xiàn)了高浮雕形式。

表3 五山紋鏡Tab.3 FIve-mountain pattern mirror

續(xù)表3
2.4 六山紋鏡
六山紋銅鏡出土較少(見表4),尺寸更大,均圓鈕座,多三弦、四弦鈕;在六山紋銅鏡中出現(xiàn)鑲嵌裝飾,綠松石、琉璃等材料的應用表明工藝技術(shù)成熟,更注重材料美感。“蜻蜓眼”作為琉璃裝飾之一早在公元前2 000 年的兩河流域和埃及已流行,是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產(chǎn)物[11]。大尺寸的六山銅鏡并不多見[12]。凸顯六山銅鏡的設計形式、制作工藝更加成熟,審美追求趨于穩(wěn)定。同時,六在周禮中有著特殊含義。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公羊傳》皆云:“天子駕六”。可見展示出楚王的禮制王權(quán),并成為與周朝分庭抗禮的物證。

表4 六山紋鏡Tab.4 Six-mountain pattern mirror
通過梳理對比相關“山字紋”銅鏡,“三山”和“六山”鏡較少,“四山”“五山”鏡居多。鏡緣通常不加裝飾,寬窄不一,多素窄卷緣,見圖6。

圖6 鏡緣、鈕座、弦紋及地紋分析Fig.6 Mirror edge, button seat, string pattern and ground pattern analysis diagram
從鈕座看,均采用山字合圍鈕座形式,分圓形鈕和方形鈕,弦鈕有三弦、四弦;圓形鈕居多,不同山字鏡中均有出現(xiàn),方形鈕主要集中于四山紋銅鏡。其中四山銅鏡中,方鈕與“山”字的排列形式分為兩類:一是山字置于方鈕四角或一角置于方鈕中間,二是山字與方鈕平行排列;從鏡鈕與周邊“山字”、地紋設計的關系看,第一類構(gòu)圖飽滿,山字粗短,地紋花葉較大;另一類構(gòu)圖更為寬松,山字趨于細條,地紋花葉較小且趨于細密。
從“山”字單個形態(tài)看,分為粗短外擴和修長內(nèi)收;粗短、修長是根據(jù)山字整體形態(tài)判斷,外擴、內(nèi)收則根據(jù)山字兩側(cè)短豎判斷;同時,銅鏡中山字的兩短豎劃有明顯內(nèi)折尖角的細節(jié)造型。
從“山”字組合形式看,根據(jù)鏡面構(gòu)圖分為飽滿且動勢平穩(wěn)和寬松且動勢較強兩種形態(tài)。主要根據(jù)圓鈕座的山字紋鏡布局構(gòu)圖形式分析,其中在四山紋鏡中構(gòu)圖較寬松,山字動勢相對平穩(wěn),亦是由特殊的形態(tài)決定,還有變異性四山紋鏡,可見山字形態(tài)結(jié)合多要素進行組合變化。
從地紋裝飾內(nèi)容看,主要分為羽狀紋、植物紋、獸紋三大類。其中植物紋和獸紋的出現(xiàn)使地紋裝飾更加細密緊湊,與山字組合使鏡面更加飽滿,裝飾性更強。“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植物紋包括梅、蓮、花朵、花葉、柿蒂、藻、樹。”[13]從植物花葉紋看,集花、蕊、枝、葉結(jié)構(gòu)組合于一體,有的紋樣單一,多單葉紋,有的花莖與蔓直曲相連,還有變形夸張花葉,作幾何式變化;從植物花葉紋的設計變化看,形式美感更強。單從造型看,很難確定自然界中的對應原形,但可以判斷是對植物紋樣進行藝術(shù)加工的結(jié)果。
從工藝技術(shù)看,分普通浮雕工藝、高浮雕工藝和其他材料裝飾工藝(綠松石、琉璃等),可見其做工精細,工藝精湛,說明人們有意將更多工藝技巧、材料用于銅鏡裝飾,是當時審美趨勢和山字銅鏡走向成熟的顯現(xiàn)。從出土地看,“山字紋”銅鏡集中于當時楚地,即今日湖南、湖北、河南(東南部)、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及江西,也有少數(shù)出土于廣州、陜西及西域等地。
同時,結(jié)合考古發(fā)掘中山字紋銅鏡出土年代,反映了山字紋銅鏡裝飾形式和審美趨向的變化,以及不同階段對藝術(shù)審美和文化價值的追求。“在今蒙古國境內(nèi)的阿爾泰山西麓也有發(fā)現(xiàn)‘四山紋’鏡。[14]”表明當時銅鏡流動的廣泛性。說明當時多地域間的溝通往來和銅鏡工藝的繁榮對物質(zhì)文化所起的推動作用。
2.5 “山字紋”設計形式分析
古人崇尚天地相通,山與天接,圓(鏡緣)象天,“山”紋中道(豎劃)切于鏡緣意為“頂于天”;不同山字造型有所差異,粗壯或細長;其余兩筆較短豎劃轉(zhuǎn)折呈尖角,部分外框有細邊相連,呈(或左或右)旋轉(zhuǎn)流動之勢。
從形式構(gòu)成角度分析(見圖7),“山”呈順、逆時針方向旋轉(zhuǎn),從山字數(shù)量和傾斜角度看三山旋轉(zhuǎn)角度較大,在 110°~125°;六山旋轉(zhuǎn)角度較小,在55°~60°,山字越多,旋轉(zhuǎn)角度越小;四山角度通常在90°,五山角度通常在75°左右;同時,從單個“山”字的形體傾斜角度看,每個在60°左右。總之,“山”字根據(jù)圓形銅鏡形制、大小及山字自身傾斜角度而改變,形態(tài)排列、形式構(gòu)成有所節(jié)奏韻律,構(gòu)成與鏡面空間相符的“適合紋樣”。

圖7 山字動勢和單個“山”字分析Fig.7 Momentum of the mountain character and the analysis diagram of a single "山" character
2.6 “山字紋”設計視覺審美分析
黑格爾曾說:“工藝的美不在于要求實用的外部造型、色彩、紋樣去摹擬實物,再現(xiàn)現(xiàn)實,而在于使其外部形式傳達和表現(xiàn)出一定的情緒、氣氛、格調(diào)、風尚、趣味,使物質(zhì)經(jīng)由象征變成相似于精神生活的有關環(huán)境”[15]。可以說特定的工藝創(chuàng)造了特殊的視覺表現(xiàn)形式,更塑造了一種無限想象的視覺效果。
首先從構(gòu)圖形式看,“山”字具有一定秩序性。從“山”字的層次感來看,山字主體突出,與地紋陪襯紋樣和諧;從“山”字的視覺牽引來看,動勢具有一定規(guī)律,并在不同數(shù)量的鏡中均有整正,不論是哪種類型的山字紋,都給人一種平衡感、舒適感。從銅鏡整體設計特征變化看,趨于裝飾性、豐富性、成熟性,特別是注重動物、植物紋應用于羽狀地紋上,并選擇新工藝、新材料等增強山字紋銅鏡的整體視覺效果;同時,“山”字紋不論在視覺還是觸覺體驗上,均具有對比性,強化“山”字的視覺形態(tài)體驗和沖擊。
再次從造型和表現(xiàn)方式看,在看似重復的“山”字中追尋微妙的變化。楚人崇尚字體纖細,故“山”字形態(tài)中修長內(nèi)收的特征更趨于當時審美,兩短豎內(nèi)折尖角細節(jié),以及夸張的動勢,使山字在造型、形式、構(gòu)圖更加講究。盡管銅鏡的利用空間有限,底紋中的紋樣占據(jù)大面積裝飾,但人們利用陰陽相間的淺浮雕工藝技術(shù),通過“山”字的負空間表現(xiàn)方式和運用負空間視覺表現(xiàn)方式,打破了原本空間裝飾的局限,使人們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山”字的形態(tài)動勢變化中,也表明了工藝技術(shù)與審美在視覺傳達上是密不可分的。“山”字即是圖,圖即是“山”字。“圖形跨越地域的限制,突破語言障礙,有著‘一圖頂萬言’的傳播效能,不論具象與抽象,立體與非立體等,均因整體設計效果而適當變化。”[16]
最后從整體的視覺審美效果看,基于“山字紋”變化特征較弱,設計者更關注地紋空間裝飾,從早期帶有宗教神性崇拜的羽狀紋,到日常所見的植物、動物紋等,體現(xiàn)出地紋裝飾趨于世俗化,并結(jié)合其他工藝、材料做裝飾,以求鏡面視覺審美更加強烈。“人們對隱喻的理解不可避免地有著想象、理解、情感等因素的參與。[17]”地紋裝飾不僅強化了“山”字的主題性,而且聯(lián)系底紋裝飾內(nèi)容進行了視覺隱喻的渲染,使整幅鏡面喚起了人們心理審美和情感的想象。值得強調(diào)的是山字紋銅鏡可分為山字粗短外擴簡地紋(羽狀紋為主或簡單花葉)、山字粗短外擴繁地紋(多種花葉紋或、獸紋及其它裝飾)、山字修長內(nèi)收簡地紋、山字修長內(nèi)收繁地紋幾類特征,山紋和地紋設計也根據(jù)銅鏡鈕座的方圓造型不同進行排布,見圖8。

圖8 山字紋銅鏡不同特征及圖底關系分析Fig.8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untain-shaped bronze mirro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ttom of the picture
由此可見,從視覺審美的視角分析,其遵循著一定秩序性和規(guī)律性,使銅鏡中紋樣的比例、位置、動勢、層次按一定規(guī)律聯(lián)系在一起。同時,山字紋銅鏡中的負空間表現(xiàn)方式,不僅可以突出“山”字的主題核心,而且在視覺形態(tài)審美上被增強,具有明顯的視覺沖擊力,并在統(tǒng)一中存在微妙的創(chuàng)新與變化。
2.7 “山字紋”銅鏡設計原理分析
古代銅鏡多以鏡鈕系繩懸掛,或鏡架支撐擺放,唐代出現(xiàn)帶柄銅鏡,操持和使用更加便捷[18]。從“山字紋”鏡出土尺寸看,徑短者在9~13 cm,徑長者銅鏡在14~20 cm,甚至更大,有的長達27 cm,擺放于固定位置。
“根據(jù)古代墓葬中畫像石、壁畫或古代繪畫作品中有關使用銅鏡的圖像資料分析,手持銅鏡時,鏡鈕中穿系紡織品或植物編制綬帶,然后手持綬帶映照面容。[19]”,東漢持鏡陶俑,從侍女操持銅鏡方式看,尺寸可能在10~12 cm,便于手持使用或隨身攜帶,見圖9;再如山東嘉祥縣東漢武梁祠,刻“梁高行割鼻拒聘”照鏡圖(見圖10),呈現(xiàn)出手持銅鏡綬帶的方式。

圖9 東漢持鏡陶俑Fig.9 Pottery figurines holding mirrors in Eastern Han

圖10 武梁祠梁高行照鏡操持圖Fig.10 Liang Gaoxing's mirror operation in Wuliang Temple
從銅鏡材料配比看,銅、錫、鉛三元合金配料決定人影成像的清晰度;當含錫量大于20%,成像效果較好,在20%~25%成像效果最好;只有合金硬度達到一定程度,鏡面打磨后才會產(chǎn)生光澤。結(jié)合銅鏡材料、尺寸對映容效果分析(見圖11),當銅鏡放于距面孔15~20 cm 處,以相對平視姿勢可能較為清晰的映射人臉細部;以此為標準,徑長9~12 cm,方便攜帶,若想映射人臉全貌,可手持調(diào)節(jié)映容距離角度;若以人像呈現(xiàn)最大面容為準,徑長要大于14 cm,如前文所分析的銅鏡中,鏡面尺寸較大,更方便映照面孔全貌和細節(jié)。

圖11 銅鏡使用操持圖Fig.11 Operation diagram of the use of bronze mirror
3 “山字紋”銅鏡設計文化評析
“春秋戰(zhàn)國巫文化和道家學說作為楚文化一大特色,對古代哲學和宗教產(chǎn)生深刻影響,其標新立異對后來居上的中原文化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20]。體現(xiàn)出楚人對人與鬼神、仙人仙境的渴望,并產(chǎn)生上天入地的幻化空間意識。
早期銅鏡主要功能并非映容,而是代表先人太陽神崇拜的神器法物,用于宗教活動,人們在生活中遭遇困境時,利用鬼神信仰和巫術(shù)活動,借以鏡為特殊法器,祈求神靈旨意,這一觀念與銅鏡反光映物的物理特性有一定關系。“銅鏡拋光面被稱為正面,使用時映照面容,另一面(背面)有鏡鈕,四周環(huán)以圖像;從背面的裝飾中可獲得非直接的指涉性含義,如道教仙山、儒家典范等,每種設計和材料都與鏡子擁有者特定的身份及自我形象相聯(lián)系,甚至暗喻了秘密的幻想和個人欲望。[21]”同時,古時安裝于房屋宮殿、車輿或佩鏡都為了避邪求吉,至今在很多地區(qū)仍延續(xù)著鏡子辟邪的信仰。
戰(zhàn)國時期,神仙之說在楚國高談,融合老莊等道家學說,糅合民間思想信仰、崇拜道教方術(shù)。《抱樸子·內(nèi)篇·登涉》載:“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表明道士學仙成仙,必入山才可得,并以銅鏡作為入山尋仙必備法器之一。《拾遺記》載:“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猶華山之似削成。三壺,則海中三山也。”[22]表明以銅壺外觀比擬三神山。圖12 為戰(zhàn)國銅羽紋壺,高31.8 cm,腹徑24.3 cm,肩部兩側(cè)飾兩獸首銜環(huán)耳,肩腹部四周素帶相隔飾羽狀紋,圈足飾繩紋。“圓鏡方圖,鏡中安圖,使‘天圓地方’的宇宙結(jié)構(gòu)論和‘道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論通過醮祭儀式完美結(jié)合。”[23]

圖12 戰(zhàn)國銅羽紋壺Fig.12 Copper pinnate pot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楚辭·遠游》載:‘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xiāng)’,王逸注《山海經(jīng)》:‘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24]表明羽化登仙形象深入人心,祈求長生之愿。如“袁氏神人龍虎畫像鏡”中二神四侍(見圖13),兩側(cè)侍為人,主神為東王公與西王母。“秦漢之際眾多仙人神獸鏡、飛仙鏡,以鏡寄托現(xiàn)世幸福的愿望,裝填長生不老的祈術(shù)、祈禱。”[25]因此,銅壺、羽紋、“山字紋”銅鏡、山形(字)的裝飾等皆是對道教信仰的反應。在“山字紋”銅鏡中以羽狀紋做裝飾,出現(xiàn)的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方式,依然延續(xù)羽狀形態(tài)特征和道教文化寓意,見圖14。同時,在不同時期出現(xiàn)了相關道教的事略(見表5),并在各類實用品、裝飾品、禮器、祭器及文學作品中呈現(xiàn)。

圖13 袁氏神人龍虎畫像鏡Fig.13 Portrait mirror of the Dragon and Tiger of Yuan's God and Man Image Source: Unearthed in Jingmen, Hubei

圖14 羽狀紋形態(tài)Fig.14 Schematic diagram of pinnate pattern

表5 戰(zhàn)國時期道教相關美術(shù)年表[26]Tab.5 Chronology of Taoism related ar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續(xù)表5
4 結(jié)語
通過對戰(zhàn)國“山字紋”銅鏡,山紋(字)的設計源流、“山字紋”銅鏡設計特征及設計文化評析,展示了戰(zhàn)國時期青銅藝術(shù)制作成就,同時,從單個“山”字形態(tài)、山字組合形式、地紋裝飾及工藝技術(shù),都展示出山字鏡設計是集歷史、工藝、審美、功用、信仰、文化于一身的佳作。山字紋銅鏡中山字粗短外擴簡地紋(羽狀紋為主或簡單花葉)、山字修長內(nèi)收繁地紋(多種花葉紋或獸紋及其他裝飾)等裝飾特征,反映出當時特殊的視覺審美趨向,表現(xiàn)出浪漫瑰麗的楚地對信仰、文化、審美的追求,是人們對山岳神仙世界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戰(zhàn)國時期周王畿作為中原文化的中心,楚國迅速成為政治與文化強盛的大國,青銅工藝達到的高超水平作為當時物質(zhì)文化繁榮的表征,在文化史上出現(xiàn)前所未有的繁華絢麗。”[27]從戰(zhàn)國時期“山字紋”銅鏡出土數(shù)量和“山”字在其他器物中的應用看,表明該器物和紋樣的稀缺,且沒對當時紡織物、陶器、漆器等器物裝飾產(chǎn)生影響。值得肯定的是,戰(zhàn)國時期“山字紋”銅鏡既有傳承又有創(chuàng)新,其成熟的鑄造工藝和獨特的紋樣設計,不僅在當時創(chuàng)造了新的藝術(shù)形式,而且是楚地文化、審美的引領,其優(yōu)秀的設計思想對現(xiàn)代設計亦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