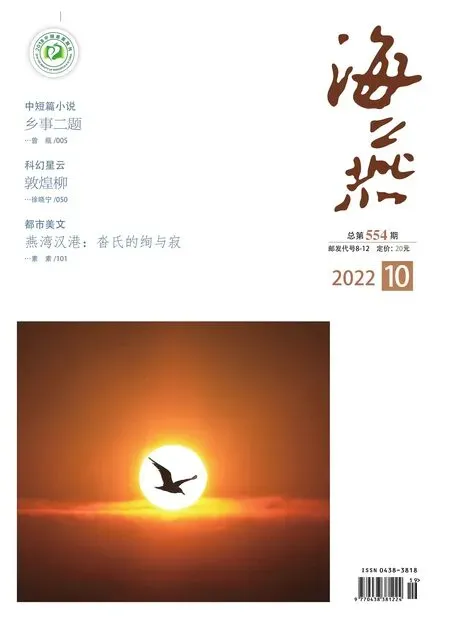文人三壺茶
文 朱明東

第一壺:圈子
圈子,實(shí)屬文人們交流、交往、交際的平臺(tái)和空間。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歷朝歷代都有文人為研討學(xué)問、切磋技藝、寄情山水、暢談人生,結(jié)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圈子。這圈子或叫沙龍或叫學(xué)會(huì)協(xié)會(huì)什么的。不管叫什么,其宗旨就是為了使志同道合的文人們相互學(xué)習(xí)、取長(zhǎng)補(bǔ)短、共同進(jìn)步。
史料記載,明朝時(shí)期大大小小的文人圈子不下兩百個(gè)。這些圈子有詩(shī)文應(yīng)和的,讀書研理的,譏評(píng)時(shí)政的,吹彈說唱的,還有專品美味的。“海內(nèi)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看看,文人的圈子,除了以文會(huì)友外,還能時(shí)不時(shí)地搞搞聚會(huì),推杯把盞品菜香呢。
小圈子是伙,大圈子是組織。一個(gè)為單兩個(gè)為雙,三個(gè)為伙四個(gè)為幫。古時(shí)候單純以文會(huì)友的圈子并不多見,各界互通有無、相互結(jié)盟倒是司空見慣。這和時(shí)下各種聯(lián)誼會(huì)極為相似。畢竟,是一種聯(lián)誼,不是拉幫結(jié)伙,自不必瞻前顧后,徘徊不定。當(dāng)然,圈子有風(fēng)險(xiǎn),入時(shí)須謹(jǐn)慎。入一個(gè)不著邊際甚至找不到北的大圈子,有時(shí)候不如不入。在大圈子里再搞個(gè)小圈子,那就得不償失了。正所謂,文有文道,圈有圈規(guī)。話說回來,有無資本入圈子,想不想入圈子以及人家讓不讓你入圈子自是不同。但肯定的一點(diǎn)是,入文人的圈子,結(jié)文人的圈子,絕對(duì)是一件值得羨慕和推崇的好事。
古代文人就很善于做這樣的好事。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的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咸等七人,為了把好事辦好,就組成一個(gè)令后人仰止的圈子,即“竹林七賢”。除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縱歌外,山濤和王戎不僅成了名,還當(dāng)上了司馬朝廷的高官。對(duì)“肩無挑擔(dān)之能,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而言,這樣的誘惑力又怎能不讓人動(dòng)心呢?于是乎,拜師傅、認(rèn)鄉(xiāng)黨、交學(xué)友繁衍開來;于是乎,達(dá)官貴人、市井小販紛至沓來,投機(jī)鉆營(yíng),樂此不疲。就連有清規(guī)戒律、超凡脫俗的和尚,也對(duì)圈子情有獨(dú)鐘。在“竹林七賢”出現(xiàn)后不到一百年時(shí),廬山有一個(gè)叫慧遠(yuǎn)的和尚,也結(jié)了一個(gè)叫“廬山僧團(tuán)”的圈子。這個(gè)圈子除了勤凈修行、講法說道外,還與天下文人交往甚廣,被當(dāng)時(shí)朝野名士所欽敬。由此,廬山也被譽(yù)為“道德所居”之地,成為當(dāng)時(shí)與姚秦政權(quán)的長(zhǎng)安并峙的佛教中心。作用如此之大,內(nèi)涵功效如此之強(qiáng),已非一個(gè)簡(jiǎn)單的文人圈子可以匹及了。
文人在圈子里相互尊重理所應(yīng)當(dāng),可事實(shí)上卻時(shí)有相互貶低、相互詆毀的現(xiàn)象,以致為圈子詬病。前面提到的“建安七子”,在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可謂重要。他們與“三曹”一起,組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軍。他們對(duì)于詩(shī)、賦、散文的發(fā)展,都曾作出過貢獻(xiàn)。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yīng)玚、劉楨等七人,雖然各自經(jīng)歷不同,但是都親身經(jīng)歷了漢末的離亂之苦,也都先后投奔了曹操。同為一個(gè)圈子,彼此又同病相憐,按說應(yīng)該相互關(guān)照相互支撐才對(duì)。可七子們呢,不僅誰也不服氣誰,還私下在曹氏父子那里說對(duì)方的壞話。那個(gè)能讓梨的孔融被殺后,其他六位啞然失聲,既無同情的言論,也無同情的筆墨。圈子的冷漠乃至冷酷著實(shí)令旁觀者不寒而栗。難怪人家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大談“文人相輕”之論。這不僅是曹氏的感嘆,也是文人們的無奈。
圈子有冷暖,文人心自知。好不容易挖空心思削尖腦袋擠進(jìn)夢(mèng)寐以求的圈子,卻一不小心卷入是非旋渦,不僅評(píng)不上什么獎(jiǎng)項(xiàng),撈不著什么好處,還時(shí)常險(xiǎn)象環(huán)生、危機(jī)四伏,有的甚至連命都丟了。上面提到的那個(gè)孔融,說白了就是冒犯了圈子里的老大曹操。老曹可不管你小時(shí)候讓沒讓過梨,再說了,老曹也不稀罕吃什么梨。人家連三分天下都能掌控,還奈何不了你這個(gè)孔融?那個(gè)平時(shí)對(duì)圈子不以為意的王安石,也有類似遭遇。在變法中,他不僅觸及了富商大戶利益,無意中也惹惱了一個(gè)很重要的文人圈子。這個(gè)文人圈子非比尋常,隨便點(diǎn)上幾位都令人咋舌:司馬光、蘇洵、蘇軾、蘇轍、文彥博、歐陽修等等。這些文人一改謙恭禮讓、飽學(xué)詩(shī)書之態(tài),對(duì)王安石群起而攻之。他們個(gè)個(gè)言辭激烈、毫不客氣,大有不鏟除之,大宋江山社稷就難以安泰和鞏固。你想,那個(gè)未入啥圈子的王安石還能好得了嗎?
唯一沒入圈子又安安全全、樂哉優(yōu)哉的文人當(dāng)數(shù)陶淵明。能做到這一點(diǎn),得益于一種歸隱。陶文人的歸隱不同于那種借歸隱買名邀譽(yù)的假隱士,他是真隱,是一種對(duì)人生的理性選擇,也是一種對(duì)“舉世皆濁”“眾人皆醉”的厭惡。陶文人始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后仕職于桓玄、劉裕、劉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職彭澤令八十余日,因不肯為五斗米向鄉(xiāng)里小人折腰,毅然辭職歸耕田園。歸隱后的陶淵明親自參加田園勞作,接近勞動(dòng)人民,歌頌勞動(dòng),這使得文人的田園詩(shī)更具勞動(dòng)生活氣息。至于圈子,陶文人才不稀罕呢,也不在乎什么評(píng)價(jià)和認(rèn)定,一門心思在真隱之中安心創(chuàng)作,憑真人格魅力說話,憑高質(zhì)量的作品來說話。“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yuǎn)見候,疑我與時(shí)乖。”從詩(shī)中,不難看出在閑適的田園生活中,陶文人心情已豁然開朗,寧?kù)o致遠(yuǎn)遂自形成。所以,我一直認(rèn)為,陶淵明應(yīng)該成為廣大文人推崇的榜樣。這不是勸誡文人們?nèi)w什么隱,而是倡導(dǎo)文人們?cè)谌虢】等ψ拥耐瑫r(shí),不僅要培養(yǎng)一種出污泥而不染的境界和精神,更要在名利取舍中,多出一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逍遙與睿智。
一個(gè)文人逍遙不奇怪,整個(gè)文人的圈子一起逍遙那可就嘆為觀止了。假如你不小心出生在明末清初,又渴望一種逍遙,那么,我建議你一定要入李漁那個(gè)圈子。這個(gè)李漁,對(duì)圈子有著深刻的認(rèn)識(shí),知曉“君子朋而不黨”“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膠如漆”等道理。他在《交友箴》中寫道:“飲酒須飲醇,結(jié)交須結(jié)真。飲醇代藥石,交真類松筠。”有史料稱,與李漁交往的八百余文人雅士中,上至位高權(quán)重的宰相、尚書、大學(xué)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藝人,遍及十七個(gè)省,二百余州縣。可以說,李漁是中國(guó)古代交友最多、結(jié)交面最廣的文人。眾多的文朋學(xué)友,使李漁自由往來于朝野文人之間,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識(shí),懂得了許多人情世故,更為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生動(dòng)的素材。坐堂賞《美人香》,臥榻讀《肉蒲團(tuán)》,這個(gè)有著“湖上笠翁”雅號(hào)之稱的李漁在自己的作品中,將整個(gè)文人圈子里的逍遙一網(wǎng)打盡。
文人的圈子聚了散,散了聚,一個(gè)圈子成為過去,自然會(huì)有新的圈子誕生。不知不覺,魯迅在圈子里吸了一支煙走了,老舍在圈子里喝了一碗茶走了,豐子愷在圈子里畫了一幅畫也走了。來了一個(gè)又走了一個(gè),文人的圈子已是百花齊放、光怪陸離。慨嘆中,我恍然又回到了那個(gè)無圈子思想?yún)s敢于創(chuàng)辦文學(xué)社的純真年代。
第二壺:嗜好
1765年,42歲的紀(jì)曉嵐陪同乾隆皇帝微服私訪窯灣,偶得當(dāng)?shù)貐切绽习屦佡?zèng)的煙絲和二斤八兩重的白金水煙袋,“紀(jì)大煙袋”由此而來。
除指特殊的喜好之意外,“嗜好”更多地被解讀為不良的愛好。對(duì)此,許多文人都感同身受。吃喝嫖賭抽,是公認(rèn)的五毒或?yàn)槲宸N不良嗜好。有些嗜好因文人而得典故,有些文人因嗜好而獲傳播,比如蘇東坡。蘇東坡愛喝蜂蜜,在流放黃州和惠州時(shí),他曾養(yǎng)過蜜蜂,因而深愛之。不喜歡喝甜的,那就來點(diǎn)咸的。“揚(yáng)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在咸口上倒是體味頗深。傳說鄭板橋在揚(yáng)州賣畫,只要有人送他一碗狗肉,他就會(huì)回贈(zèng)一幅小畫;但達(dá)官貴人、富商豪賈,如想以千金買他的畫,還要看他臉色,倘若不高興,雖千金亦不屑一顧。話說有一位足夠咸的大鹽商,向鄭板橋求畫被拒。正一籌莫展時(shí),獲悉鄭嗜吃狗肉,乃設(shè)一圈套,騙走了鄭板橋的畫。鄭板橋得知真相,十分羞惱,于是將鹽商告進(jìn)官府。此事轟動(dòng)揚(yáng)州城,成為廣大人民群眾茶余飯后的笑料。
“酒有別腸,唯文者近”。小到品,大到飲,文人的嗜好從古至今就一直沒有間斷過。或縱飲狂歌、放蕩不羈,或淺酌低吟、把盞暢飲,無不顯露文人的灑脫和儒雅,展現(xiàn)文人的風(fēng)格與情趣。所以我說,文人對(duì)酒的滋味品嘗最為直接,那深藏酒中的各種道理,也只有文人才能悟出。“李白街上走,提壺去買酒。遇店加一倍,見花喝一斗”,家喻戶曉的李白不僅有著卓絕的才情,更有著世人為之驚嘆的酒量。“舉杯當(dāng)歌,無酒不成詩(shī)”,是李白無愧于“詩(shī)仙”雅號(hào)的真實(shí)寫照。很多文友都有我的感受,每當(dāng)讀李白的詩(shī),讀著讀著就能聞到一縷酒香來。從“花間一壺酒,獨(dú)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duì)影成三人”到“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從“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到“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這句句優(yōu)美絕倫、膾炙人口的名詩(shī)佳句,無不展現(xiàn)出李白對(duì)酒的癡迷與愛戀以及他對(duì)多變?nèi)松牟涣b和傲視。詩(shī)仙乎,酒圣焉!
古代有賭博嗜好的文人也不在少數(shù)。王安石在《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shī)輸一首》中寫道:“華發(fā)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倍堆。鳳城南陌他年憶,香杳難隨驛使來。”可見,弈棋賭已成為宋朝時(shí)期重要的賭博方式。在婉約派與豪放派成為宋詞主導(dǎo)風(fēng)格的同時(shí),文人們的賭博也開始在各個(gè)階層蔓延,給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發(fā)展帶來了很多不良影響。為此,朝廷頒布了禁賭律令,但終因彼時(shí)的賭博之風(fēng)甚囂塵上而宣告失敗。能如此,與那個(gè)一天不賭就渾身癢癢的宋徽宗不無關(guān)系。據(jù)曹勛《北狩聞見錄》記載,在宋徽宗被金國(guó)擄去的途中,隨身還不忘帶著象棋。于是乎,上行下效,法律成了一紙空文;于是乎,不良的嗜好最終敲響了亡國(guó)的喪鐘。
文人嗜煙,紀(jì)曉嵐算一位。而好吸煙者,現(xiàn)代文人更多。徐志摩、梁實(shí)秋、林語堂、郭沫若也曾經(jīng)有吸煙的嗜好,有的終身未戒。這也就形成了一種現(xiàn)象:似乎不吸煙,就不算真文人;似乎不煙霧繚繞,就無法文思泉涌。所以,很多文人都拿創(chuàng)作需要拒絕戒煙;所以,很多假文人,不會(huì)抽煙也要擺弄幾支掐于手中。我欣賞真文人的那種狀態(tài):能吸煙而思不散,能撰文而性不亂。童年時(shí),第一次看到魯迅吸煙的畫像,我就被先生獨(dú)有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先生安坐藤椅上,手舉紙煙深思凝望,輪廓極為鮮明。煙霧繚繞中,先生的那種憂慮的形象顯得更加高大。當(dāng)然,吸煙算不上先生唯一的嗜好,但不吸煙,那還是魯迅嗎?在魯迅吸煙時(shí),一個(gè)民族學(xué)會(huì)了思考。
風(fēng)霜馳騁,雨雪縱橫。大浪淘沙后,琴棋書畫、品茶論道,依然是文人高雅的嗜好;收藏炒股、駕車旅游,又成為文人引領(lǐng)時(shí)尚的嗜好標(biāo)志。“我的嗜好就是看你撒嬌,你想要的我都盡量做得到。有多費(fèi)力勞心都不重要,心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嗜好就是將你擁抱,要做你最暖和的依靠。”在古巨基的歌聲里,“嗜好”被解讀得面目全非。有文友相邀,說浙江省桐廬縣城南的嚴(yán)子陵釣臺(tái)是個(gè)好去處,稱嚴(yán)子陵為一塵不染山高水長(zhǎng),遂心向往之。不是嗎?天下再好的嗜好,莫過于潔身自好。追求高雅的文人,當(dāng)效仿嚴(yán)子陵。
那夜,與紀(jì)曉嵐對(duì)話。我說:“我不喜歡拿煙當(dāng)?shù)谰叩难b腔作勢(shì)者,更討厭自詡無不良嗜好的偽君子。如果創(chuàng)作需要我再次把煙撿起來,我將義無反顧重新點(diǎn)燃思想之光。”紀(jì)曉嵐說:“拉倒吧,你已戒過一次煙,再戒煙也難成就一部當(dāng)代的《閱微草堂筆記》,更不會(huì)有哪位宮女來服侍你。”我不以為然,宣布再次成功戒煙。
第三壺:氣節(jié)
有人用六月雪來比喻蒙受奇冤,比如《竇娥冤》。在明朝,有一個(gè)比竇娥還冤還慘的人,他就是方孝孺。
方孝孺在短暫的46年生涯中博學(xué)多才,在明惠帝時(shí)期官至文學(xué)博士,相當(dāng)于今天的文化部長(zhǎng)。皇帝朱允炆十分倚重方孝孺,燕王朱棣起兵篡權(quán),朱允炆進(jìn)行討逆,其詔檄皆出方孝孺之手,可見方孝孺文采何等了得。
其實(shí),篡權(quán)奪位不一定非要搞血腥鎮(zhèn)壓,畢竟各為其主,應(yīng)該給予諒解。你把皇位都奪到手了,還糾纏原來那些瑣事干啥?早在朱棣篡權(quán)時(shí),謀士姚廣孝就對(duì)朱棣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方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方孝孺可以說是當(dāng)時(shí)天下文人中的領(lǐng)軍人物,不殺他就會(huì)籠絡(luò)一大批文人,就會(huì)安撫民心。
篡權(quán)成功后,朱棣立即召見方孝孺。出乎意料的是,方孝孺穿了一身孝服,一路痛哭不已。見著朱棣就問:“皇上去哪兒了?”朱棣說:“自焚死了。”方孝孺哭著說:“那為何不立他的兒子來當(dāng)皇帝?”朱棣說:“這是我的家事,你就不必操心了。”說完,就讓方孝孺幫起草安撫詔文。方孝孺執(zhí)筆寫了,寫的卻是大大的“篡”字,寫罷,把筆摔在地上義正詞嚴(yán)地說:“萬世之后,你也擺脫不了這個(gè)字。”朱棣氣暈了,站起身大聲喝道:“方孝孺,你別以為你有才華我就不殺你!”方孝孺輕蔑一笑:“隨你便。”朱棣大怒:“你就不怕被株連九族?”方孝孺剛烈地回答:“滅十族都不怕!”
方孝孺是史上唯一被誅十族的人。一個(gè)敢殺,一個(gè)敢死,這在歷史上十分罕見。在方孝孺放棄生命時(shí),妻子鄭氏和兩個(gè)兒子一起上吊自縊,兩個(gè)女兒也投了秦淮河。滅族其狀慘不忍睹。史料稱,一共殺了七天,共八百七十三人。其間,方孝孺始終鎮(zhèn)定自若,還慷慨賦詩(shī)道:“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jì)兮,謀國(guó)用猶。忠臣發(fā)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孰不我尤!”其弟方孝友臨刑前還和了一首告別詩(shī):“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方孝孺被腰斬后,以肘撐地爬行,手蘸血連書“篡”字,一共寫了二十四個(gè)半才氣絕身亡。在處理方孝孺上,朱棣最沒氣量。任其后多少雄偉功績(jī),也難掩濫殺無辜惡名。
什么是文人的氣節(jié)?我想,有氣節(jié)的文人應(yīng)該是這樣的:他忠誠(chéng)正義,有道德和操守;他深曉事理,明辨是非,能抵御各種正常需求之外的所有誘惑;他寧可站著死也絕不跪著生,更不會(huì)違心改變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信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文人的氣節(jié)最終戰(zhàn)勝了膽怯,方孝孺始終未向嗜殺成性的朱棣屈服。方孝孺非簡(jiǎn)單的愚忠,也非大腦不開竅,而是有一種東西在主宰著他的思想和精神,這就是氣節(jié)。他用凜然正氣和慷慨赴死來詮釋了什么是文人的氣節(jié)。令人遺憾的是,楷模很美麗,現(xiàn)實(shí)很骨感,像方孝孺這樣有氣節(jié)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在歷史上不害人不誤國(guó)的文人,就算是個(gè)好人。倘若放在別人身上,遇到朱棣邀請(qǐng)寫詔文,不說激動(dòng)萬分,至少也不會(huì)去直接違抗并口誅筆伐。若真如此,方孝孺也就不是方孝孺了。
方孝孺死了,明朝的雪在不散的冤魂中無助地飄著,不知該如何向天下蒼生訴說自己的無奈。